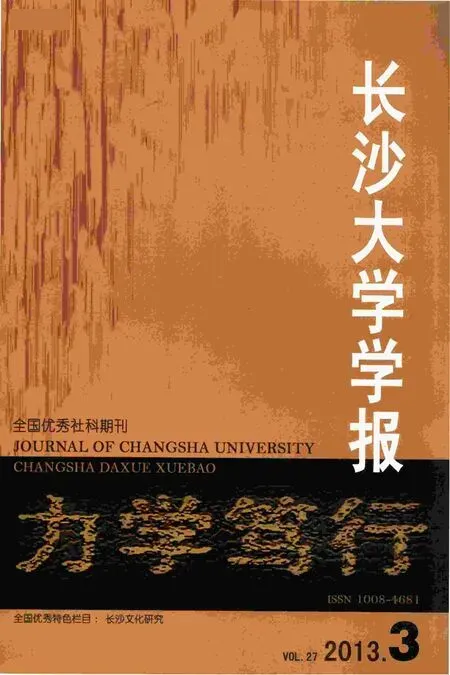走向文化復調與融合
——從流散視角解讀《接骨師之女》
李 瓊
(廣東商學院華商學院,廣東廣州511300)
一 流散文學與美國華裔流散作家譚恩美
“流散”(diaspora)一詞源于希臘語,指的是猶太人亡國后被迫流亡世界各地,處于流離失所的狀態。后來,流散主要指人們由于某種原因從自己國家無奈被迫放逐或主動遷移,背井離鄉,久居異國,處于一種漂泊狀態中,同時又努力在現實中尋找自己的物質和精神家園。于是,流散者們開始通過書寫創作來表達他們身處異國的心靈體驗,從而就誕生了這種獨特的文學方式——流散寫作或流散文學。流散文學是“流散”這一歷史社會文化現象的產物,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其主題也主要圍繞流散族群在居住地的生存境遇,在異國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困惑與迷惘,被排擠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生活經歷以及內心情感等等而展開。流散者們夾雜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內心經受著巨大的煎熬和折磨。在這些流散者身上很好地體現了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闡述的“混雜性”特征:他們“一方面,為了生存和進入所有國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與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認同,但另一方面,隱藏在他的意識或無意識深處的民族記憶卻又無時無刻不在與他新的文化身份發生沖突進而達到某種程度的新的交融”[1]。因此,流散文學體現了不同國家之間的一種文化張力:既相互沖突又相互融合,它是“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接觸、文化沖突、文化融合、文化變遷等重要文化事實的表征和反映”[2],體現了多元化時代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和文學現象。筆者認為,在當今多種文化共存的格局中,流散文學正以其特有的方式促進著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
譚恩美是一位典型的流散作家,是美國華裔流散群體中的一名文化代言人。盡管在美國土生土長,但對于美國主流社會、主流話語而言,她仍算是一個流散者,曾不被白人認可,徘徊于中西兩種文化之間。這種身份的特殊性以及文化背景環境的雙面性賦予了譚恩美敏銳的意識,促使她用獨特的視角去審視中西兩種文化,在流散下書寫了一代代生活在中美兩種文化夾縫之中的華裔移民及其后代,從這些流散者們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了他們對待中西兩種文化的不同態度以及他們對文化認同的發展變化過程。《接骨師之女》是譚恩美的第四部流散作品,本文以這部小說為研究對象,從流散文學視角分析小說中人物在流散狀態下的心靈體驗,以及他們之間因文化不同而造成的種種矛盾和沖突,并最終在文化的沖撞和交流中實現了中西異質文化的復調和融合。
二 流散下異質文化的碰撞與沖突
離開祖國,流散在外的族群都處于一種尷尬境地,他們夾雜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經歷著強烈的思想震蕩和精神折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經常發生碰撞,從而導致生活中矛盾與沖突不斷。《接骨師之女》敘述的是流散在美國的一個華人移民家庭的故事,主要圍繞著華人移民母女之間的矛盾以及她們與西方人之間的矛盾而展開,描寫了他們在流散中的生活經歷與內心體驗,暗示了中西兩種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碰撞與沖突。
(一)文化沖突中的母親與女兒
小說中的母親茹靈在中國傳統文化下成長,擁有著中國式思維方式和倫理道德標準;她帶著傷痛流散到美國后顯然很難融入美國這個崇尚自由與獨立的國家。然而,她的女兒露絲,在美國出生成長,從小就被西方文化環境所包圍,接受美國式的教育,她無法理解母親那中國式思維和教育方式,于是,兩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矛盾。
茹靈希望露絲能按照她的意愿成長,從小就向露絲灌輸中國傳統文化,讓她學寫漢字,說中文;茹靈非常重視家庭觀念,認為孩子應該聽從父母孝順父母,會習慣性地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露絲,如果露絲不聽從就認為她不孝順,經常會生氣地說:“我趁早死了的好!”[3]而露絲從小受美國文化的影響,追求個性獨立和自由,她從內心里抵觸母親的這種傳統文化,無法接受母親日常生活中對她的種種干涉和嘮叨,于是就和母親對抗。茹靈努力地教露絲認識漢字,告訴她每個漢字都包含一種思想,但露絲卻不愿學習,在她看來,每個漢字每一筆畫“活像是根踢了肉的骨頭。”[4]一天,露絲在校園里玩滑梯,茹靈見到后便朝著她叫嚷“不要,不要”;別的孩子都笑她,她感到很羞愧和生氣,為了表達對母親的反抗,她不顧后果地把頭朝下沿著滑梯沖下去,結果摔斷了腿。由于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使他們不能相互理解和溝通,從而產生隔閡和沖突。茹靈認為女兒不應該有秘密隱瞞母親,母親關心女兒的生活和思想是責任所在也是理所當然,于是她開始翻看露絲的日記。而露絲在美國文化背景下成長,認為母親無權干涉自己的隱私,最終母女間的矛盾升級。一次,露絲關門躲在房間里抽煙被茹靈揭穿后,露絲對著茹靈大叫:“我有隱私權,有權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活著不是為了滿足你的要求。”[5]之后在日記里還寫著希望母親去死,結果茹靈看了日記后真從樓上摔了下去。此時,母女之間的沖突達到高潮。
茹靈和露絲的矛盾與沖突從表面上看是由代溝造成的,但實際上這是中西兩種文化相沖突的結果。茹靈從小在中國長大,雖然流散到美國,但身上始終保留著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而女兒露絲從小接受的是西方文化,追求個性自由和獨立。因此,不同的文化導致了她們在美國流散狀態下種種沖突與斗爭。
(二)文化沖突中的露絲與亞特
露絲生長在美國,一心想融入美國主流文化,但與生俱來的東方面孔和中國血液使她難以被主流社會完全接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流散者,處于無根的狀態,夾雜在兩種異質文化之中。同時,在母親茹靈傳統文化的長期教誨和熏陶下,中國文化和倫理道德思想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她,不知不覺地擁有了東方女性的一些特點。所以當她和美國男友亞特一起生活時,兩種文化便在這個家庭得到了充分的碰撞。
中秋節聚餐事件就表露了露絲和亞特之間的矛盾。中秋節在中國文化里是個非常重要的節日,它象征著團圓和幸福,在這天,所有家庭成員會聚集在一起吃飯賞月。露絲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也決定舉辦一次中秋節家宴,邀請所有的親戚朋友來聚餐。然而,代表西方文化的男友亞特根本不理解中秋節這種精神文化傳統,他認為中秋節的聚餐“不過是大家一起吃個飯罷了”[6]。文化價值觀的不同拉開了露絲和亞特的距離,加深了他們之間的隔閡。露絲關心亞特建議他晚上少喝些酒,但亞特卻認為露絲像她母親茹靈一樣在干涉他的自由。露絲和亞特之間的沖突還表現在對照顧患有老年癡呆癥的母親茹靈這件事上。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思想,夫妻雙方應當共同來贍養雙方父母,然而亞特在談話中表現出否定態度,認為這是露絲自己的事情,與他沒有關系。亞特的這種態度讓露絲感覺到親情的疏遠,使他們之間矛盾加劇,直至后來露絲從家里搬了出去。中西文化價值觀的不同造成了露絲與亞特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三 異質文化的復調與融合
《接骨師之女》中茹靈、露絲及亞特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與沖突實際上反映了這個中國移民家庭在流散狀態下所面臨的尷尬境地。茹靈和露絲漂泊在異國,作為流散者,她們難以被美國主流文化所接受,不得不經受著兩種文化價值觀的沖撞。但與此同時,在這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和沖突中,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又是可能的、必然的。隨著時間的過去,她們開始理解并接受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找到溝通的正確方式,沖破隔閡,認同彼此。在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的沖突中,最終她們邁過了那巨大了溝壑,從對立和沖突走向了中西文化的復調和融合,實現了文化的和諧共存。
小說中母親茹靈為了讓女兒了解自己,消除她們之間的隔閡和誤會,就用書寫的方式來告訴女兒關于自己的一生。當女兒露絲閱讀了母親的手稿,了解了母親坎坷、悲慘的經歷后,開始理解母親,明白了母親對自己的愛,認可并接受了母親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對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有了新的認識。母女間的矛盾與沖突最后通過書寫這獨特的交流方式得以和解,露絲和茹靈從對立走向了理解和交流。小說結尾處茹靈主動給露絲打電話,通完電話后露絲哭了整整一小時,不過這不是傷心的淚水,而是幸福之淚。最終露絲認同了中國文化,接受了自己的中國血統,最終,中西方文化在她身上得到很好地交融。
同時,露絲與亞特之間的矛盾也最終和解,兩人言歸于好。經歷了種種碰撞和沖突后,亞特開始理解茹靈和露絲身上所代表的中國文化,主動地找露絲溝通;在照顧茹靈的事情上,亞特也提出送茹靈去一家高檔的安養院,并承擔一切費用;他開始站在露絲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對于露絲提出的建議,他也很爽快地答到:“只要她愿意,隨時可以來跟你我一起住。”[7]露絲聽到亞特這次說的是“你我”而不再是“你”,頓時感到一股暖流滑過心間,兩人最終冰釋前嫌走向和解。茹靈、露絲、亞特之間的理解和認同實際上也意味著中西兩種文化之間的理解和認同,標志著他們身上多年來中西文化對立的消解,同時也暗示了異質文化的復調與融合。
在這部小說中,盡管流散者們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出現了各種碰撞和沖突,但最終這兩種文化還是從對立走向了融合;它們就像一首復調音樂中的兩個聲部,雖然發出不同的聲音,卻能和諧地結合在一起,湊出美好的樂章。我們相信,隨著全球多元化的不斷發展,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必然會從對立走向對話,在互動互補之中達到一種和諧共存的境界。
流散文學使流散者與異質文化發生著充分的文化接觸,在接觸過程中難免出現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但與此同時也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成為了必要和可能。《接骨師之女》向我們展示了流散在美國的兩代華裔女性的生活經歷及內心情感。流散者的特殊身份使她們被困于兩種異質文化之中,由于文化價值觀的不同,導致了生活中的種種矛盾與沖突;但不管他們之間(即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隔閡和矛盾有多嚴重,最后雙方還是達成了和解,認同了彼此的文化,實現了文化的融合。譚恩美作為一位美國華裔流散作家,在作品中一直關注著流散者們在中美兩種文化碰撞中的生存狀態。她行走在兩種文化之間,既看到了兩種文化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又看到了兩種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在她看來,中美文化其實是世界文化的兩個聲部,雖然它們之間存在著碰撞與沖突,但最終還是會趨向和解,從而共同營造一個多元共存、和諧相處的復調世界。走向異質文化的復調,實現文化的和諧共生,筆者認為這是華裔作家譚恩美所表達出的美好信念。
[1]王寧.文化身份與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J].甘肅社會科學,2002,(1).
[2]劉洪一.流散文學與比較文學:機理及聯結[J].中國比較文學,2006,(2).
[3][4][5][6][7]譚恩美.接骨師之女[M].張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