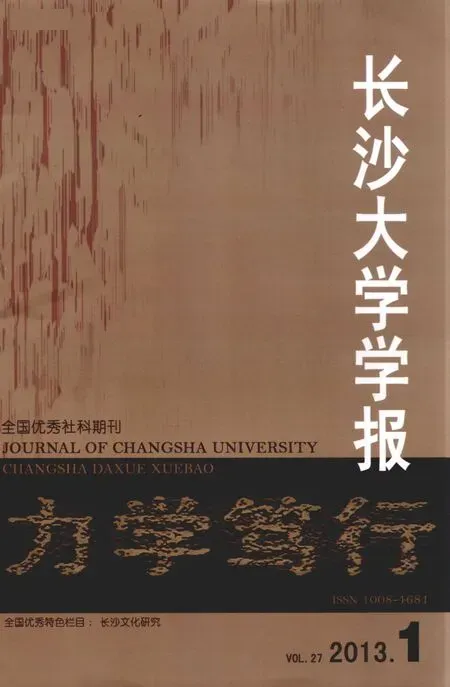找回城市的社會本真——重思當代中國城市化的動力嬗變及其發展導向
吳越菲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上海 200241)
到2050年,全世界將有大約60億人居住在城鎮地區,占全人類的三分之二,以城市為主要居住形態的人類世紀已經到來[1]。人們有理由歡迎這樣的發展趨勢,因為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性順應了人類追求自我發展的人本傾向。
歸溯人類城市化的歷程,18世紀的工業革命通過帶來生產要素在城市的聚集無可置疑地成為了西方城市化的最大“功臣”,并直接促使城市從防衛形態走向生產形態,也使得人類的居住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中國的城市起源于4000年以前的夏朝,經過春秋戰國時期城市與國家政治的同構,以及后期經濟功能的逐漸突出,明清時期城市發展的狀況已較為繁榮。然而由于農耕經濟時代城市化的局限性,真正具有突破意義的城市化發展階段則發生在當代。以1949年國家政權的建立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兩個時間點為界,大致可將中國整體發展階段進行粗略地劃分,而作為社會發展其中一個部分的城市化進程也與此時間截點有著密切的同時性關系。
一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動力嬗變及其內隱價值
(一)前改革時代:“政治工具型”的城市化
建國后,中國重要的任務就是進行工業化的前期努力,努力將傳統的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將一窮二白的城市轉變為積極的生產體。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大規模工業勞動力需求的產生吸收了大批農村青年進城。同時,建國初期的“三大改造”帶來了來自手工業、農業、手工業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人也流入了城市。由此帶來了建國早期城市人口的大規模增長。1958年開始“大躍進”,“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口號自上而下地進行動員,繼而出現了“爆發性的工業化過程和超高速的城市化過程”[2]。直到1960年的11年中,中國城市人口以每年7.7%的速度增加[3]。
然而,當工業化目標被城市化所阻礙的時候,城市化便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目標下的“犧牲品”[4]。“大躍進”造成了工農部門失調而被迫流產,加之三年自然災害的饑荒,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之間初步建立的協同性分崩離析。面對緊缺的資源,政府開始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削減吃商品糧的人口以此來保護城市。1958年正式通過的戶口登記制度以及1959年中共中央接連發出的《關于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指示》、《關于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等行政指令,硬性劃定了城市“內部人”和“外部人”的界限,將“城市-農村”的結構性體系人為切割為兩個獨立系統。1961-1963年,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非正常的“逆城市化”現象。從1960年底到1963年上半年,在“下放”運動中,全國共下放城鎮人口1600萬人[5]。接下來的十余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三線建設”、“上山下鄉”的影響,致使全國范圍內出現了第二次非正常的“逆城市化”過程。這樣,中國城市化水平從1965年的17.98%跌到了1978年的17.92%[6]。
反觀這一時期的城市化狀況,政治力量儼然成為了影響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主要來源。城市化的命運取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因此可將其稱之為一種“政治工具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因深受毛澤東時代“反城市化意識形態”(anti- urbanization ideology)[7]的影響繼而表現出了緩慢發展甚至逆轉的發展態勢。
(二)改革時代:“經濟工具型”的城市化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邏輯下的實用與效率原則替代了原有的意識形態而成為社會秩序形成的基礎。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不得不在強大的經濟大潮下得以妥協,城市和農村的邊界開始被打破,從而真正開啟了中國城市化的大門。隨著戶籍制度的放松,我國的城市化速度得到了快速發展,雖然仍然遠遠落后于工業發展速度,但總體上城市化水平已經有了很大提高,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了50%[8]。改革時代,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城市化背后的經濟邏輯,城市化已經不再成為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而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
通過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而實現的經濟轉型,直接催生了影響中國城市化的三股主要力量: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9]。而城市化之能夠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啟動內需和經濟增長的經濟功能成為了城市化之于國家和社會的最大意義。對于個體來說,城市化亦具有微觀層面的經濟意義。數以萬計的務工人員涌入城市尋求新的生存資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理性的驅動下開始進入城市從事非農行業,盡管這種帶有暫時人口特征的群體大多數不能獲取正式的城市身份。不僅人口城市化充滿了對經濟利益的考量,城市空間擴張過程也無不打上經濟邏輯的烙印。中國的城市化還突出地表現為大規模的造城運動,正如蔡繼明等人所言,“我國城市在空間上實現了‘攤餅式’的快速擴張”[1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是“經濟類型”的城市化,因此,類似于“推進城市化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11]這樣的表述時常出現。而“推進城市化”背后所隱含的就是城市化的經濟導向和工具理性。
二 工具與價值之間——當代中國城市化之路的偏頗
回顧當代中國城市發展之路,城市化以數字和規模形式得到了迅猛發展,而城市的工具性亦得到彰顯。但是,一個重要的反思在于:工具理性驅使下我們究竟造出了什么樣的城市?當城市被經濟性束之高閣,其社會價值究竟在哪里?
嘗試反思經濟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為我們帶來了哪些困境:經濟邏輯絕對主導下的城市化,在繁榮了經濟的同時卻消解了城市正義、城市身份認同和城市社會的有機團結這些社會維度。甚至政府職能錯位,公共權力助強抑弱,與利益共謀[12]。公平正義的嚴重缺失消解了城市正義的存在;人口城市化帶來了農民市民化的挑戰,其中所要處理的不僅是市民身份和市民福利的獲得,更要處理的是角色的轉變和自我身份建構的問題[13]。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還處于“半城市化”的尷尬邊緣,如果城市無法真正實現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就可能像拉美一些國家所出現的“虛假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14];過分數字意義上的城市化削弱了城市身份認同的可能和意義,個體化經濟對于傳統的消解直接體現在對共同體的瓦解上,城市變成了老死不相往來的個體化集合,城市精神和共同體文化在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中式微。這些,就是我們的經濟邏輯對我們的城市構成的威脅。
無論城市化的進程如何能夠承載經濟發展的夢想,其最終的意義應當皈依于社會以及社會成員,即它的社會性。城市化決不是僅以政策技術層面而存在的,最終的落腳點應當回歸到城市的社會本真上來。然而與其相悖的是:我們的發展過分倚重城市化的工具傾向,卻忽視了城市本身作為一個共同體所應具有的倫理、道德、價值和意義。一個潛在的危機在于,我們越來越將城市化的工具性當成是城市化的終極意義,城市化中暗含的工具理性正在不斷吞噬著城市所應有的社會價值。
三 找回社會本真——后改革時代對城市化偏頗的修正
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在根本上被定義為按照我們的意愿去改變城市的權利,是人們對城市生態、組織和經濟的一種干預權力[15]。當我們意識到城市化是如何改變我們的時候,我們也要開始懂得如何改變城市。因此,面對以往的城市化之路所構成的威脅,我們也應當以城市權利的視角出發去反思并重構自我的道路,對城市作積極干預。而找回城市化中的社會邏輯,重返城市化的主體“人”,對城市化的社會性加以更多的考慮,讓改革和現代化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這將是我們對“城市權利”的最好回應。筆者認為,要找回城市化中的社會邏輯,必須解決三大基礎命題:重建城市福利、重建城市社會關系以及重建城市正義。
(一)重建城市福利
正是因為城市生活能夠提供農村無法提供的福利,人們才愿意離開農村走向城市,并最終獲得城市的身份認同。社會福利是依賴城市發展的社會現象,城市是產生社會福利、管理社會福利和受益于社會福利的中心[16]。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城市福利可以理解為城市中每個居民個人福利的總和,它充分地表現為市民各種各樣的欲望或需要得到滿足和由此感受到的生理的或心理的幸福或快樂[17]。從具體構成來講,它不僅包括以政府為主體提供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以社會為主體提供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中國歷來是“強國家”的典型,完全以社會至上的角度呼吁政府權力的撤出在中國舉步維艱。從國家權力的角度來說,存在的問題并非是簡單的過強而是錯位。更多的人寄希望于合作主義的路線使強國家帶動強社會,以此形成更有利于群體福祉實現的權力結構。因此,國家的頂層設計和社會力量的介入對城市福利的意義都非常大。
(二)重建社會關系
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是一個“城市危機”(urban crisis)的時代,城市作為空間的擴張體不斷強化著它鋼筋混凝土的物質形象,而作為共同體的城市及城市意義正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進程中消解。城市化如果僅以經濟和物化的形態而存在,這便是一種異化的城市,而通往這種異化城市的城市化之路必須得到反思和重構。我們過去的城市化道路太多地忽略了城市的共同體意義和價值關懷,以至于我們對城市化的態度隱含簡化論的取向,即將“城市化”與“城市擴張”、“城市規模和城市建設現代化”之間劃上等號。理想的城市化圖景應該是一個相互有效連接的城市共同體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市民在城市中得以現代性的獲取,與此同時不乏大眾參與、互動、公共責任與精神。讓城市真正能夠成為生活的家園,而不是“去生活化”的物化空間[18]。中國的城市發展需要更多的社會價值、倫理關懷和精神能量。如何打破“區隔的個體化城市人”,而重建一種“融合的公共性城市人”,這將是未來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取向。
(三)重建城市正義
在城市問題和“城市非正義”越來越凸顯的時代,“城市正義”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雖然對于“正義”的定義幾乎無法取得一致,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和直覺主義的正義觀也無法調和[19],正義的社會性存在至少應當與社會的主流價值和道德以及群體性利益相一致。對于城市正義來說,應當更多地包含城市化目標和手段上的恰當性和合理性。因此,城市的生態系統、社會系統以及空間系統被破壞這些問題的存在和凸顯日益要求人們開始反思城市化發展,并要求人們從社會正義與生態正義,現實正義與代際正義相統一的角度思考城市秩序、城市正義的建構問題[20]。目前學界更多地從城市正義的空間向度即空間正義發起呼吁,但城市正義的維度不僅限于此,還存在于生態正義、社會正義、分配正義等等。中國的發展包括中國城市的發展越來越訴諸于正義性,這種訴求實際代表了社會價值回歸的群體性需求。因此,城市的發展應回歸城市正義背后的價值光譜,應當讓正義性始終優先于效率。
[1]聯合國秘書長在世界人居日上的致辭[EB/OL].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sg/2006/habitatday.htm,2006 -10 -02.
[2]鐘秀明,武雪萍.城市化之動力[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3]XU Xue- qiang.Trends and changes of the urban system in China[J].The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1984,(1).
[4]Stephen A.Urbanization and urban government in China’s development: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community?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78,(3).
[5]肖冬連.中國二元社會結構形成的歷史考察[J].中共黨史研究,2005,(1).
[6]Kaixun Sha,Tao Song.Rethinking China’s urbanization: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erspective[J].Building Research & Information,2006,(6).
[7]Jianfa Shen.Understanding dual-track urbanis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J].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06,(12).
[8]中國科學院.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R].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9][11]吳建峰,周偉林.新時期我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及政策選擇[J].城市發展研究,2011,(5).
[10]蔡繼明,程世勇.中國的城市化:從空間到人口[J].當代財經,2011,(2).
[12]姜杰.城市管理問題聚焦[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13]文軍.農民市民化: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14]李強.城市化進程中的重大社會問題及其對策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15]David Harvey.麻省理工大學《城市面貌:過去與未來》課程第二講[EB/OL].http://v.163.com/movie/2004/1/E/J/M73893VHQ_M7389RKEJ.html,2004 -01 - 01.
[16][17]胡小武.廣義城市福利的內涵與指標體系研究[J].東岳論叢,2011,(6).
[18][20]鄭蕓.空間生產、城市正義與中國問題——全國首屆“全球空間理論與中國城市問題”學術研討會綜述[J].哲學動態,2010,(8).
[19][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