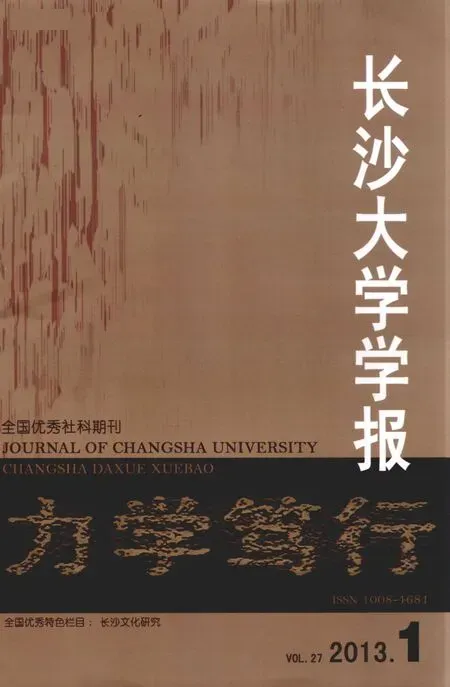抗戰(zhàn)時期秘魯華僑對祖國的支援初探
潘 澎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福建廈門361021)
一 抗戰(zhàn)前期的秘魯華僑
秘魯位于南美洲沿太平洋西岸,位于赤道與南緯20度之間,面積約有128萬平方公里,多山脈、礦產(chǎn)。秘魯華僑旅居此地至今約有160多年歷史,早期秘魯華僑的形成與西方殖民者在澳門猖獗的苦力貿(mào)易密切相關。主要是因19世紀中下葉南美洲開發(fā)亟需大量勞力,秘魯政府在1849年頒布《華人法》,獎勵進口華工,但合法的勞力引進根本滿足不了秘魯巨大的勞力缺口,故葡萄牙商人在澳門大肆販賣廣東、福建的“豬仔”,進行罪惡的苦力貿(mào)易。這些前往秘魯?shù)娜A工中,除1851年太平天國失敗后太平軍中有部分應招前往外,其他絕大部分是被威逼誘騙出洋的華工。據(jù)1889年曾奉命考察秘魯華工情況的傅云龍統(tǒng)計,“華工之僑秘魯,自道光十八年始,計至光緒年間,無慮十一萬有奇”[1]。第一批華工自澳門乘帆船抵達秘魯,而后進入工廠、棉花園、甘蔗種植園做工和修路,成為第一批旅居秘魯?shù)娜A僑。1874年清政府與秘魯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允許華人移民秘魯且受法律保護,而華工契約期限滿后成為自由人,開始了在秘魯?shù)钠D辛謀生。
自1909年以后,秘魯工黨和土著以華僑奪利為由開始進行排華限華,對華僑入境進行嚴格限制,規(guī)定華僑入境人數(shù)不得超過本國人數(shù)的千分之二,并且歸國后不得再前往秘魯。至20世紀20年代以后,世界經(jīng)濟危機開始波及秘魯,農(nóng)工商業(yè)凋敝,華僑人數(shù)愈來愈少,據(jù)1931年利馬和介休兩埠人口統(tǒng)計,華僑只有5,704人,加上秘魯其他地區(qū)華僑估計約有一萬余人。
秘魯華僑在商業(yè)上主要經(jīng)營茶葉、白米、豬油、巾紗布料、雜貨店等行業(yè)。抗戰(zhàn)期間,秘魯全國共有華僑商店二百五十多家,其中以永安昌、伍于贊等進出口貿(mào)易最為發(fā)達[2]。不過絕大部分秘魯華僑經(jīng)營規(guī)模很小,收入低微,僅依靠經(jīng)營一些雜貨店以維持生計,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逢世界經(jīng)濟危機波及秘魯,失業(yè)者過半,有些華僑淪為乞丐甚至自殺[3],廣大秘魯華僑的生存狀況尤為困難。但秘魯華僑的愛國熱情并沒有因此減退,九一八事變后花邑聯(lián)合會首先致電僑委會轉國民政府蔣介石,促其“速克復失地并息內(nèi)訌。”[4]面對日軍侵占東北覬覦淞滬,盡管秘魯華僑經(jīng)濟上處于非常困難當中,依然以祖國之后盾為己任,在遼沈失陷后毅然于1931年10月5日成立“旅秘全體華僑對日宣戰(zhàn)籌餉總會”,積極籌集抗日軍餉,在其出版的總會征信錄序言中就明確提到“聯(lián)合全僑組織戰(zhàn)日籌餉總會,一方面執(zhí)行對日絕交,一方面積極籌戰(zhàn)日餉項”,在國難當頭時期對籌款態(tài)度則是“總之,日賊一日未退,失地一日未復,則我們籌款責任一日未了”[5]。除成立籌餉總會以外,秘魯僑胞還紛紛行動起來支持祖國抗日,成立了旅秘華僑航空建設委員會秘魯分會、秘魯華僑抗日救國總會等抗日組織。
二 抗戰(zhàn)時期秘魯華僑踴躍捐款
秘魯華僑在抗戰(zhàn)初期就已有自發(fā)、分散性的臨時捐款活動,直到“旅秘全體華僑對日宣戰(zhàn)籌餉總會”的成立,才使得秘魯華僑社會凝聚在其組織下,并盡可能地號召華僑籌款支援祖國,表現(xiàn)出秘魯華僑的強烈愛國熱情。據(jù)1933年“秘魯華僑對日宣戰(zhàn)籌餉總會征信錄”第一期和第二期收支表記錄,第一期共籌得227,628元,第二期共籌得38,607元,兩期合計266,235元。這僅僅只是有直接記載的捐款數(shù)量,還不包括秘魯華僑在籌餉總會成立前后的單獨性捐款。在1937年前,其捐款數(shù)保守估計至少有30萬元。此后從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zhàn)當中,秘魯華僑對祖國捐款數(shù)達1,047,840元[6],占整個南美洲華僑捐款數(shù)量近二分之一。據(jù)國民黨中央海外部三十年度每周工作報告統(tǒng)計,海外各地繳到“傷病之友”捐款數(shù)額中秘魯華僑捐款數(shù)有9,970,249元,比墨西哥、澳洲及巴西三地華僑捐款數(shù)額還多。以人均計算,八年抗戰(zhàn)中每人捐款近100多美元,按1940年匯率折算,人均捐款約1400元,可見遠離祖國的秘魯華僑愛國熱情并不輸于其他地區(qū)華僑。
捐款對象遍及秘魯華僑社會的大部分成員與組織,除個人性質(zhì)的捐款外,捐款力度最大的為秘魯華僑中小工商業(yè)者,有些規(guī)模較大的公司出力較大,他們往往以自己商號的名義進行捐款,如伍于贊公司,其董事長為伍于贊,其個人捐款數(shù)次,并積極參與籌餉總會,身體力行,擔任該會執(zhí)行委員與會計主任,鼓勵秘魯華僑捐款,在這些僑領富商的帶領下,許多華商踴躍捐款。其次是以秘魯華僑的地緣性組織如中山會館、古同州會館(臺山、開平、惠平、新會、鶴山五縣籍人團體)、番禺會館等社團為名義進行募捐,特別是1908年成立的中山隆鎮(zhèn)隆善社,當時成員不過四、五百人,但是他們到1939年已相繼籌辦過三次募捐活動,由于成績斐然,當時國內(nèi)的軍政要員紛紛題詞,表彰他們的愛國義舉[7]。1939年1月,周恩來在重慶特為隆善社題詞:“萬里外六千僑胞,統(tǒng)籌債捐達二百萬秘幣,是僑胞之模范,是抗戰(zhàn)之光榮”。除上述以外,其余大部分捐款屬于個人性捐款,屬于捐款的中堅力量,其中有姓名記載的人數(shù)達千人以上,“遠在南美的秘魯,華僑為數(shù)僅七千人,到1938年底,就捐款二百八十萬元,占華僑大多數(shù)的窮苦僑胞,捐輸更多踴躍。有的華工為了多捐款,寧愿加班加點,每天勞動時間多至十六個小時”[8],雖捐款金額數(shù)目較小,但積少成多,在當時整個秘魯華僑經(jīng)濟處于困難的時期,他們的愛國行為實屬不易,難能可貴。
三 抗戰(zhàn)時期秘魯華僑籌款方式及途徑
秘魯華僑為支援祖國抗戰(zhàn)時毀家紓難,在籌款方式上除常規(guī)的靠宣傳鼓勵捐款外,還另有新意,例如籌餉總會婦女部和秘魯中華白話劇社及其他華僑社團通過義演的方式進行募集捐款,這些募捐活動都得到了秘魯華僑社會的大力支持。秘魯唐藏戲院在中山會館、古同州會館、番禺會館等各大會館與眾多華商的支持下,在秘魯各地進行義演,僅1933年2月17日就籌得3110元,秘魯中華白話劇社在該年1月23日也籌得3986.5元[9]。據(jù)秘魯華人何蓮香女士回憶:“當年抗戰(zhàn)爆發(fā)時她還是利馬一中學生,祖國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秘魯華僑華人個個心急如焚,我和學校話劇團的同學在老師帶領下,走上利馬街頭,長途跋涉,到秘魯南北各地,到凡是有僑胞的地方去演出,激勵僑胞們積極參加義捐,經(jīng)過幾次高潮,各僑團共籌得上百萬美元,受到國內(nèi)的高度贊揚。”[10]除義演外,還組織義賣活動進行募捐。中山隆鎮(zhèn)隆善社在1939年第三次籌捐抗日軍餉活動中,從祖國籌集到200多件國共兩黨軍政要員和抗日將領們的親筆題詞,以及文化藝術界名人的書畫作品,在秘魯舉辦“國家元首及抗日將領書畫展覽”,展品中有來自周恩來、蔣介石、馮玉祥、白崇禧、張群、孫科等名人墨跡,秘魯華僑反響熱烈,踴躍訂購,紛紛認捐,這些展品均被社團及個人買下,義賣活動共籌得200多萬元秘幣,將款呈“秘魯華僑抗日籌餉總會”代轉匯返祖國供軍餉之需,對祖國抗日做出了有力的支援。除常規(guī)捐款外,還有一項籌款的主要方式就是購買公債和進行國防獻金,公債包括救國公債、國防公債、金公債、節(jié)約建國儲蓄券等,其中,秘魯華僑踴躍購買救國公債,雖沒有秘魯華僑購買公債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但已有資料顯示,秘魯華僑在認購公債的人數(shù)眾多,且國民政府1937年頒布的《救國公債條例》規(guī)定:“自戰(zhàn)事結束后第三年起由國庫指撥基金,分二十年還清”,但國民政府根本無力還清,戰(zhàn)時華僑認購的債券,其實與捐款無異。
秘魯華僑對祖國的支援最主要是通過直接或間接捐款方式,其次是與日本經(jīng)濟實行斷絕[11],抵制日貨,打擊日本在秘魯?shù)纳虡I(yè)貿(mào)易。除此之外,在秘魯華僑抗日救國總會的帶領下,通過秘魯?shù)娜A文報刊如《民醒日報》大勢宣傳支援祖國抗日,籌集軍餉救國。秘魯華僑直接回國參戰(zhàn)人數(shù)很少,主要是由于秘魯華僑在抗戰(zhàn)時期人數(shù)已非常少,且回國路程遙遠所致。秘魯華僑捐款的流向,從籌餉總會征信錄第一、二期進支表可以看出,其捐款流向主要為兩個部分:一是匯給馬占山部隊,二是匯給上海淞滬駐軍,兩者同為軍餉,表現(xiàn)出秘魯華僑對祖國收復失地和抵抗日軍的堅強決心。在抗戰(zhàn)初期,國民政府對于華僑捐款的接收和保管未予以統(tǒng)一,財政部、僑委會、紅十字會等單位皆可接收,但1939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規(guī)定華僑捐款均由財政部統(tǒng)一接收。秘魯華僑抗戰(zhàn)前期和抗戰(zhàn)期間的匯款大部分由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接收,再轉至馬占山部隊和遼吉黑民眾后援會(會長朱慶瀾)及上海駐淞滬部隊。除匯款外,小部分捐款用于籌餉總會內(nèi)部運轉費用及宣傳印刷費用。
[1]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晚清海外筆記選[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2]蔡仁龍,郭梁.華僑抗日救國史料選輯[M].北京:中國華僑歷史學會,1987.
[3]秘魯華僑勸國人勿往秘[J].南大與華僑,1930,(10).
[4]案卷號(1)6839[A].海外華僑與抗日戰(zhàn)爭[C].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5][8][9][11]旅秘華僑概況[J].秘魯華僑對日宣戰(zhàn)籌餉總會征信錄,1933,(1).
[6]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華僑革命史(下冊)[M].臺北:正中書局,1982.
[7][10]陳鎮(zhèn)坤.籌款百萬美元,鮮為人知的秘魯僑胞抗日義舉[N].中華民族報,2005-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