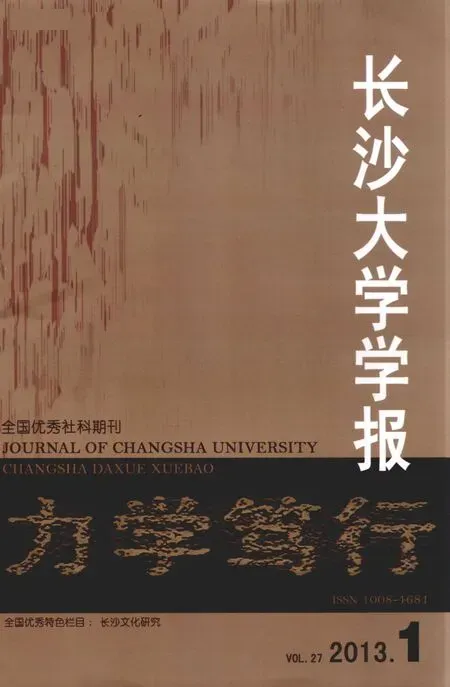詩人朱湘的翻譯歷史考察
谷 峰
(巢湖學院外語系,安徽巢湖238000)
以朱湘為代表的新格律派詩人曾對我國新格律體詩的建設做出了種種大膽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富有建樹的詩學主張,然而他的種種新詩理念很大程度上“反哺”于外國詩歌翻譯的經驗。朱湘在進行外國詩歌翻譯工作時,目的是很明確的——“別求新聲于異邦”,求得我國傳統詩學的“別立新宗”。朱氏的新詩創作和詩歌翻譯為我國新格律體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朱湘的詩歌翻譯活動及其譯論進行觀照,將有助于增強人們對朱湘詩歌翻譯歷程的認識,并提高朱湘在我國譯界的歷史地位。
一 朱湘擇譯外國詩歌的特點——譯作無疆,譯著等身
朱湘擇譯外國詩歌呈現了幾個顯著的特征。其一,擇譯的詩歌源語種類多。朱湘一共翻譯了多達15個國家的詩歌120余首,主要有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臘、羅馬、意大利、西班牙、德國、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等,幾乎世界各國凡產生過較大影響的詩歌都被他注意到了。朱湘對于這些諸多不同的源語詩歌,要么直接從原文譯出,要么由英語轉譯;其二,擇譯的體裁相當廣泛。從《朱湘譯詩集》來看,共收入119首詩,而且體裁種類繁多,包括敘事詩、民歌、民謠、十四行詩、格律詩、史詩、格律詩、寓言詩、說唱詩等。其三,擇譯的外國詩歌,時間跨度大,僅從他的《番石榴集》來看,擇譯的最早的外國詩歌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紀,而最晚的則是公元后十八世紀乃至二十世紀初,時間跨度達幾千年;其四,擇譯的外國詩歌大都為世界公認了的名篇佳作。這些域外詩歌集中展現了世界各國詩人們的才智,也集中反映了人類在詩歌這塊沃土上長期耕耘的勞績和長期積累的經驗。朱湘之所以選譯不同國家多種體裁的詩歌,是因為我國傳統詩學體例中“抒情詩的偏重,使詩不能作多方面的發展”[1]。
二 朱湘不朽的翻譯遺產——鋪架橋梁,創新開拓
在朱湘的文學生涯中,譯介外國文學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朱湘前后共發表譯詩120余首,出版多部譯詩集。朱湘最早的譯詩集是192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路曼尼亞民歌一斑》,該集包括朱湘的譯作14首和《重譯人跋》。從該集的選材來看,朱湘特別重視翻譯被壓迫、被奴役的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學,選擇那些可以用來借鑒、影響、改造中國傳統詩學的外國詩歌,正如朱湘在該集《重譯人跋》中所言,“民歌是民族的心聲,正如詩是詩人的。又如從一個詩人的詩可以推見他的人生觀、宇宙觀、宗教觀,我們從一個民族的民歌也可以推見這民族的生活環境、風俗和思想”[2]。如朱湘選譯了羅馬利亞詩人哀闌拿·伐佳列斯柯(Elena Vacarescu)的詩集《丹波危查的歌者》(Bard of the Dimbovitza)中的兩首短詩《瘋》(Mad)和《月亮》(The Moon)。《三星集》是詩人自編的一本西詩譯集,收錄了他所翻譯的三篇長詩,即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牧歌《邁克》(Michael)、柯爾律治(Coleridge)的《老舟子行》(The Ancient Mariner)和約翰·濟慈(John Keats)的《圣亞尼節之夕》(The Eve of St.Agnes),此三篇長詩都是英國浪漫詩歌中的名著,三首長詩后來歸入詩人逝后出版的《番石榴集》之中。《番石榴集》是繼《路曼尼亞民歌一斑》之后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36年出版的,這是詩人正式出版的第二本譯詩集。朱湘一生的譯作除《路曼尼亞民歌一斑》外,絕大部分都收錄在該集中。這本詩集在編排上分上中下三卷,收詩101首。上卷收有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古國的古詩44首,如埃及的《死書》等;中卷收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等國34位詩人的53首短詩,如英國詩人約翰·威廉·華特生(John William Watson)的《死》;下卷收入了《若木華集》中的短詩、《三星集》中的3首長詩和詩人翻譯的另一篇長詩《索赫拉與普魯通》(Sohrab and Rustum)。《番石榴集》是最能顯示朱湘在譯詩方面的實績,也最能體現他從事譯詩工作的用心。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朱湘的譯詩,除已收入《路曼尼亞民歌一斑》和《番石榴集》外,還有一些零星的譯作已經發表而未入集。這些零散的譯作后來集入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湘譯詩集》,共119首譯作,除選入譯者生前出版的兩部詩集的全部譯詩外,另收零星譯作5首,包括約翰·濟慈的《最后的詩》、丁尼生的《夏夜》、白朗寧的《異域相思》、克勞的《不要說這場奮斗無益》和拉馬丁的《初恨》。朱湘一生譯詩眾多,在向漢語世界傳播域外詩歌文化的同時,為漢語白話新格律譯詩規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以朱湘漢譯阿拉伯著名的民間詩歌中的《水仙歌》(The Song of the Narcissus)一段為例:
I consider the flowers(我凝視著百花),I talk with the flowers in moonlight(我與百花密談于月夜).My beauty gives me a throne among them(嬌容雖是高位我于花叢),Yet I am a slave(我還是一個奴隸).
原詩并不押韻,卻語言精練。朱湘的譯詩采用了歐化漢語的翻譯策略,如“consider”、“talk with”和“give me a throne”分別翻譯為“凝視”、“密談”和“高位我”,特別是第三行基本上屬于西化的表達方式。將這些陌生化的詞語和句法結構引入我國主體詩學,顯得更有詩意,更具有意境之美,這種意境之美正是中國古典詩歌美學所極力追求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新白話體詩歌的發展。
三 朱湘的譯論建樹——求真求善,別具一格
就史料來看,朱湘的諸多譯論體現在他的《說譯詩》一文。朱湘在該文中指出,“我們應當承認:在譯詩者的手中,原詩只能算作原料,譯者如其覺得有另一種原料更好似原詩的材料能將原詩的意境傳達出,或是譯者覺得原詩的材料好雖是好,然而不合國情,本國卻有一種土產,能代替著用入譯文,將原詩的意境更深刻地嵌入國人的想象中,在這兩種情況之下,譯詩者是可以應用創作者的自由的”[3]。從這段話來看,朱湘的譯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朱湘主張“詩人譯詩,以詩譯詩”,突出意境,即譯詩不可滿足于達意,“首先力求保持詩歌的意義和意境”[4]。正如著名譯家黃新渠所言:“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不但要充分理解原詩的內容,還要理解詩的感情和言外之意,在傳達原詩的意境上下功夫”[5]。第二,詩歌翻譯是一種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再創作。朱湘提倡“譯詩者是可以應用創作者的自由的”,強調詩歌翻譯的“創作論”,“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時候翻譯比創作還要難。”朱湘主張“然而不合國情,本國卻有一種土產,能代替著用入譯文,將原詩的意境更深刻地嵌入國人的想象中”,也就是說,詩人在翻譯詩歌文學作品時,在堅持“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路徑的同時,為了將域外文化引入本土,主張在異化的基礎上,采用歸化的翻譯規范。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異國情調”,譯入語讀者不僅可以接受,而且還會欣賞[6];另一方面,還可以“讓譯文接近讀者”,如詩章的結構、詩行的排列以及詩歌的押韻,朱湘都盡可能照原詩傳達出來,力求做到既“信”又“達”。以他漢譯布里吉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的《冬暮》(Winter Nightfall)為例,原詩單行為三音步,雙行為二音步,且雙行押韻。朱湘直接將原詩的形式移植到他的譯文,其譯詩的單行采用了7個字,雙行是4個字,而且還可以劃分出整齊的三音頓和二音頓,并保留雙行押韻。他的譯文吸收了西洋詩歌的章法特點,其詩行長短錯落,整飭對稱,使得譯文節奏既有規律又有變化,讀者很容易將其與中國古代的民歌聯系起來,真正做到了“讓譯文接近讀者”。
[1]朱湘.北海紀游[A].中書集[C].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
[2][3]朱湘.重譯人跋[A].路曼尼亞民歌一斑[C].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4]劉重德.譯詩問題初探[J].外國語,1989,(5).
[5]黃新渠.中國詩詞英譯的幾點看法[J].中國翻譯,1981,(5).
[6]孫藝風.翻譯與跨文化交際策略[J].中國翻譯,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