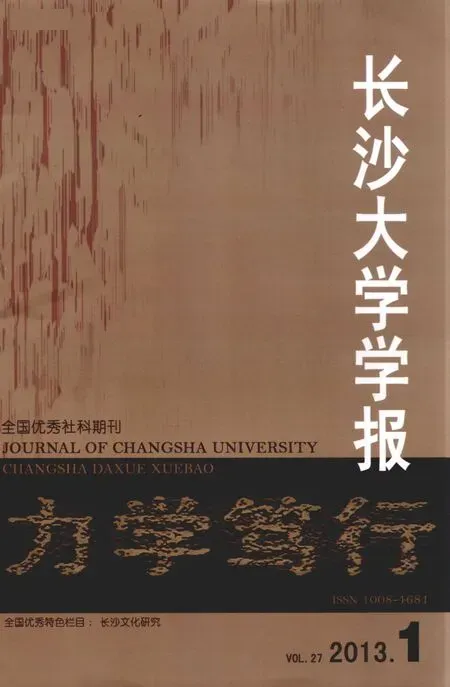從歸化和異化論看《駱駝祥子》的三個英譯本中人名的翻譯
郭 麗
(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基礎課部,江蘇無錫214092)
一 “歸化”和“異化”
傳統上翻譯被認為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然而,隨著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不斷增加,翻譯家們逐漸認識到文化差異才是翻譯中最主要的障礙。隨之有了美國翻譯家兼理論家韋努蒂(Venuti)提出的“歸化”和“異化”這一對概念。他認為:歸化策略是要“按照譯入語的文化價值觀對原文進行我族中心主義的分解,把原作者帶回家”,即“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語言表達方式”[1]。換言之:“歸化”是指譯者采用適合目的語語言文化習慣的流暢易懂的文體來翻譯,其宗旨是盡可能減少目標讀者對外文本的生疏感;“異化”則是指翻譯文本有意識地保留原文本的異國風味,從而打破了翻譯文本的語言及文化習慣。在老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的三個重要譯本中出現了許多的人名,其中的翻譯充分體現了“歸化”和“異化”這一理論概念。
二 三個不同譯本中人名的翻譯
(一)伊萬·金譯本中人名的翻譯
伊萬·金認為“中國人的名字里都含有一個意義”,但是如果把這個意義用英語表現出來,就會使這個名字不像個名字。正如黃新渠教授在翻譯《紅樓夢》時,把“林黛玉”譯成“Black Jade”,“賈寶玉”譯成“Magic Jade”,“薛寶釵”譯成“Precious Hairpin”,又如劉音凱教授在《歸化——翻譯的歧路》一文中所說,這樣翻譯人名有無根據地把這些人名形象化之嫌[2]。這些名字導致外國人在讀這本中國的經典著作來,非但不會有美的感受,體會不到中國古典的詩情畫意,反而會覺得這些名字晦澀繁瑣。英國學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曾經這樣評價按歸化法翻譯的人名:“……姑娘的名字譯成英文后成了‘寶貴的玉’、‘金色的蓮花’和‘冬季的櫻桃’,這樣越發給人一種矯揉造作的印象。”[3]作者老舍首先對伊萬·金譯本對于人名的翻譯法表示質疑。老舍在1948年10月21日致勞埃得的信中說道:“在中文中‘祥子’的‘祥’可以解釋為‘忠實’、‘幸運’、‘吉兆’、‘成功’等意。而伊萬·金譯文中的‘Happy’很明顯不怎么貼切。另外,伊萬·金將原著名‘駱駝祥子’改成‘洋車夫’,把祥子的綽號‘駱駝’在書名中省去,也削弱了著作的表現力。”[4]
“駱駝”出現在小說的名字里,是因為它與祥子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并一直影響到全篇。正如波蘭留學生阿格涅什卡在其論文《論老舍名著<駱駝祥子>的人物及語言》中所說的:“老舍把‘駱駝’這個動物的名字擱在祥子的前面,是有寓意的。這是說祥子老實、耐勞得像一只駱駝。人變成了走獸,多么可悲,這是藝術形象告訴人們的真理:這樣的舊社會應該改造。”[5]其實,“駱駝祥子”與“祥子”并不僅僅是名稱的不同,而且代表了祥子精神世界的改變。當他還是“祥子”的時候,對未來一切都充滿了希望,他靠自己的努力攢錢買車,也贏來了好名聲。而當他變成了“駱駝祥子”的時候,雖然他還沒有喪失誠實、善良這些優秀的品質,但對于金錢越來越在乎的態度使他越來越向個人主義的深淵滑落。伊萬·金將“虎妞”這個名字翻譯成“Tiger Girl”,雖然能使美國的讀者聯想到這個女性形象的“兇猛殘暴”,但這樣的翻譯法使名字看起來很怪異,與原文中描寫的舊中國婦女形象虎妞相去甚遠,沒有達到尊重原文的目的,當然無法起到文化傳遞的作用。
在伊萬·金譯本中有很多人名的翻譯如:“祥子”——Happy Boy;“虎妞”——Tiger Girl;“小福子”——Little Lucky One;“小馬兒”——Little Horse;“黃天霸”—Tyrant of the Yellow Turbans;“小文”——Little Elegance[6]。
譯者為了使英語讀者能夠易于理解小說的人物名稱,對原著作中的人名用了歸化的翻譯法。但是這樣的譯法實際上無法傳遞原著中的所富涵的中國特色文化的東西,無法使外國讀者真正了解中國文化和小說所要反映的當時的歷史特征及人物形象.
用異化翻譯的人名如下幾個:“阮明”——Yuang Ming;“左先生”——Mr.Tso;“馮先生”——Mr.Feng;“曹先生”——Mr.Ts’ao;“高媽”——Kao Ma[7]。
歸化和異化結合起來的:“劉四爺”——Founh Master Liu;“王二”——Wang Two;“老程”——Old Ch’eng[8]。
(二)施譯本中人名的翻譯
施曉菁的譯本中人名的翻譯如下:“駱駝樣子”譯成:Camel Xiangzi;“虎妞”譯成:Tigress;“劉西爺”譯成:Fourth Master;“小馬兒”譯成:Little Horse;“黃天霸”譯成:Huang the Tyrant;“高媽”譯成:Gao Ma[9]。
她的譯文中歸化和異化的翻譯方法皆有體現,而施譯與伊萬·金對人名的翻譯的差異原因在于對于中國文化本質認識上的差異。中國人和英美人的名字不僅在語言結構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別,在語言含義上的差異也普遍存在。
(三)詹姆斯譯本中人名的翻譯
詹姆斯譯本中人名的翻譯如下:“駱駝樣子”譯成:Hsiang Tzu;“曹先生”譯成:Mr.TS’ao;“老劉”譯成:Old Liu;“黃天霸”譯成:those great heroes Li K’uei and Wu Sung[10]。
(四)三個譯本中來自典故的人名的翻譯
而對于來自典故中人名的翻譯三個譯本的處理也不同,如“有急等用錢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黃蓋,愿打愿挨!”(Lao She 1955:100)的三個譯本分別是:
——When you had on one hand a person who had money and was willing to lend it.And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 whose need for money wouldn’t wait,it was like Chou Yu and Hwang Kai in the story of“The Three Kingdoms”.Chou struck his head Hwang to prove to an enemy general that they no longer friends;one was happy to strike and the other to be struck?(Evan King 1945:105)[11]
——There were those who needed the money and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lend it.It Was mutual aid!(James 1979:69)[12]
——Some people needed money,and others were willing to lend it to them.The punishment is skillfully given by one side,and gladly accepted by the other.(Shi Xiaojing(1981:163)[13]
伊萬·金把“周瑜打黃蓋”的典故翻譯了出來,但譯入語讀者未必對這個典故就了解,所以看了他所講的東西應該是一頭霧水,而詹姆斯和施曉菁的譯文都通過意譯做到了傳神達意,更容易讓譯入語讀者明白所要表達的意思。
三 結語
通過對比分析,可見老舍作品《駱駝祥子》中人名所具有的文化因素濃厚,這是譯者翻譯過程中的難點之一,也是譯者之間產生差異的地方。這說明翻譯不僅是語言信息的轉換,而且也是文化信息的移植。因此,對于文化信息移植的兩種主要策略“歸化”和“異化”的選擇取決于特定時代下的文化輸入觀在譯者體驗下的反映,是時代文化需要的折射。另一方面也說明譯文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接受與否,是譯者選擇、處理文化因素的決定性因素。
[1]周昕.從奈達理論看《駱駝祥子》施譯本[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2][3]劉彤.北京方言與文化負載項的翻譯——以《駱駝祥子》英譯本翻譯為例[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4]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 and New York:Pergamon,1981.
[5]盧媛媛.《駱駝祥子》的伊萬·金(Evan King)英譯本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6][7][8][11]Lao She.Rickshaw boy[M].Evan King,trans.New York:Reynal& Hitchcock Publishing House,1945.
[9][13]Lao She.Camel Xiang Zi[M].Shi Xiaoqing,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8.
[10][12]Lao She.Rickshaw[M].Jean James,tran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