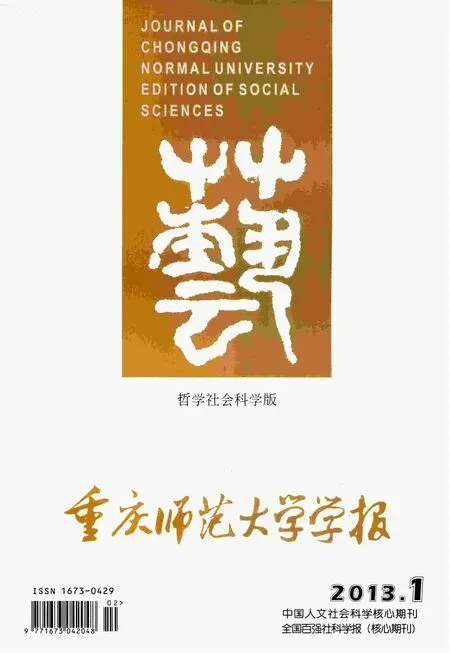從《詩》學到詩學
——劉勰《詩經》闡釋與《文心雕龍》詩學理論
石了英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文學院,廣東 佛山 528000)
劉勰“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在“宗經”視野下“彌綸群言”著作《文心雕龍》,沈約謂之“深得文理”。作為“六經”之首的《詩經》是《文心雕龍》的一個最大的接受對象。掃描《文心雕龍》的《詩經》接受現象,我們發現劉勰的諸多詩學觀念的生成與他對《詩經》的闡釋緊密相關。
一、《文心雕龍》對《詩經》的征引
《文心雕龍》(本文所引《文心雕龍》參見范文瀾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后文凡引本書,只注篇名)中共引述著作500余部,涉及到對200余位作家的評論,作為“六經”之首的《詩經》被征引的次數最多。據統計,《文心雕龍》對《詩經》的征引,從表現特征的“顯與隱”來看,可分為明引和暗引兩類。《文心雕龍》共50篇中,明引《詩經》的達34篇,高達99處。這個數字的得出僅以篇中出現的“《詩》”、“《風》、《雅》”、“《雅》、《頌》”、“詩人”、“三百”、“四始”和《詩經》原句這些直接指涉《詩經》的出處為計算依據。暗引包含兩種情況:以“經典”、“比興”、“圣文”等指代性說法暗含對《詩經》的評述,襲用、改裝《詩經》的成辭。《詩經》不僅充斥在《文心雕龍》的字里行間,也滲透進《文心雕龍》的理論肌理、論文脈絡之中。
(一)以《詩經》為文體之源頭
從曹丕《典論·論文》把文體分為四科八體以來,《文賦》、《文章流別論》一步步細化文體的區分。劉勰在博通經史子集的厚實知識視野中縱論文體,涉及70多種。《文心雕龍》中所述出自《詩經》的文體有:
賦、頌、歌、贊,如“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宗經》)。“賦自詩出,分歧異派。”(《詮賦》)“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明詩》)“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明詩》)“周人”的“匡諫之義”實際指《詩經》。
楚辭,如“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固知《楚辭》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辨騷》)
誄,如“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誄碑》)。
哀,如“《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哀吊》)
吊,如“詩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哀吊》)。
章,如“《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章表》)。
譜,如“鄭氏譜《詩》,蓋取乎此”(《書記》)。
諺,如“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圣賢《詩》《書》,采以為談,況逾于此,豈可忽哉!”“《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并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書記》)
刺,如“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書記》)
騷,如“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通變》)。
箴,如“及揚雄《百官箴》,頗酌于《詩》、《書》”(《事類》)。
從文體譜系上論證《詩經》為各種文體之源,對其“宗經”視野提出了有力論證。
(二)以《詩經》為文學創作的范本
劉勰把《詩經》作為文學創作的范本。一把《詩經》作為文學創作取“意”的最高范本。所謂“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宗經》),“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奇貞,玩華而不墜其實”(《辨騷》),“號依詩人”(《事類》),“本經典以立名目”(《詔策》),都明確把《詩經》推到“規式存焉”(《頌贊》)的典范位置。二把《詩經》作為文學創作取“藝”的最高范本。《詩經》為各種藝術手法的活水源頭,“《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比興》),“《詩》總六義,風冠其首”(《風骨》),六義可以說是中國古典詩學的藝術精髓所在。劉勰盛贊《楚辭》“依《詩》制《騷》,諷兼‘比’、‘興’”,并設《比興》篇來說明比、興兩種創作手法。劉勰還從《詩經》批評中概括總結出“以少總多”的詩歌創作手法:“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物色》)劉勰認為《詩經》“義固為經,文亦足師矣”(《才略》),內容與形式都值得后世典范。
(三)以《詩經》為文學批評的標準
以《詩經》作為文學評價的標準。劉勰在“文之樞紐”部分,特別拈出《正緯》《辨騷》兩篇,并“按經驗緯”、“依經辨騷”來對緯書與騷體作出辨析。劉勰“依經辨騷”,認為《離騷》“同于《風》、《雅》者”有四,“異乎經典者”亦有四,都是以《詩經》的準則來評說。《離騷》“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四者同乎《風》《雅》。“典誥之體”指《尚書》,后三者均與《詩經》相關。“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等四者“異乎經典”,也就是不合《詩經》“無邪”的溫柔敦厚的表現手法。
(四)對《詩經》文本語言的化用
除了直接對《詩經》文本大量征引和批評外,劉勰還大量化用《詩經》文本語言、成辭來行文達意。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事類》中指出《文心雕龍》之辭采,“仍染時尚,未脫駢文窠臼,惟‘奇’字較多,頗見新風,故暗引成辭,所在多有”[1](466-467)。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化用也是一種接受、一種闡釋。在遣詞造句上將《詩經》與《文心雕龍》作比照,可以發現劉勰不僅在用語而且在思想上深受《詩經》影響。從語言襲用出發,可以探尋劉勰對《詩經》的改裝及這種改裝對于其相關詩學思想的積極作用。
《詩經·大雅·文王》中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思想重在變革求新,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政治哲學觀念。劉勰《文心雕龍》四次援引“維新”之說:“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史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時序》)“相如封禪,蔚為唱首……固維新之作也。”(《封禪》)“后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奏啟》)《史傳》、《時序》二例之“維(惟)新”涵義,與《大雅·文王》相一致,但《封禪》、《奏啟》的“維(惟)新”,則具有明顯的文學批評意味。司馬相如于兩漢封禪之文有首創之功,且文采華茂,故稱之“維新之作”,西晉以后,“奏”體的應用范圍日益寬廣,故曰“惟新日用”。《文心雕龍》全文中“新”字出現了48次,所謂“通變”的“變”也就是求“新”。劉勰對“新”重視的思想淵源,即便不是直接來自《詩經》,也顯然是受到《詩經》啟發。從政治觀到批評觀,劉勰對《詩經》進行了語言與思想的雙重襲用與改裝。
《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邶風·柏舟》是一首婦女自傷不得于夫、見侮于眾妾的詩,詩中以不能如鳥奮飛,表達心情的憂傷。《文心雕龍》中多次襲用這一成辭。“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辨騷》)“后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夸飾》)“至于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封禪》)劉勰筆下的“奮飛”不再是心情的表達,而指一種充滿力量感,能夠超古沖天的行文氣勢,如《楚辭》就具有這種氣勢之美,而邯鄲《受命》由于“風末力寡”就達不到奮飛的境地了。“奮飛”之境與劉勰所謂的“風骨”、“氣”、“勢”等詩學范疇有著內在的關聯。從《詩經》的達情修辭到《文心雕龍》的審美風格論,二者之間實現了會通。
又,從《小雅·鼓鐘》的“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到《宗經》的“則義直而不回”,從《衛風·碩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情采》的“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從《小雅·角弓》的“翩其反矣”到《情采》的“真宰弗存,翩其反矣”,諸如此類化用,大量播散于《文心雕龍》文本中,由此可以探出劉勰對于《詩經》的熟稔,以及對《詩經》的全方位接受,通過接受生成、闡明自己的詩學觀念。
二、《詩經》闡釋與劉勰的審美理想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劉勰在《明詩》篇給出了“歷史”與“比較”兩種考察文學的方法論,以之審視“九代詠歌”,則是:
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虞歌《卿云》,則文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通變》)
劉勰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九代文學拋物線式的向上與向下兩個發展階段,從黃帝、唐、虞、夏的醇厚質樸到商、周的典雅華麗,這是向上的發展,從商、周的典雅華麗轉向楚漢的夸張富艷,繼而轉向魏晉的浮淺綺麗,再到宋初的詭誕新奇,這是向下的發展。拋物線的高峰是商周文學,兩端是遠古文學和宋初以來的文學。
“商周篇什”最有代表性的顯然是《詩經》,所謂“商周麗而雅”其實可以理解為《詩經》“麗而雅”。劉勰以“雅、麗”二字來說明《詩經》的審美風格,這在《文心雕龍》文本中亦隨處可見,如“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征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明詩》),“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夸飾》),“詩人麗則而約言”(《物色》)。“雅”傾向于指《詩經》的內容方面,“麗”則說的是《詩經》的形式方面。
“雅”的內涵指的是什么?《頌贊》篇劉勰解釋道:“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可見劉勰從儒家詩教角度來解釋雅,關鍵在一個“正”字。儒家詩教由來已久,孔子以“無邪”論《詩》,指《詩經》內容純正,《毛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毛詩序》訓“雅”為“正”,又以“政”解之,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為雅,“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教成為政教的手段。“以正釋《詩》”、“以正訓雅”的歷史循環闡釋中,《詩》與“雅正”的合法關聯被建構起來,并成為漢代乃至其后若干世紀士人不可動搖的共識。
劉勰在這些前理解的基礎上對《詩經》進行再闡釋,同樣“以正釋雅、以雅釋《詩》”。劉勰云:“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明詩》)《說文解字》中對“持”的解釋是“持,握也”,也就是“持守”、“把握”、“節制”、“約束””的意思。詩是用來“順美匡惡”,約束、持守、把握、節制人的性情而不使其失正,可見劉勰對于孔子詩論和《毛詩序》的因襲。
由此也可以看出,劉勰認為文學創作內容“雅正”才是關鍵。《體性》篇提出:“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意謂童子學習,要分清雅正的和淫糜的,先學習雅正的,因為“本體不雅,其流易弊”(《諧讔》)。劉勰提出的八種文學風格,首要一種便是“典雅”,“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體性》),典雅之作需從經書中熔化出來,合乎儒門,以“經”為寫作學習對象,自然能得到典雅的文風。在《文心雕龍》中,劉勰還經常提到“雅言”、“雅聲”、“雅章”、“雅歌”、“雅文”、“雅義”、“雅詔”、“雅制”、“雅詠”等術語。他還把“雅”的風格分成很多種類,如“舒雅”、“雅贍”、“雅而澤”、“博雅”、“儒雅”、“明雅”、“淵雅”、“典雅”、“密而兼雅”、“雅有懿采”、“文雅”、“英雅”、“精雅”、“溫雅”、“傲雅”、“麗雅”、“雅壯”、“雅潤”、“雅麗”,并一律持肯定態度。從《詩經》的解讀到對“典雅”風格的歸納,可以見證劉勰從《詩經》批評到詩學觀念演化生成之間的聯系。
劉勰以“麗”來歸納《詩經》的美學特色,但他對于“麗”的態度非常矛盾。我們比較一下劉勰對《詩經》和《楚辭》的批評態度即可看出。劉勰認為《楚辭》“雖取熔《經》旨,亦自鑄偉辭”,對《詩經》是既有繼承又有發展,一方面“《楚辭》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另一方面《楚辭》“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辨騷》),“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時序》)。也就是說,劉勰雖然認為《楚辭》內容上不及《詩經》雅正、純正,但辭采上“耀艷而采深華”、“驚采絕艷”、“艷溢錙毫”,無可比并,絕對超越了《詩經》。如此說來,應是《詩》以“雅”勝,《騷》以“麗”勝,內容上《詩經》不愧為典范,辭采上最高的典范則應是《楚辭》,而不是《詩經》。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劉勰提出了“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的創作指導原則。
可是,劉勰雖然對《楚辭》之“麗”勝過《詩經》有充分認識,但他“為文立則”,所歸宗的還是《詩經》。筆者認為劉勰之所以有如此矛盾態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他的“宗經”思維過于根深蒂固,“是以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征圣》)“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史傳》)劉勰時代,《詩》的經典地位已經確立,而《楚辭》則尚未能得到儒家知識分子的普遍認同。二是劉勰認為《詩經》以后文學的發展趨勢是“彌近彌澹”,走向了一條不斷退化的路。從文學史的角度看《詩經》、《楚辭》和漢賦,時代上歷經“圣人時代—去圣未遠—去圣久遠”,內容上呈現出“正—變—訛”、“雅麗—艷麗—淫麗”的發展趨勢。近代辭人的轉變,劉勰以為是從《楚辭》開始的,“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馀影,于是乎在。”(《時序》)“楚艷漢侈,流弊不還”(《宗經》),《楚辭》作為流弊產生的源頭,如果被提倡,難免會對當時文壇發出不正確的導向信息。對這一點,劉勰非常謹慎。漢人辭賦滔滔不返地走向“訛濫”,正是劉勰“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的動機,目的是使文學發展能回到“正末歸本”的道路上。以“雅”為正,從“補偏救弊”上考慮,劉勰自然選擇提倡《詩經》之“雅麗”,而不是《楚辭》之“艷麗”。
“麗”在《文心雕龍》中共出現60次。不同于劉勰對“雅”的一概贊同,他對各種“麗文”、“麗句”、“麗辭(詞)”的態度不一。結合《文心雕龍》“麗”字的源出語境考察,劉勰持肯定態度的有“佳麗”、“雅麗”、“偉麗”、“壯麗”、“弘麗”、“清麗”、“夸麗”、“綺麗”、“絕麗”、“巧麗”、“組麗”;持否定態度的有“縟麗”、“靡麗”、“淫麗”。劉勰對“麗”有一個“度”的要求,即“麗而雅”、“麗則而約言”、“麗而不哀”、“麗而動”、“麗而規益”。從“麗而……”這種句式中,可以看出“麗”有許多規約。文辭之“麗”的前提是內容之“雅”,即能“持人情性”,“麗”文指向“哀而不傷”,指要能“動人”,能感化人,要有所“規益”,有勸誡功能。“麗則而約言”是言辭表達上的規定,“膏腴害辭”、“繁華損枝”就是不知道“約言”而使文章流于淫麗的表現。所以文學創作重要一點就是“酌雅參麗”,“麗”是“雅”的制約下有限度的自由,“雅”和“麗”在相互制約下達到平衡。
《詩經》文本體現了劉勰的“雅麗”文學審美理想,這一審美理想也通過《詩經》闡釋得到張揚與釋放。正如劉紹瑾所言:“從圣人經典中解讀出來的‘雅’與‘麗’似乎構成了劉勰心目中文學的本質,核心特征。”[2](255)劉勰《詮賦》云:“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麗詞雅義,符采相勝”不但是劉勰論賦的本體要求,也可以說是劉勰論述一切文體的最高審美理想。《詩經》文本與劉勰的詩學觀在“雅麗”這一最高的審美理想中達至視野融合。
三、《詩經》闡釋與《文心雕龍》創作論
《文心雕龍·序志》篇中,劉勰自序“為文”三大結構:“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采”。劉勰以論文來“樹德建言”,是有著強烈的理論建構雄心的,尤其是“剖情析采”的創作論部分,從《神思》到《程器》,幾可與現代版的《文學理論》相媲美。“六經”之中,最有“文采”的《詩經》順理成章成為劉勰心中的典范文本,從對《詩經》的批評中,劉勰提出了諸多文學創作上的重要問題。
(一)“為情而造文”
劉勰認為“情、文”關系分為兩種:“為情而造文”和“為文而造情”,各自以“詩人”(《詩經》的作者)和“辭人”為比附: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一語,道出了《詩經》“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的創作特色。《詩經》中的國風、小雅多是老百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抒懷,情感的表達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極富生活氣息。而近人辭賦“為文造情”,必然導致“繁彩寡情”,只是語言能指的華麗盛宴。劉勰繼而具體闡述到:“詩人之告哀焉。”(《才略》)“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時序》)“哀”、“勤而不怨”、“樂而不淫”、“怒”都是從情感的角度評價《詩經》。把《詩經》之“為情而造文”鋪展開來,則是以下兩點文學創作論的發現。
1.情動辭發,自然之道。《詩經》的“為情造文”的創作最高旨趣在于“真”、“自然”,也就是“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詩》)。“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紀昀評《文心雕龍·原道》說:“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3](24)對于情、辭的關系,劉勰指出:“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情采》)也即“情、志”為內,“辭、采”為外,情志為主,辭采為次。文學創作從內(中)到外,由情及辭,從內容到形式,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為文而造情”是對于“情本”的偏離,“真宰弗存”,實折本逐末之舉。
劉勰雖主張“為情造文”,但并非一切情皆可自由發抒。他對情提出了諸多限制和要求。(1)“雅正”。從“雅麗”的審美理想來看,情自然要符合“雅”的標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傳》)要以“正”束“情”。“四言正體”、“義歸無邪”的《詩經》為正,而“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所謂“新學之銳”即指齊梁文章“趨近”、“適俗”成風,偏離“雅正”,所以劉勰高呼要“確乎正式”,“執正而馭奇”,這樣才能使文學發展走向正途。(2)“要約而寫真”。針對齊梁文風,劉勰有感于“后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以至“繁采寡情,味之必厭”(《情采》)。文辭上不知節制,情感上遠離真實,華美形式掩蓋了作品的內容,豐富文采遮蔽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背離了“以情為本”、“因內符外”的創作思路,所以劉勰寫作《情采》力圖挽救當時文風。正如紀昀所評點:“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而質亡,故彥和痛陳其弊。”[4](297)劉勰從《詩經》中提煉出“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情采》)的詩學原則,“真”與“約”成為制約“情采”的兩大要求。劉勰并把這一詩學原理貫穿于整部《文心雕龍》中,認為“約舉以盡情”(《頌贊》),才能達到“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熔裁》)。文章既要表達“真”情,又要在“約束”下有的放矢地斟酌情感的表達。
2.以情為本,文辭盡情。劉勰《宗經》標“六義”,首要一義是“情深而不詭”,《熔裁》標“三準”,首要一準是“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可見“情”在劉勰心中的顯要地位。“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知音》)“情”是鏈接作者和讀者的心理通道。正如戚良德所說:“整個《文心雕龍》的創作論,正是以感情之表現為根本和中心,對感情之產生、感情表現的原則以及感情表現的方法等問題進行全面、系統闡述,從而構成一個‘以情為本、文辭盡情’的‘情本’論的話語體系。”[5]“情”固然為為文之根本,但只有通過“文辭”才能形成物質媒介的文章,才能被讀者接受。所謂“文質附乎性情”(《情采》),“文質”是偏義復詞,指文采。文采是以性情為依托的,文采運用要以有助于情感表達為宗旨。又所謂“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比犬羊;犀兕有皮,而色姿丹漆:質待文也”。此處,文即辭采,質即情理。文采必須依附在質地上,質地也需要文采來修飾,辯證地道出了“情采”二者在文章寫作中的關系。
從肯定《詩經》的“為情而造文”出發,劉勰以“情采”勾連了整部《文心雕龍》“內容與形式”兩個維度的理論建構。《熔裁》篇云:“萬趣會文,不離辭情”,文章旨趣千變萬化,但都離不開“情”、“辭”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在行文中,劉勰常常“情(義、志、理)采(言、文、辭)”并論對文章寫作提出要求,如“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征圣》),“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宗經》),“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雜文》),“情與氣偕,辭共體并”“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風骨》),“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可以說,劉勰詩學是以“情采”為經緯二維,并以此為軸向外延展,從而形成了《文心雕龍》以“情采”為核心的又在意義上不斷外延的本體論詩學邏輯體系。
(二)比興
“比興”大量運用于《詩經》文本中,“《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比興》)。作為“六義”之二的“比、興”是詩人(《詩經》作者)抒情言志最重要的表達方法,是劉勰論《詩經》藝術的又一重點。那么,劉勰是怎么認識《詩經》的比興呢?又從中衍發出什么詩學話題呢?
劉勰將《詩經》中的“比興”手法理論化抽離出來,對其修辭美學內涵進行總結,使之成為兩種恒定的藝術修辭手法。“故比者,附也”,“蓋寫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比”是比附、比喻,用事物來打比方,明白而確切地說明用意。《詩經》用“比”例如:
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比興》)
劉勰從這些實例中歸納出“比”可以分為“比義”和“比類”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的“比”都要以“切”作為使用標準,“凡斯切象,皆比義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切”即切合,比體和喻體要在某些相似點上切合對方。故而,劉勰在《比興》“贊曰”中總結到“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比的兩樣事物雖然象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那樣絕不相關,切至相合就可以象肝膽般相親。這既對《詩經》“比”的運用實踐進行了歸納,又恒定了“比”這種修辭手法的美學內涵。
“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興”是起興,依照含意隱微的事物來寄托情意。《詩經》中用“興”例如:
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疑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后見也。(《比興》)
劉勰所取的“興”例,襲用《毛傳》而來。《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注“興也。”關雎這種鳥成對后,感情深摯和別的關雎分別,所以詩人用關雎起興,用來比后妃有貞潔的德行。《詩·召南·鵲巢》:“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毛傳注“興也。”斑鳩住在鵲巢里用心專一,所以詩人用斑鳩起興,用來比婦人有專一的用心。劉勰認識到,這種隱幽發微的涵義,讀者是不容易看到的,故要“發注而后見”,因為“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用鳥來起興,是“稱名也小”,用來比貞潔和專一的德性是“取類也大”。雖然劉勰受“宗經詩教”觀的束縛,未能正確把握《詩》旨,而過度闡釋了以鳥起興,但他道出“興”之“以小見大”的方式,具有某種普遍性意義。
此外,劉勰以“美刺”釋“比興”,“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比興》)比興是懷著憤激的感情來指斥,用委婉的譬喻來寄其諷刺。劉勰以“美刺”解釋“比興”,難免產生如漢儒釋《詩》時,不顧《詩》本義,一概以政教倫理比附《詩》旨的弊端,比如承《毛傳》以“后妃方德”、“夫人之義”之論闡釋《關雎》的詩旨,顯得牽強附會。從“史”的角度考察“比興”時,發現從《詩經》到《離騷》到漢人辭賦,“比興”經歷了一個日漸衰微的過程,從“詩人之志有二”到“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再到“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查乎此,劉勰不禁發出“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的感嘆。大量運用于《詩經》的比興手法消失了,根本原因在于其美刺傳統喪失了。在“美刺”闡釋視域下,比興成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在歷史的循環闡釋中被約定俗成地加載了政治道德倫理內涵,在不斷道德強化中定型化為一種特定的修辭符碼。
另一方面,劉勰將“比興”擴展到藝術創作的論述中,表現為一種“含蓄蘊藉”的審美風格和“情物交感”的藝術創作機制。王元化認為:“我國的‘比興’一詞,依照劉勰‘比顯而興隱’的說法,亦作‘明喻’和‘隱喻’解,同樣包含了藝術形象的某些方面的內容。”[5](143)以“隱”來理解興,確實是如此。《宗經》篇云:“《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攡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劉勰認為《詩經》采用比興的手法,比喻婉曲,最能切合人之情懷的抒發,《詩》要感人就要注意表達方式上的“依違諷諫”。“比興”手法是言辭“譎諫”的有效方式,因為“比興”都不是直接說出看法,而是通過一定的物象,需要讀者的感發聯想的參與,完成作者義向讀者義的傳達。與此同時,也就容易造成一種“意境深遠,含蓄蘊藉”的審美風格。“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詩品序》),此之謂也。“隱也者,文外之意旨者也”,“隱以復意為工”(《隱秀》),亦此之謂也。后世諸如“象外之象”、“韻外之味”與“興”一脈相承。
在《文心雕龍》中,“興”還有一個顯著意義:興感。“起情故興體以立。”“起情”即動情、觸物生情,“為情而造文也”。詩人內心有了憤恨,情動而發,即為“興”。劉勰還提出“觸興致情”(《詮賦》)、“睹物興情”(《情采》)、“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物色》)。創作“興感”隱含著一種從情到物,從物到情的交感往返的藝術創作機制,涉及到藝術想象的問題。在藝術構思中,劉勰還提到:“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面對激蕩人心的物色,創作者要注意內心的閑靜,也就是“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神思》)。
(三)“以少總多,情貌無遺”
劉勰認為詩人之麗與辭人之麗大有區別,“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物色》)“約言”即少,指語言之少而非意蘊之少,這里提出了一條“以少總多”的創作原則: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暳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物色》)
“灼灼”出自《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是一首祝賀女子出嫁的充滿喜慶的歌,“灼灼”狀桃花盛開時的鮮明色彩,也比喻出嫁女子嬌好美麗的容貌。中國古詩有“人面桃花相映紅”名句,桃花之鮮與女子之美相映成趣,把二者聯想在一起,便各自愈增其美,且人面桃花的意境及詩人由衷欣喜之情自然流露出來了。“依依”出自《小雅·采微》:“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一首守邊士兵歸途中回憶往事之勞苦的詩,“依依”狀寫春天柳枝的婀娜飄柔,也狀寫妻子與“我”難舍難分之情意。在我國詩詞傳統中,“柳”成了離別的象征,莫不導源于此。劉勰列舉《詩經》語言表達的諸多精妙之處,詩人或用描寫或用比喻,但目的只有一個,即用簡單而形象的意象描寫,用最精簡的語言把情與景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詩經》用少而精當的語言描摹形象,表達無盡的意蘊,這與中國“無中生有”、“虛中生實”、“言外之意”的詩學息息相通。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說的:“而藝術形象的塑造就在于實現個別與普遍的綜合,或表象與概念的統一。這種綜合或統一的結果,就構成了劉勰所說的藝術形象‘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個別蘊含了普遍或具體顯示了概念的特性。”[5](148)“以少總多”正是劉勰從審視《詩經》創作藝術而提煉出的詩學原則。
《文心雕龍》中論及《詩經》修辭藝術的還有《聲律》、《章句》、《麗辭》、《夸飾》、《事類》、《練字》等篇,蘊藏了豐富的詩學創作原則,對《文心雕龍》詩學理論的整體建構有著重要意義。中國詩學的形成原本就與《詩經》有著扯不斷的親緣關系。正如比較文學學者厄爾·邁納在其《比較詩學》中所揭示的:“當文學是在一種特殊的文學‘種類’或‘類型’的實踐的基礎上加以界定時,一種獨特的詩學便可以出現。”[6](Ⅱ)邁納從人類接受的角度來考查世界兩大詩學體系的最初發生,認為西方的摹仿詩學是亞里士多德對戲劇進行描述和定義時建立起來的,中國的詩學是對《詩經》的定義上建立起來的。文學的批評與文學理論的生成本是一體兩面,在接受中生成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又促進接受的深入,《文心雕龍》為中國文學理論之“從《詩》學到詩學”生成模式提供了典型范例。
[1] 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2] 劉紹瑾.復古與復元古[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3] 劉勰撰,黃叔琳注.文心雕龍輯注[M].中華書局,1957.
[4] 戚良德.《文心雕龍》與中國文論話語體系[J].文史哲,2004,(3).
[5] 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 [美]厄爾·邁納.比較詩學[M].王宇根,宋偉杰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