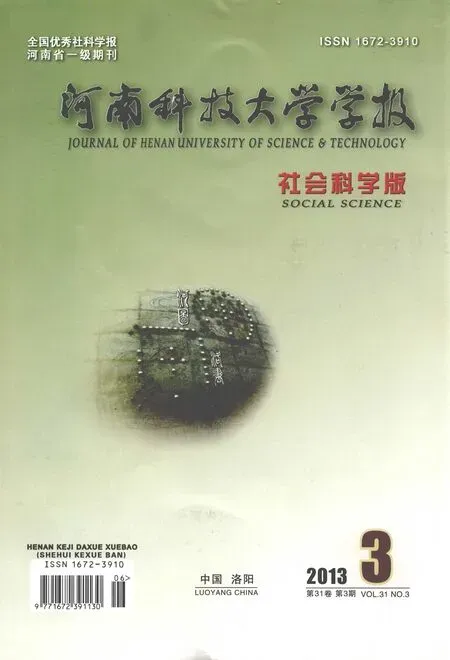從《棉被》看日本自然主義的形成與突破
賀黎
(長沙學院外語系,長沙 410003)
【藝文尋珠】
從《棉被》看日本自然主義的形成與突破
賀黎
(長沙學院外語系,長沙 410003)
《棉被》是日本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品之一,被認為是完成了從前期日本自然主義的單純模仿到具有日本特色的后期自然主義的轉變的作品,也是花袋的成名之作。在小說中,花袋在借鑒西方自然主義關于本能、自然、客觀描寫等觀點基礎上,結合當時日本社會現實和日本傳統文學觀,形成了獨具日本特色的自然主義文學作品,突破了西方自然主義的觀念和模式,體現了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對自我的不斷追求。
田山花袋;《棉被》;自然主義
《棉被》是日本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品之一,被認為是完成了從前期日本自然主義的單純模仿到具有日本特色的后期自然主義的轉變的作品,也是花袋的成名之作。
在創作這部小說之前,田山花袋曾經閱讀了西方自然主義作家如左拉、莫泊桑、福樓拜等人的作品,受到了西方自然主義深刻的洗禮。其前期也創作過一些具有浪漫主義性質、模仿西方自然主義痕跡較明顯的作品,如《女教師》、《重右衛門的結局》等,而《棉被》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日本自然主義特色的集大成之作。它不再是對西方的簡單模仿,而是注入了內在的東方品質,呈現出一種異樣的色彩。本文將從自然主義的幾個主要方面,即對自然的看法、對客觀描寫的看法以及作品寫作動機入手來分析《棉被》對西方自然主義的吸收與超越。
一
“自然”是田山花袋的小說、評論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詞之一,也是理解花袋文學的關鍵所在。在發表于1904年《太陽》雜志上的《露骨的描寫》一文中,花袋對“自然”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解釋。他認為“一切必須露骨,一切必須真實,一切必須自然”,[1]370追求一種“天衣無縫、如行云流水般具有自然之趣”[1]431的文章。這種“露骨”、“大膽”、“真實”、“自然”的文章直接指向了本能描寫。
《棉被》是根據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的。主人公時雄的原型是作家本人,芳子的原型則是其女弟子岡田美知代。小說描述了一個郁郁不得志的中年作家竹中時雄對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女學生芳子心生愛慕,最后無果而終的故事。小說最后關于主人公抱著女學生蓋過的被子、嗅著被子上女弟子的余香傷心不已的本能描寫,在當時引起了很大震動。
這種描寫人自然本能的傾向顯然與西方自然主義的影響密不可分。西方自然主義作家也將生理情欲作為“實驗小說”研究的內容之一加以提倡,如左拉的《戴蕾絲拉甘》中就充滿著情欲與本能描寫。西方自然主義作家認為:“一切藝術家都必須研究與再現真實的自然。”[2]在他們看來,真實的“自然”是現實的社會和生活。客觀真實地反映“自然”就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去描寫生活事實,反映社會現狀。他們提倡要按照社會的原始形態去描寫生活,描寫人生,把生活事實一絲一毫都不遺漏地記錄和表現出來,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是真實的。他們提倡生理情欲的描寫,但是在他們的作品中,這常常是作為實驗小說中人物命運變化發展的一條線索貫穿在作品中,作為一種因素、一種題材、內容表述的某個方面、人物形象的一種氣質特征而表現出來的。對生理情欲的描繪,理性的成分占主導地位。作家創作的目的不僅僅停留在生理情欲的表層描寫,更在于其包含的內在的、深層的意蘊。作品或預示人物的悲劇命運,或意指社會的墮落罪惡,或啟迪人生,常常具有一定的積極社會意義和審美傾向。對生理情欲的描寫,體現了自然主義深邃的理性主義和嚴肅的價值取向。左拉說:“以生理學為依據,去研究最微妙的器官,處理的是作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人的最高級行為。”[3]他的《盧貢·馬卡爾家族》與其說是生理情欲、生物遺傳的實驗展示,不如說是自然主義作家以生理學、遺傳學觀點解釋社會現象,研究人的思想行為的作品。
花袋雖然接受了西方自然主義作家強調文學描寫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沖動和人的生理情欲的一面,卻更為注重內心的寫實,體現出非理性的一面。島村抱月曾經這樣評價他:
這是一篇肉欲的人、赤裸裸的人的大膽的懺悔錄。自明治有小說以來,早在二葉亭四迷、藤村等人就已出現的這種端倪在這部作品中被明確地、有意識地揭示出來了。這種沒有附會的美丑描寫,毫無疑問更進一步地代表了傾向于描寫丑陋面的自然派的特性,這種丑陋是人自身不易覺察的人的野性的呼喚。同時,與理性的一面相對照,他將具有自我意識的現代性格的模本,用難以正視的赤裸裸的方式展示給公眾。這正是這部作品的生命和價值所在……這些內容除之前列舉的諸作家外,新近的作家并不是沒有寫到。然而,他們大多是描寫丑陋的事而不是寫心。《棉被》的作者則與之相反,是描寫丑陋的心而不是事。(筆者拙譯)
島村抱月在這里對《棉被》進行了極高的評價。首先,他借用盧梭《懺悔錄》的題名,指出《棉被》是一部揭示“肉欲的人、赤裸裸的人”的告白小說,而且這種告白性早在二葉亭四迷、島崎藤村等人就已經初露端倪。接著,他又指出小說中關于丑的描寫代表了自然派的特性,通過這種描寫表現出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現代性格”。最后,他對作品中描寫的“丑陋的心”激賞不已。
花袋的《棉被》中,故事情節都是隨著時雄的心理變化而展開,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從這一點來看,《棉被》確實是一部描寫“丑陋的心”的作品。而且,這是“人自身不易覺察的人的野性的呼喚”,是具有“自我意識的現代性格”的。正如吉田精一所說:“在《棉被》以前沒有比它更接近作者自己的實際生活,更忠實地記錄事實的作品了”,它將“羞于示人的內面,即自己的‘丑陋的心’赤裸裸地描寫出來,拋棄了社會慣有的形式,直面自己真實的面貌,這種態度表現了作者正直而真摯的本性,令世間震驚”。[4]
可見,《棉被》中的本能描寫與西方自然主義所說的本能是有一定差異的。它并不僅僅是對人的生理本能的實驗性的客觀記錄,而是隱藏在人內心深處的“丑陋的心”。這種非理性的力量表達出主人公對“自我”的追求。
二
田山花袋還借鑒了西方自然主義作家關于客觀描寫的觀點。法國自然主義作家注重普遍的客觀自然,認為作家應廣泛收集資料,攝取社會生活內容,對社會進行客觀寫實。龔古爾兄弟經常結伴外出考察、取證,收集積累風俗人情材料,他們的作品中很多內容涉及到當時的社會狀態和人物情貌;莫泊桑的《羊脂球》也是以小見大,從一位妓女一天的遭遇,普遍而真實地暴露出普法戰爭期間的社會百態;左拉則常常親自去礦井、交易所、巴黎菜市、妓院、貧民窟、法律事務所等處觀察、體驗生活,其作品也以紀實的手法刻畫了普遍的社會人生。
花袋在要求文學排除一切技巧、虛構和想象,對生活和人物作純客觀展現方面與西方自然主義作家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提出“平面描寫”論,認為應“將從眼睛映入頭腦里的活生生的情景,原原本本地再現在文學上”。[1]370他認為作家對人生要采取靜觀的態度,不要摻雜絲毫的主觀,不要求解決任何人生問題,僅僅將所見所聞的日常生活細節原原本本記錄下來就夠了。作家要忠實地對待自己,單純表現自己的所見所聞,排除所有道德規范和標準,對自己描寫的事物,不做任何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學的理解和評價,完全采取自我本位的態度,純客觀的態度。正如他在《野之花·序》中所說:“莫泊桑的《貝拉米》和福樓拜的《情感教育》雖然把自然主義的不健全的惡習發揮到了極致,但是,由于沒有摻雜進作者絲毫的主觀因素,所以處處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面影,人生的真諦也被指引出來。”[5](筆者拙譯)
雖然花袋反復強調客觀描寫,但是他所追求的真實不是西方自然主義作家所追求的科學意義上的純客觀的真實,而是傾向于表達內心情感的真實,作內面的寫實,將主觀客觀化。他傾向于選取身邊的經歷、家庭等經驗型題材,強調作家個人的經驗式描寫,而有別于西方自然主義文學在科學意義上所主張的客觀、科學的態度。
在《棉被》中,田山花袋將主人公作客觀化、對象化的描寫,也可以說是一種平面描寫。為了描寫客觀,在敘述上,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稱有限視角,故事的敘述主要由視角人物竹中時雄來承擔。小說中雖然也有一個外在于主人公的視角,但是這一視角通常僅僅作一些人物背景情況方面的介紹或者故事展開時所必需的過渡性的敘述。它既不深入其他人物的內心世界,也幾乎不對小說中的任何人物進行評論,保持一種局外人的立場。試看小說的開頭部分:
就要走下小石川的切支丹坂通往極樂水的緩坡時,他心想:“這樣一來,我和她的關系就算告一段落了。三十六歲的年紀,還有三個子女,竟然還動過那種念頭,想起來自己都覺得荒唐。可是……可是……這真是事實嗎?她向我傾注了那么多的愛,難道只是愛慕而非戀情?”
《棉被》的許多情節雖然取自作者幾年前的經歷,但是田山花袋并沒有將寫作這部小說時的“我”化為一個顯露的敘述人塞進小說里,并讓這個敘述人反省自己過去的經歷。《棉被》中主人公竹中時雄對其女弟子表現出的戀情雖讓人觸動,但是總給人感覺在敘述他人的事情,也就是說讀者是在看他人演繹人生。作者自始至終都很冷靜地描寫主人公竹中時雄的心理狀態和感受。
這也是為什么這部小說被諸多評論家視為主觀的告白小說的主要原因。花袋在《主觀與客觀》一文中曾提出“大自然的主觀”與“作者的主觀”,認為“大自然的主觀”是潛入作者內心深處,并無限伸展開來,使作者產生冥想,令作者感動,從而達到入神之境的,是能夠包容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各種主觀并將之具象化的。這其實是將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與作者精神的內部自然融合在一起,從而使作者的主觀與“大自然的主觀”相一致,并能夠進入人物和事件的內部,遵循“自然”。而“露骨的描寫”則是這一理論向描寫個人的“自我”的世界延伸時的一種嘗試。
三
通過《棉被》這部作品可以看到,花袋對西方自然主義作家關于自然、本能、真實和客觀等觀點進行了借鑒和吸收,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并運用到創作中。這種現象的產生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從當時的社會狀況看,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確立其文壇地位并成為當時文壇的主流是在日俄戰爭后的1906年至1907年間。這一時期,日本近代文學開始走向成熟。日俄戰爭的勝利加速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是同時,社會的貧富分化也日益加劇,導致一些社會問題的產生。與西方世界更為深入的接觸使人們的自我意識進一步加強,這都促使作家探求個人在現實社會中的出路,用冷靜的頭腦觀察社會問題。然而,一方面由于日本文學忽略社會性的傳統,另一方面由于1910年發生的大逆事件對當時文人的打擊,作家們普遍感受到一種“幻滅的悲哀”。對此,石川啄木在1910年發表的《時代閉塞的現狀》這篇評論中進行了詳細論述。正因如此,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無法像西方自然主義文學那樣對人生、對社會進行深刻的發掘、揭露,轉而描寫家庭、描寫自己的經歷。《棉被》寫于日俄戰爭后,花袋剛從日俄戰爭的戰場歸來,對這些應該是有深切體會的。所以花袋在接受西方自然主義的時候,并不是單純學習法國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而是同時注重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對人物心理刻畫較深的作品以及易卜生晚年的具有象征主義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描寫中所具有的內傾性滿足了花袋對于主觀的客觀化的藝術追求的需要。
其次,從當時文壇的狀況看,明治維新使得西方各種富有現代精神的思想在極短的時間內涌入日本,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發生并不像西方那樣有個先后順序,而是并存著,這使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具有一種浪漫主義文學的特征。而自我的肯定、情感的解放是浪漫主義文學最突出的特征。花袋最初也創作了一些崇尚感情與理想,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特征的作品。《小詩人》、《故鄉》、《野花》等,幾乎都是愛情小說。這些作品在清新的意境中,流露著感傷的情調。他的《重右衛門的結局》被認為是從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過渡的作品,而《棉被》被認為是完成這種過渡的真正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文學作品。而且,1903年硯友社的主帥尾崎紅葉的去世使花袋獲得了一種解放感,他隨即寫出了《露骨的描寫》一文,提出了一種與硯友社作家相對的文藝理論。
再次,從作者經歷和當時作家創作的境況看,花袋出生在一個低級武士家庭,12歲入漢學塾學習漢詩,14歲的時候就編寫了漢詩集《城沼四時雜詠》。之后他又師從桂園派一歌人學習和歌。同時,他還寫作了大量的紀行文。紀行文是日本傳統的一種文學形式,是記錄旅行中所見所聞的,類似于游記。松尾芭蕉的《奧州小路》、龜井勝一郎的《大和古寺風物詩》都是紀行文。紀行文雖然注重客觀、真實地記錄作者的所見、所感、所聞,關注的卻是身邊的瑣事。這對花袋在提倡客觀描寫的同時又傾向于描述主觀所感是有一定影響的。同時,花袋在發表了《露骨的描寫》以后,雖然受到關注,但是還未成氣候。而與花袋同時期的島崎藤村和國木田獨步都陸續發表了具有影響的作品。花袋要想取得成就,就需要有所突破。而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暴露內心赤裸裸的真實,是之前的文學作品中所沒有的。因此,花袋在焦躁中選取了師生戀這一題材,并用一種客觀的描寫方式使得主人公主觀的矛盾的心理充分顯示出來,果然一舉成功。
通過對人內部自然的凝視,花袋的《棉被》已不同于早期日本自然主義對西方自然主義文學進行簡單照搬和模仿的作品,具有了日本特色的近代性格。而這種近代性格是追求自我的體現。可以說,對于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來說,《棉被》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它是對西方自然主義文學的超越,標志著日本自然主義的創作和理論開始走向成熟。
[1]吉田精一,和田謹吾.近代文學評論大系:第3卷[M].東京:角川書店,1978.
[2]柳鳴九.自然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476.
[3]柳鳴九,自然主義大師佐拉[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14.
[4]吉田精一.自然主義の研究:下卷[M].東京:東京堂,1958:99.
[5]稻垣達郎,佐藤勝。近代文學評論大系:第2卷[M].東京:角川書店,1978:145.
Japanese Naturalism Viewed from Tayama Katai’s Futon
HE 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Changsha College,Changsha 410003,China)
“Futon”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Japanese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which fulfill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mitation in early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to late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with Japanese style.Katai borrowed ideas such as instinct,nature and objective description in western naturalism and combined these ideas with social reality and traditional ideas in Japanese literature,thus“Futon”presented distinct naturalism with Japanese style.This novel exceeds conception and models of western naturalistic literature and embodies selfpursuit of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ayama Katai;“Futon”;naturalism
I313.45
:A
:1672-3910(2013)03-0062-04
2013-01-08
賀黎(1981-),女,湖南雙峰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中日比較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