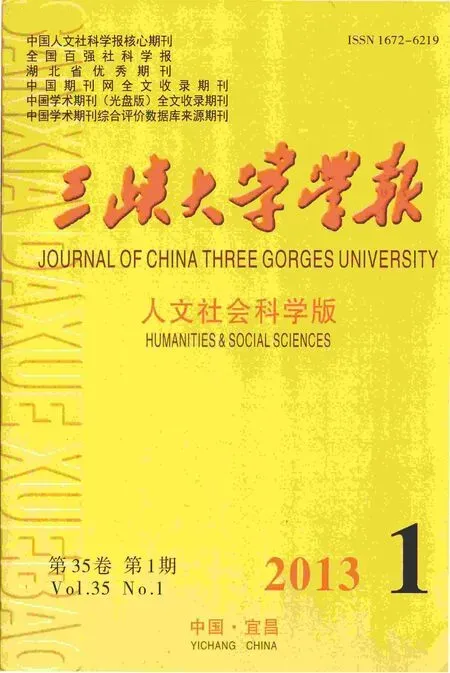立法哲學芻論
李店標
(大慶師范學院法學院,黑龍江大慶 163712)
“立法哲學”(philosophy of legislation)這一概念對于立法學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如果能夠證立的話,有可能整合現有立法學理論研究的資源,將分散的立法學理論予以哲理化并體系化,改變長久以來立法學偏向規范研究的學術形象,一定程度上豐富和完善立法學的學科體系。在我國,“立法哲學”的研究目前還處于萌芽階段,其在理論基礎、框架和內容等得到證立的程度相當低。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筆者嘗試從“立法哲學”的概念、學科體系、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探討,以期引起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和關注。
一、“立法哲學”概念的提出
“立法哲學”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我國目前日益發展并逐步繁榮的部門法哲學的影響。部門法哲學(applied legal philosophy,西方學者稱為“應用法哲學”)是我國法學界近十多年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法理學家和部門法學家們的共同推動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一個新興研究領域。“作為現代法哲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部門法哲學對法學領域經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難的問題的研究正在成為推動法學理論創新和發展的新的知識增長點。”[1]在我國,近年來部門法哲學研究異軍突起,大量的部門法哲學著作與讀者見面。在法理學領域,一些學者先后出版了《部門法哲學通論》、《法理學與部門法哲學理論研究》、《部門法哲學講座》、《法理學與部門法哲學》等;在部門法領域,《刑法哲學》、《刑法哲學專題整理》,《民法哲學論稿》、《民法哲學》、《行政法哲學》、《知識產權法哲學》、《憲法哲學導論》也先后問世。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學者出版了未冠以“法哲學”之名,但其實屬于部門法哲學的論著。
然而,遺憾的是在作為法學理論學科重要組成部分的立法學領域,至今對立法哲學的研究仍然屬于尚未開墾的處女地,立法哲學一詞使用的頻率相當低,更談不上對其概念、學科屬性、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專門化和系統化研究。在國外,明確提及“立法哲學”并加以詳細研究的是亞歷山大·蒙代爾(Alexander Mundell)[2]。在我國,周旺生教授最早提出要“對立法問題做法哲學研究”[3],但其并未提及“立法哲學”這一概念,也沒有進行詳細探討。明確提出“立法哲學”這一概念的是石東坡教授,其在《論當代中國立法學學科建設問題》一文中指出立法哲學是立法學的哲理化而非哲學化,立法哲學不同于立法法哲學,前者追求的是立法的哲理化,后者追求的是立法的哲學化;立法哲學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命題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三個層次[4]30-41。筆者贊同“立法哲學是立法的哲理化”這一提法,但對立法哲學的研究范圍加以限定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方面卻不敢茍同,因為隨著法學研究的轉向,方法論問題也應是立法哲學必不可少的研究內容,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究竟何謂立法哲學,該文并沒有給予明確的闡釋。
那么,究竟什么是“立法哲學”呢?這是一個難以回答但又必須首先予以回答的問題。因此,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筆者始終都有如履薄冰之感,唯恐誤導讀者、貽笑大方。但正如羅素所言,“最終證明是正確的和重要的理論,最初是由于它們的發現者有一些不切實際的、荒謬的考慮而想出來的。由于最初人們不可能知道一個新的學說是否正確,因此,在提出新真理的自由中必然包含著相等的犯錯誤的自由。”[5]因此,筆者不揣冒昧地嘗試闡述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從詞義上講,立法哲學是以研究“應然”立法為中心的一門學科,主要以人的理性和人性作為出發點,以為人類為什么要進行立法,人類需要什么樣的法律和人類如何通過立法達到目的為邏輯起點,尋求和證明立法的“正當性”,并據此評價法律規范的正當性與否。可以說立法哲學既符合立法學的一般理論也符合法哲學的一般理論,是立法的哲學或形而上之學。
立法哲學本身具有基礎性、現實性、評價性和批判性四個特征。所謂基礎性,是指立法哲學在未來的研究與發展中,必須加強對立法本體問題的關注,將厘清立法哲學的研究范圍、層次、方法與視域等問題作為立法哲學研究的首要問題,探尋立法哲學在立法學研究中的價值,促進立法哲學研究的廣泛化;所謂現實性,是指立法哲學是通過假定人類本身具有一些內在或固有的屬性,進而驗證立法行為和法律規范的正當性,但人的理性和人性本身是抽象的和難以證明的,各種假設所體現的形式正義又必須通過具體個案的實質正義予以體現,因此,立法哲學的形而上之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返回到形而下的生活本身;所謂評價性,是指就立法法哲學研究而言,所有對立法行為和法律規范思考不外乎是關于正當性的理解以及根據什么標準去確定正當性,在這種意義上,它是一種“道德信念的證成”過程和理論,其兼具有規范性和方法論的屬性;所謂批判性,是指立法哲學是對立法學進行反思批判的基礎上建構“應然”立法的一門學問,其應秉持理性批判的態度,以借鑒性而非移植性吸收為圭臬,通過對現實立法價值基礎的分析,著力于“應然”立法發展方向的思考和理論體現建構。
二、立法哲學的學科體系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如果要對立法哲學這一概念進行證立,必須闡明其在研究對象上不同于其他學科。這就首先涉及一個問題,立法哲學如果是一門學科的話,應該是什么樣的學科,即“立法哲學”是“哲學”還是“法學”?當然,這是一個頗為費解的問題。本文主張“立法哲學”不屬于哲學而屬于法學,是表達法學框架內的立法學“哲學氣質”的一門學科,其本身并不解決立法的實際操作問題,而是探尋立法正當性的哲學基礎,即實現立法學研究的哲理化。從其學科屬性上來講,立法哲學屬于部門法哲學、立法學和立法法理學的范疇。首先,立法哲學屬于部門法哲學的范疇。部門法哲學是以一定的法理學基本觀念為基礎,按照法理學的結構與方法,以某一法律部門的制度規范及其實施為對象,揭示其中特殊規律的法學分支學科。而立法哲學就是運用法理學或法哲學的理論對法創制的理論觀念、法典結構、認識基礎、調整范圍等方面的理論加以闡釋。因此,立法哲學屬于部門法哲學的范疇,是法哲學與立法學相交叉形成的中介性的法學學科。其次,立法哲學屬于立法學的范疇。在我國,立法學一般被認為是研究立法現象和過程及其規律的一門科學,主要由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立法技術三部分內容構成。而立法哲學本身是在哲學的路徑下探討立法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為立法原理所涵攝,自然應屬于立法學的范疇。二者的區別在于立法學是追求立法的學理化,立法哲學是追求立法的哲理化。
證立立法哲學所涉及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立法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這就必須對立法哲學尋求的“正當性”加以分析。筆者認為從立法哲學的研究中心和邏輯起點來看,其學科體系應由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四部分內容構成。
1.本體論問題
本體論是法學體系也是立法學體系的基石,立法的本體論是法的本體論在立法活動中的體現。雖然我國法學研究的中心已經實現了有本體論到方法論的轉向,但并不意味著本體論問題研究可有可無。立法哲學研究的本體論問題即以立法本質為中心的立法本體論問題,包括立法的本質在于“法的發現”抑或“法的創制”問題,立法的本源在于理性抑或經驗問題,立法的實質實現法的階級性抑或社會性問題,立法的屬性在于政治性抑或獨立性問題等等。
2.認識論問題
立法認識論屬于法的認識論范疇,是關于立法的基礎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疇的認知。“我們知道,一個學科的成立,往往在于該學科能有貫通其全部內容、統攝其方方面面的基礎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疇。如果有這樣的概念和范疇,人們就會覺得該學科具有系統性,反之,如果缺乏類似的概念和范疇,該學科給人們留下的只能是凌亂的印象。”[6]建構立法哲學學科首先要說明和論證的認識論問題,至少包括:立法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立法與政黨的關系問題、立法權的分配問題、立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立法理由問題、立法的社會認同問題、立法機關的權利和義務問題、立法權威問題等。
3.價值論問題
立法價值則是在立法過程中立法主體對立法客體的需要和滿足關系。立法價值論是立法學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法的價值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價值論問題“其中至少包括:立法價值在法律實踐活動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立法價值的宏觀結構與微觀結構,立法價值主體,立法價值觀念、價值原則與價值標準,法律價值的形成與確定,法律價值目標與法的構成要素的關系,法律價值的表達途徑與反映手段,法律價值與法律文本、立法價值的實現機制,法律價值與社會價值體系之間的關系,社會文化思潮與法律價值的演變等問題。”[4]38
4.方法論問題
立法哲學獨立的一個標志,就在于其研究對象本身具有方法論的特征。立法哲學的方法論是以“應然”和“實然”二元論為邏輯起點,運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對立法學的具體研究與實踐方法進行理論反思所形成的一套研究立法方法的理論體系。如立法哲學的研究需要從歷史上的偉大的立法學家中尋找思想的厚度,達到當代人與歷史偉人在精神上的理解和溝通,形成對歷史人物思想解釋的解釋學。在立法哲學研究中,解釋“正當性”問題或“方法論”問題,就是要解讀和探求立法學獨立于其他法學的“方法論”根據。
三、立法哲學的研究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對立法哲學的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對立法哲學的研究意義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只有明確了立法哲學的研究意義,才能有效開展這一學科的研究,而其研究意義至少體現在以下幾點:
1.拓展立法學的研究領域
關于我國立法學的研究對象或內容,一些學者闡明他們的觀點。如周旺生認為立法學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立法思想、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立法技術四個部分[7];黎建飛認為立法學新體系的建構應以立法目的、立法活動和立法實效為重點[8]。從這些研究內容來看,雖然對立法學的研究重點都給予了揭示,但跨學科研究并不明顯,與當前學科發展趨勢不相吻合,因為跨學科研究已逐漸成為當代學術發展和創新的重要生命力所在。加強立法哲學的研究,可以以“正當性”的尋求這一主線將立法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關聯起來,以新的研究視角分析拓展立法學的研究領域,實現理論創新。
2.推動立法學的研究轉向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重視立法學的研究并嘗試建構立法學的學科體系。但經過30多年來的發展,在我國立法學研究領域雖然出現了大批的研究成果,但立法學在研究內容、方法等方面的創新性表現并不明顯。為此,筆者認為要改變當前立法學研究匍匐前進的狀況,實現立法學研究的轉向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由立法本體論到立法方法論的轉向和由立法制度到立法技術的轉向已日益顯現出來,但由立法科學到立法哲學的轉向表現并不明顯。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科學的立法學研究自然離不開哲學理論的支撐,因此加強立法哲學的研究能有力推動立法學研究的轉向,使立法學研究的基石更加牢固。
3.豐富立法學的學科體系
我國當前的立法學學科體系還不健全,大多數學者將立法學的學科體系劃分為立法學基礎理論、立法制度和立法技術三個部分,而忽視了立法學與其他學科交叉研究所帶來的優勢和所形成的新學科。如西方學者近年來所研究的立法法理學就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立法學的學科體系。比利時法學家盧卡·溫特根斯(Luc J Wintgens)最早提出了立法法理學(legisprudence)這一概念,并指出“論證的義務就是立法法理學的論題。立法法理學被界定為一種理性的立法理論。它由對作為原理的自由的觀念的闡發所構成。”[9]筆者認為健全的立法學學科體系除了上述研究內容外,立法哲學、立法解釋學、立法社會學、立法經濟學也應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立法哲學的研究如果能夠引起法學界的重視,并形成體系化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那么其對于豐富立法學學科體現的意義則是相當明顯的。
四、立法哲學的研究方法
明確了立法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意義,接下來就涉及到研究方法的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的立法哲學如果能夠證立的話,其研究方法既要遵循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規律,也應遵循法學研究方法的規律。當然,包括法學在內的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都不應該是單一的,而是應該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而且各種研究方法之間還會具有一定的邏輯關系。對于立法哲學研究而言,思辨(哲學)方法、實證(經驗)方法、反思(批判)方法應是最為基本的研究方法。
1.思辨(哲學)方法
思辨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抽象的或者定性的方法,即一般通過描述和解釋,提出政策性建議和預測。思辨的方法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應用于哲學和法學研究當中。馬克思在提到法學的研究方法時提出,沒有哲學,一個人就不能成功地理解法律問題,因此他計劃“詳細地闡述覆蓋法律所有領域的法哲學。”[10]在我國法學研究領域,法的思辨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指法哲學,思辨方法和哲學方法也是在同一種意義上使用。立法哲學就是用思辨(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立法行為、立法思想、立法制度等立法現象之“正當性”的一門學科。作為一門法學理論學科,立法哲學在研究立法現象的時候,不是簡單地進行描述,而是要分析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后的規律,并加以證立。而要完成這一任務,思辨(哲學)方法必不可少。當然,要推進立法哲學的研究,提高當前立法研究者的思辨能力和理論素質是當務之急。
2.實證(經驗)方法
實證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具體的或定量的方法。實證方法拒斥“形而上學”,反對動輒探求事物的本質,而是強調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的對“經驗事實”觀察實驗,以獲得的客觀的實地感受和感性知識來建立知識體系。因此,可以說實證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經驗方法。迪爾凱姆在強調實證方法的重要性時指出:“科學要想成為客觀的,其出發點就不應該是非科學地形成的概念,而應該是感覺。科學在最初所下的一些定義,應當直接取材于感性資料。”[11]立法哲學的中心任務在于對“應然”立法的研究,但“實然”立法也是其研究對象,而且拋開了對“實然”立法的研究,“應然”立法的研究將會成為無本之木。實證(經驗)方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針對立法的實然進行研究,而實證(經驗)方法的運用自然離不開測驗法、個案法、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具體方法的支撐。因此,立法哲學的研究必須綜合運用各種具體方法對立法主體、立法程序、立法權限、立法質量、立法實效、立法形式等方面進行實然的定性研究。
3.反思(批判)方法
哲學的本質即在于批判和反思,但哲學家們往往用批判來修飾和表征“反思”,將反思叫做“批判的反思”。反思(批判)方法既是哲學的研究方法,也是法學的研究方法,自然也是立法哲學的研究方法。立法哲學的反思方法決定了它的批判本質和批判精神,當然這種批判是辯證法的批判。在終極意義上,批判只是形式,深刻的理解和科學的重構才是目的,沒有任何新的建設性的方案修正過去的錯誤,也不能稱之為立法哲學。立法哲學的反思(批判)方法,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要在大膽懷疑和系統反思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人的理性和人性作為出發點,尋求和證明立法的“正當性”,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要求無論是徹底的批判和反思,還是探索性的重構,開放與謹慎的態度應貫穿于立法哲學研究的始終。因此,從事立法哲學研究要求我們不僅要具有積極進取、勇于開拓的學術姿態和自我反省、自我抑制學術自覺性,還要具有強烈的學術責任感和學術包容態度。
五、結語
任何一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是在立足于先前的理論基礎,并在不斷的探索和積累過程中逐步實現。筆者堅信,對“立法哲學”這一問題的探討必將成為立法學界需要認真對待和深入思考的重大課題。盡管本文所闡述的內容是一種探索,對一些問題的思考也許并不成熟,但之所以將其表述出來,目的在于引起學界對立法哲學更為深入和全面的討論,以拓展和深化對立法理論的研究。
[1]張文顯.部門法哲學引論——屬性和方法[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5).
[2]Alexander Mundell.The Philosophy of Legislation:An Essay(1834)[M].Whitefish,Montana:Kessinger Publishing LLC,2009:6 -7.
[3]周旺生.立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
[4]石東坡.論當代中國立法學學科建設問題[M]//周旺生.立法研究: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陳興良.刑法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
[6]謝 暉.法的思辨與實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1.
[7]周旺生.論創建中國社會主義立法學[J].法學評論,1998(6).
[8]黎建飛.立法學新體系的建構論綱[J].學習與探索,1991(1).
[9]溫特根斯.作為一種新的立法理論的立法法理學[J].王保民,譯.比較法研究,2008(4).
[10]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1845 -48(Vol.6)[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6:12.
[11]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