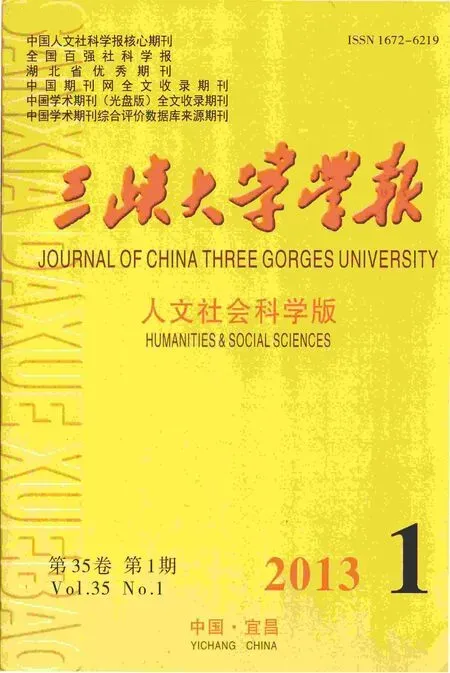略論重玄學對全真教的影響
朱 俊
(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一、重玄學的概念
重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重要內容,尤其是道教義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受到學界重視則是近代以來的事。著名學者蒙文通先生于1946年發表《校理<老子 >成玄英疏敘錄——兼論晉唐道家之重玄學派》,據其所校《老子》成玄英疏和唐末五代著名道教理論家杜光庭《道德真經廣圣義》卷五“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禇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一說,提出了重玄學派的概念,并指出“自裴處恩、梁武父子、大小二孟以來,皆以四句百非為說,以暢重玄、三一之義,接踵釋氏,隋唐道士劉進喜、蔡子晃之屬,亦其流也。成公之疏,不舍仙家之術,而參釋氏之文,上承臧、孟,近接車、蔡,重玄一宗,于是極盛,萃六代之英菁,而垂三唐之楷則者也。”
蒙先生的發覆使重玄學引起學界重視。隨著研究的深入,海內外學者對于蒙先生的定義多有辯駁。如重玄學是否是一個有傳承譜系的學術流派,重玄學的著作范圍,某些義理學者的學派分屬等,都存在較大的爭議。但總體而言,學界大多將廣義上的重玄學視為一個興起于南北朝梁陳時期,到隋唐達到繁榮,五代兩宋繼續流傳發展的,以“重玄之道”的方式解說道教經典、闡述道教義理,追求“重玄之境”的學術思想流派。其著述主要有兩大類,一是重玄家的注疏作品,其中以注疏《道德經》、《莊子》的作品最多。二是直接闡發重玄思想的道教經典與著述,經典如《太玄真一本際經》、《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無上內秘真藏經》、《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災護命妙經》,著述如《三論元旨》、《道體論》等。
所謂“重玄之道”,來源于《道德經》首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唐代重玄學大師成玄英解釋“玄之又玄”說:
有欲之人唯滯于有,無欲之人唯滯于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于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滯于滯,亦乃不滯于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這一言說傳達了重玄學的幾個基本特質:一是運用雙重否定的方法,以否定性思維來破除修行者的滯著心,進而將“否定”也放棄,所謂“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二是通過雙重否定以進入難以言說的形而上“重玄至道之鄉”;三是倡導精神解脫,注重心性修煉。
二、重玄學的源流及影響
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學術思潮,重玄學既是兩晉南北朝玄學理論深化的結果,也是道教謀求自身義理發展的必然。
就前者而言,魏晉時期,以王弼為代表的崇無論倡導順任自然,反對名教綱常對人性的束縛,而以裴頠為代表的貴有論則肯定名教秩序的真實合理。雙方各執一理,爭辯陷入僵局。學術思想的發展需要調和這一矛盾,解決名教與自然的沖突,使人生達到更加融通的境界。而重玄學以破除偏執,超越有無,通達無礙為義,較好地解決了玄學的思想難題。
就后者而言,道教本興起于民間,后來逐漸向上層社會滲透,贏得了許多士大夫的信奉。士人的加入既提高了道教的文化素養,也要求道教改革其民間面貌,向上層社會的文化要求靠攏。特別是促使道教深化其教義教理,向思想精深、境界高邁的成熟宗教發展。而此時佛教的興起也刺激道教思想家深化本教義理,與之抗衡。
重玄學自東晉孫登舉唱以來,高道輩出,明哲如云。自六朝至隋唐間,名聞于世,出入宮廷,論衡三教的道士,如孟智周、景翼、臧玄靜、韋處玄、禇糅、劉進喜、方惠長、孟安排、李仲卿、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等,多為重玄學者。此外,當時號為天下道學之宗的茅山派,其宗師如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等亦對重玄之學多有闡發。
唐王朝興起,尊老子為族祖,以政權力崇揚道教,對道教義學亦頗多留心。高宗曾親自向上清宗師潘師正請益道教義理,又令天下士子研習《道德經》。玄宗以御筆注疏《道德經》,發揚重玄教義。斯時重玄學高道明哲輩出,道教面貌遂為之一變。自此以后,道教學術與義理,無不浸染重玄之風。
中晚唐時期較為著名的道教著述如《道德真經廣圣義》、《三論元旨》、《無能子》、《道體論》、《化書》等,雖所論主題有所差別,但均對重玄義理有所闡發。
五代宋初劉若拙所撰《三洞修道儀》中列道士教階有升玄部、洞玄部、高玄部,其所習經典皆與重玄學相關,可見重玄學已經被列為道士必修內容。
宋代重玄學繼續盛行。張君房編《云笈七籤》,后世目為小道藏,其中雖保留諸多方技小道,然而論理則廣引玄義,重玄要典《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經文屢見其中。兩宋解老釋莊者仍多以重玄為宗。其中陳景元最為翹楚,其著述、編輯諸多道典,發明玄義,集前輩重玄家之言頗多,故近代以來輯校重玄遺書,多受其澤。宋皇室利用道教神化皇室皇權,道流漸好虛妄,當時道門領袖為遏此弊而上書請以三經十道義考核黃冠,三經為《道德》、《南華》、《度人》,自南北朝以來皆為重玄家注疏之要典,史稱道風為之一變。此后高道賈善翔編《太上出家傳度儀》,為道流出家儀則,引《太玄真一本際經》經文論說“出家”意。
另外,唐宋以來道教講經之風極盛。其風由來既久,則所講論必承前代遺風而于重玄學有所發明。如前列陳景元、賈羽翔,皆重玄學明宿,雖身居高位、繁于著述,而講經不輟。流風所及,連重符箓的天師道,其領袖人物亦廣論玄理。至于新出之天心派、神霄派(傳雷法)等,雖以術顯,而其說皆明義理。
重玄學既滲透入道教思想的方方面面,其影響后代道教的發展,實為必然了。
三、全真教的重玄學色彩
重玄學的廣泛傳播對后世道教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南宋時期興起于北方陜西、河南、山東一帶的道教新派全真教即是顯著例證。全真教于金大定年間(南宋初年)由陜西咸陽人王重陽創立,經門下弟子發揚光大,特別是其高足丘長春應成吉思汗之聘后,獲得蒙元政權的支持保護,臻于鼎盛,流傳至今。全真教以性命雙修為旗號,發揚唐宋以來由鐘離權、呂洞賓等提倡的內丹道,但在性命問題上特別重視心性修煉與精神超越,受到重玄學的深刻影響,這通過閱讀全真家的著述可以找到許多證明。
首先,全真家熟稔地運用了重玄學雙重否定的思辨方式。
全真祖師王重陽詩云:“抱元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其法孫王棲云釋“一”為“混成之性,無分別時”,故“抱元守一”既不著有,亦不著無,相當于重玄家所謂破滯之“玄”、“中道”、“一中之藥”,而“一也無”則與“復遣此玄”義同。全真第二代宗師馬丹陽語錄中記載:
師曰:一念勿絕一世休。龔道升問曰:湛然常寂時如何?師答曰:將來和湛然都不用。
“湛然常寂”本是表述修行者有無雙泯的清靜狀態,而丹陽卻說“將來和湛然都不用”,也是“玄亦自喪”的理路。
全真第三代高道王棲云語錄中,運用重玄思辨的言論極多。如:
師云:無為者天道也,有為者人道也。無為同天,有為同人,如人擔物,兩頭俱在則停穩,脫卻一頭即偏也。若兩頭俱脫去,和擔子也無,卻到本來處。
此處以挑擔為喻,“若兩頭俱脫去”,是指將“有為”、“無為”都放下,既破有執,亦破無執,后云:“和擔子也無”,則是將破執也放下,正是重玄學的雙重否定思辨模式。又如:
或問曰:心無染著,放曠任緣,合道也未?答云:起心無著,便是有著,有心無染,亦著無染,才欲靜定,已墮意根,縱任依他,亦成邪見。無染無著,等是醫藥,無病藥除,病去藥存,終成藥病。言思路絕,方始到家,罷問程途矣。
醫藥之喻,本是重玄學常用的比喻,如成玄英說“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棲云之論與此同出一轍。再如其論“不昧”、“知覺”:
不明自己,便是昧了也,便與托生底一般,不知不覺透在別個殼子內,只待報盡方回,此為昧了故也。若專用知用覺,又被知覺昧了也。
若言有知有覺,又專欲常知常覺,乃是自纏自縛,無病自灸也。
告誡修行要“知覺”,又要防止執“知覺”,也屬重玄式的以藥療病,又防執藥為病之意。
其次,全真家將重玄之境作為其修道之追求。
王重陽有詩云:“勘破行功無作用,于斯便可認玄玄。”“玄玄”者,即“玄之又玄”;“認玄玄”,則是將“玄之又玄”作為修行所要達到的境界。
丘長春亦有詩云:“東海西秦數十年,靜思道德究重玄。”此處更是明確將“重玄”作為修道的核心追求。
再如全真掌教宗師尹清和曾說:“至寂無所寂之地,則近矣……須入真道,方見性中之天,是為玄之又玄。”馬丹陽弟子王丹桂《草堂集》詩云:“早早悟重玄”。王棲云弟子姬志真《云山集》詩云:“重玄妙法身”,又云“嚼破重玄色色真”。全真高道劉志淵《啟真集》詩云:“默默究重玄”。皆以“重玄”為修道之鵠的。
另有全真高道牛道淳謂:“二邊俱不立,中道亦非安。回首二乘外,靈光射廣寒。”既破兩邊,亦破中道,其“靈光射廣寒”所描述之境界當即重玄學所追求的重玄之境。
再次,如眾所知,全真教特別重視心性修煉,追求精神超越。
《重陽立教十五論》云:“心忘慮念,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見,即超無色界”。又云:“離凡世者,非身離也,言心地也。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今之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
《重陽真人授丹陽二十四訣》載:“丹陽又問:何者名為長生不死?祖師答曰:是這真性不亂,萬緣不掛,不去不來,此是長生不死也。”可見重陽立教之初,便將精神超脫視為目標。其高足譚長真《示門人語錄》云:“若一念不生,則脫生死。”其法孫尹清和亦云:“認得亙初微妙物,堪親。喚作神仙不喚人。”皆將解脫安頓于心地。
全真家號稱道德性命之學,其修煉較為排斥傳統道教的各種方技、法術的修煉,專一注重心性磨煉,鍛煉塵心,除情去欲,甚至對內丹道功法亦有所不取。如馬丹陽以修道“但清靜無為,逍遙自在,不染不著”十二字。王棲云以“本來真性”為金丹,以煉心為修道徹頭徹尾功夫。尹清和以“心得平常”、“心不動”為修道入門等。全真教各宗派雖然在修道思想上有所差別,但將心性修煉放在核心地位、將精神超越作為最終追求則是一致的。
道教自東漢興起后,長期被認為以肉體不死為追求目標。如《抱樸子內篇》廣論肉身不死,金丹可成,《黃庭經》等亦盛言服氣養形,雖有《三天內解經》、《西升經》、《升玄內教經》等破斥其說而倡導精神超越,但直到重玄學興起后,心性修煉、精神超越才真正成為道教的主流思想。因而全真教的心性思想、精神追求實在是繼承了重玄學對道教義理的改革。
不僅如此,全真教還高度重視重玄學思想的指導意義,除了廣泛征引重玄經典立說外,《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太上洞玄靈寶升玄消災護命妙經》等精要闡述重玄思想的經書亦被列為全真道徒日誦功課。可見全真教視重玄學為本教的根本義理所在。
全真家尚有許多以“重玄”為號者,如高道孟志源、李志方、樊志應等。當時人已經注意到全真教與重玄學的親緣關系,如《重修蟾房靈泉觀碑》云:“長春掌教,普化群生,闡祖師重玄之路,立全真大教之門。”
[1]正統道藏[M].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影印本,1988.
[2]張繼禹.中華道藏[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3]任繼愈.中國道教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4]盧國龍.中國重玄學[M].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
[5]張廣保.道家的根本道論與道教的心性學[M].成都:巴蜀書社,2008.
[6]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7]陳 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李作勛.隋唐道教心性論研究[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
[9]卿希泰,詹石窗.中國道教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蒙文通.道書校輯十種[M].成都:巴蜀書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