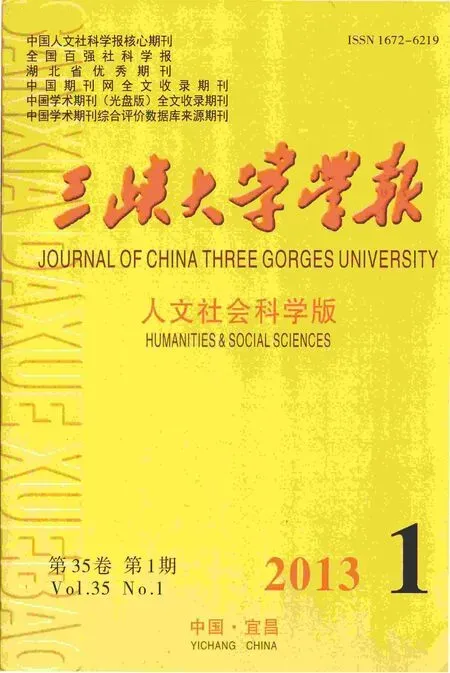從羅斯金看有機整體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演繹
許瑾瑜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廣東廣州 510970)
夾在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兩大思潮之間,維多利亞時代在文學批評領域中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一方面,緊隨浪漫主義時期之后的維多利亞文藝思想的確深受其影響;而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思潮已憑其鮮明的時代特性將前人遺產繼續發展了。
約翰·羅斯金,作為維多利亞時期最重要的評論家,對當時的工藝設計乃至社會美學影響深遠。其父母的宗教態度和培育方式使羅斯金對宗教從小有獨立的思考,并且熟讀了大量華茲華斯的作品,對早期浪漫主義詩人的“有機形式”頗為贊同[1]。因此在其美學體系建構中他既沒有跟隨基督教神學思想,也沒有盲從傳統的藝術審美觀,而是秉承有機整體觀大力推崇自然主義和哥特式風格。
他的社會和藝術評論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浪漫主義者最重要的建構:有機整體,是如何影響著維多利亞美學思想,并帶上新時代印記向前發展的。
一、有機整體與維多利亞時期的印記
有機形式最早是柯爾律治從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那里借來的概念,是一個如植物一般從內部自我生發的整體,體現的是對世界最高整體的全新理解,亦即對“自然”的重新定義。自然,或者世界背后的絕對精神,被看成是一個擁有生命和動態變化屬性的存在。
早期浪漫主義者的“有機整體”隱含著鮮明的泛神論特征,如內在性、動態性、多樣性的統一和有機生命論。華氏的有機整體首先涵蓋了一切個體,卻并非如上帝一般超越于萬物之外的存在,而是同時內在蘊含于萬物之中的形式。其次,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從斯賓諾莎處獲得靈感,將一切個體的生命進程與變化都囊括進最高統一體的無限生命循環中,這便是有機形式最為突出的生命性與變化性。此外,在這個絕對整體中個性被賦予了特殊意義,在理解和把握“無限”的過程中,強調對象經驗性質以及個體的體驗與想象。
有機形式在維多利亞時期得以傳承有其特殊的歷史社會土壤。政治經濟正處于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在其社會精神層面卻是一個繁榮與失落并存的時代。1830~1880年的英國與歐洲大陸處于一個半隔絕的狀態,保持著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相對穩定,這對于傳統傳承以及國內文藝美學體系的建構提供了有利環境。但是由于達爾文理論所帶來的巨大撼動,整個知識界越來越多地受到科學唯物主義的影響。因而在受教育階層中,對于傳統基督教的歷史根基和教義日漸產生了深刻懷疑。學者和知識分子開始在基督教思想之外去尋求新的信仰根基以闡釋當時面對的一系列社會變遷和危機。這也是為什么羅斯金會回溯至浪漫主義者的有機整體論。因此,維多利亞時期一方面對科學和經濟發展充滿自信,一方面也彌漫著在自然面前的不安與社會精神消極主義[2]。這些既導致了對科技文明大膽接納的同時卻備感危機和焦慮的深層矛盾,也使羅斯金在華氏有機整體論影響下大力推崇新的藝術形式,并將其融合進自己的美學思想中。因此,有機整體到了羅斯金這里已經打上了在浪漫主義時期所沒有的特殊時代印記。
二、科技文明的矛盾角色
同樣作為自然詩人,羅斯金對于科學進步的態度顯然比華茲華斯更為開放。在羅斯金看來,科學并非是與自然相對立的存在,植物學、地理、化學等新興的科學學科發展都可吸收進無所不包的體系中來,成為一種理解和闡釋世界乃至無限整體的途徑。因此,一方面他對自然的詩意探求已不僅限于文學性的詮釋,而是欣然跨界尋求科學例證的支援。在探討哥特式精神的組成元素時,他便獨辟蹊徑地舉了化學成分的構成作為例子:“比如,粉筆并不是由炭或者氧或者石灰組成的,而是這三種化學物質以特定比例組合而成的。這三種元素都在與粉筆完全不同的物體里存在著,而且炭和氧本身與粉筆毫無相似之處,但是它們對于粉筆的存在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反之,當要向公眾解釋科學體系或理念時,他也并不囿于嚴謹抽象的客觀敘述,例如在展現地質構成與個體表述的內在聯系時,他的地理記錄則儼然是一幅跟隨遷徙候鳥的眼睛展開的生動宏大的詩篇[3]。華氏的有機形式對自然的重新定義顯然對羅斯金產生了深刻影響,他的一系列自然社科著作都隱含著對華式有機整體的懷戀,不管是他的植物學還是地質學闡述都從未脫離過對自然的詩意理解[4]。
盡管如此,羅斯金對華氏有機整體的繼承與發展背后,是對機械文明所帶來的一系列缺失和異化所感到的焦慮。雖然早在浪漫主義時期已經開始,但到了維多利亞時期,分工的完善愈發加劇了這種由現代工業所帶來的人的異化感。因而羅斯金斷言,關于“分工”,人們給了它一個錯誤的名字:“并不是工作被分割了,而是人被分割為個體生命的碎片和碎屑。于是留存在人身上的智慧小碎片不足以生產出一根針或一枚釘子,而只能將精力耗盡在生產針尖釘腦上。”[3]個體不再是一個自足的整體,而是斷裂成了碎片,這成了機械文明帶給羅斯金最大的焦慮。懷著對心目中個體與無限相呼應的和諧整體的向往,他在華氏的有機整體那里找到了共鳴。盡管華茲華斯一直未敢將這個神秘的存在等同于上帝,羅斯金卻大膽認定他所闡述的這個泛神論整體就是“基督教價值體系”。因為他要創造出一個“基于華氏泛神論無限的新宗教詮釋體系”,展示一個“貼近的、可見的、必然的但是慈愛的上帝,他的存在會使得塵世本身即為天堂”[4],以此作為對機械文明異化的救贖。
三、實用藝術的興起——時代認同感&視覺推崇
羅斯金對維多利亞藝術的一大貢獻便是對包括各種建筑和工藝裝飾在內的實用藝術的系統討論,并且將其提到和詩作繪畫等純藝術形式對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上來:“并不存在任何最高級的藝術,只存在裝飾藝術。……從性質或者本質上來說,它(裝飾藝術)不過是將藝術運用于一個特定的地方;而且,在這個地方,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相伴,形成一個偉大、和諧的整體的一部分。”[5]這一大膽宣言顯然也是深受有機整體觀的影響:美學價值的最高體現,不在于作品中的某一特性(如構圖),也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某些外在標準,而在于它與“整體”的一種互相構成。
實用藝術的興起,最為顯著地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性。維多利亞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了歷史進步的不可阻擋,正如卡萊爾所說,維多利亞人已不再帶有感傷主義的懷舊,因為他們毫無疑慮地承認,現代工業化進程已完全改變了過去社會的性質[2]。同樣,羅斯金也完全接納這一特性,甚至認為最好的藝術就應該體現出這種時代性,它要表現的是所處時代的事實,即使表現過去,也必須帶有自己時代的痕跡,因為“畫家沒有必要成為文物研究者……我們要他清晰的斷言來尊重現代的事物”[3]。這一藝術標準的全新之處在于它僅著眼此時此刻,拒絕了傳統藝術強調的永恒性和絕對性,并且強調了主體的參與。
城市化發展和工業繁榮促進了中產階級的發展以及對工藝裝飾和實用藝術的需求,實用藝術在時代的需要中應運而生,時刻反映著社會大眾的審美趣味;它不僅是可供遠觀和冥想的對象,而是創造者和使用者(欣賞者)都可參與其中共同經驗,正如在華氏那里個體觸碰無限的方式一樣。
認為藝術的本質屬性是裝飾性,這也強調了維多利亞人對視覺形式的推崇。曾立志要成為一位詩人的羅斯金還極其擅長水彩繪畫,因此在寫作中往往傾向于視覺思維,通過意象和畫面來傳達自己的理念。而且正如戴維·希克瑞所觀察到的,羅斯金癡迷于視覺藝術,在他之前沒有人能比他更認真地對待過視覺藝術,比他對此更具有熾熱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辨[6]。這也恰好體現了維多利亞時期視覺中心趨勢的興起。
和華茲華斯一樣,羅斯金也深受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影響,在對自然的把握中強調主觀觀感。他在一篇書評中提到,他只關注可視的東西,人們理應用自己的眼睛,而非顯微鏡來認識自然[1]。這與華氏對“無限”的一種非超驗的、與個體體驗緊密結合的界定是相契合的,但卻比前人更突出地推崇了圖像的地位。當華式選擇詩歌代替哲學語言來還原對象的經驗性質的時候,羅斯金則依賴各種視覺的意象作為表達。在他的藝術評論中有許多如臨其境的視覺描寫,他從不泛泛地敘述“龍膽生于阿爾卑斯山脈,橄欖長在亞平寧山脈”,而是用攝影般的寫作展現“像鸛鳥和燕子乘著熱風遠遠看到龍膽和橄欖所生長地域”的圖景。他認為科學“將大量知識投入狹窄的意義空間”,但是這些知識細節上的差異沒有意義,真正實質性的東西在于“視野和理解上的廣泛差異”[3]。
四、結語
在文學批評研究中并不受重視的維多利亞時期,其實既蘊含著浪漫主義思想以新形式在后期的扎根演變,也可看出后現代主義的焦慮與革命大爆發前的醞釀。羅斯金在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對科技文明的融合和反思,以及對實用藝術的推動,處處都反映著維多利亞的時代特性;這種時代特性和思潮的演變在兩大運動的緩和過渡中間無疑扮演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1]Birch,Dinah.“Who Wants Authority?”:Ruskin as A Dissenter[J].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2006(36):65 -77.
[2]Sanders,Andrew ed.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398-403.
[3]羅斯金·約翰.藝術與人生[M].華 亭,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0.
[4]Bidney,Martin.Ruskin,Dante,and the Enigma of Nature[J].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76,18:290 -305.
[5]羅斯金·約翰.芝麻與百合[M].翟洪霞,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241.
[6]希克瑞·戴維.拜讀羅斯金[J].史與論,2001(2):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