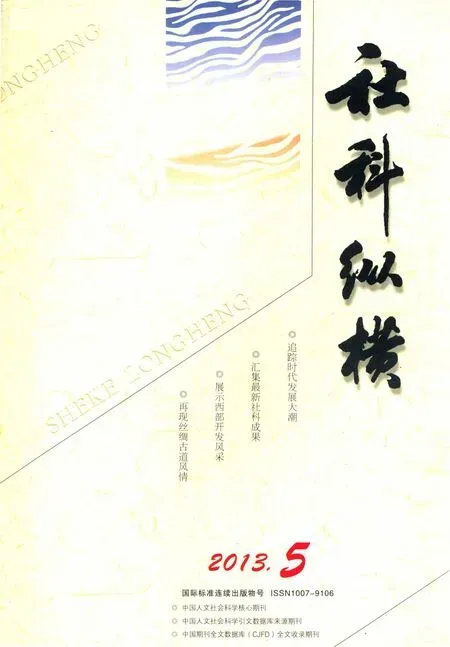建國初期西部民族地區農村基層政權的變遷與重構——以西康省雅安縣蔡龍鄉為中心的研究
鄧小林
(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一、解放前夕及建國初期西康省農村基層政權之變遷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根據重慶國民政府的命令,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建立,省府設在康定。劉文輝任省主席,段班級任民政廳廳長,韓孟鈞任教育廳廳長,李萬華任財政廳廳長,葉秀峰任建設廳廳長,王靖宇任保安處處長,張為炯為秘書長,其它省府委員還有格聰、黃述、楊永浚。據《中央日報》記載,當時西康省總人口2144031人,轄境46縣2設治局,即金沙江以東33縣2設治局及金沙江以西13縣。實際上,當時西康省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金沙江以東33縣2設治局,而金沙江以西鹽井縣等13縣則為西藏政府控制,并未收回。”[1]這說明省一級的政府機構建立起來了。
但是如果細觀其基層政權建制,則早在清末就已開始具備雛形。因為清末改土歸流之時,就“改川邊各歸流行政機構為府、所、州、縣、鄉,政府亦開始向農牧民征收農業稅,歲收糧稅七萬余兩。”[2]這表明,在縣級政權之下,開始設鄉。
對此,有學者也說到,“趙爾豐在川邊改土歸流,首要措施就是廢除原有的土司制度,在西康設立道、州、廳、縣、理事官、設治委員等官職,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地方行政系統。在基層建立了‘首舉’制度,由百姓公舉頭人管理村務。頭人任期3年,其薪水由村民共攤青稞30克寸(約120斤),任期滿后如再獲公舉,可連任3年。如頭人辦事不公,經稟告地方官后隨時公舉更換。這儼然是以選舉為基礎的地方自治制度,頗有現代‘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的意味。”[3]在此,鄉村中的“頭人”就成為了農村中最基層的一員。從名義上似乎與民國建立之前有了區別,實則不然,因為至解放前夕西康省仍然繼續著由“土司、頭人、寺廟上層的少數人”三大集團控制的封建農奴制。“統治者利用政權維護神權,利用神權強化政權,這一專政特點構成了農奴主階級對農奴的特殊統治形式。”[4](P19)
1949年10月,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新政權的領導下,西康省逐步實行了有步驟的社會改革。“1950年3月西康藏區解放,11月建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終結了傳統的政治制度權力體系。藏族人民當家作主實際上既是把社會公共權力交給了人民,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但是,這種政治體制的設計在剛剛解放的西康藏區卻并未馬上收到實效,因為“由于藏區社會的復雜性和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封建農奴制統治形式在一些基層還未徹底消除,制約政治制度變革的經濟制度尚未摧毀,所以,這時的康區社會政治制度僅僅實現的是初步轉型。”[4](P25)
1951年2月2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十五次行政會議,批準并通過了西南民委提交的《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及建立民主聯合政權的意見》(簡稱《意見》),呈請中央民委后,作為實行西南少數民族建政的具體方針。《意見》規定:‘本區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暫就其所在行政區如省(暑)、專區、市、縣、區、鄉等)分別建立各級民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對于少數民族和別的民族雜居的地區,“應就其所在行政區,按民族人口比例選出相當名額的代表,組織各族人民聯合的政府。各族按照人口比例選出代表時,對區內人口較少的民族應予適當照顧。”[5](P2-3)即是說,對于基層政權來說,開始建立縣級以下“區、鄉”兩級政權。此后,隨著西康省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經濟財政狀況的好轉,在鄧小平同志的指導下,西康省民族地區基層政權的建政工作也逐步實施開來。
1951年3月底,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和《意見》提出了具體的建政綱領,這主要是依據西康省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建議各省區民族政權的建立先從專區級搞起,由上而下的進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和聯合政府的建立以專區級一層為重點,主要是考慮到‘一個專區的范圍內,包括的民族較多,了解各族間的問題比較全面,而一縣范圍內的民族問題,往往牽涉臨近各縣,縣級政府就無法處理解決,”[5](P7)那么,從1951年 3月開始,按照省(暑)、專區、市、縣、區、鄉等建制建立起來的西康省政治機構情況如何呢?
從1950年開始至1953年4月,西康省建立的專區、縣、區、鄉情況大致如下:首先在民族自治地區,1950年建立了1個專區;1951年建立了9個區,4個鄉;1952年建立了3個區,31個鄉;1953年建立了1個縣。因此,總體是1個專區,1個縣,12個區,35個鄉。其次在民族雜居地區建立的聯合政府,1950年未建立任何機構;1951年建立了1個專區,7個縣,5個區,18個鄉:1952年建立了9個縣,19個區,36個鄉;1953年無任何機構建立。雖然“,區級以下管理社會的成員一般仍有許多是當地的上層人物,但是藏族聚居區以往完全由封建領主的統治系統管理社會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4](P25),這說明基層政權的管理主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村基層政權從人員構成到權利規定已經有了重大變遷。在這變遷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包含著重構的一面。尤其是象征著最基層的鄉級政權,其變遷與重構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更顯復雜,因為,畢竟傳統的“頭人”制度統治鄉村的時間太長,統治者不想放棄,被統治者亦有慣性思維,故從傳統到新生,實則是一個不易的轉換過程。
二、建國初期西康省農村基層政權的重構——以蔡龍鄉為中心
西康省解放以后,為了取得建設農村基層政權的經驗,進一步推廣與健全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基層組織,使鄉村政權成為人民民主的堅實基礎,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之需要,在西康省民政工作會議后,由西康省民政廳與雅安專署、雅安縣府,共三個單位組織建政工作組,人員一共七個(內有專縣各一人),于1952年10月10日開始在西康省雅安縣蔡龍鄉展開建立農村基層政權的試點工作,在同年11月3日結束,歷時23天,取得了良好成績。
蔡龍鄉是雅安縣第一區基礎比較好的鄉,共轄10個自然村,82個居民組,共1553戶,計5609人,并有水碾磨28座,油房7座,磚瓦廠10座。解放后經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1951年又進行了“土改復查”,在各種運動中,涌現出了大批積極分子,他們一般都比較純潔,作風正派,并能聯系群眾,為群眾所擁護。而群眾覺悟亦比較高,絕大多數都加入了自己的組織。蔡龍村在土改前后共開過九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土改結束后,在農代會的基礎上選舉了鄉政府委員及鄉長(鄉主席)。并在1952年的7、9兩月份召開過兩次人民代表會議(實際還是農代會因為除農民外,并未吸收其他各界一個人)。這說明,建國后在建立農村基層政權的初期,農民是最主要也是唯一的力量,雖然成分單一,但是由農民自選的這種方式,卻也恰恰體現了農村基層政權中“農村”二字的特色。這與解放前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該時滲透農村的基層政權是保甲,而無論保長還是甲長的任命,都與普通老百姓是無關的,保甲長本身也是由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士擔當,與普通百姓關聯甚少。如李巨瀾先生在論述民國時期新鄉紳階層的形成與影響時就曾說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政權即根據‘以黨治國’方針,采取各種舉措加強對鄉村地區的控制,建立新的鄉村基層政權。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努力培養出一個受過新式教育、依附和服務于國民黨政權、迥別于傳統的新式鄉村精英階層,作為鄉村社會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取代土豪劣紳對鄉村權力的控制,以確保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對于國民黨政權的效忠以及國家政令的貫徹執行”。而這些新式鄉村精英階層,“往往兼具官紳商學多種身份,他們所具有的知識、聲望、財產及政治身份,是其地位形成與穩固的基本前提。”[6](P17-18)而蔡龍鄉的這種實踐,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部民族地區農村的特點,因為,在缺乏近代工業而且商業也不是十分發達的情況下,加之建國以后農民翻身做主了,農民成為主要的選舉與被選舉者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在具體建立鄉村政權的過程中,蔡龍鄉結合著民族地區的特點,比較穩妥地實施了建政工作。
首先,在具體建政的過程中,根據蔡龍鄉的實際情況,把群眾當前的迫切需要,作為了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以期獲得群眾的支持,即堅持走群眾路線。在建政的過程中,工作人員認識到必須發動群眾大力進行防疫衛生運動,制止死亡,搶救病災,否則要發動群眾建政將是空談。因此,蔡龍鄉是在解決群眾這一迫切需要的基礎上來結合當地中心工作(秋征)進行建政的。在具體步驟上,大體上分為了解情況宣傳政策,劃分居民組、選舉代表、召開代表會、確定今后制度等幾個步驟:(一)首先通過各種會議,如干部會、群眾會、建團會和家庭座談會、個別訪問等,了解情況;然后根據活生生的事實,進行關于防疫衛生、秋征減免,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性以及居民組與互助組的性質、團結生產等一系列的宣傳教育工作。同時并組織了雅安專區的防疫衛生隊,到病情最重之獅子村,經過整整五個整夜免費搶救之后,治好四百余人,嚴重的病情被壓下去,停止了疫病的蔓延,安定了人心,因而把群眾對政府埋怨的情緒,轉變為熱情擁護政府的情緒。如龍洞村代表說:“真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鄉病死人了,政府覺得心痛,即設法搶救,要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哪怕死上一萬一千個人,他還管你那個,該要什么還是要什么”[7]。在此基礎上,這樣工作組就進一步啟發群眾,以新舊政府對比,回憶過去的生活情況、社會地位等,從而提高了群眾的覺悟。之后,群眾們從飛仙關大橋的建筑和給他們免費治療等問題中,認識到了人民政府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給順利完成征糧任務,作了思想準備。從回憶過去中,群眾亦認識到沒有人民政府和共產黨,蔡龍鄉的惡霸地主也無法打垮。
為了改善干部與群眾關系,加強團結,啟發干部群眾自我檢討,對不合理的問題提出處理意見,蔡龍鄉建政工作組又對群眾進行了特別說明:雖經過一系列的運動,打垮了敵人,但私人至今還在伺機活動,如不團結,就會給敵人造下可鉆的空子,我們農民就要吃苦。對某些退坡松勁思想,工作組采取了兩種辦法:一種是盡量采取一人一職制,裁并重疊機構,對某些臨時性的委員會,宣布撤消(任務已完畢的)代表主任副主任等。村干部輪流值班,農忙時若在鄉以上政府開會誤工,三天以上者可適當幫工,以解決其實際困難。如澄清村代表李漢清說:“這回建政弄好了,分工明確后,各負各責,辦事人多了,工作一定能辦好,生產也能推得走”。另一種是對些落后思想,則發動群眾,在選舉代表中,進行適當的批判。如龍洞村張士彬(常委),經小組會群眾教育后,自己做了檢討,又積極干起來。(民政部按:應本團結愛護精神教育提高,一般應避免開群眾性批評會,以防形成“一腳踢開”的意外事故。)隴陽村武裝小隊長李明沛,在啟發回憶教育后說:“今天翻了身,我不能忘本,我曉得這碗飯來得不容易,工作我一定要干,我不干叫誰干。”平石村三組群眾評論李在言(當時鄉長)時說:“他懂得政策,就是工作中不積極負責,只要今后能改,我們還是要選他。”[7]李亦對病人的問題,作了痛心的檢討。在解決了這一系列的問題的基礎上,進行了社會主義前途教育,使干部群眾堅定了建設幸福生活的勝利信心。
其次,工作組依據區劃的原則和居住自然情況,經過群眾充分的醞釀討論,在取得全體群眾的同意后,具體而詳細地重構了蔡龍村基層政權。具體做法是,將蔡龍村調整為九個自然村(原十個村,昝村與石梯村合并),七十一個居民組,最大的二十七戶(平原),最小的十一戶(山地),一般平均在廿戶左右。組與組、村與村、鄉與鄉的劃界,首先取得雙方群眾同意,經過上一級政府批準才劃的(如不能先經農會討論,亦要經擴大干部會議討論)。在居民組劃定后,以村為單位,召開了居民會議,說明村不是一級政權,代表主任、文教衛生、治安保衛、護林水利等五個經常性的工作委員會,各委員會的人員九人到十一人(原則一村一個,便利工作),以政府名義聘請積極分子、技術人才參加。主任委員由有關的鄉政府委員兼任,正副鄉長依據地區、部門分工領導,委員特別是村主任,絕大多數都是一人一職,村代表正副主任等,進行輪流值班分工。村上視需要有的還設有小組,如擁軍、治安保衛小組等。鄉政府委員會及各種委員會,會議匯報時間為十天至十五天。
最后,在基層政權基本建立的情況下,工作組還對前期建政工作進行了總結,并準備發動群眾再繼續進行各種建政后續工作。如在蔡龍鄉代表會議后的第七天,全鄉進行了衛生大檢查,召開了全鄉的評比、發獎大會。在六天之內,全鄉清除垃圾十六萬多斤,通溝1401丈,滅鼠979只,填塞耗子洞460多個,除草742方丈,積肥5800多斤,滅蒼蠅14斤,臭蟲跳蚤1斤2兩,蚊子2斤5兩,打撈沙蟲5斤3兩,修人行道1400多丈。并出現了一個模范村(原死人多,病情重的獅子村),九個模范組,九個模范戶,而這些也都獲得了廣大群眾的稱贊和政府的獎勵(錦旗、毛巾、肥皂等)。這些巨大成績的取得,再一次證明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過去干部與群眾之間的某些不團結(如獅子村)、鬧宗派(如澄清村)也迎刃而解了。
三、農村基層建政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及教訓
雅安縣對于蔡龍鄉在農村基層建政過程中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但與此同時,縣政府也實事求是地對建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教訓進行了總結。如1952年12月23日,在蔡龍鄉建政工作結束后不久,西康省人民政府就對于蔡龍鄉建政試驗工作作了總結報告。報告總結道:“雅安縣蔡龍鄉的實驗建政工作,解決了過去存在的若干問題,又發現了很多嚴重問題。其處理問題的觀點和方法,是依據群眾當前迫切的要求而著眼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值得我們某些農村工作同志仿效:但對建政本身的具體工作,解決的還不夠徹底,亦應引起注意”[8]:
第一,該鄉部分鄉村干部,存在著換班思想,工作組雖用對比和回憶的方法教育了干部,并啟發他們作了自我檢討,但未進一步結合當前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某些破壞事實,來提高鄉村干部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警惕,并深入細致地解決鄉村干部的實際困難、使之從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解決問題,對縣、區某些干部的強迫命令和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也未予以及時糾正。
第二,根據鄉村的實際情況,如硬性規定“一人一職”,是有困難的。如何減少會議,也缺乏具體明確的辦法。各地在今冬明春建設工作中,應切實注意解決鄉村干部的工作與生產矛盾,如對非脫離生產的鄉村干部,在農忙時因公耽誤生產超過幾天,可酌情給以適當的幫工,每年最多不能超過幾天,以免鄉村干部脫離群眾,并經縣級批準為宜。鄉村干部一般的最多不能兼幾職。哪些會非開不可,哪些會可以不開或少開,每月不能超過幾次會議等,應由今冬第一批建政的地方,將這方面的經驗,加以綜合報省,以便統一規定,俾能有效的解決鄉村干部困難,健全鄉村的組織和制度。為了減少鄉村干部麻煩,各級各單位任意往下發表格的現象,必須適當的控制,應由辦公廳召集有關單位商定控制辦法。
第三,各級機關,要搞實驗工作,或到鄉村作任何工作,都應估計到鄉村干部和群眾的時間與精力,一個鄉不能允許有兩個不同性質的實驗工作(據說雅安縣這種現象還不是個別的)。且各級機關典型實驗,也不必都到基礎較好的鄉去進行工作,否則不僅使鄉村干部煩不勝煩,疲于應付,形成三頭受氣,以致產生松勁換班思想,甚至可能使好鄉變為壞鄉,且我們的各種政策,也將難于貫徹。關于省、專、縣、市要到雅安縣及市所屬各鄉去做實驗工作,應由民政廳協同區黨委農村工作組與雅安專、縣、市各有關單位,擬定具體辦法,經領導批準后,加以實施,以統一典型實驗的步驟和減少各鄉村干部的麻煩。即是說,在選擇典型的同時,也要照顧全面工作。
第四,該鄉今年就病死了一百零一人,這反映了我們某些干部,只要任務,不要政策,把上級要求和群眾利益對立起來,這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表現,應由人民監察委員會和有關單位加以檢查,追究責任后,給予應得的處分。今后要徹底糾正這種壞現象的發生。此種情況,估計干部中還不是個別的,應引起各縣警惕和檢查。
第五,該鄉個別村,互助組與居民組混淆不清,甚至硬性規定要本居民組在一起互助,不許和其他居民組互助,這是違反自愿兩利原則,各地在建政時,也檢查一下。
第六,土改中有些遺留問題,在這次建政中沒有得到解決,這也說明了單純的建政觀點,各地須在這次建政工作中,將土改遺留問題全部解決。
綜觀上述總結出來的六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建國初期雅安縣以蔡龍村作為農村基層建政的重點,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這個事例來發現與解決西部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建政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在總結蔡龍村經驗的同時,西康省人民政府對于蔡龍鄉建政試驗也提出了幾點經驗教訓:
第一,不管何種部門進行任何工作,若把廣大群眾當前最迫切的要求,置之于不顧,要想單純完成自己的所謂“中心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包括農村基層建政在內的一切工作,都要發動群眾,與依靠廣大群眾,才能取得勝利,即前面所提群眾路線才是工作中應該堅持的路線。蔡龍村這次所以能在短期內完成建政任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把群眾當前最迫切的要求,確定為壓倒一切任務來解決。如果工作組對嚴重的病疫情況置之于不顧,那么要取得上述這些成績,是難以設想的。
第二,經驗證明,在進行工作時,必須采取“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推動指導全面”的領導方法,才易于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蔡龍村這次以平石村這個自然村為重點,干部配備較強,因之易于取得經驗推動指導各村工作。
第三,必須依靠各種組織活動,去進行各項工作,否則就無法擺脫包辦代替的形式。蔡龍村工作組這次工作開始時,沒有很好的依靠農協發揮其組織作用,使工作在開始時,受到了某些影響。
第四,選舉代表或委員時,要充分發揚民主,根據條件展開評比,使干部以自我檢討和群眾批評相結合,不僅對干部進行了教育,堅定了工作信心,且亦教育鼓舞了群眾,加強了團結,改善了干群關系。但仍有個別干部(區)對疫病流行所遭受的痛心損失,沒有深刻檢討,以致影響了群眾批評政府的勇氣。特別是西部民族地區,由于處于基層的農民過去很多都是奴隸身份,根本就無權利可言,建政中更應該抓住這一特點,充分使農民享受到新政權帶來的新權利,只有有了這個比較以后,他們才會積極參與新政權建設與擁護新政府。
第五,在人民代表會議中,任何一個提案,都必須分別輕重緩急,慎重處理,務使“事事有著落,件件有交代”,這樣才能取信于民。蔡龍村在對待個別提案時,就沒有明確答復,致使某些代表感到“沒有解決他的問題”,這也是應該糾正的。
對此,蔡龍鄉建政工作組在前期建政經驗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一些建議:第一,由于工作組的時間緊迫,以致對某些少數干部多占果實,個別貧雇農未分到房子、土地等問題,未能及時處理,只有留待土改復查中給予解決,以利團結生產。第二,建政后,蔡龍鄉雖已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組織和制度,但縣、區領導上,必須繼續耐心的幫助他們,以便使他逐步健全和鞏固起來。第三,各級各部門派往農村的工作組,盡可能和當時當地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并通過一定的組織去進行工作。否則彼此強調重要,干部與群眾勢必處于無法應付的狀態。尤其是某種材料和表格,在省直屬各單位即可解決,有的縣區就可能解決,不必一一都到鄉村去調查,以免增加鄉村干部和群眾可以避免的麻煩。如有萬分必要,可經過一定的機關(縣或區)控制,再到鄉村調查,以免混亂。第四,對鄉村干部,特別是村干部,工作和生產的矛盾,有關機關應制定適當的幫工和補助辦法(如在農忙時連續誤工三日以上者可讓群眾幫工等),以便逐步解決這個歷史的矛盾。
四、小結
西康省解放后,在農村基層,面臨的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就是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新的基層政權建構,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此中,它也與別的地區農村基層建政工作有著共性,這在全國幾乎一樣,即在取得政權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外來的陌生者,為了對農民進行充分的社會動員,就需要進行鄉村社會的動員和重建工作”[9]。而在西部民族地區尤其顯得重要,個中原委,一是因為西部邊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二是因為長期以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不發達,致使處于基層的民眾根本沒有機會享受到任何民主,也沒有感受到基層政權給予他們的任何保護。因此,作為新政權的塑造者,為了政權獲得基層民眾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必須對鄉村社會的基層政權進行重構,但是,推倒一個舊政權雖說不容易,但是,重建一個新社會更談何容易。在西部民族地區,更因其地域特點與歷史原因等,農村基層政權的重建與漢族聚居區有所不同。本文之意,意圖通過對建國初期西康省基層人民政權的建立和鄉村權力結構的重構進行探討,總結其經驗教訓,可為當今的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建設,尤其是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基層管理人員的素質和水平,解決目前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完善基層社會民主管理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一定的歷史借鑒。
[1]黃天華.論民國時期西康省[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4):98.
[2](英)榮赫鵬著.孫熙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282.
[3]吳建國.試論西康建省與康區的早期現代化[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41.
[4]郎維偉.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四川康區社會[J].西藏研究,2008(3).
[5]宋鍵.鄧小平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權建立[J].貴州民族研究,2010(5).
[6]李巨瀾.試論民國時期新鄉紳階層的形成及其影響[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4).
[7]四川省檔案館藏.西南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通報),建川全宗號 044,目錄號1,卷宗號 31,民政(52)字第0324號,1952年12月5日.
[8]四川省檔案館藏.西南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通報),建川全宗號044,目錄號1,卷宗號31,民政(52)字第0324號,1952年12月5日.
[9]陳益元.醴陵縣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1949—1957)[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內容摘要”第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