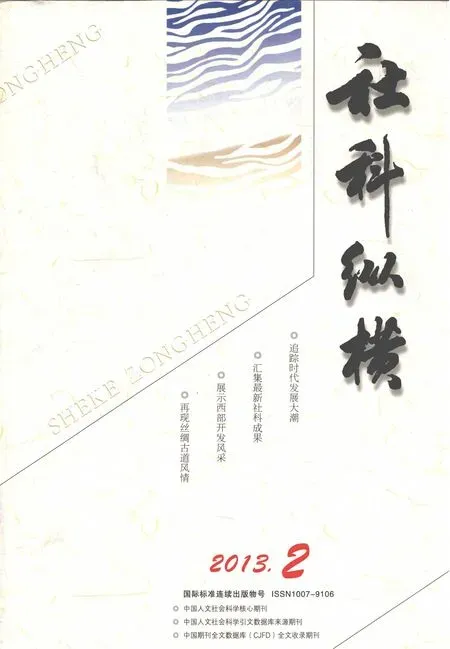金融危機后華語大片的文化整合——文化崛起與輸出的有效表達
馬麗敏
(衢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文化全球化正日益成為當前文化發展的趨勢,然而這樣的趨勢在表現出全球追求價值多元化的同時,也表現為對某一價值文化認同上的偏愛和趨于一致的合謀性。對于當下的中國,全球化既是中國文化走向國際的一次的機遇,但同時又不得不遭受更多共享資源下的文化障礙、文化霸權等問題。中國文化迎來了史前最為糾結,也最為尷尬的境遇。所謂的交流碰撞融合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價值觀蓋住了底蘊深厚的本土文化,民族話語權看似緊握在雙手,高唱的卻是被西化的論調,表現的和諧其實只是以犧牲傳統文化的身份得來,文化安全的問題日益凸顯[1]。
如何在全球化中贏得勝利,避免當前這種表象的融合狂歡和陷落,在當下為中國文化的表達找到一個好的出口顯得既迫切又必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全世界的經濟帶來不小的震動。然而西方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似乎也在表明一種整體感官的震動。全球的視野不再緊盯著美國、英國和法國,次貸危機的發生正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在某個環節出了問題,而作為社會運行的主體的人以及觀念也被推上了審視的前臺。尤其是危機后,中國經濟的有效規避讓我們的話語權向國際舞臺邁進了一步。
面對機會,我們的文化如何尋找有效的途徑和出口,是我們必須審慎面對的問題。據文化發展產業報告稱,電影產業是文化產業中最有活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在文化產業中占有支柱性地位[2]。由此,中國電影史無前例地被推到一種使命性的位置,那就是必須承擔起輸出文化,構建國家形象的重任。而在這個任重道遠的艱巨使命中,我們理性地管窺中國電影,這里我們主要以華語大片為對象,審視在文化傳承的發展。
自《英雄》問世以來,華語大片呈現出了一種隱晦但又逐漸清晰的文化特征,渴望取之有道但又表達得急切而混亂。放眼望去,中國代表性的大片似乎皆存在這樣的癥結。我們看到它們繁華地開啟,但粉墨登場后迎來更多的卻是無盡的唏噓,隔靴搔癢的模糊難能做到云日輝映,空水澄鮮的明朗。于傳統與現代、后現代的相互糾結、沖突、難融的歷時進程和當下共時的存在狀態中,華語大片的文化表達需要更多地修正。
一、現實精神與古今共鳴的缺乏
《英雄》盡管在宏觀題旨上下足了功夫,電影藝術手法的運用也可謂新鮮,但關乎這里每個人的敘事發展,主要人物的國仇家恨近似空穴來風,人都是浮云般的存在,為著最終的一個理念艱澀地行走在早已擺好的棋盤上,至于“天下”畢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輕易理解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幾部大片的相繼出現無疑增強了中國電影走類型化路線的信心,但比起《英雄》,故事中似乎只剩下了毫無所指的杜撰。商業化賣點多了,內涵少了,遠離了現實。這之后張藝謀有意識地發展了古裝武俠的中國大片類型,古裝功夫、當紅明星、視覺特效,這也使隨后出現的大片外觀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2005年的《無極》,導演陳凱歌在頗費心力的形而上的哲學精神上,講了一個關于“信任”的故事,夾雜著一個還算簡單動人的青蛙王子與白雪公主的愛情,這些無疑是與現實社會對話的良好砝碼,但最終的謎底告訴大家:那個不再“相信”的無歡,他的冷酷和殘暴只因兒時傾城奪回饅頭時一個小小的欺騙而導致。這內在邏輯的輕浮似乎扛不住沉重的人性之災吧,“相信”的命題在現實生活的投射上再次失敗了;“滿神”從一出場就幾乎沒有融入敘事,那個為傾城量身打造的人生圈套是為何而設呢,“得到榮華富貴就要付出得不到真愛的代價”,這在現實生活中也并不是一個什么非成立不可的命題;至于影片中的愛情因誤會的錯位投射而顯得輕飄飄,最終奴隸昆侖背著傾城飛向宇宙的瞬間,宣布了這里的愛,這里的人生只是一個在現實生活中毫無發生概率的、荒誕的夢,這樣的電影難以讓觀眾情感投入,少了靈魂相通。“無極”這個“道”的終極性主題在這里難掩“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的失落和尷尬。
馮小剛一直走現實主義路線,賀歲片的標簽和票房魁首,但在大片利益的驅使下,耐不住寂寞于2006年炮制了一部《夜宴》,這里你再找不到馮氏幽默和現實反諷。電影將古代中國的那些糟粕都拿出來了,宮廷內亂,血腥刺殺,亂倫之戀。真真一個殘忍了得,血漿四濺的酷刑因為特技顯得非常真實可感;三綱五常也作為葛優的臺詞被鏗鏘有力呈現在觀眾的面前,很容易被女權主義者看到這其中的野心;太子被暗殺一幕唯美而虛假,隨從們為了掩護太子,沒有一個要逃命,都一個個呆在原地等著被砍死。電影里,沒有人的概念,只有太子、皇帝、皇后們,他們的爭斗,他們的情感,而老百姓能在這里看到自己嗎?女性觀眾倒是可以從青女這里看到如何為了太子犧牲自己。且不說性別文化全無,基本女性生存價值也就被限定在奴隸時期。在當下價值觀混雜的語境里,《夜宴》中的這些情節仍然可能成為再生產劣質文化觀念的工具。
2007年香港導演陳可辛的一部《投名狀》,依然是一部古裝功夫,但和內陸大片相比,其戲劇沖突增強了可觀性,影片以兄弟情作為主要承載內容,抓住了“人性”這個大主題,一個戰敗的將軍和兩個重情義的土匪之間的兄弟情,真摯感人。但作品最后發生的兄弟相殘的戲,將整部電影的格調最終還是定在了濃黑與悲涼。世紀末本身無可阻擋的后現代文化因子,其否定和不確定感,已經讓這個社會沒有了信任和確信,而電影對“失信”的濃妝重抹更讓受眾對這種質問確認無疑,虛無和蒼涼,冷酷與無情。“投名狀”在影片伊始的厚重和情誼至此化為烏有,最后讓我們不得不看到,三個兄弟之間的相殘,錯就錯在這一紙“投名狀”。到此,影片本可傳達出的那種濃濃的人性漸行漸遠,卻轉換為一種無以復加的對“信”的否定。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并非只有現實題材才可以反映當下社會主體精神。所以我們梳理厚重的歷史,就一定要有意識地表達當下的精神和價值訴求,即使是古裝題材,也應該將廣泛的現實問題包裹入故事的框架模式中,并予以想象性的解決對策。而華語大片史上相繼登場的《英雄》、《無極》、《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和《投名狀》等,當然我們無法否定它們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中國文化給予了一種想象性的梳理。但其對現實社會缺乏燭照,缺乏古今共通的情感內核,受眾對銀幕世界的故事沒有共鳴,使得觀眾無法從影片中獲得現實意義的對鏡自照。觀眾感覺不到電影是在關懷這個世界,關懷這個社會,關懷當下生活,關懷生存中的人;更重要的是,作為輸出中國文化的有效窗口,華語大片的這些缺陷將世界了解中國的視域只能鎖定在那個遙遠古老的和封建的國度。
二、建構意識不足,民族形象模糊
我們不用費盡心力地尋找歷史,上下文化5000年,隨便指點江山便是令人心悸,動人心魄的中國故事。可華語大片寧愿將崇高的、偉大的棄之不用,不約而同地對那些邪惡、血腥、殘暴的東西樂此不疲。華語大片的先聲《英雄》開辟了這樣的傳統,緊跟其后的幾部如《十面埋伏》、《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等都表現出了同樣的調子。《英雄》無疑有著中國特色的文化表征,如人在國家利益面前的舍小家,顧大家的大愛精神,這本身沒錯,可我們硬是看到了電影竭盡所能地將這種大愛精神擺在了小愛的對立面,國愛和情愛非得爭個你死我活,只有這樣,我們似乎就可以看到人的崇高和偉大。這看起來符合簡單的邏輯,可是細推就覺得特別站不住腳。當今是21世紀,以人為本的文化思想理應處在社會主義文化的中心地位,我們不止愛國,我們希望愛國的同時,可以愛家庭,愛妻子,愛孩子。殘劍為了空洞的“天下”,背棄了飛雪,而飛雪也懷著虛空的家恨最終與愛人痛苦分別,將劍刺向了昔日親密的愛人。而核心人物無名更是有著耶穌一樣的情懷,他背叛了一切,最終將抱負投向了大眾難能理解的“天下”。后來的《十面埋伏》、《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那些宮廷險惡,我們聞到了陰暗腐爛的味道,看到了血肉模糊的殘殺。更甚之,電影給我們呈現這些的時候是非大片不能做到的、花巨資打造的特技,用來雕琢發生在這里的每一個殘忍的鏡頭。我們將太多心思用在了每一個鏡頭對邪惡的呈現上,夠不夠恐怖,夠不夠血腥,電影最終夠不夠壓抑,夠不夠讓你鄙視歷史幾乎成了大片夠不夠大的標準。長此以往,我們觀眾只能認識到,中國的歷史怎一個亂字了得!
我們多了毀滅,而對人性的愛與美提升不足,所以很難看到大多好萊塢大片那種人性之光熠熠生輝的美好場面,從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華語大片在中國文化的表達上,少了悲憫,少了敬畏,對于民族形象的設計和想象力都顯得不足。
在日益強調國家形象,國家文化安全的今天,中國電影對國家形象的設計和想象一直沒跟上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電影塑造的中國形象需要強化現代性和國際性意識,亦需關注多元化、綜合化的藝術表現,才能適應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的真實效果和競爭形勢。
三、危機后華語大片逐漸凸顯的文化自覺性
危機后,我們在考證2009年以后的幾部大片,就可以發現,很多影片有意識地抓住這次崛起的機遇,他們將“主流精神、創新的藝術理念和鮮明的市場意識相結合”,力求“更加貼近中國觀眾情感訴求、更加貼近中國社會現實生活和日益豐富多元的創作理念和手法,將社會責任、文化使命和藝術品格相結合”,為了建構國家電影的命題,擔當重塑中國形象的重任,他們努力著[3]。
危機后,中國電影呈現出“拍片類型化,創作國際化,投資多元化,運作市場化”的發展格局[4]。整體上看,2009年后上映的幾部大片,凸顯了文化整合的意圖、文化保護的國家安全意識。從《白銀帝國》、《孔子》到《十月圍城》、《建國大業》、《葉問》等等,能看到它們試圖抓住機遇的努力。
首先在創作觀念正在走向成熟,古裝片的現實精神有大的進步。《白銀帝國》在2009年上映,正當全球人討論金融危機,評說西方資本經濟的弊端,走進電影院,老百姓在恰當的時間看到了這部電影。可以說這是一部價值觀迷茫時期,中華文化抓住時機的一次展示。此片重通過山西票號“天成苑”在清末那段特殊歷史中經歷的事件,展現大仁大義的恢弘氣度——商人重義及經商的仁義精神。將儒家思想放在商人世界這個平臺,既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發揚光大,得以傳播;其次,近代由于歷史原因,對商人偏激的看法,在這部電影中也得到了現實的觀照,為商人的地位提升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白銀帝國》作為經融危機后華語大片的開篇之作,一改如前,大片對歷史過度負面的關注,它對當下社會的表達恰當適時。
《葉問》是一部敘事上幾乎沒有缺漏的影片,情節緊湊,在票房和口碑上都盡如人意。不過更重要的是,它能作為大片屢獲好評,是因為在文化表達上,走了一條既小又大的賦有張力的承載之道。說它小,是因為在電影中,觀眾們看到了一個別樣不同的民族英雄,一個完美英雄首先是個好丈夫,是一個能尊重妻子,好好去愛護家庭的人。這個文化小命題抓住了很多女性觀眾,也使得這部電影為女性主義者們看好,真正意義上將華語大片性別文化的缺失在熒幕上來了一次成功的拾起。另外一個“大”命題就是它在老百姓與侵略者抗爭的這個故事中,再次塑造了民族形象,展示了民族精神,站在世界的窗口打了一套詠春拳,傳送了一股不可忽視的中國力量。影片充滿著現實精神,擔當文化輸出的使者不辱使命。
其次商業化元素的主流電影將大愛精神與平民意識交織融合。除古裝武俠片外,危機后近代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影片一時促成了有效文化的輸出表達。如《建國大業》、《十月圍城》等等。將主流價值觀放大,它們不再一味地概念先行,更多地將主流題材加大了商業元素的投入,整合了很多藝術手法,對其并立交融。
《建國大業》在節奏上,在歷史的講述上,在敘事蒙太奇的運用上都堪稱佳作。遠景的運用,結合了鏡頭的高空運作,越景的立體感極強。千軍萬馬在鏡頭的高放置到低境特寫,攢足了戰爭場面的宏大,遼闊。音像的環繞運用,將飛機的轟鳴、槍炮的真聲響徹全場。大片的氣魄絲毫不遜于好萊塢制作。
注重細節的情緒體驗讓觀眾感覺他們就是活生生的人,再也不是神龕上的偶像。他們生氣,罵人,摳門,他們在勝利面前的無法承受;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酩酊中把酒歌唱國際歌,手舞足蹈;毛澤東坐在桌旁的一角靜靜地、咪咪地似笑非笑,而眼角中又分明是帶著歷經萬劫的滄桑淚痕。作為觀眾,你不能抵擋愛國題材的影片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感性操作,深深抓住了老百姓的心。這不僅大大摒棄了之前大片概念化的空洞,還達到了影片訴求的那種深刻的內在精神和歷史政治話語的完美結合。
《十月圍城》被很多媒體,稱為最完美的商業片,“利用真實背景講述虛構故事”,很符合好萊塢的套路。線條比較簡單,但故事能在錯綜復雜的小人物這里,為一條總線服務,不凌亂,且張弛有度。影片將小人物的情懷寫真融進了社會主流文化價值觀,“樸素的信仰”中看到了小人物身上涌動著的“人性暖流”[5]。最終小人物促成了大事業,悲壯富有深旨。
結 語
危機后中國電影已然成為大眾文化和文化消費的中心,華語大片的商業化之路漸入佳境,應當看到,每一部大片的公映都是一次文化的輸出,影響著國民素質的形成,傳達著主流的價值觀,而華語大片的文化理念更是代表了中國特色的文化取向,走出國門更是一種文化安全的建構。我們看到了華語大片已經回應了危機后大國崛起的機遇性戰略,不斷創新,它們似乎找到了商業化與藝術美學的融合之道,大眾娛樂與文化承載的和諧相生,先進技術與藝術內涵的整合機制。以中國正文化為輸出力量,介以全球化商業運作的技術策略,實現了一種新的有效的探索。
[1]王岳川.大國文化創新與國家文化安全[J].社會科學戰線,2008(2).
[2]張曉明,胡惠林等主編.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3]童剛.2010電影局新聞通氣會報告[OL].http://www.sina.com.cn,2010-1-8.
[4]王一川.當前中國國家電影業的新方向[J].當代電影,2009(9).
[5]尹鴻,劉浩東主編.中國電影藝術報告[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