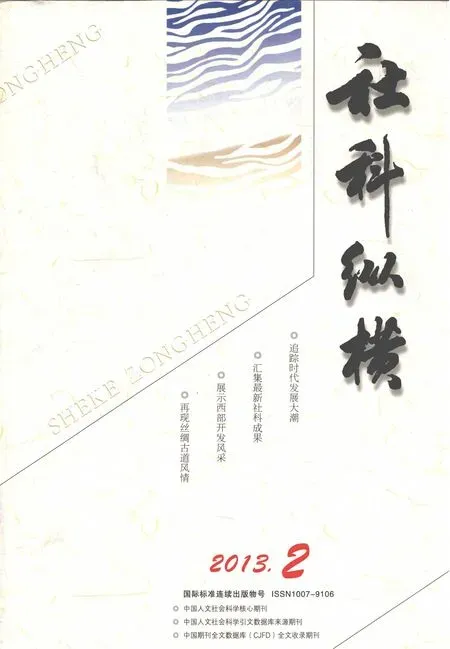略論發遣刑與清代的邊疆開發
劉炳濤
(西安石油大學人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5)
我國古代的刑罰中,有一類刑罰是把犯人發往邊疆地區服刑。這類刑罰在歷朝歷代名稱不一,有遷、徙、徙邊、流放、長流、充軍、發配、發邊外為民等說法,但從刑罰種類上來區分,都可以歸入流刑。這些被流放到邊疆的犯人是很多的,他們雖為罪犯,但對邊疆地區的開發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到了清代,除原有的流刑、充軍外,又出現了發遣刑,明確規定把犯人發往北部邊疆,使清代留駐邊疆的犯人大增,為我國西北和東北地區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便著力闡述發遣刑對清代邊疆開發的意義,使那些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遣犯們能夠不被人們所遺忘。
一、發遣刑的含義與特征
在清代,發遣一詞有兩種含義。其一是指發配,作動詞用,指把軍犯和流犯發到指定地點服役。《大清律例·名例·犯罪免發遣》條規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這里發遣就是指發配。在清代的條例中“照例發遣”之類的用語較多,即是把罪犯照條例前面所定的刑罰發配。其二,即是指一種特殊的刑罰,指把罪犯發往東北地區或新疆分別當差、為奴,被發遣的罪犯則稱為遣犯。按照《清會典》的解釋,發遣刑是“發往黑龍江、吉林、伊犁、迪化等處,酌量地方大小,均勻安插,分別當差、為奴。” 由此可見,發遣有著特定的含義和特點,與充軍和流刑有著一定的區別。
第一,發遣是僅次于死刑的重刑。在五刑之中,流刑本來是僅次于死刑的刑罰,明清充軍比流刑為重,而發遣比充軍更重,原因在于發往邊疆與當差、為奴相結合所產生的懲罰功能更強。發遣為奴人犯在到配后一般被分給當地駐防兵丁或少數民族群眾為奴,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生活待遇,均極為低下。為奴實際上是清代入關前的奴仆制度的延續,在入關之后,又結合前代的統治手段,將其正式法律化,制度化。
第二,發遣地點固定為東北地區和新疆兩大地區。從清初到乾隆中期,遣犯主要發往東北地區,并且逐漸由南向北轉移。清初,遣犯大多發往尚陽堡、盛京、遼陽、鐵嶺,以后漸次向吉林、黑龍江方向擴展。乾隆中期,新疆納入清朝版圖,清廷開始把遣犯大規模地發往該地。新疆的主要發遣地是伊犁和烏魯木齊兩處,此外還有巴里坤、哈密、南疆各回城等地方。遣犯發往東北與新疆是發遣與充軍的重要區別。“軍罪雖發極邊煙瘴,仍在內地,遣罪則發于邊外極苦之地,所謂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此軍與遣之分別也。”[1](P9955)從乾隆朝開始,發遣新疆、發遣黑龍江與充軍極邊煙瘴相互調整,共同組成了清代的邊疆流放體系。
第三,遣犯服刑的主要方式是當差和為奴,在新疆還有種地一項。這是與軍流罪的又一重要區別。流犯到配后官府對其稍加約束,聽其自謀生計,沒有實際的刑罰約束內容。軍犯的情況與此沒有實質差別。明朝實行的是衛所制和軍伍世襲制,軍犯要入軍籍為兵,而清朝實行八旗和綠營兵制,廢除了衛所制,士兵的來源固定,罪犯被充軍后不可能再入伍當兵,只能由配所州縣進行管束。與軍流犯相比,遣犯到配后當差,給士兵為奴役使,實際是服勞役,有具體的刑罰執行內容。在清廷看來,這樣能有效地懲治罪犯,所以發遣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成為常用刑,適用范圍漸廣。
第四,發遣刑不僅僅是一種刑罰,還具有移民法的性質。發遣刑出現于順治朝后期,在立法上正式確立是在康熙十九年頒行的《刑部現行則例》。此后到乾隆朝,不論是在立法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發遣刑的規定與使用逐漸完善。乾隆中期,新疆納入版圖,朝廷制定條例開始規定向新疆發遣人犯,以補充當地的勞動力。為增加人口和防止遣犯脫逃,還規定家屬同遣之制。光緒年間,為補充因新疆戰亂而喪失的勞動力,修改遣犯安置辦法,新疆遣犯照民屯章程辦理。由此,發遣刑的刑罰懲罰功能減弱,而移民實邊發展當地經濟的功能占據了主導地位。
在發遣刑的執行過程中,并沒有規定遣犯統一的服刑期限,而是根據對遣犯的役使形式和發遣地的不同,規定了不同發遣年限及遣犯的不同出路。其中,一小部分遣犯永遠為奴,另有一部分遣犯因立功和服役十年以上回原籍為民,大部分遣犯則是在服役三年、五年、十年后在當地為民,不準回原籍。乾隆三十一年,規定烏魯木齊遣犯“有家屬者,查系原犯死罪減等發遣者,定限五年,原犯軍流改發,及種地當差者,定限三年,如果并無過犯,編入民冊。”[2](卷744)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又延長了為民期限。“發往伊犁、烏魯木齊為奴遣犯在配安分已逾十年,令其永遠種地,不得為民。若發往當差遣犯果能悔過悛改,定限五年,編入該處民戶冊內,給與地畝,令其耕種納糧,俱不準回籍。其有捐資入鉛鐵等廠效力者……如系為奴人犯,入廠五年期滿,只準為民,改入該處民戶冊內,不準回籍。”[2](卷742)準入民籍意味著在邊地落戶為民,不能再回到原籍。為充實新疆人口,對于為民遣犯清廷給予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比如把遣犯眷屬官費資送到遣犯所在地,貸撥給遣犯生產生活資料使其能夠生活下去。以上措施施行后,不斷有遣犯附籍為民。據記載,乾隆四十三年烏魯木齊一地就有為民遣犯一千二百四十二戶[3](P59)。遣犯為民后,多從事農業生產,逐漸成為新疆土著居民。
總之,從歷史上看,清代的移民規模是非常大的,這其中既有內地之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也有內地向邊疆的人口遷移。在后一種移民中,既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而發遣就是被動的一種移民方式。因發遣而移民的流向主要是兩大發遣地東北和新疆。東北地區由于是滿族的發源地,清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禁止內地民眾向東北遷徙,對東北實施封禁政策。從清初就開始的發遣把大量不愿遷移的罪犯發往東北,這些罪犯大部分不再回內地,而是成為當地居民,間接促進了東北地區人口的緩慢增長。與東北相反,清廷對向西北的移民卻大加鼓勵,從罪犯發遣新疆開始,就帶有增加新疆人口的目的。經過不斷發遣,遣犯及其家屬在新疆人數之多,實為歷史上所罕見。紀昀在遣戍烏魯木齊期間所寫的《烏魯木齊雜詩》之一“鱗鱗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戶家。斜照衍山門早掩,晚風時裊一枚花”的景象,就是遣犯移民生活的真實寫照。由此可見,清朝利用發遣刑來促進邊疆的發展,取得了成功。
二、發遣刑對清代邊疆開發的意義
對于遣犯個人及其家屬來說,發遣是降死一等的重刑,意味著受苦受難,但是如果把發遣刑放到邊疆開發的大環境下,它對我國東北和西北邊疆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增加了邊疆地區的人口,為邊疆開發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東北地區經過明末長期的戰亂和滿洲人的大量入關,人口稀少,而清廷采取的封禁政策又限制了內地人口向東北遷徙,使東北人口不能大量增加。新疆經過清廷與準噶爾部的長期戰爭,也是人口凋零,一片荒涼景象。把遣犯發往邊疆地區,正好彌補了當地人口一定程度的不足。在發遣的高峰期,遣犯本人加上家屬,一次發遣人數常至數百人以上。乾隆中期,今齊齊哈爾一地就有遣犯三千多名。光緒九年,黑龍江將軍咨呈軍機處稱該省歷年接收遣犯二萬六千多名[4](P1122),新疆的遣犯數目當不必此少。據估計,清代發往新疆的遣犯及其家屬的總人數約在十萬至十六萬之間[5](P142)。如果東北和新疆兩地遣犯加在一起,當有數十萬人。考慮到當時整個邊疆地區地廣人稀的狀況,這個數量應當說是很大的。這么多的人口改變了邊疆勞動力不足的狀況,為邊疆發展提供了比較充足的人力資源。
第二,為抵抗侵略、鞏固邊疆地區的國防作出了一定貢獻。康熙年間,沙俄侵略東北地區,當時有大批遣犯被編入水師營、火器營中充當水手和匠役,他們為抗俄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乾隆十年,黑龍江將軍疏稱:“本處水師營內發遣當差人犯,俱系順治、康熙年間,發寧古塔等處安插之人。后征俄羅斯,作為鳥槍、水師二項兵出征,凱旋后編為六個佐領,令入旗披甲,錄用官員。”[6](卷243)道光二十七年,南疆和卓后裔叛亂,有遣犯數千人隨清軍作戰,為平叛作出了貢獻。清廷“以隨征回匪有力,釋回遣犯一千一百七十四名”[7](卷449)。道光二十八年,“以派赴巴爾楚克防堵出力,釋回遣犯五百名”[7](卷445)以上史實說明,遣犯為保衛祖國的北部、西部邊疆,反擊外國侵略、鞏固祖國的國防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第三,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北部邊疆經濟上較內地落后很多,遣犯通過艱辛的勞動,為改變邊疆的落后面貌,促進邊疆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首先是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發往東三省和新疆的遣犯,無論為奴、當差,大部分從事的仍是農業生產。在新疆,種地遣犯被組織在一起,專門進行屯田,形成了“犯屯”這一新的屯田形式。通過遣犯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共同努力,邊疆的土地被大量開墾,糧食產量和品種顯著增加,農業生產技術與工具得到了改進。有學者經過調查,指出乾隆四十二年時,新疆“南北兩路兵、犯墾地共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余畝”[8](P278)。糧食產量的增加,使“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者”[3](P172),這其中自然有遣犯的一份功勞。其次,促進了手工業和礦冶業的發展。發往邊疆的遣犯,有很多具有手工業技術,在服役的過程中,他們把這些技術傳承給當地,改變了邊地技術落后的狀況。發往新疆充當苦差的遣犯,從事挖礦、冶煉銅鐵等最為艱苦的勞動,為新疆礦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四,促進了邊疆地區文化的發展。邊疆地區不僅經濟落后,文化也很落后。遣犯中有不少文人,即舉貢生監。職官或舉貢生監,都是清代社會中有身份的人,他們一般并不發遣為奴,而是當差,從而有較多的時間傳播文化知識,為改變邊疆地區文化落后面貌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這些人士中,最著名者當屬康熙時著名學者陳夢雷。康熙二十一年,陳夢雷因三藩之亂的牽連被從重發往盛京給新滿洲披甲為奴。他到配后,“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者踵接”[4](P972),促進了盛京地區文風的轉變,從而改變了該地文化荒蕪的面貌。此外,還有許多默默無聞的文人,在發遣地傳經授徒,也對當地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綜上所述,發遣刑是清代獨具特色的刑罰,它既有刑罰的功能,也有移民的作用。對個人來說,它刑罰殘酷,對國家來說,它功勞甚大。我們在評價它的時候,既要看到它落后的一面,更要看到它移民實邊,促進邊疆地區發展的一面。
[1]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昆岡.清會典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91.
[3]王希隆.新疆文獻四種輯注考述[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4]李興盛.中國流人史[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
[5]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0.
[6]董誥.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
[7]花沙納.清宣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
[8]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