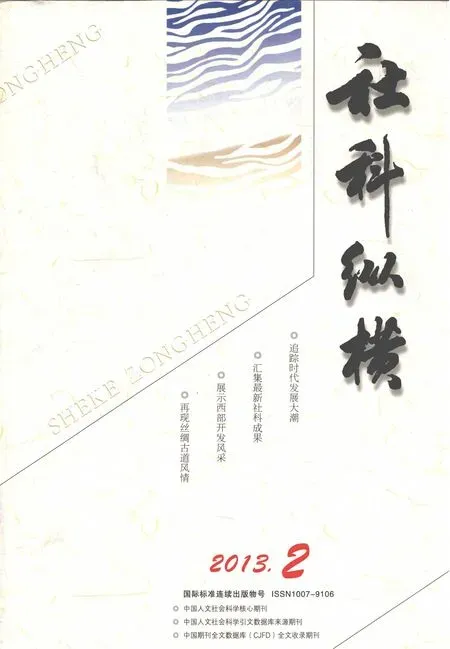對馬克思的價值理想——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一點理解
于淑紅 張永俠
(中共秦皇島市委黨校 河北 秦皇島 066004)
一、不能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來代替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地位,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認知和重視。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并不能不指出:該理論有些基本問題被一些研究者“輕易”地忽略了。其典型表現是這樣一種普遍流行的提法:人的全面發展。而馬克思始終一貫的提法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應當說,這是兩種具有質的差別的提法。因為在馬克思的提法中,“每個人”、“自由”、“全面”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語,而是有著豐富的內涵和科學的規定。它不僅涉及到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質的看法,而且反映著馬克思歷史觀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指向。
考察馬克思有關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論述,我們發現,在很多論著中,馬克思在談到“全面發展”、“自由發展”或“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時,在前面冠以的都是“個人”一詞。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共產主義是“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的社會”,“個人的全面發展……正是共產主義所向往的”,“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革命……本身就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有“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在《資本論》中,有共產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等等。可見,“每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確實是馬克思始終一貫的提法。馬克思之所以用“每個人的”而不用“類”,同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關。
二、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據此,有人把人的本質定位于社會性隨之還可以推論:社會本質是惟一的,個人本質是不存在的。而一旦忽視了獨立的個人在社會中總的來說的前提地位,抹殺了個人本質,那么,人的本質豈不成了無源之水。不少研究者認為,馬克思對人的本質也有一個分析過程,其間有多種表述。除了社會關系的總和,他還分別從人本身、勞動、自由自覺的活動、人的自然本質等多方位對人的本質作過闡釋,對此應聯系起來統一起來歸納理解,不能簡單片面取其某一種說法。
所謂在其現實性上,亦即在其實際表現上,也就是說,人的本質從這里表現出來,從社會關系的總和里面表現出來。那么,所謂社會關系的總和或社會性,首先說,是一個形式,提綱第七條也明確指出來了:抽象個人屬于社會形式。其次是說,是一種現象,表現出本質的現象,當然這是社會有機整體的復雜現象。費爾巴哈不理解這種意義的現象,只看到單個的人及其抽象的愛等等機械相加的現象。馬克思批評了費爾巴哈,也為我們指出了歸結人的本質的社會化方法;或者說,通過社會關系的總和,才是尋找人的本質的途徑;還可以說,人的社會性也是人借以實現自己本質的手段。
可見,所謂社會關系的總和或社會性,是形式,是現象,是方法,是途徑,是手段,什么都是,惟獨不是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什么?還有待繼續探求,這個問題不會那么簡單。在提綱里,馬克思對此并未提供任何現成的答案。但在提綱第八條,馬克思又寫道:“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筆者認為,前一句話,已經為人的本質是什么作了再明確不過的提解,后一句話,對于我們正確回答這一大哲學難題以及其他所有哲學難題也都是一個寶貴的啟示。人的本質從人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之中表現出來,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此,人的本質就在于人的實踐性。這就是提綱的一個鮮明邏輯,這就是我們在人的本質的探討中首先應該得出的一個確切答案。
人的本質在于實踐,實踐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這是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實踐具有社會性的特征,社會性是人的存在的根本屬性,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每一個人與他人互為前提,即每一個人的存在都以他人的存在為前提,每一個人的存在又是他人存在的前提。而這里的每一個個人,在馬克思那里,都是完全平等的,同樣重要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沒有抹殺個體存在,而是給個體的人以一定的地位,而且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的展望中能夠從個體主體的自由度上反觀人類總體的發展達到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才把“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提到了重要地位。
在第一部系統地申說剛剛誕生不久的唯物史觀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他們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的前提,“是一些現實的個人(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現實的人必然也只能以個體的形式出現和存在),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這種唯物史觀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出發”來考察人的發展的。也就說,唯物史觀并不籠統地、抽象地講人的發展,而是把人的發展分為類的發展與個體的發展,并把著眼點放在人的個體發展上。作為歷史,總體、理性高于個體,但作為歷史成果,總體、理性卻必須積淀在個體感性中。
唯物史觀重視“現實的個人”,但這里的個人,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中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個人,而是從事實踐活動的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個人。生產力和社會關系,是社會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面。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人的個體發展呈現出一種“原始的豐富”,但是由于受狹隘的生產能力和狹隘的地域性的社會關系的制約,個人的發展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物質變換的擴大,個人能力和社會關系也日益朝著普遍性和全面性發展的階段;這時,個人雖然擺脫了物的依賴關系而呈現出獨立性,但卻又受到物化——異化社會關系的統治。此外,談到人的個性發展,不能不涉及到階級和階級關系。在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抗社會中,人們之間的關系必然要表現為階級關系,個人不可能超脫階級而獨立地表現自己作為真正人的個性,“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一員處于這種社會關系中”的,也就是說,個人雖然作為個人存在,但卻被他們結成的社會關系抽象化了。因此,以人的個體發展為著眼點的人的發展觀,在考察個人的歷史發展時,不僅不排斥階級與階級、個體與類之間的沖突和對抗,相反地,卻正要以這種沖突和對抗為前提和背景。這種考察表明,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人的個體發展與類的發展不是直接統一的:類的發展既要以個體的犧牲為代價,又為個體的發展創造前提和條件。與人的個體發展受階級地位局限和制約相適應的,是整個人類能力的發展與個體發展之間的劇烈沖突和對抗。小生產者的浪漫主義觀點,不理解類與個體發展間對抗和沖突的歷史內容,因而把生產力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同個人對立起來,幻想用犧牲生產力和社會文明發展的辦法來換取個人的福利。這實際上是主張:“為了保證個人的福利,全人類的發展應該受到阻礙”。資產階級以及歷史上的一切統治階級,則企圖把他們進行統治的社會形式說成是為了整個人類的需要而實行的唯一合理的形式,以便永遠維持剝削和壓迫。只有馬克思才既揭示了這種對抗和沖突的必然性、進步性,又揭示了它的歷史性、暫時性,從而堅信:“人”類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人的發展相一致。而這種同個人發展相一致的,即“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的社會,正是馬克思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總之,在馬克思看來,在資產階級社會“告終”以前的“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人們的社會歷史雖然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但由于個人或隸屬于群體,或隸屬于階級,作為階級的成員而存在,所以,不但對于被統治階級來說,而且對于統治階級來說,個人的自由和發展都是有限的,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作為真正個體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才能成為現實。因為“共產主義所建立的制度,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基礎,它排除一切不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的東西”。到那時候,就可以把個人從階級的符號、生產的工具、科技的附庸或供買賣的勞動力中解放出來。這雖然仍是遙遠的事情,但今天應為此遠景而展望、而奮斗。
三、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價值觀建設的啟示
長期以來,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時,奉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現代社會面臨許多的挑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肯定與我們長期以來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處理不當,對集體主義的理解有偏差有關。集體主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對于個人來說,應努力地為社會,為集體做貢獻;對于集體來說,應努力為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提供條件。而我們片面強調一個方面的做法,大大削弱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威信。而馬克思恰恰是從人出發來設定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對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加以理解,以充分發揮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優勢。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