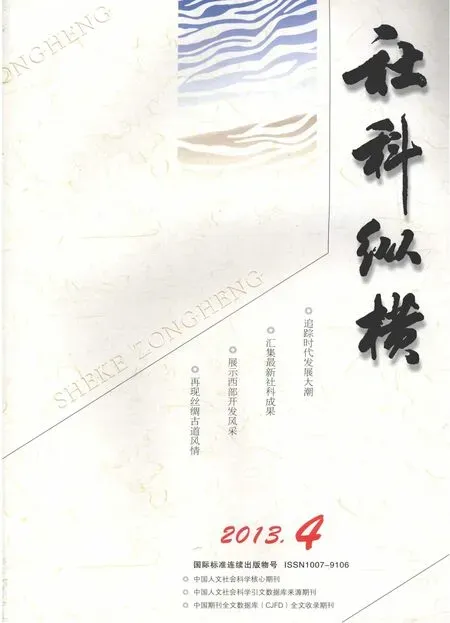論法人權利能力的限制
宗 寧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 重慶 401120)
任何權利都有限度,法人權利能力也不例外。國家對法人權利能力的限制體現了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這個過程伴隨著民法基本觀念的轉變,即私法自治的絕對性向相對性的轉變過程。首先,私法自治原則是現代民法的基本原則,其保障了民事主體在進行民事活動的過程中,不受國家和他人非法干預的意志自由。其次,私法自治是相對的。世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絕對無限制的自由。正如蘇永欽所言:“國家在私法關系的形成到消滅過程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旁觀者。”[1]
一、法人權利能力的性質限制
法人權利能力的性質限制主要體現在法人性質的特殊上,即其與自然人不同,法人是團體,而自然人是具有生命力的個體。因此法人與自然人的差異導致了法人不可能享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天然性”權利和義務,具體說來:
就財產權來說,法人不享有自然人基于特殊身份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比如自然人之撫養請求權。
就人格權而言,與自然人息息相關的,如生命權、健康權、肖像權等,法人皆不具備。較為特殊的是法人人格權,如鄭永寬所言:“法人人格權否定論者那種將法人人格權作為財產權來對待在法律技術上是不具有妥當性的,因為此時對自然人的權利保護具有不周延性。”[2]
二、法人權利能力的法律限制
法人的權利能力授之于法律,法律考慮到某些情形,有必要對法人活動做出控制,自得以法律限制法人的權利能力[3](P131)。這就是法律對權利能力的限制。但涉及兩個傳統的法律理念:自由與秩序。法律盡量不干涉經濟主體的經營活動,他們能按照其意志開展經濟活動。若法律干預的過多,自然影響經濟主體活力,抑制法人的自由性而扼殺其積極性。但法律又必須對經濟進行限制,否則經濟主體將陷入無序狀態,最終影響法律秩序運行。
(一)現行公司法①對轉投資的限制
現行公司法改變了舊公司法對公司轉投資諸多方面的限制,反映了現行公司法注重公司自治、股東自治,符合了風險和利益一致的原則。但現行公司法并非完全放開轉投資相關制度,在某些方面仍有限制。
針對轉投資問題,學界曾有激烈的爭論,轉投資的利弊都很明顯。就利而言:第一,轉投資可增加資本效率,擴大利潤來源,并可形成關聯公司、公司集團,利于公司規模化經營和快速發展。第二,投資本身是公司內部經營業務的范疇,應由公司自主決定,這也是充分尊重公司經營自主權,順應現代商法“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就弊而言:第一,公司的轉投資行為實質上是將股東的投資進行轉投資,直接影響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違背股東對公司投資的目的,增加了股東的投資風險。第二,轉投資會降低公司實際控制的經濟資源,降低公司償債能力,增加債權人風險,與資本維持原則相悖。第三,轉投資數額在母子公司之間均計入公司資產,社會資源總量不變,而導致資本虛增現象,使得債權人錯估公司的償債能力。
現行公司法15條規定,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除對自己所投資企業之外,公司可以向其他企業投資。該規定改變了舊公司法12條的限制,有學者認為,這是法律解除了公司對外投資的限制,但筆者不這么認為,解讀此條款不難看出:
第一,必須承認現行公司法規定,公司可以轉投資。但不能因此斷定現行公司法對公司轉投資就沒有任何限制。
第二,公司不得成為對所投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爭論點在,公司能不能對子公司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筆者認為,按照語義解釋,“投資企業”包括其子公司。因此,公司不得向其子公司債務提供連帶保證,這也體現了公司法對法人權利能力的一種限制。
第三,法律另有規定的含義。現行公司法第15條中間“除法律另有規定之外”,如《合伙企業法》第3條規定,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社會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這些企業組織不能成為普通合伙人。目的在國有企業的保值、增值,及上市公司整個投資人利益,但這些公司仍然可以成為有限合伙人。可以看出,公司法對轉投資的限制轉移到其他配套法律的規定之中,從而完善了對轉投資的法律規制。
(二)現行公司法對法人擔保的限制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并未在法律中予以規定對于法人擔保的限制,僅臺灣地區《公司法》第16條規定:“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4]
我國《公司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該條第2款規定:“公司為公司的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根據此法律規定,公司可以據此為他人提供擔保。此擔保的對象可以是本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也可以是本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以外的其他合法主體。
但與此同時,立法者對公司擔保也作出了限制。其原因是,立法者必須在公司擔保制度中對禁止和放任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既要放寬公司對外擔保的限制,以符合交易習慣和適應市場要求,又要考慮到公司對外擔保可能產生的風險,減少因公司的對外擔保行為可能給公司、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造成損害[5]。具體而言,公司法對公司擔保行為的制約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對于主體的限制。公司應當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為本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以外的主體提供擔保,程序由董事會、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通過。為本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董事會無權決議。
第二,利害關系股東表決權的限制。為保護公司、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3款規定,公司表決為本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事項,該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表決。
第三,對于擔保數額的限制。現行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規定數額,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不得改變,這是從數額方面對擔保的限制。
三、法人權利能力的目的限制
法人的存在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就如前所述,法人之所以為團體,是因為他們具備了共同的意志,而非人的一般群體性組合,各國民法無一例外規定法人目的,如在法人章程中必須就其目的進行公示。下面就以法人目的為重點論述法人權利能力的限制問題。
(一)兩大法系之比較
德國曾經有學說認為,法人與自然人的權利能力應當是有限制的平等。因為法人畢竟不像自然人是“無特定目的的存在體”,法人仍用于追尋章程所規定的目的[3](P111)。根據此學說,法人之主體資格僅限于目的范圍之內。超越目的范圍的活動則法人不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該法律責任由行為人承擔。德國法經過整體思考,從交易安全出發,規定了這樣的處理方式:法人的所有行為,不論目的范圍,對外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關系及其后果;同時,對于法人內部部門與機關的責任,通過逾權規則,違反準委任關系的方式予以處理[6]。日本學界在明治維新時期,普遍贊成法人權利能力受目的事業限制的觀點。此觀點在第三人的信賴利益的考量下,態度有所緩和認為應當對法人權利能力的事業限制進行從寬解釋。至日本大正15年,法人權利能力的目的范圍在判例上已作消極解釋,認為法人在不背于章程或捐助行為所定目的范圍內有無限制之能力,由此,“實際上目的限制對對外交易關系來說已喪失其機能”[7]。
法人權利能力受目的事業范圍的限制,在英美法被稱為越權原則(doctrine of ultra vires)。1985年公司法根據這一原則的應用而規定,公司行為包括公司內部的越權行為,不能因此而向外對抗善意第三人。而1989年公司法則進一步廢除了越權原則的適用,這種限制僅為公司內部限制對相對人而言已無任何意義[8]。
(二)目的限制之思考
產生于資本主義萌生階段的權利能力目的限制說,其目的在于維護資本的所有權和資本主義市場運行秩序。權利能力目的限制的理論基礎是:首先,確定了法人章程之登記公示的公信力,善意第三人不可適用于目的外行為;第二,目的范圍為出資者的意志,法人進行任何活動不可逾越此范圍;第三,法人章程經國家法定機構核準登記,因此也體現了國家對法人活動范圍的許可與認定[9]。
伴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上述三個基礎已經喪失了合理性。首先,雖然法人章程規定了法人的范圍,但是去查閱公司章程者少之又少。在我國大陸更是如此,公司章程作為公司成立的必備要件之一要進行審查,而大多數公司為了省時省事都是照搬公司法的相關規定,這使本應相對“獨特”的公司章程變成了千篇一律的法律條文。因此,期望于法人章程的規定而相對人就能知曉其經營目的的假設是很難成立的。其次,法人的投資者的確是著眼于法人的經營范圍,而這個時空點只限于投資以前,當投資之后股東更加關心的是企業的盈利問題,至于是否按照目的范圍去經營倒是其次的事情了。最后,特許主義和許可主義已經被準則主義所取代,成為市場準入的首選準則。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起者可以自由選擇法人的經營范圍。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法人權利能力目的限制的法理基礎已經發生改變,現在的法律制度要符合當今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司法實務界長期以來堅持凡超出法人目的范圍所實施的行為一律無效,這種做法弊端明顯,不符合當今的社會發展。筆者認為,我國應該確立行為能力限制說,亦即法人的目的限制只是針對它的行為能力而言,超出此范圍的經營活動應該認定無效,但是法人可以通過法定程序變更其目的而使該行為變成有效行為。
注釋:
①本文將2006年修訂的《公司法》稱為現行公司法,將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稱為舊公司法。
[1]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J].中外法學,2001(1):92.
[2]鄭永寬.法人人格權否定論[J].現代法學,2005(3):76.
[3]黃立.民法總則[M].臺北:三民書局,1994.
[4]王文杰.兩岸公司法中對于公司權利能力的比較[A].民商法縱論——江平教授七十華誕祝賀文集[C].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635.
[5]蔡鍛煉.公司對外擔保的自由與限制——兼評新《公司法》公司對外擔保的規定[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6(3):137.
[6]龍衛球.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390.
[7]田村淳之輔.公社法讀本[D].轉引自鄧曉霞.法人權利能力范圍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02年碩士論文,第27頁.
[8]許明月.“企業法人目的范圍外行為研究”[C].民商法論從(第6卷),第158頁.
[9]張俊浩.民法學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