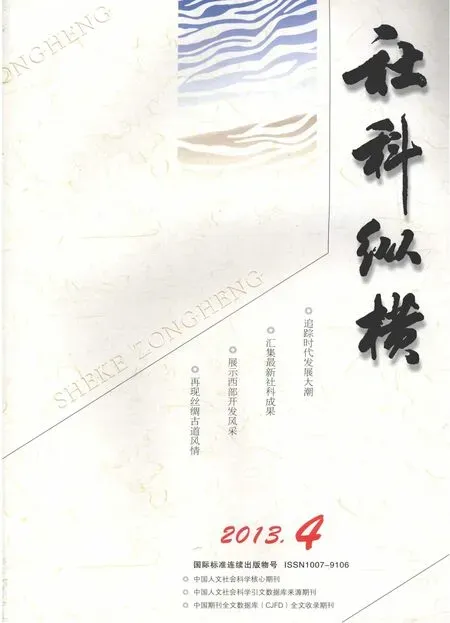從 GDP、CPI說起——論全球化背景下的漢民族語言保護
曹 寧 張志華
(隴東學院外國語學院 甘肅 慶陽 745000)
一、引言
語言是維系一個民族的文化紐帶和精神支柱,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尊嚴,是一個民族最后的遺產,它記載著這個民族物質的和精神的歷史,對于培養其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結和發揚民族文化有著極強的凝聚作用[1]。隨著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面貌徹底改變,全球化的到來也直接沖擊著民族語言的生存和發展,使得很多國家的語言面臨被滅絕的境況。
二、GDP、CPI頻繁出現的背后動因
如今,打開電視,GDP(國內生產總值)、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表述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新聞報道中。翻開報紙,閱讀書籍、瀏覽網頁,漢語篇章中不時地會冒出幾個英文字符。日常談話隨口夾雜英文的例子更是枚不勝舉,“APEC的記者招待會后,我約了幾個CCTV的朋友和一群MBA、MPA的研究生,討論中國加入WTO后的IT業前景,以及IT業對GDP的影響”。短短三十幾個漢字中,竟有二十多個英文字母。不僅如此,去飯館吃飯要冰鎮啤酒說“要涼beer”,把辦公室一種復印紙叫做“A4paper”,似乎只有這樣表述才顯得自己有文化、很新潮。
而時下“中英混說”的現象在中小學生中也已漸成氣候。下課后兩個穿著中學校服的女生隨口問道:“今天中午想吃什么?”“你有什么好的idea嗎?”聽著她們這番對話,有人感到迷惑,于是上前詢問。其中一個女生說:“這種中英文摻雜在一起的說話方式很好玩,同學們都這樣說”,而另一名女生則表示,這種“中英混說”在網絡中經常用到,尤其是網聊的時候。不僅如此,“有事兒你就say啊”、“晚上記得call我”等也是常被學生們掛在嘴邊的潮語、潮句。
那么這種漢語中夾雜著英文的表達方式為什么會在電視、報紙、影視、書籍和日常生活中頻頻出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呢?究其原因,主要不外乎以下幾種:
第一,凸顯中國與世界接軌。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全球各個國家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這已成為共識。然而,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是英語全球化,英語作為國際性語言[2]的地位已經確立。面對這種趨勢,部分人士認為,要拉近中國跟世界的距離,讓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只好大量使用外來詞,以西方人易于理解的方式傳播中國語言文化,才能實現與世界接軌。
第二,個人媚外心理作祟。在互聯網時代,語言之間的相互交流越來越頻繁,彼此之間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由于網絡傳播信息的門檻較低,青少年在網絡媒體中就有可能很方便地接觸到各種外來詞語。于是,一些英文單詞就被賦予特殊的含義,廣泛應用于微博、聊天,日常對話中,這些英文單詞也頻頻出現,形成了“中英混說”現象。如今,日常談話仿佛只有夾雜幾個英文單詞,才夠時尚,才有炫耀的資本,否則就“out”(太過老土)了。
第三,語言經濟原則的作用。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經濟原則[3]。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傾向于盡可能地用最少的精力做最多的事情。于是在日常生活中,語言交流也力求簡潔方便,用最少的詞來表達最充分、最豐富的意思。漢語中GDP、CPI等外來縮略詞的廣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追求語言經濟原則的一種體現。
三、全球化形勢下民族語言的生存危機
然而語言表達中的這種中英混雜現象決不能被當成一種社會現象而聽憑其任意滋生蔓延。實際上,經濟全球化在促進世界上不同國家經濟交往和發展的同時,也直接沖擊著這些國家民族語言的生存和發展[4],不少民族語言即使大語種也面臨著語言文化安全危機。
早在2000年,聯合國就已確認,英語已經成為世界185個聯合國成員國中60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還有一些國家把其作為半官方或通用語言[5]。而據《劍橋語言百科全書》[6]所載數據,在全球五大洲,英語或占優勢,或得到充分的確認,書籍、報紙、機場與空中交通管理、國際商業會議與學術會議、科學技術、醫學、外交、體育、國際比賽、流行音樂、廣告宣傳等均以英語為主要語言。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科學家用英文寫作,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郵件用英文書寫。在全世界所有電子存儲系統的資料中,80%是英文,120個國家大約1.5億人收聽英語無線廣播節目。英語儼然已經成為主導世界的霸權語言。
然而與此同時,其他民族語言的生存現狀則令人擔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9年2月19日“世界母語日”前夕推出了新版世界瀕危語言圖譜的電子版[7],其所呈現的世界上2500多種瀕危語言的最新信息再次引發人們對瀕危語言的關注。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大約有80種語言消失,數千種語言處于消亡的邊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約有2000種語言,在未來的幾百年內,其中至少10%的語言將會消失。新版圖譜將全球瀕危語言按照危險程度的不同分為不安全到滅絕5個等級。其數據表明,在目前存世的6000種語言中,607種不安全,632種危險,502種非常危險,538種情況危急,200多種語言將在最近三代人的時間內滅絕。
四、全球化形勢下漢語言所面臨的生存危機
如今,英語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大大超出了所有與之競爭的語言如法語、阿拉伯語等,這使得許多國家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民族語言,而另一些國家正面臨著民族語言消亡的危機[8]。漢語作為我國的民族語言,盡管有著多達13多億的使用者,然而,面對經濟全球化洶涌而至的英語全球化,作為華夏子孫精神家園的漢語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
(一)漢語文字面臨被褻瀆的危機
語言文字的純潔性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該民族身份的純潔性,它容不得任何被玷污、被褻瀆的行為。然而,在當前全球化浪潮中,語言神圣的純潔性卻面臨著被玷污的危險,而且這種玷污語言純潔性的行為有愈演愈烈之勢。
西方外來縮略詞直接楔入漢語,GDP、CPI等直接在漢語行文中出現已經成為一種慣常現象。而一些科技新詞如DVD、MP3等詞的大量引入,更使漢語常常像一種“四不像”的文字。這些中文中的外來詞既不音譯,也不解釋,更不翻譯,而是直接嵌入,這種做法極不嚴肅,也極不規范,它嚴重影響了漢語的規范性與純潔性。
而媒體對這種褻瀆母語純潔性的行為卻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些媒體甚至公開用漢英混雜的形式做標題,比如,《上海加入Live8》、《MG:My生活的GENE》、《從哪款AOC賣到了VDP》。如果不是英語專業人員,要讀懂這些標題恐怕很難。大眾媒體是國家形象的窗口,是其他國家了解中國的平臺,同時對國內民眾有著極大的輿論導向作用。然而,中國媒體的這種“半中半洋”的做法無疑對漢字的純潔性造成了極大的玷污。
任何一種成熟的語言,都具有一定的規范性、穩定性和純潔性。這是一種文化得以延續的基礎。現代人之所以還能夠讀懂兩千多年前的著作,主要原因在于語言的規范、穩定和純潔。如果任意地去“改造”甚至“惡搞”母語,將會給自身以及后人制造無窮的麻煩。
誠然,中英文混雜的現象日益嚴重固然與世界開放格局下全民學英語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時下出現的中英文過度混雜現象已經到了中國人必須先學會英語才能看懂漢語的程度。長此以往,這種“中不中,洋不洋”的表達勢必造成語言運用乃至思維能力的混亂與漸退。面對此情此景,保護漢語語言文字純潔性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二)母語地位危機
母語地位的下降是母語危機的標志,無論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及母語的學習現狀上還是在科技應用、文化內涵和傳承上,母語地位危機都已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文津講壇”上,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對漢語的現狀表示擔憂,他在2005年題為“漢字的再認識”的講座中[9]指出,在校大學生沒有英文字典的很少,有些人甚至有幾本英文字典,然而有漢語字典的卻屈指可數。由于不重視母語,年輕人的漢語水平令人擔憂。任繼愈先生認為漢語的危機不在外國而在中國,不在別人而在自己。漢語的危機,已不僅僅是表層上外來語和網絡語符的大舉進入,對母語的輕率褻玩的態度才最使人深切憂慮。
母語地位下降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教育。教育危機,是母語的基礎危機,也是危害最大、最久遠的危機,是一切危機的源頭。而國家職業資格證考試、技術職稱晉升的評定標準中很少見到關于漢語使用水平的規定,由此造成了漢語的社會地位下降。如果漢語不能用于社會、學校、只能退到家庭里,那漢語離消亡也就不遠了。
漢語行文中英文字母的植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種無形的自卑思想和媚外思想的植入。漢語的真正危機是精神上的,失去了高貴和尊嚴。如果對自己民族語言失去了最起碼的尊重和敬畏,讓它變成可隨意揉捏的軟泥,人人得而褻之,那這種語言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
(三)漢語教育空間被擠兌
教育是一種戰略性投資,它著眼于未來,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素質的提高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英語作為國際語言,已經在中國的教育產業中占據半壁江山。據數據[10]顯示,英語教育已經成為中國一大市場,年產值高達數百億元,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更有大量的金錢流入英美澳等英語國家,以至于英國人自豪地說“只要出口英語,便足以保持對華貿易平衡”。
由于受到英語全球化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國內形成了重英語的傾向,普及英語的浪潮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已有近4億人在學英語,超過英美兩國人口總數,占了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教育市場上,漢語的生存空間則嚴重被擠兌。每當進入書店的時候,首先進入眼簾的是各種各樣的英語輔導教材,這些教材前人山人海。而漢語書籍則在不起眼的地方沉睡著,無人問津。
(四)漢語網絡話語權嚴重缺失
網絡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影響著人類生活,人類已經進入了網絡時代。根據《第十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11]顯示,中國內地網民總人數已達1.37億,網民平均每周上網16.5小時,國家頂級域名CN注冊量也首次突破百萬。盡管如此,由于英語的超強勢地位,它在科技和網絡等方面仍占有全球80%的使用率和占有率,其網絡話語權仍占絕對優勢。相比之下,漢語網絡話語權就顯得有點勢單力薄。
當今時代是信息化的時代,用信息技術帶動經濟發展,語言文字負載了80%的信息,而英語又占了信息傳遞的60%以上。英語占了這么多的份額,意味著許多國家成了語言負債國。信息化不僅影響虛擬空間中的語言,而且對現實空間語言狀況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誰的語言不能進入網絡,誰就會被淘汰,就有被邊緣化的危機。不能成為網絡語言的語種,其生命力將會逐漸喪失,在網絡上處于劣勢的語種也會逐漸衰落,甚至死亡。因此,能否在互聯網上取得主動權,將決定一個語言的未來。目前英語主導著互聯網,英語信息占據著互聯網信息資源的60%以上,法語信息占5%,而漢語信息尚不足1%。漢語網絡話語權的缺失使得我國語言面臨更加嚴峻的現實。
五、語言保護的巨大意義
語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都認為語言只不過是一種交流思想與情感的工具,把多種語言的存在看成一個問題,認為它造成各民族之間思想交流的困難。然而,正是因為語言的多樣性,才有了文化的多樣性,才使這個世界多姿多彩。
(一)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家園
語言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為重要的記錄者、傳播者和標志牌,它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全面儲存著文化的整體信息,它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語言一代一代往下遺傳,民族的全部文化內涵、精神內涵也緊緊附著在語言之上得以傳承。“語言是民族文化的基座,是民族文化最后的家園”[1]。語言的滅亡意味著文化的滅亡,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
1.語言全息地反映了所屬語言群體的文化
語言和文化之間具有全息的關系,即是說,語言和文化各自作為宇宙中的一個系統,它們相互包含著對方的信息,沒有文化血肉的語言是不存在的[12]。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它還凝結著所屬語言群體的文化,凝結著使用這一語言的群體自身在長期的生存發展過程中對周圍世界和生態環境的特殊認識、積累的生產生活中共同或獨特的認知等。即語言反映特定的社會經濟、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社會形態以及民族關系等文化內涵。
2.語言的存亡關乎一種文化的潰散與持守
使一種文化與它種文化相區隔并使自身得以存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語言的不可共量性[1]。所謂不可共量性即任何兩個文明或者文化之間的隔膜和難于交流,這種難于交流性首先反映出的是差異性,即一種語言有適應于該語言的藝術形式,如漢語的古詩詞和英文詩詞,各有自身的特點。一種文化支持一種語言,一種語言共同體下有一種文化支持。如果一種語言消亡了,那么它所反映的文化也會在不久的將來消亡,而要保持一種文化的存在,保護其語言的存在是前提條件。正如韓少功所說“:與昨日能對上號的,唯有語言,它可以從歷史深處延續而來,成為民族最后的遺產。”[13]
(二)語言是民族認同的載體
一個民族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該民族大多數成員都將該語言作為自己的母語來使用。在本民族內部,該語言即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又是最明顯的民族認同載體。在本民族外,由于語言符號的封閉性,該語言就像一排排籬笆,擋住了本民族與外民族之間的交際,成為區分本民族與外民族的一個標準。這種對內具有民族認同、對外具有民族劃界功能的本族語是該民族最主要的標志。正是因為有了共同的語言,一個民族的身份才得以確認,一個民族的凝聚力才得以加強。語言的衰落和枯竭,意味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命力的衰退,它被粗暴對待以致扭曲變形,就是對一個民族心靈的直接傷害。語言是一個民族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底座。語言的滅亡意味著其民族身份標志的缺失。
六、應對措施
面對外來語的入侵和國內民眾的輕率可能造成的國家語言文化安全危機,我國應以一種積極的心態對待。為了使漢語得到更好的發展和完善,使我們自己民族性的東西不受侵蝕,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增強公眾對母語憂患意識和捍衛意識
要走出語言困境,必須喚起民族的憂患意識,要喚起憂患意識,就必須從自我反省開始。公眾應了解到漢語的危機即文化的危機,文化的危機攸關整個民族的存亡,是關系到每個人的事,它呼喚著每個人的良知與責任心。保衛漢語在更深的意義上,其實是在保衛漢語背后的文化、保衛中華民族。應該對自身文化自覺尊重和愛惜,摒棄對異域文化與新興文化的盲目崇拜,并從中吸取科學化的新思維[14]。
因此,首先應增強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對母語的憂患意識和捍衛意識。青少年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也是中國語言文化的最終傳承者。中華民族在21世紀能不能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能不能得到弘揚并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多元文化中強有力的一員,關鍵在于今天的青少年。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本土精神的延續和傳統文化的繼承主要是通過國民教育體系和媒介宣傳兩大渠道完成的。學校應提高母語教學地位,通過母語教育進一步激發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凝聚力,引導青少年深入理解母語在自我生命中的位置,自覺承擔尊重、敬畏、熱愛、捍衛母語的文化意識和精神責任。新聞媒體、文化藝術等領域,也應在這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應以純潔的漢語形象、漢語思維在繼承中華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吸收外來優秀文化,進一步增加中華文字的魅力。
第二,加強漢語的規范化建設
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不斷進入漢語的外來語,要研究并適時進行規范引導。引進恰當的外來詞可豐富漢語詞庫,但是如果直接把英語文字注入漢語,將會破壞漢語的語言特征,污染漢語的純潔性。漢語言文字中混入越來越多的英語字母,是漢語言文字被侵蝕的表現,這應當引起我們的嚴重關切。中小學生是規范化語言的學習者,中小學教師應該重視在日常教學中規范地使用漢語,并指導學生規范使用。從長遠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應該明確立法規范漢語中外來詞語的使用。
第三,加強漢語信息化建設
面對信息化的挑戰,漢語信息化的程度明顯不夠。漢語最終要強大要走向世界,就必須加強漢語信息化建設。
在當今世界,信息是一種戰略資源,對于以信息接受為主的非英語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網絡的互聯有可能造成對本國語言文化的沖擊,本國的信息資源得不到很好的保護,信息自主權就會受到危害。發展自己的信息產業是保護民族語言文化的根本,在參與全球信息共享的同時,我們要積極生產自己的文獻數據庫,向國外推介反映民族語言文化的數據庫。在信息政策上,必須強調信息自主,確認獨立的國家主權和語言文化主權。堅持信息事業的自主權,并通過法律保護信息安全和信息活動中涉及到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在語言信息活動中贏得總體的利益,以防被動,求得漢語在網絡空間上的話語權。
第四,實施“走出去”戰略,完善語言推廣
“以攻為守”不僅適用于軍事方面,在民族語言保護方面也同樣有用。語言的國際化是國家軟實力強大的一個重要標志,更是保護本民族語言的絕佳手段。早在1999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提出倡議,語言是保護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母語傳播運動,不僅有助于語言多樣性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夠提高對全世界各種語言和文化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進世界人民的團結。
為適應未來教育、文化發展和人才戰略的實施以及推動中國在世界上的和平發展,我國應抓住全球化帶來的契機,以語言為載體向全世界推廣我國文化,增進中國與世界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建立文明多元化的世界。制定符合國際形勢變化的漢語推廣戰略,把漢語作為和平崛起的軟實力的重要輸出品,努力推廣其在國際組織和會議中成為工作語言,利用“世界貿易博覽會”、“國際漢語周”、“中華文化展”以及“中國文化周”等活動,營造經貿、旅游、留學、外交等領域漢語需求的氛圍。繼續發展孔子學院,促進漢語盡快走向世界,使我國成為語言強國,保證語言文化的安全狀態。生產商要在產品上使用漢字,讓漢語伴隨著優良的“中國制造”走出國門。學者們在科學研究和國際交流中要盡力爭取漢語的國際話語權。
七、結語
全球化和人類生活信息化為各國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同時也使人類社會顯出脆弱的一面。各民族語言在全球化和外國強勢語的逼迫下困境重重,甚至處于瀕危狀態[15]。語言的喪失會帶來文化的失落[16],造成民族身份認同的缺失。經濟全球化是不得不乘坐的大船,但是本民族語言決不允許被大浪吞沒,更不能為了追求暫時的經濟利益而將本民族語言拋棄。全球化與民族語言的多樣性應得到統一協調發展,要在全球化形勢下推進語言的平等和多樣化,這是促進和實現漢語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1]錢冠連.語言,人類最后的家園[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5.
[2]Crystal,D.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Martinet,A.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M].0xford:Clarendon Press,1962.
[4]Cheshire,J.English around the World: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5]Nettle,D.&S.Romaine.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M].0xford:0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克里斯特爾,劍橋語言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530.
[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版世界瀕危語言圖譜[EB/OL].(2009.2.19)http://www.unesco.org/culture/fr/endangeredlanguages.
[8]Singh,M.&J.Han.Global English:the Loss of Language Communities and Their Knowledge[J].Australian Mosaic,2006(10):34—36.
[9]任繼愈.漢字再認識[N].人民日報,2005-12-12(11).
[10]教育部.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237/201 001/76011.html.
[11]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十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07-1-23.
[12]韓少功.世界[J].花城,1994,6:36.
[13]錢冠連.信息全息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4]陸谷孫.留住我們的精神線索[A].余墨集[C].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138.
[15]徐世璇,廖喬婧.瀕危語言問題研究綜述[J].當代語言學,2003(2):12-15.
[16]趙樹理.英語全球化背景下弱勢民族語言的喪失與保護[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9(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