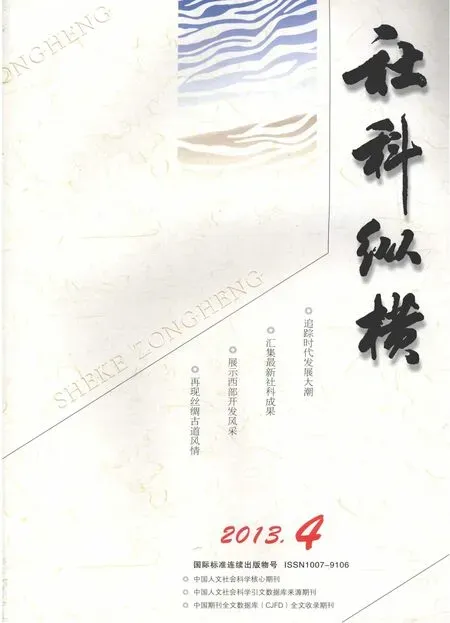試論中國俠文化對初盛唐詩歌創作的影響
李小茜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天津 300191)
一、中國俠文化探源及其發展歷程概述
“俠”一詞來源于先秦時期的士階層,可視為“是從脫序的士人中演變過來的”[1]。“‘士’是古代貴族階級中最低的一個集團,而此集團中之最低的一層則與庶人相銜接”,“(士)適處于貴族與庶人之間,是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當社會階級出現流動時,即“上層貴族的下降和下層庶民的上升”[2](P9-12),士的人數便也隨之大量增加。原本處于貴族階層最底層的士階層有相當數量的食田,接受過一定教育,大多在社會中有固定的職務。但至春秋后期,諸侯爭霸,王室衰微,造成了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士失其位局面的出現。“社會的急劇轉型帶來的社會成員的結構性變動,一下子把他們拋散向社會的各個角落,許多士再無田可食,也無原職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識和還可以一用的勇力”[3]。這些失職的士人逐漸發生了角色轉換,正如顧頡剛先生在《武士與文士之轉換》一文中所言,戰國時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復不少,彼輩自成一集團,不與文士混。以兩集團之對立而新名詞出焉,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2](P8)文中所言雖大體可信,但單純將“士”分為文、武似乎不妥。大體可應分為尚文、好武與文武兼備三種。而俠無疑是出于后兩者。“‘俠’的名稱的出現,標志著武俠階層已徹底從‘士’階層中脫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從此,‘士’便成為古代社會文人的代稱了。”[4]而在先秦時期俠的名稱出現以前,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俠”的英姿已活躍于歷史舞臺之上,如劍劫齊侯的曹沫、卻秦救趙的魯仲連、李白《俠客行》中所歌頌的“煊赫大梁城”的二壯士侯嬴與朱亥等等,他們的俠義行為千古流傳,成為了后世英豪與文人崇拜歌頌的楷模。正是以上的古俠們所產生的影響引起了人們的推崇,于是“俠”之名稱也應時而生。
“俠”之稱謂最早見于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五蠹》篇中:“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5]文中“俠”與“私劍”并稱,“帶劍者”的特征為“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很明顯,這是韓非從法家的立場出發對俠的否定與攻擊。
西漢的司馬遷始真正為俠正名。漢代俠風大盛,雖經文、景、武三代的明摧與暗鋤,但數量仍有增無減,且紛紛復出。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談到: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衿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文中已將“俠”的基本特征較為細致地勾勒出來,且贊譽之情已然顯現。漢之后,俠的身影遂不見于史傳,但詠俠詩卻已出現。
漢魏六朝時期,“俠”走出史傳文學的天地而出現在詩歌領域之中。漢代詠俠詩共有十首,且大多為殘篇和歌謠,魏晉六朝的詠俠詩共有五十余首。其中曹植的名篇《白馬篇》堪稱開詠俠詩一代之風尚。其后的唐代,俠義之風遠盛于其前后各朝。俠文化發展至唐已有著不同于以往的新內容。曹植雖曾在其詩歌中贊揚游俠“捐軀赴國難,誓死忽如歸”之舉,但俠第一次真正與報國和建功立業緊密結合在一處卻是始于唐代。報國和建功立業思想得到了空前強化。且“義”的觀念也滲透于其間,誠如李德裕在《豪俠論》中所談及:“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以諾許人,必以節氣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6]。這種對于俠義精神的強調和論述都是迥異于前代的。正因如此,在唐代的詠俠詩作中,詩人們著力歌詠的更多是俠義精神而不是俠客。
所以,詠俠詩的真正繁榮也始于唐代。唐代俠風彌漫,席卷朝野,詩篇疊出,氣蕩文壇,真正完成了由史傳文學向文人歌詠的順利過渡。其繁榮堪稱空前絕后,而最能體現唐代詠俠詩特色的無疑為處于國力迅速攀升及至鼎盛的初盛唐時期的詠俠詩創作。
二、俠義精神對初盛唐詩歌創作的總體影響
初盛唐時期的任俠精神、任俠風氣同文人的詩歌審美理想與創作實踐之間存有較為密切的關聯。任俠風氣中體現著較為一致的任俠精神,可概括為慷慨意氣、建功立業與享受人生。這種具有普遍社會價值與審美意義的任俠精神,經由一些富于俠氣的文人大力倡導,成為了初盛唐詩歌創作中的生動意象。誠如鐘元凱先生指出:“唐詩中的任俠精神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它隨著唐詩高潮的到來而擴展為詩壇上普遍的風氣。詩人們對游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對生活中俠義精神的開拓和贊美,表現了這個時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它顯然并非儒、道、釋這些意識形態所盡能規范的,這無疑構成了唐詩思想內容和美學風格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7]當然,我們視任俠精神為初盛唐詩歌的審美內容與生動意象并不是要排斥初盛唐的山水田園詩所具有的淡雅明凈的意境美。同時,中晚唐俠風不絕,詩歌創作中也不乏任俠精神,只是任俠風尚與時代精神變化了,文人們的興致并不在于抒發豪氣,而是關注離奇的故事。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初盛唐時期的邊塞和詠俠之作最能體現唐人的審美理想和時代任俠精神。
在初盛唐時期的社會意識變更中,任俠風氣對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人格理想滲透頗多,同時也具有文學史價值。而唐人任俠,在初盛唐表現出的氣質精神又與現實的需要和自我理想的社會角色選擇有著緊密聯系,故表現出將俠的形象和氣質精神更有效地與自身的人生理想、社會選擇相結合,任俠精神多與自身的需要相統一,或與改造人生的社會理想相一致。這種文化背景為初盛唐詩人的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文學審美理想打上了烙印,并進而影響了詩歌的創作。
從詩人角度關照,初盛唐時期的任俠風氣對于詩歌創作的影響,在貞觀詩壇,主要是以魏征和虞世南為代表的太宗君臣;在貞觀后期到龍朔前后,主要是以四杰與陳子昂為代表主張興寄風骨的一批詩人;在盛唐時期主要表現為以王維、高適、李白、岑參、王昌齡為代表的一批詩人。而初盛唐時期的這些代表詩人,或有從軍出塞征戰的經歷,或有任俠使氣之行為。
從詩歌創作來看,雖然俠風并沒有對詩人的所有題材創作都產生影響,但在整體上,他們的詩歌創作卻集中體現了初盛唐這一歷史時期任俠風尚的審美意識和文化心理。初唐的貞觀詩壇,主要是詩人通過邊塞、軍旅或擬古擬意的詠俠詩來抒懷言志。從四杰到子昂,除擬古擬意的邊塞、詠俠詩之外,在詠史懷古、送人贈別的詩歌中,也借俠或俠義精神抒發遠大的理想抱負和懷才不遇的時代憤懣。盛唐時期以李白為代表的詩人,詠史、懷古、贈別之作居多,且除古題樂府之外,還新創了許多變體,邊塞詩與詠俠詩創作表現出深厚的現實內容。
從唐詩發展的進程來考察任俠風氣對初盛唐時期詩歌創作的影響,可以發現以下特點:一為初唐俠風對于詩壇的影響表現為對質樸剛健詩風的追求和以俠與俠義精神為基調,以軍旅、邊塞、詠俠為主題的詩歌創作。二為盛唐俠風的高朗自由和理想色彩,導致了自由抒發個人感情、理想追求和體現民族精神、歌頌英雄主義的詩篇大量涌現。
三、初唐時期的詠俠詩創作
初唐貞觀時期的詩歌創作主體是唐太宗及其群臣,創作以尚氣節言武功見多,其基本主題是借軍旅、邊塞和游俠言志述懷。如虞世南《從軍行》為邊塞時事與俠義精神的互動,魏征《述懷》由時事入手進而述懷,借俠客來高揚己志。而直接通過對俠的描寫來言志也為貞觀詩壇的共同創作傾向。其中較有代表性者為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孔紹安《結客少年場行》和陳子良《游俠篇》等。這些詩多為擬古或擬意的古題樂府。如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橫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沉明月弦,金絡浮云轡。吹簫入吳市,擊筑游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焰焰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龍沙暗,木落雁門秋。輕生殉知己,非是為身謀。
借歌詠戰國時期的韓魏游俠,凸顯漸離與荊柯,以邊塞為背景抒發自己的有諾必誠和“輕生徇知己”的俠義氣節,該詩可視為俠義精神與邊塞時事的結合之作。
四杰執著的功名追求、無畏的犧牲精神和效命意識使俠的意象和精神成為他們抒情言志的依托。而才高命蹇的人生經歷也使他們借俠來抒發一己的慷慨意氣和懷才不遇的憤懣,形成了一種共同的創作風格。楊炯在《從軍行》中高呼“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又在《紫騮馬》寫道:“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騮。蛇弓白羽箭,鶴轡赤茸鞦。發跡來南海,長鳴向北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此詩以邊塞為背景,傲物見志,慷慨使氣,借豪俠的襟懷表達自己對于功業的追求。
盧照鄰除表達功業追求外,還注重對俠生命情調的歌詠,透露出知己之思。如《劉生》中有“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之言;《結客少年場行》也談到“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在一些贈答、詠史詠懷的詩歌中,詩人也借游俠來立意抒懷。對俠的歌詠超出了傳統樂府詩的范圍。如《詠史》四首分別歌詠季布、郭解、鄭當時、朱云四位俠士,表達了對俠義人格精神的向往,其一寫道: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為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群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此詩以季布之事連帶出朱家等俠義人物,表達了自己對俠客己諾必誠、重義輕利的人格精神和知己之遇的向往,身世之感頗深。
駱賓王是四杰中最為熱衷歌詠游俠的一位。《舊唐書》本傳稱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詩歌創作中多借俠客形象來送人贈別、言志述懷。如《于易水送人》、《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即為典范。在這類詩中,表現最為強烈的是常借俠客意象或易水寒意象來表達對功名追求的渴望和效命邊塞、死報君恩的壯志。如《詠懷古意上裴侍郎》:
三十二馀罷,鬢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買臣。縱橫愁系越,坎壈倦游秦。出籠窮短翮,委轍涸枯鱗。窮經不沾用,彈鋏欲誰申。天子未驅策,歲月幾沉淪。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一得視邊塞,萬里何苦辛。劍匣胡霜影,弓開漢月輪。金刀動秋色,鐵騎想風塵。為國堅誠款,捐軀忘賤貧。勒功思比憲,決略暗欺陳。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
聞一多先生說駱賓王“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閑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8]這首詩可以說是駱賓王自我心志的表白和形象的寫照。以俠義精神和邊塞作為抒情意象來表達自己的慷慨之氣和捐軀之志,同時流露出屈沉下僚與懷才不遇的悲哀。
陳子昂在“四杰”之后于初唐詩壇上倡導興寄和風骨。他所具有的俠氣不僅使他提倡以“漢魏風骨”重建詩歌理想,而且在他所用的意象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也是具有剛強意氣的豪俠形象。與“四杰”不同的是,陳子昂除有任俠的經歷外還兼有出塞的感受。故作品中多慷慨悲涼與懷才不遇之慨,古樸深沉,風骨剛健。如《田光先生》寫道:“自古皆有死。徇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此詩為《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之三。詩中借田光明己志,抒發自己的身世之感。
又《感遇》之三十四云:“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結發事遠游。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仇。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首未封侯”,詩中主人公即為一少年游俠,后因避仇被征邊地。詩篇在展現邊塞游俠兒的俠行和功勛中,借其戰伐有功卻白首不封的境況來抒發懷才不遇的憤懣。
從“四杰”到陳子昂,一種相同的人生感受便是有為于世的抱負和才高命蹇的命運,所以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多以俠和俠義精神為意象來表達這種人生喟嘆。
四、盛唐時期的詠俠詩創作
盛唐俠風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盛唐時期在詩歌創作中追求風骨的詩人多為具有出塞、任俠的經歷或是有俠氣的文人;二是盛唐邊塞詩和詠俠詩的大量涌現以致形成高潮,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當時邊塞時事和任俠風尚的影響;三是任俠風氣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抒發個人感情、表達理想追求的詠史、懷古、詠懷以及贈別詩的創作。
盛唐俠風遍及士林,一些有任俠或出塞經歷的文人創作也多以邊塞、游俠或任俠精神為依托對象,借以敘事或述懷,表現出濃厚的俠義內容和任俠精神。他們的邊塞、詠俠之作在內容和形式上均表現出了對初唐的超越。而凝重的歷史意識與特定的現實條件鑄就的時代精神和獨特的社會文化心理使盛唐邊塞詩并非局限于邊塞生活和風光的描寫,而是一種詩人借此來抒發昂揚的時代激情、造就雄渾的氣象、禮贊英雄人物的憑藉。同時,“游俠兒”非只是盛唐詠俠詩中的主角,也成為盛唐邊塞詩中的生動形象。在盛唐邊塞與詠俠詩的創作中,代表詩歌審美特征的當推高適、岑參和王昌齡。
《舊唐書》評價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曾出塞從軍的經歷使其邊塞詩創作充滿了效命沙場、建功立業的熱情和俠義精神,表現了蒼涼雄渾的氣象,代表作品如《燕歌行》、《塞下曲》、《塞上》、《送渾將軍出塞》等。《燕歌行》在高適的邊塞詩作堪稱翹楚,通篇表現了“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的英雄氣慨和“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的大無畏精神,成為盛唐風骨的生動寫照。《送渾將軍出塞》中寫道: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登陣常騎大宛馬。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傳有沙場千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畫角三四聲,匣里寶刀晝夜鳴。意氣能甘萬里云,辛勤判作一年行。黃云白草無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塞下應多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從軍借問所從誰,擊劍酣歌當此時。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
這首壯行之作充滿自信意氣,在蒼涼雄闊的景象中贊揚將軍的英風。“城頭畫角三四聲,匣里寶刀晝夜鳴”自然也成為了傳世名句。
岑參五次從戎入幕,其邊塞詩的主要審美傾向是奇麗,但透露出慷慨報國的英雄主義與盛唐時代精神是別無二致的。《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兩詩,一寫行軍迎戰,環境險惡,一寫正面交鋒,嘶殺酷厲。尤其是后一首,征戰的艱苦和報國立功的英雄豪氣溢于言表,詩云: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軍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云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云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此詩將征戰的殘酷、士氣的壯觀、報國的決心與立功的自信表現得淋漓盡致,慷慨悲壯,而俠的功業意識與報恩觀念在這里也轉化為詩人意欲馬革裹尸、萬古留名的慷慨之氣。有七絕圣手之譽的王昌齡的邊塞詩占據了其詩歌創作的較大比例,他的邊塞詩對于邊塞風光和邊塞生活的描寫很少,多是抒發激情,多以七絕為主。如《從軍行七首》和《出塞三首》等。在這些詩中,他常將三軍將士的效命沙場轉化為自我意識的英雄化寫照。
此外,盛唐邊塞詩除表現英雄主義和民族精神外,任俠精神也多有展現,存在著邊塞戰事與任俠風尚的合流、民族精神同俠義精神的互動。這也成為了盛唐邊塞詩的特征之一。在此類創作中,游俠兒成為了主角。正如高適《薊門行》所寫:
幽州多騎封,結發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在這首詩中,沒有出現凄厲的戰爭場面,卻集中筆墨歌頌邊塞游俠兒的英雄風范與其游獵生活。邊氣俠風交相生輝。王昌齡《少年行二首》云:
西陵俠少年,送客短長亭。青槐夾兩路,白馬如流星。聞道羽書急,單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
走馬遠相尋,西樓下夕陰。結交期一劍,留意贈千金。高閣歌聲遠,重門柳色深。夜闌須盡飲,莫負百年心。
兩首詩均為描寫游俠從軍邊塞的征戰生活。其一側重描寫“西陵俠少年”的游俠生活與其義無反顧赴邊救難的俠義精神。第二首突出這位游俠結交重義、走馬飲酒的豪情,雖不乏狂放的任俠氣節,但濃郁的哀愁也可見于其間。崔顥《古游俠呈軍中諸將》和李白《行行且游獵篇》二詩所描寫的卻是生活在邊塞的游俠兒。李白《行行且游獵篇》寫道: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游獵夸輕巧。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蒼迸落連飛削。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下幄復何益。
這首詩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但已脫離其它擬古詩歌的風格。全詩在“胡馬”、“白草”、“沙磧”、“海邊”構成的時空意象的融匯中,集中筆墨塑造了邊城游俠兒“猛氣英風振沙磧”的英雄形象,作者在俠儒對比的感嘆中,表現了盛唐時期重俠輕儒的時代精神。
盛唐詠俠詩潮的形成表現著時代風氣對于詩壇的直接影響。“俠”已成為了盛唐詩歌審美意象和文化精神的象征之一,同詩歌創作具有廣泛的聯系。除在詠俠詩中的直接歌詠,在一些詠史懷古和贈別之詩中也多用俠來抒情言志。如王昌齡《雜興》詩:
握中銅匕首,紛銼楚山鐵。義士頻報仇,殺人不曾缺。可悲燕丹事,終被狼虎滅。一舉無兩全,荊軻遂為血。誠知匹夫勇,何取萬人杰。無道吞諸侯,坐見九州裂。
此詩所詠為荊柯刺秦王之事,但表現出的并非是對這位大俠的歌頌,而是傳達出雖名就而功不成的感嘆和蔑視,抒發了作者強烈的建功立業意識,這是盛唐士人文化心理的表現。《答武陵田太守》詩也寫到:“仗劍行千里,微軀感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直接以信陵君和侯贏事來抒發冀遇知己之情。
李白作為盛唐詩人中詠俠詩作最多詩人,其詠史懷古與贈答送別之作始終不離俠義精神和俠客意象。如《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卻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云。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諾,意氣遙相托。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江猿。
此詩以信陵君竊符救趙之事贈鄭太守,以信陵君喻鄭太守,以侯贏、朱亥、毛遂、薛公等俠士自況,抒發自己的然諾之氣和意欲見用于世的情懷。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到,俠風是初盛唐邊塞詩所表現的主題之一,突出表現為知遇報恩和效命沙場的功業意識與愛國精神。游俠兒的英雄風范為邊塞詩注入了新鮮血液,而作為初盛唐任俠風氣生動寫照的詠俠詩更時直接來源于對俠風的推崇。如果說邊塞詩表現了初盛唐時期的英雄色彩,那么詠俠詩所表現的是無疑就是初盛唐時代精神所獨具的豪放個性。
[1]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M].學苑出版社,1999:72.
[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汪涌豪,陳廣宏.游俠人格[M].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16.
[4]陳山.中國武俠史[M].上海三聯書店,1992:40.
[5]朱東潤.韓非子五蠹[A].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一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2.
[6]李德裕.豪俠論[A].清董浩等編.全唐文[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224.
[7]鐘元凱,唐詩中的任俠精神[J].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4).
[8]聞一多.唐詩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