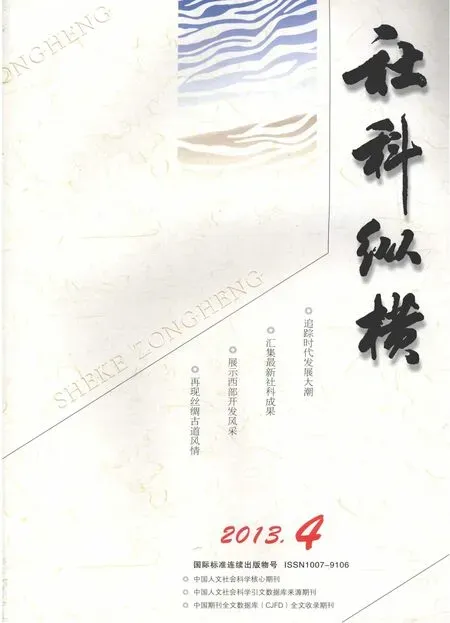由“資治”到“育民”——20世紀(jì)中國(guó)通史教育功能的轉(zhuǎn)變
魏衍華
(平頂山學(xué)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 河南 平頂山 467000)
20世紀(jì)中國(guó)通史家和中國(guó)古代史家一樣,在編纂前都為其著作預(yù)設(shè)了特定讀者群。當(dāng)然,讀者群的確立與史家所面臨、要解決的問題緊密相關(guān)。經(jīng)分析發(fā)現(xiàn),20世紀(jì)史家們?cè)O(shè)定的讀者群與功能曾幾經(jīng)轉(zhuǎn)變,主要有培養(yǎng)新時(shí)期國(guó)民、激發(fā)愛國(guó)心和培育人民等幾個(gè)方面,并構(gòu)成這一時(shí)期中國(guó)通史教育的突出特色。
一、培養(yǎng)國(guó)民的愛國(guó)意識(shí)
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人們潛意識(shí)中惟有“臣民”,“國(guó)民”概念應(yīng)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如章嵚在《中華通史·編手題解》中說:“自民國(guó)完成,從此邦內(nèi)治史諸家,不致蹀躞于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并得養(yǎng)成其社會(huì)觀念、國(guó)家觀念、世界觀念,渙其史識(shí)而擴(kuò)之意焉,矯其史才而又助其正焉;則是《中華通史》者,乃中華民國(guó)之產(chǎn)兒,中華民國(guó)之武,得以斬君史,中華民國(guó)之慈,并得以孕民史,本書之必以‘中華’為標(biāo)題者,尊所出也。然則審史名之肇始,溯新國(guó)之經(jīng)程,代君史而以一振本邦史界之槁腐者,其或在此也哉?”[1](P2-3)此處涉及一個(gè)非常核心的,即如何使國(guó)史編纂的預(yù)設(shè)讀者由傳統(tǒng)帝王將相向普通大眾轉(zhuǎn)變?進(jìn)而用新的國(guó)史培養(yǎng)國(guó)民意識(shí),這是當(dāng)時(shí)史家們說共同面對(duì)的問題。
因中國(guó)人潛意識(shí)中“臣民”觀念根深蒂固,一時(shí)很難改變,多數(shù)史家采取從小學(xué)開始培養(yǎng)“國(guó)民”意識(shí)。當(dāng)時(shí)史家特別重視中小學(xué)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和中國(guó)歷史的解讀。如劉師培在《中國(guó)歷史教科書·凡例》明申,其用意“與舊史稍異”,重點(diǎn)是“歷代政治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huì)進(jìn)化之階級(jí)、學(xué)術(shù)進(jìn)退之大勢(shì)”五端。有學(xué)者說:“劉氏該書不再以帝王為歷史記載的中心,即站在一般人民的立場(chǎng),記述國(guó)家盛衰、生民休戚、學(xué)術(shù)文化等。這種以國(guó)民為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的歷史記述最能說明晚清史學(xué)界在史學(xué)思考方式上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變。”[2]
傅斯年是典型重要代表人物,他說:“我認(rèn)為歷史應(yīng)保存在中小學(xué)中,而其目的,應(yīng)該與自文藝復(fù)興以來的士人教育用意不同,因而作用不同。所有裝飾性的,士流階級(jí)性的,記誦性的,皆不與近代生活相干,所以可以一齊不采。只有三個(gè)意議,我們似應(yīng)當(dāng)充分看重。第一是對(duì)于‘人類’(Mensch heit)及‘人性’(MenschlichKeit)之了解,把歷史知識(shí)當(dāng)作‘人學(xué)’……第二是國(guó)民的訓(xùn)練。把歷史教科做成一種公民教科,借歷史事件做榜樣,啟發(fā)愛國(guó)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前進(jìn)的啟示,公德的要求,建國(guó)的榜樣,借歷史形容比借空話形容切實(shí)動(dòng)聽的多。……第三是文化演進(jìn)之階段,民族形態(tài)之?dāng)⑹觯谥袊?guó)更應(yīng)注重政治,社會(huì),文物三件事相互影響。”[3](P312-313)這代表了當(dāng)時(shí)編纂中國(guó)通史的三個(gè)主要目的:對(duì)人性的了解、訓(xùn)練國(guó)民及了解中國(guó)文化演進(jìn)。
當(dāng)然,在大學(xué)教材中亦有明顯體現(xiàn),以錢穆《國(guó)史大綱》為例,他在《引論》中說:“欲使其國(guó)民對(duì)國(guó)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guó)民對(duì)國(guó)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rèn)識(shí)。欲其國(guó)民對(duì)國(guó)家當(dāng)前有真實(shí)之改進(jìn),必先使其國(guó)民對(duì)國(guó)家以往歷史有真實(shí)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shí),其要在此。”[4](P2-3)錢氏的宗旨是欲通過對(duì)中國(guó)歷史的真切了解而培養(yǎng)愛國(guó)之心,以達(dá)到使國(guó)家“再有向前發(fā)展的希望”的目的。由于以培養(yǎng)國(guó)民為出發(fā)點(diǎn),編纂體例和內(nèi)容自然體現(xiàn)出不同于《史記》、《資治通鑒》等書的特點(diǎn)。通過此類通史著作的刊布,中國(guó)歷史教科書逐漸走出以帝王將相為讀者群的傳統(tǒng)。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各級(jí)各類歷史教科書編纂的目的都是使青年通過中國(guó)歷史的了解,并培養(yǎng)具有愛國(guó)心的“國(guó)民”。
二、激發(fā)民眾的愛國(guó)心
一戰(zhàn)后中外矛盾加劇,特別是中日矛盾激化,亡國(guó)滅種危機(jī)迫在眉睫。為救亡圖存,史家紛紛以史書為武器,激起民眾的愛國(guó)心,以救中國(guó)于水火。具有通識(shí)眼光的學(xué)者紛紛編著中國(guó)通史,如王桐齡的《中國(guó)史》、鄧之誠(chéng)的《中華二千年史》、張蔭麟的《中國(guó)史綱》、呂思勉的《中國(guó)通史》、周谷城的《中國(guó)通史》、陳恭祿的《中國(guó)史》、金毓黻的《中國(guó)史》等。
王桐齡在《序論》中說:“諸君研究中國(guó)史,愿著眼于我邦建國(guó)之體制、歷代學(xué)術(shù)之隆替、武備之張弛、政治之沿革、文明進(jìn)步與退化、實(shí)業(yè)之發(fā)達(dá)與衰退、風(fēng)俗之變遷,與夫偉人賢哲之事跡,以激發(fā)國(guó)民之愛國(guó)心,團(tuán)結(jié)其合群力以與世界列強(qiáng)競(jìng)爭(zhēng)于此大舞臺(tái)上,是則著者之所厚望也。”[5](P1-2)他將中國(guó)六大族為主體的發(fā)展史作為最重要的內(nèi)容敘述,貫穿激發(fā)民眾的愛國(guó)意識(shí)。如鄧之誠(chéng)在《敘錄》中說:“姑以外患論之,二千年來,外患未嘗一日或息,軒黃胄裔危而復(fù)安,弱而能存,滅而再興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來。其艱難經(jīng)歷,非史事何由征之。欲知先民締造之跡,莫如讀史,誠(chéng)欲讀史,莫如注重事實(shí)先編通史。”[6](P2)此處的“群力群策”應(yīng)是編纂通史的出發(fā)點(diǎn),決定著在內(nèi)容編排上首重民族變遷、制度沿革、學(xué)術(shù)淵源及思想變遷等。當(dāng)然,他嘗試以紀(jì)事本末體例記述“世系”,以存“存通之本義”,顯然也是為激發(fā)民眾的愛國(guó)之心,奮起為國(guó)家民族的生存與發(fā)展而抗?fàn)帯?/p>
在歷史知識(shí)的普及上,張蔭麟則邁出可貴的一步,他在《自序一》中說:“在這抱殘守缺的時(shí)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xué)研究的成績(jī),把它們結(jié)集,把它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下,寫出一部新的中國(guó)通史,以供一個(gè)民族在空前大轉(zhuǎn)變時(shí)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yīng)有之事嗎?”[7](P1)他的《中國(guó)史綱》既沒有摻入考證,也不引用或采用前人的敘述,只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使有水井處皆有通史。與此同時(shí),呂思勉在“孤島”完成的《中國(guó)通史》激發(fā)民眾愛國(guó)意識(shí)更為強(qiáng)烈,甚至用“大器晚成”預(yù)祝中國(guó)抗戰(zhàn)的勝利,并充滿信心地說:“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境界,誠(chéng)極沉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者數(shù)萬萬的大族,數(shù)千年的大國(guó)、古國(guó),而沒有前途之理?”最后還用英國(guó)詩(shī)人豪倫的詩(shī)來激勵(lì)讀者,“難道我為奴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隸,今生便了。”[8](P501-507)
當(dāng)然,以考據(jù)見長(zhǎng)的專家也躍躍欲試,如陳寅恪,據(jù)其姻親俞大維回憶,早年的他“曾有志編著通史,惜乎未遂”[9](P12);如顧頡剛,其女顧潮曾回憶說,“縈繞于父親胸中的一項(xiàng)大事業(yè),是編成一部中國(guó)通史”[10](P196);又如傅斯年,盡管曾反對(duì)“史學(xué)疏通”,但在民族危機(jī)時(shí)刻,他卻積極提倡編寫普及知識(shí)性質(zhì)的歷史教科書。在《閑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他激動(dòng)地說:“編歷史教科書,大體上等于修史,才學(xué)識(shí)三難皆在此需用,決不是隨便的事。……遵循原則以選擇史事,盡考索以折衷至當(dāng),正是作教科書者所當(dāng)追步,‘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幸作教科書者留心焉!”[3](P324)可想而知,在當(dāng)時(shí)史家觀念里中國(guó)通史于激發(fā)民眾的愛國(guó)心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在國(guó)難面前,史家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意識(shí)被激發(fā)出來,其著作則成為救亡圖存的重要武器。從某種意義上說,將此時(shí)所著中國(guó)通史稱為激起民眾愛國(guó)心“加速器”,或許并不算為過。
三、以“人民”為讀者群
自唯物史觀傳入中國(guó),“人民”一詞就成為中國(guó)通史著作中的常用語。然而,要成功將“人民”作為讀者群則必須主動(dòng)適應(yīng)其要求,概括起來應(yīng)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編寫適合人民看的書;二是對(duì)在編纂的內(nèi)容上體現(xiàn)人民的內(nèi)容,特別是把農(nóng)民戰(zhàn)爭(zhēng)作為史書的重要內(nèi)容,此類著作也成為20世紀(jì)后半期中國(guó)通史的主體。
范文瀾是較早編纂此類通史的史家。他認(rèn)為,二十五史“連篇累牘,無非記載皇帝貴族豪強(qiáng)士大夫少數(shù)人的言語行動(dòng),關(guān)于人民大眾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記載非常簡(jiǎn)略”,無疑不適合人民大眾“學(xué)習(xí)歷史的需要”[11](P1-2)。為了編寫適合人民群眾的著作,他進(jìn)行了最初的嘗試。與此前編纂的中國(guó)通史不同的是,范書著重加入了歷代農(nóng)民起義內(nèi)容,并且把農(nóng)民戰(zhàn)爭(zhēng)視為推動(dòng)歷史前進(jìn)的重要?jiǎng)恿ΑK凇堆芯恐袊?guó)三千年的鑰匙》中說:“農(nóng)民應(yīng)該享有土地,但是失去了土地;地主不應(yīng)該享有土地,但是占有了土地;這是極大不公平的事。歷史上的混亂現(xiàn)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更明確的說,凡是歷史上的治,都是農(nóng)民起義造成的,所有的亂都是地主造成的。”[11](P6-7)對(duì)農(nóng)民起義推動(dòng)歷史進(jìn)步的作用給予充分肯定,以此種方式提高農(nóng)民參與革命和斗爭(zhēng)的積極性,在當(dāng)時(shí)環(huán)境下無疑是行之有效的。這應(yīng)是斯大林“歷史科學(xué)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xué),便不能再把社會(huì)發(fā)展史歸結(jié)為帝王和將相底行動(dòng),歸結(jié)為國(guó)家‘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底行動(dòng),而是首先應(yīng)當(dāng)研究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者底歷史,勞動(dòng)群眾底歷史,各國(guó)人民底歷史”[12](P159)理論的應(yīng)用,也是毛澤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dòng)歷史前進(jìn)的動(dòng)力”這一“著名論斷”的“典范”實(shí)踐[13](P32)。當(dāng)然,以此為指導(dǎo)的中國(guó)通史還有郭沫若主編的《中國(guó)史稿》和呂振羽的《簡(jiǎn)明中國(guó)通史》等。
以人民為讀者群的通史著作應(yīng)首推張舜徽的《中華人民通史》,他是欲給廣大人民一提綱挈領(lǐng)式的中國(guó)中國(guó)通史,用一種新觀點(diǎn)、新方法,“編寫出一部適合于工人、農(nóng)民以及一般干部閱覽的淺明通史,以節(jié)省讀者的精力時(shí)間,于平易處取得應(yīng)有的歷史知識(shí),是史學(xué)工作者責(zé)無旁貸的重任”。他說:“在打破王朝體系后,應(yīng)以事物為記載中心,將歷史上重要事物的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情況講個(gè)清楚,務(wù)求使讀者從中得到系統(tǒng)的知識(shí),以激發(fā)其愛國(guó)之心。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迫切需要去做。此書既以人民為歷史的主人,又是給廣大人民看的,便可名之為《中華人民通史》。”[14](P1-2)此書一出,變?cè)趯W(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強(qiáng)烈反響,因?yàn)樗鼮榘雮€(gè)多世紀(jì)以來以人民為預(yù)設(shè)讀者群編寫中國(guó)通史畫上了一個(gè)圓滿的句號(hào),是史學(xué)自身不斷發(fā)展的結(jié)晶。
若拋開特定環(huán)境,讀者群已成為衡量通史著作重要的指標(biāo)。沒有讀者的著作最起碼不具備當(dāng)前的社會(huì)價(jià)值,就很少有再版機(jī)會(huì)。因此,采用怎樣的體例、編寫怎樣的通史已成為擺在史家面前的一項(xiàng)重大課題。如白壽彝說:“現(xiàn)在要以人民為重要的內(nèi)容,并且能供給大多數(shù)人民閱讀為最大的目標(biāo),以后的史書形式必須是能適應(yīng)這種內(nèi)容、這種目的的體裁才是最好的體裁。”[15](P434)因此,中國(guó)通史編纂的體裁要隨著閱讀對(duì)象和時(shí)代的變化而不斷地調(diào)整、推陳出新。能為預(yù)設(shè)讀者群所接受,也自然成為當(dāng)前及未來中國(guó)通史類著作的重要目標(biāo)。
總之,20世紀(jì)編纂的不少通史或許都不具備此條件,成為學(xué)界一顯曇花轉(zhuǎn)瞬即逝,但它們?cè)谥袊?guó)近代學(xué)術(shù)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盡管筆者只是對(duì)有限的幾部通史進(jìn)行分析,但也算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據(jù)此也可以透視中國(guó)近代學(xué)術(shù)思潮的轉(zhuǎn)變,彰顯史書由古代“資治”向現(xiàn)代“育民”功能的轉(zhuǎn)向,為未來通史編纂及發(fā)揮教育功能都具有重要意義。
[1]章嵚.中華通史[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4:2-3.
[2]都重萬.論辛亥革命前劉師培的新史學(xué)[J].中國(guó)文化研究,2002年(秋之卷).
[3]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 4冊(cè))[C].臺(tái)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312-313、324.
[4]錢穆.國(guó)史大綱[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5]王桐齡.中國(guó)史[M].北京:北平文化學(xué)社出版社,1934.
[6]鄧之誠(chéng).中華二千年史(第 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張蔭麟.中國(guó)史綱[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8]呂思勉.呂著中國(guó)通[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2.
[9]王家范.中國(guó)歷史通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
[10]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
[11]中國(guó)歷史研究會(huì)編.中國(guó)通史簡(jiǎn)編[M].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0.
[12]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布).歷史簡(jiǎn)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3]羅新慧.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古史分期問題論辯[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14]張舜徽.中華人民通史[M].長(zhǎng)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15]白壽彝.白壽彝史學(xué)論文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4:434.
- 社科縱橫的其它文章
- 大學(xué)生閱讀方式轉(zhuǎn)型分析研究——以蘭州市安寧區(qū)部分高校為例
- 大學(xué)治理結(jié)構(gòu)視角下的高校職稱評(píng)審模式選擇
- 全媒體背景下的西部媒體現(xiàn)狀與出路
- 戶籍制度改革“半城鎮(zhèn)化之痛”的現(xiàn)狀、問題及法律對(duì)策——來自重慶“一圈兩翼”地區(qū)294戶農(nóng)民的調(diào)查
- 職業(yè)成熟度對(duì)大學(xué)生職業(yè)指導(dǎo)的幾點(diǎn)啟示
- 加強(qiáng)教學(xué)規(guī)律的研究 提高品德教育的實(shí)效性——兼論思想品德課教學(xué)過程的特殊性及其教育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