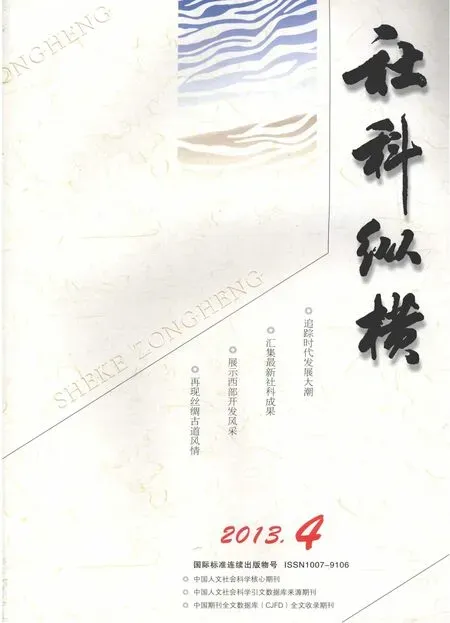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栩栩如生”的中國傳統雕塑——試談藝術考古學與中國傳統雕塑研究的關系以及存在的問題
楊宇輝
(西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00)
日前,周曉陸先生在和西美研究生的講座中談到當前藝術考古學者在美學方面的知識匱乏時曾風趣地說到,學考古的學者們在描述古代藝術品時最愛使用的詞是“栩栩如生”,似乎除此之外無以表達對藝術作品的具體感受,而這種似是而非的概念化理解居然一直作為對傳統藝術的規范描述文本在社會上大行其道,周先生玩笑道:“我看吉祥村的小姐們就很‘栩栩如生’嘛”!眾皆嘩然。笑畢細想并聯系我所學習的雕塑專業,不禁深有感觸。本文的探索,只是進行局部的驗證——它并不企望成為系統的論述。尤其因為,本文不打算過多探究有關文化的溯源及雕塑本體論等方面的問題,而僅僅想指出當代中國雕塑應當或可能具有的語言形式。換言之,本文將僅提供一些分析假設的雕塑“語言工具”。
中國傳統雕塑的研究與藝術考古學的關系歷來極其緊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二者幾乎可以相互轉化,這主要是由于藝術考古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從分類來講,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考古學研究中的人類精神文化創造物及其遺存,主要分為藝術遺跡和藝術遺物兩大類。其中藝術遺跡主要分為壁畫和雕塑,藝術遺物則主要分為繪畫、雕塑、碑刻和工藝美術等。不難看出,除了其中的繪畫部分以外,其他各種類型幾乎都與雕塑有著緊密聯系。從藝術遺跡中的建筑雕塑、宗教雕塑、陵墓雕塑到藝術遺物中的玉器(雕)、陶器(雕)、銅器(雕)、瓷器(雕)以及其他如漆、木、金銀等各種材質的遺物,無不反映中國傳統雕塑形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這豈是區區一個“栩栩如生”便可概括得了的。
但是,翻開中國古代雕塑史,長期以來在中國傳統雕塑研究中使用的卻多是類似于“栩栩如生”的模式化稱述。例如:“青銅器藝術代表了商周雕塑的最高水平,渲染了威嚴神秘的氣氛,形成了端莊、華麗、氣質偉岸、形象乖張的藝術特性”;“秦始皇兵馬俑其兵俑體態與真人相等,數量眾多、形態各異、栩栩如生;其馬俑形象寫實、身材矯健、活靈活現”;“漢代雕塑在繼承秦代恢弘莊重的基礎上,更突出了雄渾剛健的藝術個性,霍去病墓石雕群在形式上突出了石雕作品的雄渾之勢和整體之美”;“隋唐佛雕作品既顯博大凝重之態,又不失典雅鮮活之美”……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看似嚴謹縝密,實則空洞無物,對中國傳統雕塑的形態特征和美學取向,僅停留在表面稱述的層面,缺乏對其內在精神和形態機制方面的研究,而其方法論的核心部分更是未能擺脫過去唯意識形態的思想束縛,將社會學考察作為研究的主要方向。如此,既不利于對傳統雕塑深化研究和理論總結,更不利于對傳統雕塑的核心價值進行當代轉化和繼承。
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很復雜。首先是由于在中國美術史上雕塑一直未能擺脫實用性功能的束縛而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因而缺乏系統化的發展脈絡。雖然出現了眾多雕塑藝術形式,但其核心價值,即基于形而上追索的美學追求卻從未真正獨立出現。另一方面,中國傳統雕塑的創作者主要是工匠,正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傳統雕塑不但未能像中國傳統繪畫那樣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甚至主流知識分子對雕塑的記載文字也屬鳳毛麟角,如此才造成面對中國傳統雕塑時考古學界與雕塑學界的普遍失語,因此可以說:精英文化的缺位直接導致了傳統雕塑理論的缺失,而價值系統的重建則需要藝術考古學與中國傳統雕塑研究重新定位,回歸藝術的本源。
藝術是源自人的形而上沖動的關照人的終極境域的物化行為,其價值首先表現為確立人的精神歸屬。而其中形式的功能則表現為提供恰當的途徑,也即語言符號的功能。言說方式對于言說內容而言,則僅表現為一種符號媒介。“符號思維和符號活動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這個條件”(恩斯特.卡西爾)而文化,是人的外化、對象化的結果,或說是符號活動的現實化和具體化。在人—符號—文化的三位一體結構中,符號無疑是人類文化活動的核心問題。正是“符號功能”建立起了人之為人的“主體性”,也正是因“符號現象”構成了“現象界”——文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形而上的諸因素(哲學、宗教、藝術)通過符號活動實現著其超越現實的形而上品格。其中,藝術則負擔著人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達至超越之境的絕對中介作用。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圍繞著這種絕對中介作用的各個符號系統(藝術形式)不斷完善,同時也使人的混沌地存在轉化為明朗地形而上的價值存在。或許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對中國傳統雕塑的美學研究與藝術考古學研究才有真正實現契合的可能性。
在對藝術考古學研究成果給予關注的基礎上,也有必要關注這樣一幅人文圖景:一對對應的形式因素,矛盾對立的兩極。它代表了天與地、剛與柔、動與靜和所有對立的自然因素,在內部張力和外部壓力的作用下由兩極的對立狀態向對方彎曲、運動,產生了對立事物的相互轉化,而這個轉化的聯系形態則必然是圓形。在圓形空間中,對立的兩極挪讓呼應、聯系扭合,而圓的外界面則曲潤光滑,體現著對立兩極的渾然一體以及自然造物相互依存和循環往復的人文價值規范——這就是代表古代中國人把握世界和理解人的存在境遇的終極圖景:“太極”。
與太極所揭示的人文價值相對應,中國的傳統雕塑正是通過對雕塑造型的全部內在矛盾,如動與靜、實體與虛空的轉化、協調中獲得了形勢和精神的平衡與自足。雕塑的“實物感”被強烈自足的“實體感”所取代。這種“實體”的物理形象特征被自足的形式所弱化,轉而代之以強烈意向化的符號特征,雕塑的語言符號功能因此突破了以形、以象描摹事物的主客分離的審美距離,直接切入古代審美人群的“天人一體”的終極關懷。雕塑的實體存在與泛靈論的“道”的追求之間的矛盾被弱化并調和了。從某種意義而言,作為形而上的語言符號系統,中國的傳統雕塑正因其對自然物象客觀描摹的有意舍卻,從而使其符號功能達至相對純化的境界。這并非古代中國人缺乏摹寫物象的能力,而是源自對物象之后的形而上追求及對雕塑這一符號化的言說方式的形而上要求。
在中國傳統雕塑的動力學形態上,所有向外放射的、外拓的形體都被扭轉、壓制,形體內部的矛盾因素被主動強化,從而更加突出了力的內外對抗。同時在整體形態的內斂、收聚特征下,通過對矛盾因素提供不同的空間范圍,也即造成可控的內部力環境,實現了雕塑中運動與靜止之間矛盾的動態平衡。雕塑帶給感官的物理實在被力的形式化運動所取代,故而使雕塑的整體形態呈現出完整、運動、充滿矛盾但又平衡自足的審美特征,這也正是中國雕塑傳統中最為本質的造型原理和形態機制。
面對傳統藝術,我們不免一次次被其中超然、從容的終極體驗所感動,這是人的本然狀態,也是藝術的必然歸屬。傳統,并不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程并參與到傳統的進程中。而在這個理解并參與傳統進程的過程中,我們只有對藝術這一符號系統所承負的精神內涵予以充分而深入地關注,時刻關懷人的本然處境和終極境域,建構中國化的當代語言符號體系才將成為可能。
[1]孫長初.中國藝術考古學初探[M].文物出版社,2004.
[2]恩斯特.卡西爾[德].人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3]潘知常.中國美學精神[M].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