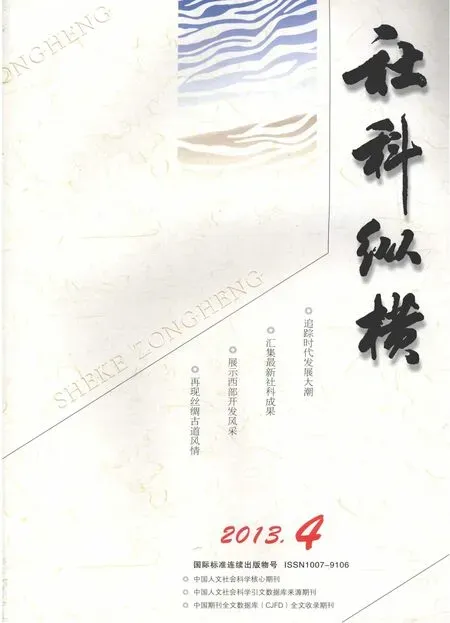自然與人、資本的辯證關系——馬克思的生態辯證法管窺
蔣明偉
(百色學院政治與法律系 廣西 百色 533000)
隨著生產的世界化和交往的全球化的交錯發展,人改造外在自然的領域也從狹隘的地域邁向了廣闊的世界。然而大多數的生產主體和交往主體仍秉承狹隘的個人主義、地區主義或單純經濟理性,為了滿足個人利益、集團利益或純粹經濟利益不惜犧牲他人利益和外在自然,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世界性失衡。盡管諸多世界性主體(如國家、民族、組織或個人)或多或少都意識到外在自然的重要性,但缺乏理性和科學認識外在自然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價值,以致人與自然的世界性失衡關系的解決成效甚微。馬克思的生態辯證法以辯證語態系統地科學地論證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破斷和重塑,為人們正確認識和合理處理人與自然失衡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南和思維路徑。因此,以馬克思恩格斯原始論著為立足點,深入挖掘馬克思的生態辯證法思想內涵和理論外延則成為當下學術界的責任使然。
一、人的類本質與自然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以辯證唯物主義視角揚棄了思辨哲學詮釋的人的抽象性本質,又否定了機械唯物主義解讀的人的單純受動性本質,以生產勞動為認識中介深刻闡明了人區別其他物種和群體的本質性特征即人的類本質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1](P57)。與此同時,馬克思又以自然的視角論證了自然與人的類本質的內在關系。
首先,自然界是人的類本質存在的外在保障
馬克思認為人的類本質是人區別其他物種的特有屬性即自由的有意識的生產活動。人的類本質的存在需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人需有意識地存活于自然界和人需有意識地享有自由地從事生產活動。因而首先需確認人有意識地存活與外在自然的關系。從事生產活動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的有血有肉的人,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2](P11)。外在自然不僅賦予人于手、腳、身體等天生肉體組織,也借助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形式提供人維持肉體存在和延續的所需物質,更為人的意識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外在的感性的現實的對象,使人得以有血肉有意識地存活于外在自然界變為可能。其次,人有意識地享有自由地從事生產活動與外在自然的關系。人是有血肉有意識地存活于外在自然界,借助自身意識的認識功能使自身得以從受動自然物轉變為能動自然物,從而才能使自身的本質屬性即有意識的自由的生產活動變為可能。然而人的類本質從抽象可能變為現實可能仍不能離開外在自然。生產活動的存在得以生產對象的存在為前提,自然界不僅提供了人肉體直接消費和意識選擇認識的外在對象,也為人的生產活動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改造對象,從而使人以自身意識深刻把握和認識外在對象的內在尺度和聯系機理、擺脫外在自然對人的生存和生產的外在束縛、合理融合自身欲求與外在自然的內在尺度和改造自然界為既合符自然自身發展規律又符合人所需所欲之形態等變為了現實可能,從而為人自由的有意識的生產活動提供了外在保障。
其次,自然界是人的類本質的實現基石和外化形態
馬克思認為自然界不僅作為人的類本質存在的外在保障,也作為人的類本質實現的現實基石,更作為人的類本質的外化形態。一則自然界表現為人的類本質得以實現的現實基石。馬克思認為人為了生存于外在自然界就必須不斷地與自然界交換能量、信息等物質,借助這個活動過程人的大腦內部系統得到進化,從而具備了能夠記憶、識別和建構他物的功能,從而使人從無意識或低意識的人發展到具有高級意識的人。與此同時,人自身意識的特殊功能借助對實踐活動直觀反映或間接反映的事物(植物、動物、空氣、光等)的外部特征和內部屬性的記憶、識別、判斷和整合,內化和把握和外在自然的內在屬性和聯系機理,摒棄外在自然律令與他物的尺度對自身的約束和限制,才能使人能夠按照外在自然的內在尺度來加以改造和按照美的規律來加以生產,才能使人從必然走向自由從而實現人的有意識的自由的生產活動即人的類本質的全然釋放。二則自然界是人的類本質的外在形態。馬克思認為人有意識的自由的活動并非囤于精神領域而是存于外在自然領域,外在自然不僅表現為人的類本質存在的外在保障更是人的類本質的外化形態和外在確證。因為人不僅以內在意識內化和把握外在他物的內在尺度,也以自身的欲求為標準判別外在他物內在價值,從而擇取具有較高價值又屬于自身熟知范疇的外在自然物作為改造對象,不僅以自然自身內在屬性為改造立足點,更以人的自身的欲求為改造切入點,從而使外在自然不僅以符合自身內在屬性又以人的類本質物化形態加以呈現。因此外在自然此時雖然本質仍屬自然范疇但它更是扮演了人的類本質的外在對象物和外在確證物的重要角色。換言之,如沒有外在自然提供意識對象和改造對象,那么人的類本質不僅無從產生更無從確證。
二、私有資本與人、自然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從私有資本的現實破壞性視角深刻分析了私有資本與人、自然的辯證關系,他認為私有資本不僅作為工人分工協作的勞動產物且不為工人所占有而存在于工人之外并反過來控制和支配工人及其活動的外在抽象存在物,也作為私有資本所有者的抽象的外在的主人,更是作為破壞外在自然的罪魁禍首。
首先,私有資本與創造者的否之否定關系
馬克思認為私有資本作為工人經過分工協作勞動將自身體力和腦力融入外在被改造物體并借助等價交換加以實現的抽象勞動的外在表現形式。既然它作為工人集體勞動的外在產物理所應當作為工人集體的勞動收入,但事實卻表現為相反形態,私有資本不屬于工人所有而為個別資本家所占有。緣由很簡單,工人在加工外在他物之前,全身除去擁有自由勞動力以外別無他物,以致他們為了維持自己和家庭其他成員的生活,不得不將自身自由勞動力以合約形式賣給個別資本家,再加上機器、原料和廠房等生產資料皆由資本家提供,因此整個生產過程和全部勞動產品皆被個別資本家所掌控,以致私有資本的創造者僅能夠獲得私有資本的極其微小部分——僅能維持他及其家庭生存與延續,從而導致了私有資本對其創造者的首次否定。從精神領域加以分析,作為工人為了維持自身和家人的生存和延續就不得不尋求更多了物質補償,以致他不斷將更多的體力和腦力注入私有資本控制的生產活動,丟棄了自身作為人的精神追求甚至是“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1](P122)也變成奢華的欲求,從而將其本質性的生命活動顛覆為維持生活的外在手段,喪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屬性而淪為資本控制下的異化人,從而導致了私有資本對人的再次否定。因此,私有資本盡管作為工人勞動的外在產物但卻演變為了工人在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追尋的單純對象,以致私有資本不僅主宰了工人的物質世界也掌控了工人的精神世界而演變為工人內在的“絕對意識”。
其次,私有資本與承載者的精神奴役關系
馬克思認為私有資本與承載者的關系從物質領域來看表現為占有與被占有的關系,然而從精神視域看并非形同物質領域的關系反成了私有資本對私有資本占有者的精神奴役。私有資本家以獲取資本及資本增值為存在旨趣,因而為實現自身的欲求,獨自占有所有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工人勞動,控制了整個生產過程和分配勞動產品的全部權利,借此以多種形式和不同花樣剝削工人寄予生存的勞動產品和生活資料,從而不僅實現了對工人階級的駕控更實現了私有資本以幾何級數遞增的心理夙愿。從私有資本家獲取資本的整個過程的物質關系分析,私有資本家將外在他物(外在自然、貧困工人和私有資本)等都視為實現自身目的的外在手段和實現工具,既控制著資本增長也奴役著貧困工人,似乎他就是整個外在世界的主人,似乎整個世界唯有他以人的姿態存活。然而從精神視域加以分析結論就截然相向,正因為私有資本的無限增值本性和“你自身不能辦到的一切,你的貨幣都能辦到”的特有功能贏得了私有資本家的特別青瞇,以致他從事的所有活動都以獲取資本增值為終極目的,從而清除自身其他的奢華欲求(包括自身的本質屬性)和以物化關系取代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最終將自身有意識的自由的活動演變為了滿足自身期望私有資本增值的欲求的外在手段,顛倒了人為之人的本質屬性,從而淪喪為了私有資本的勤快的精于算計的奴仆。
再次,私有資本與自然的異化關系
馬克思認為私有資本與外在自然不僅是外化與揚棄的關系更是異化與破壞的關系。盡管私有資本的內在屬性表現為抽象勞動的量的集合,但私有資本也需以外在自然形態加以展現。因而私有資本的物質形態就表現為蘊含了抽象勞動量的自然物體。然而私有資本不能始終維持自然物體式的外在形態,物化形態的它借助等價交換形式和以剝削外在工人為條件揚棄外在自然形態回歸自身抽象形態。借此可以得出外在自然不僅作為私有資本存在的物質保障更作為私有資本內在屬性得以展現的外在確證,是私有資本不可或缺的外在身體。然而私有資本并非以禮相待外在自然,以尋求自身無限增值的內在本質屬性驅使著私有資本極力推脫自身靜止狀態以追求自身高速倍增,正如馬克思曾言,它不僅是量的存在物,更是無限的量的集合,因而無度與無節制演變為了資本的內在尺度。正因如此,私有資本為實現自身高速倍增,那么它將需求更多的外在形態和外在對象。它會將自身投擲到適合自身發展的世界任何角落,它會將外在自然的內在尺度和承受范圍全都拋棄,更會將外在自然對自身存在和增值的內在價值置若罔聞,以致私有資本的無限增值所帶來的最終結果僅是它除了能夠創造本身以外不在創造他物,作為外在身體的自然淪為了原料倉與工具庫,外在自然的內在屬性遭到了最為惡劣的篡改和內在系統遭到最為慘烈的破壞,自然界僅作為抽象資本的外化形態而不斷被異化與丟棄。
三、世界性的人與世界性的自然的辯證關系
從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向度來看,馬克思從人與人交往的世界化和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范圍的擴深和延展雙重視角,論證了生產活動的世界化和人與人交往的世界化將推進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范圍從狹隘地域邁向廣袤世界,因而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從狹隘的自然與狹隘的人的關系演變了世界性的自然與世界性的人的關系。
首先,世界性的人以世界性的自然為始基
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歷程是從狹隘地域的人向世界性的人轉向,又認為人向世界性的人轉向又以世界性的自然為始基。馬克思最早曾在《第179號“科倫日報”社論》(1842年)一文中以哲學術語闡述了“以世界公民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3](P32)的著名論斷。毋庸置疑,人從狹隘地域的人向世界性的人的轉變不僅是人的認識對象的世界化更是人改造能力的世界化。馬克思認為人不僅作為受動的自然存在物更是作為能動的自然存在物,人可以依憑自身從事的生產活動漸次認識和改造外在自然,以內在意識內化和把握外在自然的內在尺度和特有屬性,以實踐活動改造外在他物形態和創造新型物體,借此人能夠摒棄外在他物對人存在和發展的制約和阻礙,以致人不僅能夠適應外在自然還能夠改造外在自然使其演變為適合人類生活和生產的外在環境。因此隨著人認識外在自然范圍的世界性延伸、內化外在自然內在尺度深度的世界性拓展、改造外在自然能力的世界性提升和人與人交往范圍和交換內容的世界化,人的生活范圍和生產領域也將突破狹隘地域限制向世界范圍拓深和延展,從而人也就以世界性的外在自然作為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在對象,以世界性的內在屬性取代了狹隘地域的內在特質,最終人能夠“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改造”[1](P58),“把整個自然界……變成了人的無機身體”[1](P56),從而“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1](P56),因此人也就從狹隘地域的人轉變為了世界性的人。因而世界性的人現實實現是借助認識外在自然內在屬性和改造外在自然內外形態,擺脫外在自然內在屬性和外在形態對人向世界化發展的內在約束和外在制約,從而使自身得以世界性的人的姿態存在于外在自然和內在社會。因而世界性的人是以世界性的自然為連接紐帶又以他人為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為他人的存在為生存和發展的特有模式。因此世界性的人是以世界性的自然為存在始基。
其次,世界性的自然以世界性的人為確證
馬克思認為以追求私有資本增值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動了交往世界化與生產世界化的發展,促使了個人與個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依賴性日趨加強,每個人、地區或國家都并非僅依靠自身獨立發展換之以其他個人、地區或國家的發展為前提,因此每個人、地區和國家的欲求滿足也皆已世界化了。正如其所言“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4](P31),“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態”[2](P58)。因而以交往世界化、生產世界化和消費世界化為內在屬性的人的世界化使外在自然盡管還依賴著個別空間和特殊地域且富帶著鮮明的地區特色,但是作為開采、生產和消費它的外在主體已不僅是與它同屬相同地域的個人和組織,也包含了與此特殊地域的個人和組織相互交往、生產互助和需求互足的其他特殊地域的個人和組織,換言之外在自然面對的主體來至整個世界不同區域的個人和組織。因此伴隨著人的世界化,外在自然也被世界化了,具體可從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加以審視。一則從生產領域審視外在自然的世界化。隨著生產的世界化,外在自然被開采、利用和改造不僅作為自身所屬區域的生產組織的生產原料也被輸送到世界其他區域作為其他生產組織的生產資料。與此同時,它也被來至不同地域的主體以多元價值取向和判別標準加以審視和以多元的改造方式和多元的內在尺度改造為滿足不同地域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的所需所欲之態。因此生產世界化不僅促進了外在自然物質形態的世界化,也促進了外在自然內在屬性的世界化。正如馬克思所言“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4](P31)。二則從消費世界化看外在自然世界化。生產世界化推動消費世界化促使了改造外在自然所獲產品不僅供應所屬區域或國家的個人和組織消費也滿足世界其他地區的個人和組織的消費。正如其所言“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求,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4](P31)。因此人的交往世界化、生產世界化和消費世界化使外在自然突破了地域性和民族性演變為了世界性的自然,以致它的持續健康合理的發展不僅關系到所屬區域的人的持續健康合理的發展,也關乎到世界其他地區人持續健康合理的發展。總言之,世界性的人推動了外在自然的世界化,外在自然也就演變為了世界性的人的不可或缺的外在身體。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M].人民出版社,2003.
[3]俞可平,楊冬雪等.全球化與全球化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32.
[4]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M].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