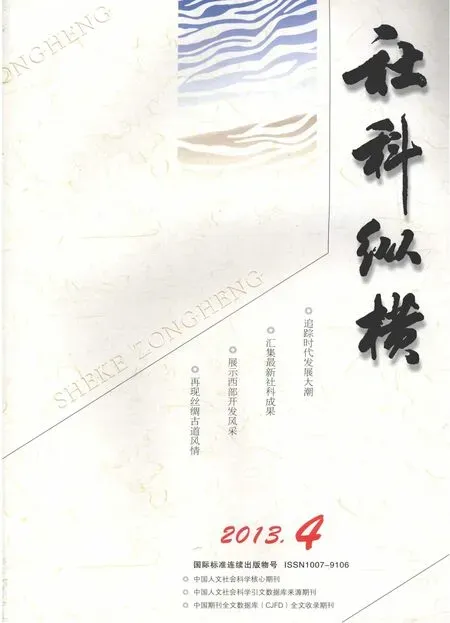以理服人辨析
馬 麗
(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 廣東 珠海 519085)
我國不同國民教育階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學校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基本方式。它們的教學效果直接關系著馬克思主義在青年學生中的大眾化。馬克思主義教育是一種以理服人的價值教育,背離了這個基本的教育理念,就容易成為沒有根本和缺乏內容的形式說教,無法抵及受教育者的心靈世界。但是,以理服人的真正內涵是什么,需要深入厘清。
一、以理服人的教育隱憂
筆者在給大學一年級新生上《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休息間隙與同學交流時,不少新生講述了他們在中學上思想政治課的一些情況。盡管筆者曾經歷過與他們類似的教育歷程,深知升學率對中學思想政治教育的擠壓,但是,他們與筆者聊天時所表現的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情緒和態度,促使筆者圍繞思想政治教育的問題,與107位新生,從2011年9月20日到12月26日,展開了深入交流。這些同學高中時代選讀的是文科或者高考時選考的是政治科目。
在105位(98.13%)學生眼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宣傳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工具。“中學所受思想政治教育,無非是愛黨愛祖國。‘政治’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統治階級為進行階級統治所使用的種種手段。‘思想政治’便可以說是,或者基本上是,對學生進行‘教化’的工具。總的來說,中小學所受思想政治教育無論出發點是什么,采取的手段是死板甚至可以說是引人反感的。”(HJ)有7位學生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引導人和發展人的功能并沒有體現出來。“至于思想道德的學習,關于做人的學問,我在課堂上沒有取得太大的進步。我們只是重復地記憶,真正去做的人很少。所以,這就還真只是一門‘課’。”(WJW)
103位(96.26%)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沒有好感。這包括對教育者教學能力的評價不高,“上課老師很少能講出課本知識的真正內涵、更高層次的內涵。”(CLY)除此以外,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課被學生想象為教化官方意識形態的課程,而教師就成為黨宣傳意識形態的工具,因此,這種角色想象也成為學生降低對教師評價的重要原因。“上這些課的老師大部分可以被稱為老古董。要不拿著無聊得課本照本宣科,要不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忠實粉絲,把一大堆馬哲理論和黨史搬出來對我們進行洗腦。”(CZH)“在我經歷的政治課中,政治老師方佛都是一些特正經的人物,會一直按書中所說的宣揚共產黨的好,仿佛就是黨派來的代言人。所以一直不怎么喜歡學校的政治課。”(KSQ)
104位(97.20%)同學認為,他們現在并不認同中學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傳導的內容。“當時總是習慣把老師的話奉為圭臬,總是很虔誠地很‘革命’地去奉行各種條條框框,真的是以‘馬列主義毛鄧思想共產黨理論’為榮。而現在看來,當時思想教育的內容未免太理想太革命,與當下的現狀相比不由得覺得可笑。”(CXY)甚至有學生極端地自我價值否定。“小的時候上思想教育課,看到賴寧救火、雷鋒奉獻,心里心潮澎湃,常感動得熱淚盈眶。但現在有種被騙的感覺。”(QSY)
101位(94.39%)學生認為,中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應試,課堂教學的內容主要是應考知識灌輸和應試技巧講解,使得思想政治課成為枯燥乏味的理論課程。“對于大學之前的政治課的感受,一是枯燥,二是官方。老師們更著重的是解題技巧與如何得分。”(KSQ)應考知識由考試大綱規定,應試技巧也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路徑遵循。因此,學生回答思想政治問題的程序基本類似流水線上生產工人的體力活。他們只需要根據不同的題目內容和類型,以相關的知識點熟練地填充到對應的答題摸板中。它無形當中壓抑了學生的想象力。“大題的答案都是有組織的。每個人對同一問題都是同一看法,不能有別的想法。”(HPY)“政治課上老師多按教學方案授課。總是一個大課題,底下分列許多小標題,從某一概念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講起,課堂上外拓是有,但比較少,幾乎全是貼著課本講,并且要我們背許多的內容。作業的題型靈活而相對單一,回答、分析每一種現象都大部分搬課本原理,‘活學活用’。”(CLY)
107位(100%)學生反映,中學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評價標準,主要是要求學生考試中能夠以儲存的知識有效地回答試題,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對這些知識的闡發和運用不被看重。“中學時代的政治課,大多是照本宣科,老師把課本的內容念一遍,做些講解,畫出考試的重點,再讓我們背得滾瓜爛熟,足以應付答卷即可。”(XJY)“高中的政治課就是講四本書,很無趣。我覺得我們學到的更多是如何利用這些理論在考試中獲得最高的分數。我們都只是很枯燥地背考點、背理論,沒有把這些知識結合到我們的生活中去。”(CYQ)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生活相脫節,學生也不會產生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產生改造主客觀生活世界的觀念,而是將之僅僅視為一門跨入更高一級教育階段的必考科目。考試結束后,這些知識也基本被遺忘了。
即便是理論知識的灌輸,也可以有多種形式。在98位(91.59%)學生看來,中學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輸方式比較單一,基本上是教育者圍繞考試要求的“填鴨”式教學和學生死記硬背的合體。“老師從上課說到下課,黑板上寫得滿滿的(全是抄課本上的要點),是老師的獨臺戲。下面的同學也不用回答問題,氣氛特悶。許多同學甚至不聽,寫別科的作業。到后來有時老師就不講了,直接告訴我們哪里要背,之后就不停地背。中學的政治課給我最大的印象是不停地背,無法擺脫無法背完的試卷、課本。”(ZYQ)“說真的,高中的政治變成了薄薄的四本書,世界仿佛向我們關了門,我們只能看書中的風景。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被老師一筆帶過。”(KSQ)學生要通過強行背誦理論知識的“死去”過程,以換取考試回答題目時得心應手的“活來”結果。
可見,這種尷尬的教育困境之所以出現,除了社會因素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學時代的學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因為教育使其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引導生命成長的價值性,僅僅因為它是考試和升學的工具。這種思維方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說理的教育,而是無理的應試教育;不是關懷人和貼近人的教育,而是遠離人和拋棄人的教育。既然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價值性沒有被透徹地闡釋出來,學生只是似懂非懂地記憶應考知識,那么,只要他們順利進入高等院校而擺脫考試的壓力,就會拋棄此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去選擇自認為是真理的其它思想流派。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必須重新深入開掘以理服人在馬克思主義教育中的當代價值。
二、以理服人的語義分析
在漢語中,語詞的理解是非常復雜而有趣的語言學現象。一詞多義或者多詞一義無論是對域外人還是域內人,都時常構成文本解釋的障礙。馬克思主義教育中的“以理服人”是比較典型的例證。一般意義上,“以理服人”的經典注解,是馬克思的論斷:“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根據馬克思的這段論述,理論只要具有真理性,就可以為群眾所接受和悅納。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教育對“以理服人”最直接的表達。但是,這種表述不僅沒有充分開掘馬克思的本意,而且歪曲了“以理服人”的本質內涵。若要完整而準確地再現“以理服人”的真諦,就必須通過語詞分析的分式,在明晰每個字所隱含的教育理念的基礎上,整體性闡發其孕育的教育精神。
“以”之“因”與“用”。漢語中的“以”因為語境的差異,或是連詞,或是助詞,或是介詞,具有不同的含義。“以學校為榮”中的“以”指代的是“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的“以”等同于“用”。在“以理服人”中,“以”同時兼具“因”和“用”的含義。它既是“因理服人”,又是“用理服人”。但是,相同的“人”在前后表述中指稱的是不同的客體或者對象或者賓語。受教育者為教育者所傳播的“理”說服,這是“因理服人”。“人”是指教育者。但是,受教育者“服”教育者的唯一而內在原因,不是師道尊嚴的習俗或者其它功利性考量,而是“理”。教育者的身份或者地位,無論帝王抑或平民,在產生說服受教育者的教育效果中,沒有參考意義。“用理服人”是從教育者的角度立論,指教育者用“理”說服了受教育者,既不是以力服人,又不是以德服人。因而,此處的“人”指受教育者。盡管從所產生的“服人”效果來看,“因理服人”和“用理服人”具有同一性,但是,它們分別有著重要的教育價值分歧。在“因理服人”中,“理”具有至上性、神圣性和崇高性,是教育者真正“服”的對象,它自身就具有目的性;但在“用理服人”中,教育者仍處于中心或者支配地位,“理”成為他“服人”的便捷手段。“理”的手段性角色暗示著,它可以因教育情勢的變遷而被廢棄或者被置換,由“用力服人”或者“用權威服人”取而代之。
“人”之“需要”與“意志”。人兼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論點。人的自然屬性使其與其它生物保持著緊密而內在的勾連,例如必須首先滿足基本的物質需要和生理需要,換言之,必須滿足生存需要。但是,人與其它生物的根本區別在于,生存需要既是其它生物的底線,又是其目標,同時成為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因此,對于其它生物而言,它們是存在于世或生存于世。但是,人不僅要努力圖謀生存,更要反思生存得更好的方式。他追求的是一種美好生活。這種反思性使得人渴望精神需要的滿足,從而在本質上區別于其它生物,呈現出人豐富的社會屬性。回應人的精神需求成為一切教育共同的追求。其它生物服從生命本能的內在沖動以實現生存需要的滿足,人卻有著更深刻的自由意志。它不僅規范和指引著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平衡著彼此間的沖突與協調,而且會因生存需要或精神需要的變化而改變。自由意志使人對其“所為”、“所是”或“所去”保持著深切的自我反思,對其“所當為”、“所應是”或“所當去”有著理性的自我覺醒,由此成為外在的價值或者觀念進入主體自我的“過濾器”。無論是自我反思或者自我覺醒,其終極的有效標準在于主體需要的實現。因此,通過教育的途徑,直接改變主體的自由意志尤為艱難;而使教育經由關注或者滿足人的需要的方式,間接引導主體的自由意志更加現實。
“理”之“真理”與“說理”。教育作為人類社會所特有的一種社會現象,“它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愿望和要求。它必須由年長一代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地把人們積累的有關生產斗爭和社會生活的經驗、知識和技能,系統地有步驟地傳授給年輕一代。”[2]因此,只有教育內容具有真理上的價值,才具有傳授的意義。這也是“以理服人”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理”缺乏真理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那么教育者即使全身心投入,也難以產生長久而持續“服人”的教育效果。教育就成為名副其實的“說教”。“說教”有兩層含義:對于教育者而言,只是說一說而已,從不指望受教育者踐行;對于受教育者而言,只是聽一聽罷了,從未想過以之指導社會實踐。但是,如果教育者缺乏“說理”的技巧,未能充分闡述教育內容的真理性價值,那么,它也難以獲得受教育者的認同或者悅納,不能產生“服人”的教育效果。“說理”不是“強詞奪理”。“強詞奪理”的本質仍是不講理,要么所依據之“理”不是真理,要么“強奪”方式本身失“理”。“說理”要求言說者不僅要清晰地闡發理論內在而嚴謹的邏輯體系,體現理論的自洽性;尤其要結合聽說者的需要,揭示其有效性。因此,為了“服人”,教育內容不能毫不講理,教育者也不能有理說不請。
“服”之“說服”與“服務”。教育有效性的直接目的是受教育者接受了教育內容。因此,“以理服人”的基本含義是受教育者認同了作為教育內容的“理”。“服”首要而基本的內涵是“說服”。它區別于“制服”或“壓服”。“說服”的教育場景想象是,教育者以講理的方式呈現教育內容的真理性,而受教育者是否接受教育內容,選擇權在受教育者。而“制服”或者“壓服”盡管為了取得“服”的效果,有時也重視講理和真理,但是,如果受教育者仍不認同,那么,就采取壓制的手段,使教育者被迫表面上認同。“以力服人”或者“以權服人”實現的是“制服”或“壓服”。“說服”也不同于“恩服”。“恩服”的動機是對方的恩情或者德行,它是依據感情行事。因此,感恩或者慕德有時會毫不講理。“以德服人”是典型的表現形式。“服”除了“說服”外,還有“服務”的意思。因此,“以理服人”不僅是以“理”“說服”人,而且這“理”必須“服務”人的需要。“理”的“服務”內涵不能僅僅從工具論角度去理解,而是必須同時將之視為“理”的本性、特質或者目的性追求。重視“理”的“服務”本色使得“以理服人”類似于“以利服人”。但是,“理”真實合法普遍有效,而“利”可以虛構、偽造或欺騙。因此,“以理服人”要統攝“理”對人的“說服”和“服務”。
“以理服人”經過逐字的語言學分析后,就可以提煉出一種整體性的概括。在教育中,真理通過說理的方式,發揮服務人的需要的功能,引導人的自由意志,產生說服人的教育效果。這就是“以理服人”的本質定義。它不僅強調內容的真理性和傳授方式的說理式,更關注理論及其呈現方式對人的需要的滿足,從而使教育的真理性表達和價值性追求統一。它的主語是“真理”,從而不僅淡化了教育者對受教育者的主導性和支配性,而且凸顯了真理的至上性,不僅傳達了教育主客體之間平等的德性價值,而且彰顯了真理在教育事業中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說理的方式”和“引導人的自由意志”內在地屏棄了說教、壓服、恩服等方式,突出了教育主客體之間自由而民主的德性前提。真理服務人的前提是了解人和發現人,因此,“發揮服務人的需要的功能”隱含了教育對人的理解的德性立場。在滿足這些德性要求后,“以理服人”就能產生“說服人的教育效果”。“以理服人”不僅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更是德性精神和德性追求。
社會價值形態的多樣化發展凸顯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教育的艱難,也彰顯了以理服人教育理念的當代意義。官方雖然可以將馬克思主義尊崇為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并在各級學校課程設置中表明其重要地位,但是,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經由教育的途徑,通過以理服人,取得更大的理論優勢,那么,教育主客體僅僅是出于功利的算計而被迫接受馬克思主義知識,無法從內心深處體察馬克思主義崇高的真理性和厚重的價值性。因此,當馬克思主義經由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證實為真理后,教育者要通過說理的方式,結合受教育者的需求,呈現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實現以理“說服人”的教育效果和以理“服務人”的教育理想。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王天一等編著.外國教育史.修訂本(上冊)[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