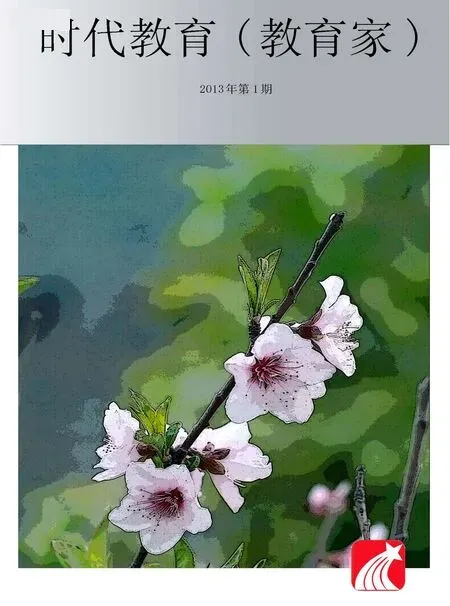白氣球
文_趙志雄
白氣球
文_趙志雄
伊朗導演賈法·帕納西善于把小事件拍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白氣球》就是這樣一部電影。
除夕,漂亮得像個小天使一樣的女孩納西亞想要買一條金魚,因為家里的魚太瘦了,而市場上的魚“擺動起來就像跳舞一樣”。她用各種理由哀求一直忙碌的媽媽,都沒能成功。最后她用氣球作為交換,求哥哥幫忙。終于讓媽媽拿出了僅有的一張500元錢紙幣(她只能用其中的100元),小女孩奔出家門,卻又被街頭耍蛇的藝人吸引。錢差點被蛇王“留”下;她好不容易把錢要回,來到賣魚的店。金魚由100元漲到200元,而且要命的是錢不見了。一位好心的奶奶跟她沿路尋找,終于找到了錢,但紙幣又被駛過的摩托車弄得掉進了下水道。
小女孩到下水道旁邊的裁縫店尋求幫助,卻遇到店主正在跟對他的活計不滿意的顧客爭吵:“親愛的朋友,……你的領子,你的臉,你的頭,這一切都與我毫無關系!別煩我你的領子太大或太小……這不是我的工作,我對你的頭不負責任!”
大人們的世界與小女孩單純的愿望是如此截然不同。影片的鏡頭不斷在大人們的身影和納西亞可愛的臉龐間轉換。小女孩的期待和大人們的忙碌、喋喋不休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制造出強烈的戲劇性效果,使得影片沒有因為表現的是“小事件”而平淡乏味,反而張力十足。
只有那個沒錢回家、看上去像個流浪漢的士兵肯停下來跟納西亞說話,但遇到的是納西亞的警惕和拒絕。身處這個忙碌而喧囂的世界,納西亞幼小的心本能地開始學習世故。
好在這個城市里還有那個賣氣球的男孩。他一開始差點跟納西亞的哥哥打起來,明白了納西亞的需要后,不但主動幫忙,還買來粘紙幣的口香糖。三個人嚼著口香糖開心地笑了——這應該是整個故事里最溫暖的鏡頭了,就像陰沉的下午里出現了短暫的一抹陽光。
納西亞的故事有很強的象征意味:在大人們繁忙、喧囂的生活中,孩子的想法、愿望往往是被忽略的。人們被各種事務、關系、各種觀點和欲望所包圍,很少停下來,傾聽自己內心——那里有一個被視為幼稚、無知的“孩子”。人們用各種“大人”的理由拒絕、敷衍這個孩子的要求;用世故和滄桑裝扮自己,直到自己都難以認識自己。而當“大人”停下來時,“孩子”卻又用懷疑和抗拒面對他。——然而,這些“哲理”并不是《白氣球》所要表達的全部。
從整個故事來看,影片的關注點似乎一直都集中在納西亞和她的心愿上,她的期待、難過、興奮、焦急,伴隨著大人們的忙碌、冷漠、熱情,直到她終于如愿以償。但是最后,鏡頭定格在賣氣球的男孩身上:他轉身離開,扛著自己的桿子——上面掛著一只賣剩下的白氣球。
在一個貌似圓滿的故事的結尾,留在觀眾視線里的卻是一個孤單、落寂的身影。就像一首詩的意味深長的結尾,影片用含蓄的鏡頭語言,把觀眾的心引向另一個、需要想象的空間:又有什么事曾發(fā)生在男孩身上呢?他有怎樣的生活和渴望?這個除夕夜他又將如何度過?他幫助兄妹兩個時的笑容,該是平時少有的吧?男孩身上破舊的衣服、很久沒有洗過的頭發(fā)、畫外音(可能是廣播或電視)對新年即將到來的倒計時般的播報、還有那個賣剩下的、掛在桿頭的白氣球,都在傳遞著暗示。
電影賦予納西亞的心愿以圓滿的結局,但把同情和關心留給了賣氣球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