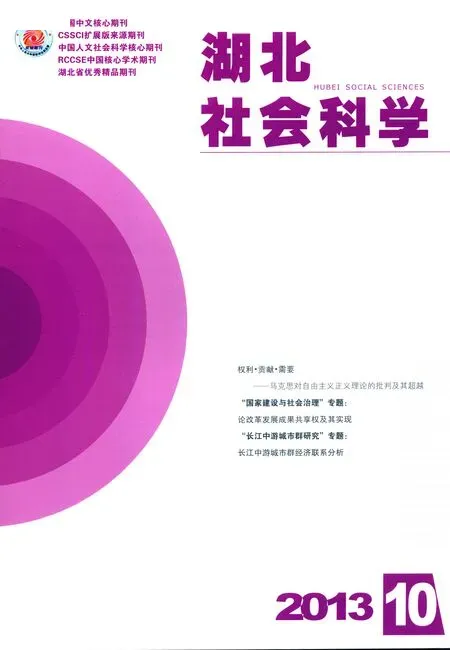《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明確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王德山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70)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明確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王德山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70)
違約可以導致精神損害,且因違約導致的精神損害均集中發生在消費合同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盡管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但仍屬于侵權責任范疇。責任競合并不能周全地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因此,該法不但應賦予消費者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權利,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確賦予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以最大限度地方便消費者主張權利,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違約;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在合同法領域,合同當事人可否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并無明確的規定,理論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違約行為能夠導致非違約方的精神損害,而這種情形均集中發生在消費合同領域。因此,筆者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應當明確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非違約方有權請求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一、我國目前關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現狀
1.立法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現狀。
我國立法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僅限于侵權責任領域。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22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精神損害賠償。在此之前,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侵害人身權以及特定的物而導致精神損害的,應予賠償。此外,有學者認為我國《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的“賠償損失”包括賠償精神損失。還有學者認為,《產品質量法》第32條規定的撫恤費、《消法》第41、42條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國家賠償法》第27條規定的死亡賠償金,在性質上均視為精神損害賠償。
但在違約責任方面,我國現有法律對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迄今還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通說認為,我國《合同法》第107條、第112條等規定,違約責任的形式僅限于財產損害賠償,而不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只是根據第122條規定,在構成責任競合的情況下,受害人可以依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2.理論界對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不同主張。
理論界對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其一是否定觀點。目前不少學者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持反對觀點,認為在違約責任場合,賠償損失僅限于財產損失,不應包括精神損害,受害人若主張精神損害,只能在侵權中提出。“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應作嚴格的區分;合同的訂立與履行只與當事人財產上的得失有關而與其非財產法益無關;對于人身傷亡、精神損害等非財產法益的損害應由侵權行為法加以救濟”。[1](p339)《合同法》第122條違約與侵權競合理論的規定可以解決當事人在違約中遭受精神損害的救濟問題,違約中也適用精神損害的賠償使得競合理論失去意義。除上述理由外,反對的理由還有:①精神損害是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難以預見的;②精神損害十分主觀,又無市場價值,其存在與否以及損害的大小難以判定,更難以通過金錢加以確定;③廣泛承認精神損害會使人的非財產法益被過度“商業化”而貶低人格,并且會使精神損害賠償案件劇增,加重債務人及法院的負擔而無法予以規范控制;④《民法通則》在侵權民事責任的范疇中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而在違約責任中并未作出相應規定等。[2](p14)
其二是肯定觀點。有學者認為,具有侵權性質的違約行為致人以非財產損害時,即使提起合同之訴,也應獲得賠償,并對反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理由進行了一一辯駁。肯定觀點認為,“從理論上看,當事人通過簽訂合同期望實現一定的利益,也可能是財產上的利益,如買賣合同;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利益,如保管骨灰盒的合同。”“無論是違反合同的主義務還是附隨義務,都有可能導致精神損害的發生。”“當精神利益由于侵權行為受到損害時,應承擔侵權責任,而當精神利益易置于契約中時,當違反契約的結果使該精神利益受到損害,同樣,應肯定違約責任中的精神損害的賠償。”[3]
但持肯定觀點的多數學者主張,在合同領域,一般情況下不可主張精神損害的賠償,只是在某些特定類型的合同違約中允許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國可以借鑒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的做法,原則上不允許在違約之訴中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但例外地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的場合以及在一些依通常觀念可預期到容易引發非財產損害的特定類型的合同場合,允許債權人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此外,依據自愿原則,當事人對于違約可能造成的非財產上損害事先約定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金,原則自屬有效。[4](p47)
3.司法實踐中判例。
關于司法實踐中對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不少學者認為,各地法院在處理違約案件時,法官根據案情,作出不同的處理,同一類型的案件在不同法院,審理的結果完全不同,有的法院支持當事人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有的法院則不予支持。“實踐中,法官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為求得個案正義,不乏創造性的突破,例外地在合同訴訟中承認精神損害的賠償。”[5](p124)如此這樣既有悖于法律的統一性和嚴肅性,也不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但筆者針對學者認為屬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眾多相關判例研究發現:第一,這些判例的確與合同有關,因一方違約而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精神損害;第二,該類精神損害均存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情形;第三,該類判例中,極少有案例中的受害人明確以違約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特別是法官在判決中明確依據《合同法》某一條款規定而判決給予受害人以精神損害賠償案件極其罕見。換句話說,司法實踐中,真正意義上的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判例基本上不存在,僅是學者的主觀歸論而已。由于該類案例均存在責任競合現象,學者便主觀地將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認定為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筆者認為,當事人并未明確主張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判決中也未明確引用《合同法》的規定,而基本上都適用《民法通則》第106條等規定判決精神損害賠償。因此,我們不能武斷的認定為違約精神損害賠償,事實上該類判例仍應屬于侵權責任的精神損害賠償。
二、《消法》應明確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筆者主張,在違約責任中,以財產損害賠償為原則,精神損害賠償為例外。而這種例外就是在《消法》中明確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賦予消費者以違約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
《消法》修正案公開征集意見稿第22條規定:“經營者有侮辱誹謗、限制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權益的行為,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該條雖然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但仍未規定為違約精神損害賠償,仍然是侵權責任范疇。如果《消法》僅規定消費者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但沒有明確規定根據合同請求違約精神損害賠償,那么,消費者在諸多領域的精神損害仍將得不到賠償。因此,筆者建議,《消法》中應當將精神損害賠償明確規定為違約性質的精神損害賠償。當然,如果符合侵權責任的,將構成責任競合,消費者可以主張侵權性精神損害賠償。
三、《消法》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理論分析
在《消法》中應當明確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賦予消費者以違約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不但必要,而且對消費者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1.消費合同的特性決定。
對于違約精神損害賠償,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僅針對特殊類型的合同允許受害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學者有關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合同類型有著不同的歸納,有的學者采取列舉法,列舉了可以適用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合同類型;有的采取概括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學者所列舉的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合同類型,總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種:醫療服務合同、婚禮服務合同、培訓合同、旅游服務合同、導致人身傷害合同以及處理尸體、骨灰等無法替代的其他遺物為內容的合同等。除上述合同外,有學者還列舉了承攬合同、美容服務合同、保管合同等。
對于概括式的合同類型,學者也有不同歸納。有學者認為,下列合同應支持違約精神損害賠償:①提供精神享受為目的的服務合同,如旅游合同;②以特定財產為標的物的合同,主要包括加工承攬合同、保管合同等;③以解除痛苦或麻煩為目的的合同等,如婚慶合同等。
有學者根據合同目的,把合同劃分為期待經濟利益合同和期待精神利益合同,對于前者,即純粹的商業合同,合同目的是為了金錢利益,一般來說,違反這種合同僅能被視為商事交易的風險,法院不支持此類合同的非違約方基于違約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所謂期待精神利益合同是指合同一方基于獲得精神利益的目的而與他方訂立的合同。如觀看演出合同、旅游合同、美容美發合同等。在期待精神利益合同的情形下,違約方的違約行為導致了非違約方的期待精神利益的喪失,而且這種損害達到了一定程度,對這種精神損害不予以賠償不足以達到公平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予以物質賠償。與此相類似的觀點是,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總的來說僅適用于具有特殊意義為合同目的的案件,屬消費合同或民事合同范疇,合同的標的一般是提供游樂、休閑、心理安慰、醫療服務、飲食服務等,以及其他有關由于違約造成肉體傷害所帶來的嚴重的精神痛苦的案件,而純商事合同應排除在外。
分析上述理論界所列舉或者歸納的合同類型,以及實踐中因違約而發生精神損害的案例,可以看出,受害人能夠主張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合同,均存在以下共同的特點。
第一,該類合同無一例外地發生于消費領域。受害人(消費者)一方訂立合同并非從事商事活動,其訂立合同的目的并非獲取經濟上的利益,而是接受經營者提供的服務(消費買賣除外),以取得心理上或者說精神上的滿足,或者解除、減少自身的麻煩。如旅游合同、婚慶合同。
第二,該類合同一般均集中于一方當事人(經營者)向另一方當事人(消費者)提供服務性質的合同,合同的標的多為服務行為。該類合同要么單純違約即可導致非違約方的精神損害。如,旅游合同、婚慶合同等;要么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因違約而侵害非違約方的人身權或者具有特殊意義的財產并導致非違約方的精神損害,如美容合同、照片沖洗合同等。
第三,受害方均為自然人,而不是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特別是受害人不是商事主體。通說認為,法人不作為消費者主體,特別是法人無心理活動,故不存在精神損害的問題。因此,法人不能主張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第四,大多數消費合同,因合同訂立的目的是取得心理上或者說精神上的滿足,或者解除、減少自身的麻煩。因此,違約后果的共同特點是,經營者一旦違約,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并非財產損害或者單純的財產損害,而受到損害最為嚴重、最突出是當事人的精神損害,而財產損害往往是次要的。如美容合同、醫療服務合同等,因違約方違約而侵害另一方當事人生命健康權,由此給受害人造成最大的是精神痛苦。
我們雖不能說凡是消費合同都將產生精神損害,但不難看出,因違約而導致精神損害的合同無一例外地都發生在消費合同領域。
2.單純違約可以導致精神損害。
違約責任是否包括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取決于違約行為能否造成精神損害。精神損害的表現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喪失或減損,這種損害的產生可以來自于生理的損害,可來自于精神、心理的損害。[6](p190-191)通過實踐中大量的實際案例分析,“違約行為完全能夠導致當事人的情緒、感情、思維、意識等精神活動的障礙,使人產生憤怒、恐懼、焦慮、沮喪、悲傷、抑郁、絕望等不良情感,而這些正是精神損害的表現形式。”[7](p41)
有這樣一則案例:新郎孫某與新娘賈某2005年在某酒樓舉行婚禮,某婚慶公司負責婚禮事宜。婚禮定于11點18分正式開始。就在婚禮即將正式開始,新郎、新娘登場之時,酒樓大廳里陸續進來了20多個腰纏白布頭戴孝帽的人。酒樓工作人員不但沒有上前阻止,而且還將他們領到里面餐桌就坐,婚禮不得不因此終止。新郎找酒樓負責人,大約過了20分鐘,酒樓才有人出面來解決此事。新郎經過一番好言勸說,辦喪事的人終于同意改換到其他的飯店。而此時已過了11點18分,婚慶又重新安排在11點38分開始儀式。婚禮結束后,新郎拒絕付款。某酒樓將孫某起訴到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孫某當庭提出反訴,要求某酒樓賠償自己精神損失20萬元。孫某稱,受該事件強烈刺激,新娘的爺爺因生氣而去世,奶奶癱瘓。孫某本人也因受該事件刺激突發精神病,曾多次去醫院就診。孫某與賈某于當年協議離婚。
本案中,新郎孫某與酒樓之間合法成立合同關系,酒樓有義務為孫某提供適合于舉辦婚禮的場所以及衛生的飯菜等。特別是盡管合同中沒有明確約定,但按照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酒樓負有一個附隨義務,即保證在其酒樓內不發生撞喪事件,孫某舉辦婚禮期間,酒樓有義務阻止披麻戴孝的人員進入酒樓,且酒樓也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而本案中,酒樓的工作人員對進入酒樓的披麻戴孝人員不但不阻止,反而將他們引入婚禮現場,導致撞喪事件發生。很顯然,酒樓雖無侵權行為,但正是其違約行為給新郎、新娘及其親屬造成了極大的精神痛苦,也正因此而導致新娘的爺爺病世,奶奶癱瘓,孫某本人突發精神病,孫某與賈某最終離婚等嚴重后果。
分析違約所造成的后果,大體上表現為三種情形:①違約單純造成財產損失或者經濟損失,不會給當事人造成精神損害。這類合同一般是純粹的財產交易型合同。②違約給當事人造成經濟損失,同時造成人身傷害,并由此導致精神痛苦,理論上即所謂的加害給付。這種合同的類型繁多,既可以是財產交易類合同,也可以是非財產交易類合同。③違約單純給當事人造成精神損害,而無財產損害,這類合同都基本發生在消費領域,且往往是提供服務類的合同。如婚慶合同等。
因此,違約不但可以導致非違約方的精神損害,而且最重要的是單純的違約行為可以造成非違約方的精神損害。本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3.因違約而導致的精神損害均發生在消費領域。
長久以來,我國民法學界一直認為,合同法只涉及合同當事人的財產得失,合同的履行與當事人的人身安全、精神利益以及其他人格利益無關。但事實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目前出現的一些新型合同已經不是純粹的財產交易。因此,合同法也不應當是再單純調整財產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
第一,除消費買賣之外,實踐中相當數量的合同,消費者訂立的合同的目的是接受經營者提供的服務,如旅游合同、婚慶合同、美容合同等,消費者的目的要么是得到精神享受,達到心理滿足,要么是為了減少自己的麻煩,減輕自己的精神負擔或身體負擔,或者是各方面的綜合。總之,該類合同中消費者的訂約目的并非從事財產交易。
第二,既然許多消費合同的目的是取得精神享受,因此,經營者一旦違約,消費者訂立合同所預期的目的必將不能完全實現或者根本未能實現,同時不少違約行為導致消費者遭受精神痛苦。
第三,消費合同領域的一方當事人必定是自然人。按照目前通說,《消法》所調整的消費者必須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而自然人是一個有心理活動的生命體,一旦經營者違約,最容易給消費者造成精神痛苦,因此而造成精神損害。
4.責任競合不能周全地保護受害人。
反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責任競合理論,即因違約而造成的精神損害,受害人可以基于侵權之訴而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并以此否定合同責任上的精神損害賠償。但事實上責任競合理論并不能周全地保護受害人。
(1)非責任競合下的“真空地帶”。違約和侵權均可能造成受害人精神損害,具體來說,對于精神損害可能存在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單純由侵權導致的精神損害;二是單純由違約導致的精神損害;三是違約與侵權并存導致的精神損害。[3]合同法的競合理論即是指第三種情形,依據現行《侵權責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在侵權或者責任競合的情況下,受害人均可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但在第二種情形下的精神損害,即某些合同中,一方當事人造成另一方精神損害的行為只構成違約而不構成侵權時,受害人將無法通過責任競合來提起侵權之訴,并進而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由此出現非責任競合下的“真空地帶”。
責任競合理論能夠解決違約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而且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所有產生精神損害的違約行為構成侵權。然而,精神損害的產生并不和侵權產生必然的聯系,并非惟有侵權行為才能導致精神損害,單純的違約同樣可以導致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而依據我國現有法律,當某一違約行為造成了精神損害但未構成侵權時,受害人因無法證明其何種人格權受到損害,也就難以通過責任競合來提起侵權之訴,并進而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在旅游、骨灰盒保管、產婦在醫院生產、演出等合同場合,侵害了什么權利?不易確定,只好求助于一般人格權。這雖然可以,但存在著裁判者向一般條款逃逸的可能。合同法若設置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嚴格限定得以產生精神損害賠償的合同類型,以及具體的構成要件,有助于防止裁判者向一般條款逃逸。”[8](p50)正因如此,實踐中合同一方有違約行為,非違約方存在精神損害的客觀事實,但依法卻不能得到賠償的問題。而這種情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型消費合同不斷出現將會越來越突出。若強制受害人適用侵權責任以求救濟,對受害人的保護顯然是很不利的。
任何法律皆有漏洞,“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時起,即逐漸與時代脫節。因社會生活不斷發展變化而法律條文有限,欲以一次立法而解決所有法律問題,實屬不能。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現實會不斷地提出各種各樣需要在法律上加以解決的問題。”[9]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固守原有理論和法律規定,而應當順應社會的不斷發展,從方便受害人主張權利、充分維護消費者權益出發,及時修正法學理論的不足,填補法律漏洞,以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強制受害人選擇侵權救濟不利于對受害人的保護。違約方的違約行為構成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依據《合同法》第122條之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可以選擇違約之訴,也可以選擇侵權之訴。表面上看對受害方有利,但事實上因違約之訴不能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所以受害方要得到精神損害賠償,只能主張侵權之訴。眾所周知,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在歸責原則、舉證責任、義務內容、責任構成要件、免責事由、責任范圍、訴訟時效等多個方面具有顯著的不同。因此,當事人提起違約之訴還是侵權之訴對其利益得失具有重大影響,如果不允許當事人請求違約責任上的精神損害賠償,則無異于強制受損害方在受到精神損害的情況下必須提起侵權之訴,這與《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及民法學界允許當事人行使選擇權的通說是相違背的。故競合理論事實上并沒有給受害人提供選擇的權利。
(3)責任競合與責任聚合。競合理論認為,不法行為人的違法行為的多重性必然產生雙重請求權。但受害人雖能選擇請求權,卻不能在法律上同時實現兩項請求權,因為實現兩項請求權意味著受害人將獲得雙重賠償,這對不法行為人來說,將使其負有雙重賠償責任,顯然有失公平;而對受害人來說,因為他將獲得雙重賠償而得到一筆本不應得到的收入,從而將產生不當得利。但有學者認為,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并非責任競合問題,而是屬于責任聚合,判處違約方承擔財產損害賠償與精神損害賠償,并未加重違約方的賠償責任。該觀點認為,按傳統理論認為,違約與侵權存在競合的問題,其實質是因為違約的財產責任與侵權的財產責任是合同法與侵權行為法所保護的共同部分,產生請求權的競合。但在特定違約行為中,違約人既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權,又侵害了他人的精神權利,受害人當然享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而違約導致的精神損害與違約的財產責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責任,故應導致責任的聚合而不是競合。筆者完全贊同該觀點,在違約責任領域,違約的財產責任與非財產責任事實上屬于責任的聚合,而并非責任競合,不應以責任競合理論來否定受害人違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
不管是違約侵權或者侵權違約而導致受害人精神損害,還是單純的違約導致精神損害,其共同的特征是雙方當事人均存在合同關系,是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了精神損害。精神損害賠償同屬損害賠償的范疇,與財產損害賠償一樣,我們應當堅持遵守“有損害即有賠償”的原則,而不管這種損失是由何種不法行為所造成。既然精神損害發生在合同之中,因違約而引發,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在違約責任中支持受害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而非要強制受害人主張侵權之訴?該主張事實上并無令人信服的理論依據,應當說完全是一種人為障礙。
四、《合同法》與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雖然主張違約精神損害賠償,但筆者反對在《合同法》中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第一,違約責任畢竟不是侵權責任,如果在《合同法》中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允許非違約方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必將破壞《合同法》現有的合同責任體系的完整性。第二,如果《合同法》中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將會給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造成混亂局面。從立法技術角度,如果對可以主張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合同類型采用列舉式,將會存在掛一漏萬的情形,達不到保護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如果采用概括式給予規定,則將出現理解不一,特別是實踐中存在大量的無名合同,將最終導致法律適用不一,破壞法律的統一性和嚴肅性。基于上述理由,筆者反對在《合同法》中規定違約精神損害賠償。
正如前面所述,發生違約精神損害的情形均發生于消費領域,而非消費領域的純商事合同并不發生精神損害的問題。所以筆者建議在《消法》中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作出明確規定,使《消法》中有關違約責任的規定成為《合同法》的特別法予以適用,與《合同法》第113條第2款規定銜接起來,并在以后修訂合同法時將該款修訂為“經營者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有關法律責任,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這樣既可以維持現行《合同法》法典的合同責任體系不變,又可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使得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法律上得以確立,且也不會因對法律規定的理解不一而導致法律適用的混亂,有利于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五、結論
社會的變遷終究要導致法律的發展。自20世紀以來,合同法從形式正義走向實質正義,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公司、大企業對生產和經營的壟斷不斷加強,消費者與其相比,在交換關系中明顯處于弱者的地位,各國立法都加強了對消費者的保護。侵權可導致精神損害,而違約也同樣可以導致精神損害,違約責任同樣屬于民事責任的范疇,與侵權責任同屬一個領域,其目的均是對受害人的救濟和補償。我們沒有理由將二者絕對割裂開來,侵權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而違約就不允許精神損害賠償。如果對同樣的精神利益的損失,追究行為人的侵權責任就可以獲得賠償,追究行為人的違約責任就不能獲得賠償,顯然在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之間是一種失衡。
筆者建議在《消法》中明確規定:“經營者因違約致消費者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賠償其因違約所遭受的精神損害。”
[1]王利明.違約責任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2]葉知年,陳埔軍.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研究[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1).
[3]蔣金泉,袁彩虹.論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必要性[EB/ OL].http://nc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2006-11-13.
[4]韓世遠.違約損害賠償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葉金強.論違約導致的精神損害賠償[J].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2,(2).
[6]王利明,楊立新.人格權與新聞侵權[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
[7]陳雪強.違約精神損害賠償的理論分析及其類型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8]崔建遠.論違約的精神損害賠償[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1).
[9]郭成,黃娟敏.違約精神損害賠償之法理分析[EB/OL]. http://www.ftcourt.gov.cn/Detail.aspx,2005-5-30.
責任編輯 周剛
DF529
A
1003-8477(2013)10-0162-05
王德山(1963—),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北京市教委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京市文物藝術品拍賣現狀與法律制度完善”(SM20121003800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