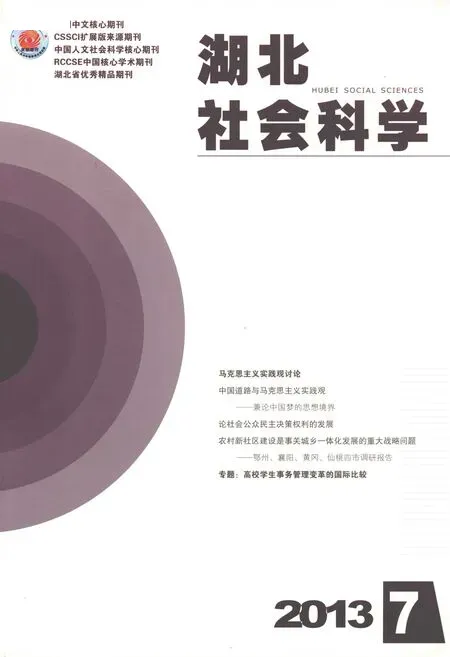從晚清到“五四”:論游記文學中的世界圖式變遷
李嵐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205)
人文視野歷史·文化
從晚清到“五四”:論游記文學中的世界圖式變遷
李嵐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205)
從晚清到“五四”前后,大量的域外游記在散文領域中涌現,成為文學領域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這一時期的游記顯影了中國社會觀念變革之心路。它是傳統中國人從自我封閉狀態逐步展開“看世界”旅程的史料,并不斷促進著社會觀念的覺醒。游記帶來了視野的開闊和視角的變更,從觀念上進行著對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反映和改造,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一時代文化格局的建構和變遷。通過對從晚清到“五四”時期游記文學的歷史線索梳理,考察其觀念變更的內在邏輯,并評價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
晚清到“五四”;游記;“世界景觀”;異域想象;
晚清時期,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中國社會歷經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國中士人學子遠游西方認識世界,或探索新知、求學避禍,或奉命出使、察考政俗;其間所歷,以日記或游記的方式記錄下來,結集成篇,一時蔚成風氣。僅清末王錫祺輯錄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便收錄清代地理著作1420種,其中游記有六百多篇;而到了“五四”前后,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里,散文領域內“打頭的是海內外的旅行記和游記”。[1](p10)據賈鴻雁的《中國游記文獻研究》統計,民國時期出版的游記集共608種,其中民國時期創作游記集和編選游記集570種,包括國內游記和游記集333種,域外226種,余者兼收中外。這還不包括發表在報刊上的游記和未入專集出版的大量游記。
這一時期的游記關注社會生活,長以景觀寫心,眼中筆下,情景互見。從晚清到“五四”的游記文學畫廊,一路看來如移步換景,其情其狀,顯影了中國社會觀念變革之心路。它是傳統中國人從自我封閉狀態逐步展開“看世界”旅程的史料,并不斷促進著社會觀念的覺醒。游記帶來了視野的開闊和視角的變更,從觀念上進行著對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反映和改造,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一時代文化格局的建構和變遷。本文擬通過對從晚清到“五四”時期游記文學的歷史線索梳理,考察其觀念變更的內在邏輯,并評價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
一、晚清游記的文化視野擴張——從“天下景觀”到“世界景觀”
晚清域外游記之初,多記載“獵奇”,以描述“異域”風光和西方近代科技為主。斌椿在1866年的《乘槎筆記》中多次提到現代化交通工具,稱自行車為“木牛流馬”,火車如“奔馬”,電梯“各法奇巧,匪夷所思”;曾與他同行的張德彝出國多次,從1866年至1878年的游記皆名《述奇》。對先進“器物”的驚奇是晚期每個出國的中國人都會有的反應,即便是有遠見卓識的王韜也未能免,“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車,雖都中往來,無不賴輪車之迅便。”[2](p112-113)只是,王韜、郭嵩燾等開明派人士的游記不僅關注這些“器物”,他們還開始觀察外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在王韜1867年所作《漫游隨錄》、郭嵩燾1876年所作《使西紀程》均有記載,歐洲諸國繁華昌盛,“天朝上國”在洋人眼中不過是“半開化”國家,他們感到了中華文化的危機。關注焦點從“器物”到“體制”的轉移,正是傳統知識分子現代性意識萌芽的表現。
最先出現在晚清游記中的西方世界,是一個“理想世界”:繁華、新鮮、先進、富有;這不能不使“外來注視者”反思的文化身份和國家前途問題;他們對此通常有種微妙的心態,即極力強調中國悠久的文化,不論怎樣欽佩西方的科技、藝術和體制,但都認為“文章禮樂”遠不如中華。面對現實的觸動,對自身文化反思的程度可以見出胸襟的深淺、見識的高下:王韜欣賞西方的科技,同樣出國游歷的保守派劉錫鴻,則沒有王韜的眼光,他認為火車不能利國利民,而且鐵軌會損壞他人田地墳塋,必將為民眾反抗,屬于“奇技淫巧”。他在游記中說,工匠的事情,文人不必勞心,關心技巧不是正途,“非謂用功于身心,反先推求夫一器一技之巧也。一技一器,于正心修身奚與?”。[3](p28)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和國家政策長期重道輕器,把科學技術蔑稱為“奇技淫巧”,“奇技淫巧”是中國人在西方最先被震撼的見聞,卻被依然輕視,劉錫鴻的觀點是相當有代表性的,其認知視野正是長期農業社會和專制制度中形成的“天下景觀”。
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是一種“天朝型世界觀”,中國以外,莫過夷狄戎蠻,“異域”一詞本身就意味著邊緣、差異和特殊。我目即中心,目極即天下,天下即世界,是一種“我族中心”的思維模式。晚清國人在“睜眼看世界”之后對天朝型世界觀的依然堅持,既是一種對既有文化優勢心態的延遲,又是傳統社會秩序對西方意識入侵作出的應急反應。同一時期的郭嵩燾由于其公使身份,當他的游記《使西紀程》直言英國“政教修明、乃文明古國”時,換來朝野上下罵聲一片,稱其“事鬼”,因為他的觀點是對人們心中的天朝世界觀的極大冒犯。
但是,總有變化在行旅間、游記中出現,這種變化是緩慢的、潛移默化的。早年王韜是堅持科技是“奇技淫巧”的,出國游歷后,他在《弢園文錄外編》、《弢園尺牘》中分別改稱“奇跡瑰巧”和“奇技異巧”了,一個詞的變化不僅反映了王韜個人對科技看法的轉變,更反映了社會觀念中價值系統的逐漸轉變;我國第一個赴西方學習社會科學并獲博士學位的薛福成在1890年的一篇日記里寫道,他本不相信郭嵩燾對西洋政教民風的贊美,詢問陳蘭彬、黎庶昌等人,都說郭嵩燾之言不假,他親自赴歐洲后,“始信侍郎之說”。到了20世紀初,在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游記》和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兩部游記中,當繁華已熟視無睹,西方“理想世界”消失了,真實的世界呈現出來,歐美也有貧病污穢,絕不是“豪富逸樂若神仙”,梁啟超更反思了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不足,照搬到中國必然無益。
從斌椿的《乘槎筆記》到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相隔近半個世紀的游記的變化所展示是華夏民族心理在新的時代狀況下所呈現出的變化,是反映社會觀念變遷的一系列文字景觀。晚清域外游記通過集體行為初步構成了對西方社會的想象和對中國社會的重塑。
二、“五四”前后游記的視角增殖——“世界景觀”的多維度
1912年以來,中國人前往外國留學的風潮日盛,單純傾聽海客談瀛洲的時代過去了。在“五四”前后的游記里,人們比較自覺地反思中西方文化差異,動蕩的世界局勢引發了行旅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思考,思考社會改革之路,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歐洲、1917年的十月革命、新興國家蘇聯,一連串的世界的變化讓中國人困惑。
經過一戰,繁榮的歐洲工業社會滿目瘡痍,從晚清中國行旅者開始建立起來的歐洲集體想象從某種程度上講已經不再異化,一些駐外記者和行旅者都寫了不少關于戰時歐洲的游記在國內發表,例如徐鐘佩的《倫敦和我》、《英倫歸來》,王云五的《戰時英國》等,在游記中不乏對戰后歐洲“山窮水盡”的描寫。
對于日本,態度比較復雜,主要是亞洲相近文化態度使然。有的游記態度友善親和,比如周作人的作品;也有如郁達夫在20年代所寫的《歸航》中那樣激烈,稱之為“強暴的小國”、“世界一等強國”、“國民比我們矮小,野心比我們強烈”,并透露出《沉淪》中那種頹廢、憤懣、感傷的個人情緒;還有的游記呈現了貧弱大國對富強小國的鄙夷態度,如郭沫若在1922年所寫的《今津紀游》中說道:“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凈,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象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凈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為東洋第一的模范國家。”[4](p308)另一方面,中國人在異域的地位依然不高,受到歧視的事情在此時乃至以后很多年的域外游記中比比皆是。
總的來說,此時的域外游記反映出三種與以往不同的傾向,這三種傾向雖然是游記中行旅者的個人觀點,但是真實地體現了國內思潮的紛紜涌動。
第一種傾向是對西方近現代文明的反思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申,用西方的思維方法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作品就是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世界局勢動搖了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中體現的對歐美文明的信心,他自籌經費,與幾位朋友到歐洲游歷。歐洲的現狀沒有給梁啟超太多的政治上的啟迪,卻給他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機會。“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5](p7),歐洲人中“許多先覺之士,著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制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5](p15)所以他認為要重新確立中華文化的地位,西方文化是物質的,東方文化是精神的,提出“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的中西融合的文化互補觀。[5](p35)《歐游心影錄》在國內發表后立即推動了當時已進行了約10年的有關東西文化優劣的爭論。
第二種傾向是向東方同類文化取經,即學習日本的一些發展方式。周作人在1919年7月訪問了日本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基地新村,非常欣賞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寫了《訪日本新村記》,把新村視為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他在游記中詳細記錄了新村的生活方式和運作模式,“深信那新村的精神決無錯誤”,“對于新村運動,為中國的一部分人類計,更是全心贊成。”[6]周作人的這篇游記詳盡寫實,坦言日本新村實驗的現狀和不足,但他聲明新村的前景可觀,主張用新村這樣平和的方法代替暴力手段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在這次訪問之前,周作人已經在國內大力鼓吹新村模式,他的一系列文章引起巨大的反響,使新村主義有了一批追隨者。
第三種傾向是人們對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興趣。蘇聯的成立無疑給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社會模式,很多人前往蘇聯旅行和考察,尤其是探索國家民族出路的知識分子,蘇聯的社會面貌比山水風光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1920年,瞿秋白被《晨報》聘為記者,到蘇聯訪問考察,寫下了《餓鄉紀程》(即《新俄國游記》)和《赤都心史》兩部游記,在《赤都心史》里,瞿秋白考察了俄國革命后的經濟狀況,描繪了蘇聯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全國集權狀況,對蘇聯臨時政策的優缺點能夠客觀的分析。總的來說,瞿秋白在游記中表達的是一種對蘇聯的向往和禮拜,從某種角度上,這時的蘇聯代替了19世紀歐洲社會想象,成為一個新的期待點。
但是也有人并不欣賞蘇聯模式。1925年,徐志摩到蘇聯游歷,寫作了游記《歐游漫錄》,字里行間多有對蘇聯的懼怕,“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文明的骸骨間,是人類鮮艷的血肉間”,整個社會沒有“新文化”、“舊文化”可言。[7](p258)與徐志摩文化淵源相近的胡適與徐志摩的觀點又不同,他在1926年途經莫斯科后感到,“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的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所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8](p74-75)他們感受的相左主要是因為各自所取的觀看立場和角度有所不同。
三、“交互認知”渠道:游記的異域想象與“自我”真相
從晚清到“五四”,使游記這種文體參與到中國人對于世界的想象和認知過程中的渠道,是人們在游記中對異域想象的營造與“自我”真相的揭示。游記一方面真實地記錄了改變的過程和過程中的心態,一方面在景觀和主體之間進行間接的溝通和互動。前文已經論述了游記里所呈現的民族和世界觀念,這些觀念是經過行旅者和游記以及作為對象的現實本身多元共生而形成的結果,三個來源缺一不可,共同產生了中國人的異域想象。對于游記的閱讀者而言,事實只是被個人陳述的,是始終缺席的,通過游記的敘述和通過行旅者的凝視一樣,都是在塑造他者形象,就是進行自我確認。異域想象與“自我”真相之間有一個鏡子式的映照關系,中國人的世界、民族、價值等觀念的改變都和這個映照有關,所以,游記里沒有直接出現的“自我”真相構成了問題的另一面,它表現著行旅者以及當時中國人的自己的理解和欲求。
在晚清的異域行旅之初,以“蠻夷”為主的西方想象尚是社會群體意識的一部分;到20世紀初,行旅者則抱有“西方科技文化先進”之期待視野。當身處其境時,期待視野會有所動搖,但是對西方的美化仍是“五四”前后游記的主流態度。游記往往最能反映一個社會的集體想象物對作者的影響,但同時它又是新的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締造者。
讓·馬克·莫哈認為,異國形象有意識形態式的和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的異國形象是按照自己的社會模式、用本社會話語重塑出來的,把形塑者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投射到作為他者的對象上,通過消解、同化他者讓其適應本社會的價值觀;烏托邦式的異國形象偏于相異性和離心性,是用符合一個作者或一個群體對相異性的看法塑造出來的,目的在于否定形塑者社會的價值觀。[9]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心態是把西方作為他者的,用中華社會的群體價值觀對西方文化進行消解,所以被稱為是意識形態式的。“世界觀”就是一種綜合表現,這種意識形態式的西方形象在閉塞的中國社會中成為自在的和獨立的,泛化為群像,代替了現實的西方,成為閉塞環境里的人們的唯一經驗,據此,對于“天朝型世界觀”在晚清的頑固和“紅毛鬼”一類的套話的長盛不衰,就很容易理解了。
西方的“奇技瑰巧”讓行旅者對西方的印象有了烏托邦式的傾向。王韜在《漫游隨錄》里記錄他看到西方戲劇,“視之甚審,目眩神移,嘆未曾有”,評西方繪畫“技也而進乎神矣。”康有為在《意大利游記》中稱“意人之尊藝術至矣,宜其畫學之冠大地也”,“吾國畫疏淺,遠不如之”。王韜和經世致用的洋務派諸君在接觸到國外政體、軍事、經濟建設、禮儀之后都頗為稱贊,他們大多希望中國也能實現這樣的改革。這些由衷的稱贊和中國社會的群體價值觀是相反的,否定了對西方的傳統想象,站在西方價值觀的立場上,對中國的“天下”、“中心”文化觀提出了質疑,呈現出莫哈認為的烏托邦的形象傾向。這些對外國的描繪構成一個共同的印象:奇異、發達、文明、開化,這個印象在眾多的游記中或深或淺、異曲同工,它是晚清中國人對外國文明的統一認識,構成了一系列“社會集體想象物”,是中國全社會對一個集體、一個社會文化整體所作的同一性或相異性的解釋。
從19世紀開始,人們通過近現代交通工具成規模地接觸到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時,異域的異質性成分大量凸現出來,排拒性的分化體驗成為現代行旅體驗的主要內容,我族與異族、我國與異國,成為行旅觀看的二元對立結構中的兩端,“天下”景觀被“世界”景觀所代替,兩者間差異的突出使得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分界更加清晰,從而有利于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實際上,在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在域外思潮直接涌入中國并發生影響之前,域外游記扮演了傳遞外界信息和引發積極思考的最有效的媒介角色,當這些游記在中國傳播之后,其中對外域的描寫就成為晚清最初的現代國家觀念,他們對東西方異域世界的描述在國內都引起了相當的反響,作為信息媒介傳遞了一系列現代國家形象。而在認識“夷狄”的同時,中國也有了初步對自己的反觀。這種反觀是完全不同于清末“天朝上國”的觀念的,它具備了一定的反思價值,不但意味著嶄新的晚清世界觀念,更直接促進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現代想象和向往。
1912年以后的中國不僅接受了西方文明,更接受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這個時期,國內對異域的態度是比較一致的,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共同完成了這個發達、文明、開化的集體想象物的塑造,并且不再感到奇異,文化心態平和了很多。人們大量翻譯外國作品,在文學、哲學、政治等各個方面被西方滲透,每當有人主張復興傳統文化時,都會引起一定規模的論戰,異域的社會模式和政治理念,總會有人熱衷地試驗和宣傳。可見從社會范圍而言,烏托邦式的西方形象占了主流地位,文明、開化、發達是現代工業西方的形象特征,落后、閉塞、愚昧是農業中國的形象特征,西學直接性地壓倒中學。當然,有一些游記所直接反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烏托邦式的西方形象,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它的文化、體制成為另一個代表先進的想象物,和原有的西方形象并不沖突,因為,同樣是中國人在向異域尋求一種新文明的源泉,用異域的話語方式去側重表現異域的特征,以便顛覆自身文化中假定有害的方面。
相對于異域想象的變化,游記里中國的“自我真相”比較穩定。從晚清開始,人們已經意識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但是還要竭力維護,在多元跨國的文化語境中發生了最直接的現代經驗,如何用這種經驗去進行對近代中國的回顧和文化想象呢?文學和藝術就成為其中賴以支撐的信念之一。然而域外游記對西洋圖景的新鮮描述已經讓他們成為異端。其實作為行旅者,文化身份始終與異域文化是相對的,他們在異域場景的凝視下,更容易被證實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中華身份被確認的同時,進一步被確認的是落后于世界步伐的共同體文化,域外文化就成為中國文化轉型的典范和契機,而他們本人就成為最初的先鋒者,例如劉錫鴻見識短淺,但也不得不承認英國政俗、海防、議院的種種好處。此時他們自我意識里的矛盾與國內態度的矛盾相交織,呈現的是文化轉型期的必然態度。
結語
概言之,晚清到“五四”的游記文學從一個獨特的側面顯示著近現代中國社會觀念和文化精神的演進軌跡。游記中的情與景、對象與視角、自我與他者關系的種種嬗變,成為中國社會和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一個投影,呈現出這個轉型時期的人們認知圖式的轉換、情感方式的更迭和文化思考的深化;同時,現代行旅體驗也推動著傳統文學觀念和技法上的更新,從內容和形式上帶來了全新的期待視野。晚清以來的游記文學作為伽達默爾意義上的“歷史流傳物”,在中國和異域之間相互傳播,接受來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注視、闡釋和“改寫”,作為“視界交融”的媒介發揮著文化參照物的作用,對自我認知和了解他者具有直接的意義;它在記錄社會觀念變化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促進社會觀念變化,并為文學史和思想觀念史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和研究維度。
[1]俞元桂.中國現代散文史[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8.
[2][清]王韜.漫游隨錄·扶桑游記[A].鐘叔河.走向世界叢書[C].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清]劉錫鴻.英軺日記[A].鐘叔河.走向世界叢書[C].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5]梁啟超.歐游心影錄[A].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C].上海:中華書局,1936.
[6]周作人.訪日本新村記[J].新潮.1919,2,(1).
[7]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3卷[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
[8]胡適.胡適文存:卷一[M].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9][法]讓·馬克·莫哈.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周剛
K252
:A
:1003-8477(2013)07-0096-04
李嵐(1979—),女,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2010q14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