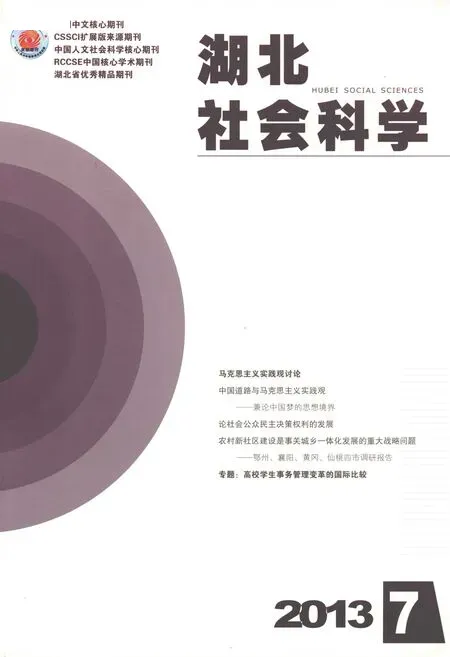唐代中央屯田管理機構探析
張珉,龔先砦
(新疆兵團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法律系,新疆五家渠 831300)
唐代中央屯田管理機構探析
張珉,龔先砦
(新疆兵團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法律系,新疆五家渠 831300)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等成文法典確立了以尚書省為核心的中央屯田管理機構,但實踐中無論是開元二十五年之前還是之后,尚書省在屯田管理體制中的核心地位都難以得到體現,其依法享有的屯田設置處分權被虛置,皇帝直接行使著唐令賦予尚書省的職權。因而,對唐代屯田管理機構及屯田法運行機制的考察不能局限于法律文本,更要關注屯田法律實踐。
唐代屯田;管理機構;行政法制;法律傳統
唐代法制是中國法制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對后世及周邊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完備的法律體系,自然需要一支成熟的官僚隊伍加以實施。屯田法作為唐代法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貫徹落實也離不開一套健全的管理機構。本文擬對唐代中央層面的屯田管理機構略加分析,以加深對唐代屯田法及其運行機制的理解,并求教于方家。
一、以尚書省為核心的法定中央屯田管理機構
唐代法律明確規定的中央屯田管理機構,主要有尚書省及所屬各部(尤其是工部及屯田司)、司農寺、御史臺等。
(一)尚書省及所轄各部。1.尚書省。《通典》載:“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1](p44)可見,開元二十五年令明確賦予尚書省屯田設置的處分權,司農寺及州鎮諸軍所轄屯田的設置均包括在內。尚書省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執行機構,下設六部分掌具體行政事務。《新唐書》稱:“(尚書省)……庶務皆會決焉……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2](p1185)各部不能決斷的大事,都由尚書省“會決”。屯田的設置權由尚書省行使,可見唐代對屯田設置是極其慎重的。2.工部及屯田司。隋朝創立三省六部制時,在尚書省下設立工部,“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3](p774)各侍郎“分司曹務”,屯田事務由工部屯田侍郎專門負責。唐承隋制,工部負有屯田管理職責,史稱“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2](p1201)工部下設四司,“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屯田事務由屯田司執掌。屯田司官吏署置及權限為:“屯田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二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咸取決焉”。[4](p222)可見,工部屯田司是中央專司屯田事務的重要機關,配備近三十名官員,從“天下屯田之政令”到屯田生產經營中的具體事項等諸多事務均在其職掌之內。3.戶部。唐代后期,戶部也參與屯田管理。后周廣順三年(953)詔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后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5](p9488)這一詔敕表明,“唐末”時戶部參與屯田管理,所屬“營田”“不隸州縣”,由“戶部別置官司總領”。戶部營田務的設置時間尚存爭議,除前述“唐末”之說外,尚有“唐后期”、[6](p2643)“唐宣宗時”、[7](p278)(“元和十三年七月以后”[8](p995)等多種見解,但其設置的廣泛性與普遍性是有共識的——“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中國歷史大辭典》稱:“唐后期,戶部在全國專設營田務,以農民強戶與高貲戶耕種營田,免其地方徭役。”[6](pp2643)《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大辭典》也認為,各地營田“由中央戶部總領,由各道設置營田務分別管理,不隸州縣”。[8](p996)鑒于營田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屯田,可以說,唐代后期戶部也是一個重要的屯田管理機關,但具體事務另設何種專門機構加以管理,以及屬吏的詳細情況,則不見諸史籍記載。4.尚書省其他各部。除工部、戶部外,屯田還涉及尚書省刑部、吏部、兵部的職責。如刑部“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凡倉庫出納……和糴屯收亦勾復之”。[9](p1839)可見,屯收勾復之職由刑部比部司掌管。而屯官的考績,則由吏部考功司負責,“耕耨以時,收獲剩課,為屯官之最”。[4](p43)此外,屯田事務與兵部職掌也有一定的關聯。如田令規定:“諸屯之處,每收刈時,若有警急者,所管官司與州鎮及軍府相知,量差管內軍人及夫,一千人以下,各役五日功,防授(守)助收。”[10]各地屯田若差管內人夫助收,往往涉及兵曹職掌。《開元年間西州諸曹符帖目》載:“兵曹符:為差輸丁廿人助天山(軍)屯事。”[11](p363)文書所載即系差遣二十人夫防守助收上報兵曹之事。既然屯田事務涉及地方兵曹,其最高主管機關兵部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又如,《唐六典》載,凡將帥出征,兵滿萬人以上,“置營田副使一人”。[4](p158)營田副使是主管屯田事務的地方官員之一,其職務與將帥出征及兵員數量密切相關,應當事關兵部職掌。
(二)司農寺。前引開元二十五年令載:“……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這表明作為九寺之一的司農寺也具有屯田管理職責。明人丘浚曾言:“我朝之制,……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12](p320)清人黃輔辰亦稱:“唐設農寺,專領其事。”[13](p53)可見,唐代司農寺確有屯田管理職責。此外,屯田收獲物的管理關涉“倉儲委積之事”,與司農寺卿之職掌緊密相關,因此司農寺也屬于唐代中央屯田管理機構。從權限上看,司農寺職掌較工部屯田司具體、細致,屯田司“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而司農寺直接管理諸屯。
(三)御史臺。御史臺是唐代最高監察機關,所屬察院設有監察御史,掌管屯田勾檢復核之事,因此御史臺也屬于中央屯田管理機構。《舊唐書》載“監察掌分察巡按郡縣、屯田、鑄錢、嶺南選補……”,[9](p1863)《新唐書》及前引田令亦稱“御史巡行蒞輸”,可見監察御史對于屯田法制的運行起著監察督促之責。《通典》載:“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1](p676)此即監察御史參與屯田管理之例證。又如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9](p3589)顏真卿兩度以監察御史充任“覆屯交兵使”,史籍所載之具體事務雖與屯田無直接關聯,但御史監察屯田事務的職權仍可見一斑。至唐代后期,皇帝詔敕仍強調御史對屯田情況的監察。敬宗即位后下詔,“軍屯營種,有侵占丁田課役稅戶者,宜委御史臺切加訪察”,[14](p719)即是明證。
可見,唐代確立了一套比較龐雜的中央屯田管理系統。這套系統中,尚書省掌管屯田設置的最高權力并會決重大屯田事務,各部分工負責管理具體屯田事務,監察御史負責勾檢復核、察舉非違,司農寺負責所屬屯田的具體管理,其他機構在權限范圍內對尚書省及各部的屯田管理予以配合。這套系統具有明顯的分散性,盡管屯田在唐代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中央并沒有一個獨立的機構專門負責相關事務的管理。工部屯田司雖以“屯田”命名,但其職掌并不限于屯田事務,還包括“在京文武職事官”、“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的職分田,以及“在京諸司”的公廨田等官田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工部屯田司級別低下,其郎中秩僅從五品上,不足以擔當全面管理屯田事務的職責。尚書省作為最高政令執行機關,且長官兼帶宰相銜,自然在中央屯田管理機構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尚書省核心地位的虛置與皇帝對屯田事務的直接控制
盡管尚書省在制度層面居于屯田管理的核心地位,但在唐代屯田實踐中,這種核心地位卻難以顯現。依唐令規定,屯田的設置由尚書省處分,這是唐代成文法典規定的尚書省有關屯田管理的最高權限。然而,唐令的這一規范在實踐中卻是另一種形態。
(一)開元二十五年令頒布之前的狀況。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之前,屯田的設置往往并非由尚書省處分。如武德初,薛大鼎“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2](p5621)此時李淵登基不久,法律制度不可能如后世完備,薛大鼎所開屯田是否經過尚書省的“處分”無從知曉。同時期的竇靜屯田則顯然并非由尚書省處分:“武德初,(竇靜)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眾,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于是征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于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9](p2369)竇靜擬屯田太原“以省饋運”,解決“師旅歲興,軍糧不屬”的實際困難,但遭到群臣反對。竇靜一再上書之后,高祖征其入朝,與反對置屯者“爭論于殿庭”,最終才使太原屯田的計劃得以實施。竇靜廷辯之時已有尚書省之設,《唐會要》載:“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尚書省”,[15](p984)但太原屯田并非簡單地由尚書省決斷,而是在廷議后由高祖定奪。可見,唐政權建立之初,尚書省在屯田設置方面地位并不突出。
武德三年(620),竇軌“遷益州道行臺左仆射……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2](p3845)次年,李孝恭遷荊州大總管,“孝恭治荊,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2](p3523)這兩處屯田的設立離不開竇軌和李孝恭個人的努力,但最終是否由尚書省定奪,未見史籍記載。
貞觀元年(627)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后言時政得失十余事,并見納用”。[9](p2507)《唐六典》載:“……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啟、牒、辭。(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為狀……)”[4](p12)六典注文明言上表的對象是“天子”,故張公謹請置代州屯田是向皇帝提出,從“并見納用”來看,皇帝批準了他的請求。可見,貞觀元年時,屯田的設置并不取決于尚書省,而是皇帝。
儀鳳三年(678)九月,“吐蕃敗洮河行軍大總管李敬玄,總管劉審禮死之。帝博咨群臣,求所以御之之術。或言不可和,或言屯田嚴守為便。其議帝俱未用”。[16](p156)可見,唐蕃前線屯田的設置初時并未得到高宗許可。盡管如此,河源軍經略大使黑齒常之仍在該地屯田供軍。調露二年(680),“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沖,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余所,度開營田五千余頃,歲收百余萬石”。[9](p3295)此處言“度開營田五千頃”,似乎在該地營田只是一個構思,但《新唐書》稱:“黑齒常之為河源經略大使,乃嚴燧邏,開屯田,虜謀稍折”,[2](p6077)似乎黑齒常之在該地屯田的計劃得到了落實,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懼之,不敢復為邊患”。河源地處偏遠,運輸困難,軍糧供應的任務頗為繁重,若無屯田供軍,黑齒常之就無法取得抗御吐蕃的成就。從史料記載來看,屯田的設置權仍由皇帝掌握,故廷議中雖有人力主屯田嚴守,但高宗不采納即不能得到落實。但此后黑齒常之的屯田究竟是自發之舉,還是得到了高宗的許可,則由于史籍語焉不詳,不便考證。
垂拱初年(約685),麟臺正字陳子昂向武后上疏曰:“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饑。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且其四十余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2](p4072-4073)疏言涼州“屯田所收不能償墾”,績效較差,而甘州“屯田廣夷”、“積粟萬計”,卻又“人力寡乏,未盡墾發”,“兵少不足以制賊”。欲制河西,則必須增加屯兵人數,擴大屯田面積。陳子昂的這一建議是采用上疏的方式向武后提出,可見在其看來屯田的決策權在武后手中。
開元年間,宰相張說請于河北置屯田而上《請置屯田表》:“……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彰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葦為秔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溥……”[17](p98)張說在表中稱“臣再任河北”,當是玄宗“敕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9](p3053)之時,即開元十年(722)。此前張說早已位居宰相之職,對當時的屯田法制無疑有清楚的認識。并且,此時距開元二十五年(737)田令的頒布也只有十五年的時間,屯田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已趨于完善。在河北屯田的設置上,張說直接向玄宗上表。這表明,張說認為屯田的設立決定于皇帝,而且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
開元二十二年(734),張九齡建議在河南開水屯,玄宗命他“兼河南稻田使”。[2](p4428)“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采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9](p3099)當時,張九齡身為宰相,設置屯田之事并未自專,而是提出建議由皇帝定奪,可見其對屯田設置權限的認識與張說如出一轍。后河南道陳、許、豫、壽等州設置水稻田百余屯,由于該地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玄宗詔罷之。“詔曰:陳、許、豫、壽四州,本開稻田,將利百姓。度其收獲,甚役功庸。何如令地均耕,令人自種,先所置屯田,宜并定其地,量給逃還及貧下百姓。”[18](p6036)可見,陳、許、豫、壽四州屯田的設立和廢罷均由玄宗直接決定。
玄宗曾下詔稱:“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眾離心,豈能無隙……近日狂虜形勢如何,屯收是時,尤需預備。”[19](p606)從敕文中可以看出,玄宗對遠在萬里之外的西域屯田深表掛慮并直接干預。
以上分析表明,開元二十五年(737)之前,在屯田設置這一重大事項上,尚書省的地位似無足輕重。這一階段內,無論是唐代屯田的實踐,還是名臣關于屯田的言論,都表明皇帝直接控制著屯田的設置權。
(二)開元二十五年令頒布之后的狀況。開元二十五年(737)令頒布之后,屯田設置并不取決于尚書省的事例也多見諸史籍。代宗大歷五年(770),“詔罷諸州所置屯田,特留華、同、澤等三州屯田”;[16](p172)大歷八年(773)七月,代宗宣布廢華州屯田,“其屯田并宜給以貧下百姓”。[20](p577)雖然這兩份詔敕的著眼點并非屯田的設置,而是“廢罷”,但作為一種影響屯田存在的消極措施,其與設置的權限應當是一致的。華、同、澤三州屯田的保留與廢罷均由詔敕決定之,可見屯田設置權由皇帝直接掌控。
李翰論及蘇州嘉興屯田時稱:“……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倡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之屯。”[14](p4375)文中提到皇帝對屯田的掛念及指示地方官員擇地開屯的詔敕。史稱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為史官,宰相不肯擬”,后“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2](p5578)可見,李翰有史官之才,其文中所述天子對屯田“旰食宵興”應不是空穴來風。
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楊炎請置屯田于豐州……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振武、天德、靈武、鹽、夏)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谷。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卒不成,然振武、天德田,廣袤千里”。[2](p1372-1373)宰相楊炎擬屯田于豐州,但未自行決定,而是“請置”,其對象顯然是德宗。京兆尹嚴郢反對該地置屯,也是采用向德宗上奏的方法加以勸阻。雖然此事以楊炎用事、郢議不用而告終,但從實際效果上看,似乎嚴郢的建議得到了落實。從豐州屯田的設置一事來看,楊炎、嚴郢均將皇帝作為屯田設置的決定者。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余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2](p1373)李絳請開營田得到了憲宗的肯定之后才付諸實施,同樣說明屯田的設置權由皇帝掌控。
從上引代宗、德宗、憲宗等時期的屯田實踐來看,開元二十五年(737)之后,屯田的設置與廢罷過程中,尚書省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沒有得到史籍的明確記載,皇帝對屯田設置權的直接掌控倒是體現得比較明顯。
三、結語
雖然開元二十五年令規定的屯田設置者是尚書省,但無論是開元二十五年(737)之前,還是之后,有關屯田設置的史料中都難覓尚書省的蹤影。這些史料一再表明,皇帝直接掌控著屯田設置權,唐令的成文規定在屯田實踐中是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試著加以理解:其一、唐初政權草創、法律制度不完善之時,屯田的設置由人主權斷甚至地方大員自行決定理所當然。竇靜屯田太原之事廷議后由高祖作出決定,以及隴右軍州大使郭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就是典型的事例。其二、不能將屯田簡單地與農業生產劃等號,很多時候它是政治策略、軍事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最高決策者統籌兼顧、合理安排。尚書省僅僅是中央政令的執行機構,雖然其長官尚書令、尚書仆射兼帶宰相銜可以參與中樞決策,但尚書省并沒有獨立的決策權,因而無法自行決定屯田的設置與否。張公謹屯田的代州、黑齒常之屯田的河湟、陳子昂建議擴大屯田的河西、張說請置屯田的河北、玄宗深表憂慮的安西等地,都是與少數民族政權交鋒的邊陲之地。在這些地方開展屯田,涉及到軍隊的調派及與周邊政權關系的處理,政治、軍事意義明顯大于經濟意義,這些事務是尚書省及其所屬各部無權自行措置的。其三、陳許豫壽華同澤豐等內地各州屯田的開展涉及到逃戶產業問題,屯田與均田的關系問題,以及中央與地方藩鎮的關系問題。這些問題對唐政權的穩固同樣具有根本性,尚書省同樣力有不逮。其四、開元二十五年(737)以前,屯田的設置權長期由皇帝執掌,這一習慣性的做法本身就具有制度的性質。中國古代,皇權至上具有不證自明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在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背景下,開元二十五年令的頒布不可能改變長期形成的傳統。
總之,雖然唐代確立了成熟完善的官僚體系,成文法對其職掌作出了明確而細致的規定,但文本意義的法并不等于實踐意義的法,不能對唐代法律規定作機械的理解。就屯田管理而言,有關屯田設置之類的重大政務由皇帝直接決策,即便是位高權重的尚書省也只有名義上的處分權,工部、屯田司、司農寺之流更無權置喙,所謂“掌天下屯田政令”理解為依照皇帝所頒政令具體處理日常屯田管理事務更加恰當。可以看出,唐代屯田中央管理機構實際上由皇帝、尚書省、尚書省各部(尤其是工部及屯田司)、司農寺組成,并由監察御史對尚書省以下各機構的屯田管理行為行使監察權。
[1][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
[2][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唐]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4][唐]李林甫.唐六典[M].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
[5][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6]鄭天挺,吳澤,等.中國歷史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7]趙德馨.中國經濟史辭典[M].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0.
[8]唐嘉弘.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大辭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后晉]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0]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J].歷史研究,2000,(2).
[11][日]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M].龔澤銑,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
[12][明]邱浚.大學衍義補[M].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
[13][清]黃輔辰.營田輯要校釋[M].馬宗申,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
[14][清]董浩.全唐文[Z].北京:中華書局,1983.
[15][宋]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
[16]張君約.歷代屯田考[M].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
[17][唐]張說.張燕公集[M].四庫唐人文集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8][宋]王欽若.冊府元龜[Z].北京:中華書局,1960.
[19][唐]張九齡.張九齡集校注[M].熊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20][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Z].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責任編輯高思新
K242
:A
:1003-8477(2013)07-0100-04
張珉(1973—),女,新疆兵團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法律系講師。龔先砦(1976—),男,新疆兵團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法律系副教授,杭州師范大學法治中國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