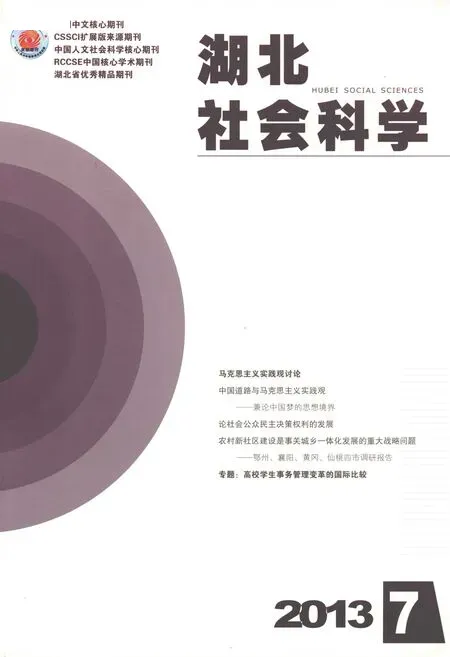墓志源流考辨
顧濤
(洛陽師范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洛陽 471022)
墓志源流考辨
顧濤
(洛陽師范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洛陽 471022)
墓志的源流問題是墓志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目前仍存在著不少分歧。墓志的起源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墓磚墓石萌芽期、墓碑過渡期和方形墓志定型期。墓志在南北朝時期定型以后,一千多年來其形制賡續不變,影響深遠,成為我國傳統墓葬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墓志;源流;階段;特征
墓志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一種獨特的石刻形式,具有歷史、考古、文獻、民俗、藝術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它不僅起源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之前,而且存世數量極大,僅唐代墓志已知的就有五千方以上,更遑論其它,何況直至今天仍不斷有新的墓志出土面世,成為一座珍貴的民族文化藝術寶庫。關于墓志的記載和研究最早起于何時,未有定論,但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中的《銘箴》篇和《誄碑》篇已經涉及到碑銘石刻的源流發展和文化作用,并提到蔡邕等人撰寫墓碑銘文之事,當然,劉勰還沒有明確提到墓志這個概念,不過可以證明對碑銘石刻的研究在南北朝時就已進入學者的視野。比較確定的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金石學家趙明誠發金石學研究之濫觴,開始對墓志有相當的關注,他們分別所著的《集古錄》、《金石錄》兩書收錄、整理了一定數量的墓志,而且進行了初步的研究。
從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把墓志納入金石研究范疇到現在也已經近千年了,對于墓志的記載和研究日漸增多,尤其是清代金石學大興之后,墓志由于其珍貴的多方面的價值,在金石學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收集、整理墓志的著作不斷面世,其中對于墓志的文獻考釋一直是研究的重點,但墓志文化涉及面極廣,學術界關于它的許多問題、包括一些基本問題到現在還存在著不少分歧和爭論。其中關于墓志的起源問題,是學術界存在觀點較多、且分歧較大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學術界對此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雖然觀點仍然有不少分歧,但認識已經越來越明晰了,所以今天仍值得專門進行探究和歸納。總的看來,學術界對墓志的起源大致有五種重要的不同看法,分別認為墓志出現在秦代、西漢、東漢、魏晉、南朝等時期,[1](p32)這些看法各有其理論依據,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已為學術界所熟知,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一個萌芽、準備和形成過程。我們考察墓志的起源,同樣應該遵循這一規律。
結合眾多學者觀點,筆者認為,墓志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墓志的萌芽期:墓磚和墓石階段
一件事物的出現,往往在萌芽期,它的某些基本特征就已經開始有所顯現。之所以把墓志的萌芽期定為墓磚和墓石階段,因為,目前發現的墓磚和墓石大多具備了后世墓志的一些重要特征,正是它們的發現為墓志的原初狀態提供了真實而必要的物證。據1994年6月19日《中國文物報》載,1987年山東鄒城出土了兩塊墓磚,這兩塊刻有銘文的墓磚大小基本相同,長25厘米,寬12厘米,厚5厘米,一塊兩面均刻有文字,另一塊一面刻有文字,內容涉及到死者的一些個人信息。兩塊墓磚上的銘文內容并不多,只有寥寥的十余字,但已標明墓中死者身份,已初步具備了墓志的功能,把它們看作墓志的最早形態和萌芽當符合歷史的真實。有學者認為它們是最早的墓志,年代也較早,應屬于戰國時期。
這樣簡單粗糙的墓中刻銘,考古發現秦代和漢代的都有。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陜西出土了18件帶有文字的秦刑徒墓殘瓦,文字多在十字以內,有的只刻了一個地名或人名,簡單記載了死者的籍貫、身份和姓名等。“在內容上,可以作為后世墓志的祖形來看待,也是值得注意的史料。”[2](p145)建國后漢代墓磚時有出土,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上世紀60年代,在古都洛陽發掘了500多座東漢刑徒墓,竟然集中出土了800多塊墓磚,成為當年轟動考古界的一大發現。這些東漢刑徒墓磚大小不一,一般長約30至40厘米,寬20多厘米,行文與內容雖與秦墓瓦相似,但刑徒墓磚的銘文內容明顯豐富了不少,對于死者的個人信息記錄的也比較詳細,除了交代死者的籍貫、姓名外,有些還注明了他們的身份、死亡時間,甚至有的還交代了死因。“這些刑徒磚雖然與后來定型的墓志還有很大距離,但是它的埋設目的與墓志基本相同,對墓志的產生與普遍使用有直接的影響。”[1](p37)
歷史發展到東漢中后期,墓葬文化在很多方面也在改變,尤其是厚葬之風導致人們更加注重墓葬材料的選擇。簡陋的墓磚相應地被堅固耐久的墓石所代替。從墓磚到墓石,表面看好像僅僅是關于墓葬材料的改變,但它實質上是墓葬意識的一次大的轉變,體現了人們對于生死觀的更深刻的思考和對于死者更深切的懷念。目前已知的刻于漢殤帝延平元年(106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石》、刻于漢安帝元初二年(115年)的《張盛墓石》、刻于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的《繆宇墓石》、刻于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年)的《徐州從事墓石》等使我們看到了墓磚到墓石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從墓磚到墓石的過渡符合歷史的自然發展趨勢,雖然這時的墓石多是粗糙的石料,刻寫也相當粗率,形制也未固定,但材料的不同仍然帶來了其他的變化,較為明顯的就是墓石的面積普遍超過墓磚,與之相應的是刻寫的內容自然也比墓磚大大增加了。如著名的《賈武仲妻馬姜墓石》,此墓石高46厘米,寬58.5厘米,隸書15行,每行13至19字不等,內容不僅記載了死者的姓名、身份、籍貫、死期,還詳細地敘述了死者的生平,并對其生前的功德進行了頌揚,“其內容、作用、制作意圖和文體格式與后世題名為“墓志”者已經沒有太大區別,應該說已初具墓志之實。”[3](p108)
從上述考古資料可以看出,墓志的最早源頭可追溯到戰國前后,但其萌芽階段主要在兩漢時期,尤其是東漢中晚期是墓志萌生的主要時段。這個時期的墓磚、墓石等,從文字內容、形制、用途等已經簡單具備了墓志的功能,但還只是初具雛形,各方面都還沒有固定的程式。
第二階段——墓志的準備期:墓碑形態階段
這一時期亦可稱為墓志的“準”形成期和過渡期。墓志在發展過程中,從東漢、曹魏到西晉時期經歷了一個墓碑形態的階段。墓碑是碑的一種。碑起源很早,《穆天子傳》中就有相關記載。“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勛績。而庸器漸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4](p138)從上述可知,碑產生后經過長期的發展,直到東漢后期才出現碑碣蜂起、盛極一時的局面。而且碑不僅起源早,在演變過程中,其形制和作用也在不斷演變。以漢碑為例,漢碑就有各種樣式和用途,僅從用途看,就有功德碑、記事碑、紀念碑等,在許多廟宇、殿堂、墓冢都能見到。《說文解字》對碑的解釋是“豎石也”,可見古代的碑基本都是豎立形式。漢碑雖然有多種用途,但目前發現的眾多漢末碑刻,有相當一部分是立于墓前的紀念和歌頌死者的墓碑,如《孟孝琚碑》、《袁安碑》、《袁敞碑》、《景君碑》等。當時的墓碑主要是立于墓前地面上,形制一般為長方形,多有碑首、碑身和碑座,碑文內容比較豐富,一般多達數百字,對于死者的家世、生平、經歷、功績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多為文辭優美的韻文,書體一般為隸書(有稱之為八分書者),也有少數為篆書,碑額多為篆書,從其銘文和作用看,它們基本可以看作是墓志發展中的一種準形成形態。從墓碑的制作看,墓碑較之于墓磚和墓石,無論是石材的質地,或是制作的工藝,都有大幅的改進和提高,“東漢立碑,對碑石的質量、制作、書刻都十分講究。碑石要派人外出采集,要打磨平光,并加以雕飾,要請賃手藝高超的石工。”[5](p145)
從墓碑內容的撰寫和書寫看,墓碑和以前的墓磚墓石比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洛陽刑徒墓磚,基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匠們隨手刻寫,不僅內容簡單,談不上文學性,而且書寫水平不高,筆畫平直粗率,結構夸張隨意,缺乏專門的訓練,是典型的民間日常書寫。而墓碑則和墓磚墓石有很大區別,從傳世的漢代墓碑看,大多墓碑的書寫者都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不少還是當時的碩學名儒,如蔡邕、崔瑗等常為人撰寫碑文。許多墓碑雖沒有留下撰寫者的姓名,但從文字內容看,大多文字典雅,韻律優美,有漢賦之風韻,應該多是一時的文人俊彥所撰,而墓碑的書寫同樣令人矚目,與墓磚墓石粗率的書寫相比則判然有別,漢代墓碑多采用規范的隸書書寫,這種規范的隸書也稱為八分書。“八分書在東漢是一種普遍用于碑刻的書體,所以又將其稱作銘石書。由于八分書在東漢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書體,故成了書法家有意去專攻而擅長的書體之一……蔡邕就是古代公認的以八分書成就之最高者。漢末魏初的鐘繇,擅長數種書體,而以銘石書最妙。”[5](p144)可見,墓碑的書寫多請具有較高書法專業水平的書手書丹,這也是漢碑受后人重視的原因之一。從總體看,墓碑的各個環節、各個要素與墓磚墓石比,都有了質的飛躍,不再僅僅是儀式和形式上的喪葬器物,而是更多地具有了文化與藝術內涵的象征物。
墓碑從地面轉移到地下墓室中,是墓志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環節。從考古發現看,東漢末期,就出現了把墓碑立于墓室中的情況,如1991年河南偃師發現的東漢肥致墓(169年),在墓室中就出土了立式暈首并帶有碑座的肥致墓碑。到曹魏、西晉時期,由于嚴格實行禁碑政策,人們不敢公開立碑,但長期形成的墓碑習俗已經根深蒂固,于是,人們采取了變通的對策,把立于地面上的墓碑轉移到了地下墓穴中,所以這時期的墓碑形制仍然繼承了漢碑的重要特點,諸多方面和漢碑如出一轍,如仍稱“墓碑”(也有稱“墓表”者),仍是長方形豎式立放,有碑首,而且不少還有底座。如1930年出土于洛陽、現珍藏于西安碑林的刻于西晉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即是豎式長方形墓碑,有暈首與紋飾,其碑額為“晉待詔中郎將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這種墓碑考古中時有發現,如1925年出土于洛陽孟津、刻于西晉元康元年(291年)的《成晃碑》,1953年出土于洛陽、刻于西晉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的《徐義墓志》等,都是此類墓碑的代表。
這種碑形墓志大多已經具備題首、志文、頌辭,從墓志文字的要求看,其內容已經非常完備了,除形制、擺放形式不同于后來正式的墓志和缺少墓志蓋外,其余基本和后世墓志比較一致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我國喪葬文化的發展歷史看,墓碑的出現是必然的,它是墓志形成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而且“墓碑的影響畢竟不可忽視,它在文體上,刻制工藝上,銘文內容上等方面的特點都直接進入了墓志,對墓志的正式定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p51)
第三階段——墓志的定型期:固定方形墓志階段
此階段主要是南北朝時期,此時的墓志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最后終于在文體、書寫、形制等方面完全確定下來,進入了固定的方形墓志階段,并長期被后世沿承下去。
一般認為,從西晉末年到南北朝之交這個時期,墓志開始進入固定的完整形態階段。學術界把這一時期的《劉賢墓志》、《劉懷民墓志》等志石的出現作為墓志這一事物正式形成的標志。《劉賢墓志》仍是豎式的墓碑形制,下有龜形底座,銘文中沒有刻寫具體的年月,但依據其內容應大致刻于北魏承平至和平年間(452—465年),碑額刻寫“劉賢墓志”四字,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確刻有“墓志”稱呼的墓志,預示著墓志獨立階段的到來。刻于464年的南朝宋《劉懷民墓志》在墓志形成史上具有不尋常的意義,它不僅在題首中明確出現“墓志銘”的稱呼,且擺脫了豎式的長方形狀的碑的束縛,不再有碑首,其“志高49厘米,寬52.5厘米……正書,書體凝重圓潤”,[6](p4)從形制上看,此墓志已經是比較標準的方形石志了,書體也從隸書過渡到了正書(楷書),同時,“劉懷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適承元嘉之后,此志銘文字導源之時代也”,[6](p5)因此,(在考古上沒有發現比之更早的新的實物之前),我們可以認為,《劉懷民墓志》從形制、文體、書寫都可以視作固定方形墓志的開端,其后這種形制就基本固定下來。除沒有發現墓志蓋,它從形式到內容完全與后來標準的墓志一樣了,可以說這是目前固定墓志階段的早期的實物見證。而墓志蓋的出現也是歷史的必然,在豎式的墓碑演變為方形墓志以后,墓碑的碑首并未被拋棄,而是碑首與碑分離,變成了墓志蓋,實際上是一塊長方形的墓碑進化成了一合帶蓋的墓志。墓志蓋和墓志上下合為一體,標志著天與地、陽與陰的相合與相通,其中墓志蓋又以覆斗形的最為典型。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帶蓋墓志是洛陽出土的北魏正始二年(505年)的《寇臻墓志》,志蓋上書“幽郢二州寇使君墓志蓋”。可見,南北朝時期,墓志已被作為墓葬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而日趨受到人們的重視,墓志到這時完全成熟了。
隋唐以后,墓葬文化繼續發展,墓志和當時的社會文化相結合,尤其是和當時的氏族、門第觀念緊密聯系,官宦大族更加重視墓志的地位和社會意義,這時的墓志無論從制作或是從文字書寫都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單從出土數據看,唐代是我國古代墓志存世最多的時期,就能反映當時墓志的風行。從目前存世的大量南北朝和隋唐墓志來看,成熟時期的墓志一般都具有這些特征:一、有固定的文體和格式,由題首(標題)、序文(墓主身世為主的傳記)、銘辭(多為四字頌文)、附注(夫人子女簡介)等幾部分組成;二、基本都是正方形(偶爾也可見少數長方形和異形墓志);三、標準的墓志一般都有覆斗形(又稱盝頂形)志蓋,這是最主要的一種志蓋形式;四、主要為石質(也有其它磚、瓷等材質);五、主要使用標準的楷書書丹鐫刻(也有少量隸書、行書、草書等書體墓志)。除這些特征之外,在很長時期內,尤其是在南北朝至唐以后的長期階段,墓志的制作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內涵和文化特征,它往往根據志主出身、官職、地位等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尺寸要求,高官顯宦的墓志還常繪有精美的紋飾,其中的許多紋飾具有復雜的文化信息和藝術意趣。大量實物證明,南北朝時期的墓志已經走向了成熟的固定期,具有上述重要特征的墓志形制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成為我國墓葬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墓志的源流問題雖只是墓葬文化中的一個小問題,但探賾尋幽,仍讓我們看到了蘊含其中的許多令人駐足、令人動情的文化景致。墓志這朵石刻文化中的奇葩,需要我們穿過歷史的時空隧道,不斷地走近它、思考它,它的許多有趣而富有內涵的待解之謎,等待著我們去探索、去破解。我們相信,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墓志中所蘊含的歷史、社會、文化、藝術等價值,也定將發揮它新的積極作用。
[1]趙超.古代墓志通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西林昭一,陳松長.新中國出土書跡[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第十二[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5]華人德.華人德書學文集[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8.
[6]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高思新
K877.45
:A
:1003-8477(2013)07-0107-03
顧濤(1970—),男,美術學博士,洛陽師范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河南省教育廳2011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北魏墓志楷書與漢字結構定型研究”(2011—ZD—014)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