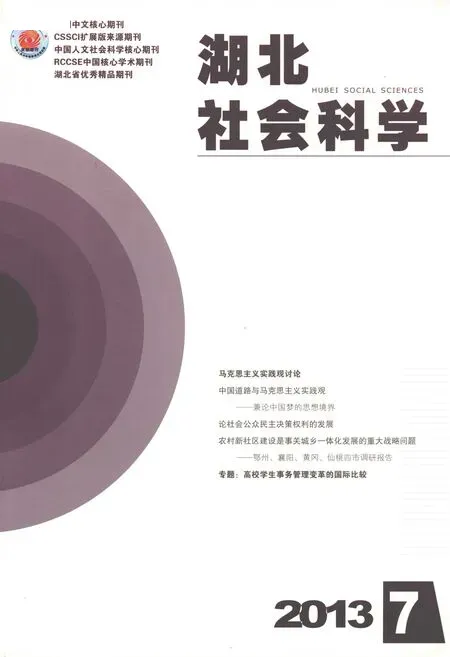新刑事訴訟法鑒定制度不足與再完善
田毅平
(西南政法大學應用法學院,重慶 401120)
新刑事訴訟法鑒定制度不足與再完善
田毅平
(西南政法大學應用法學院,重慶 401120)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對鑒定制度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強化了鑒定人出庭,創設了專家輔助人制度。這種變革具有重要意義,但也有諸多不足,具體而言,鑒定意見范疇不合理、證明力不適度、質證程序不規范;鑒定人出庭條件過嚴,未根除其后顧之憂;專家輔助人知情權保障不足,反駁意見證據效力不明;鑒定程序啟動權配置帶有強烈職權主義色彩。必須強化庭審質證,嚴格區分刑事技術鑒定和司法鑒定,制定統一的鑒定意見審查標準,消除鑒定人出庭作證顧慮,賦予專家輔助人程序參與權,保障當事人鑒定程序啟動權。
新刑事訴訟法;鑒定意見;專家輔助人;出庭作證;鑒定啟動
在司法實踐中刑事司法鑒定的需求逐漸增大,特別是高科技犯罪逐漸增多的背景下,鑒定在刑事司法領域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完善的司法鑒定制度對打擊犯罪、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以及提升司法公信力均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鑒定制度的完善無疑已成為司法程序改革的重心。繼2005年全國人大頒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和2007年司法部頒布《司法鑒定程序通則》之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基于對司法實踐需求的回應,對刑事司法鑒定制度進行了大幅度變革,共涉及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的7個鑒定條款中的4個條款,又新增兩個條款,且具有重要創新意義。主要包括:將原有的“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設立專家輔助人制度、改“醫學鑒定”為“法醫鑒定”以及強化鑒定人出庭作證,并制定了相應的保護措施。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無疑極大豐富了刑事司法鑒定制度,促進了刑事司法鑒定程序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文明化程度,但2012年刑事訴訟法關于鑒定制度的改革仍然存在諸多缺憾,需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一、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鑒定制度:亮點與價值
(一)“鑒定結論”改稱“鑒定意見”。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有關鑒定制度的最大亮點是將“鑒定結論”改稱“鑒定意見”。其重要意義在于:首先,是鑒定客觀規律的必然反映。鑒定本質上系一種相當主觀的判斷活動,這種判斷活動的精準性受制于鑒定技術的成熟度、鑒定原理的科學程度、鑒定樣本的優質程度以及鑒定過程的規范程度。司法實踐中也常出現多頭鑒定甚至錯誤鑒定的尷尬局面,使得“鑒定結論”無法成為最終結論,不具備“不容置疑”的“結論”屬性,改稱“鑒定意見”是對鑒定客觀規律的必要尊重;其次,是糾正司法人員“迷信”鑒定的基本需要。在司法實踐中,“鑒定結論”通常被稱之為“證據之王”,被認為絕對權威。這種表述方式較易使司法人員產生鑒定意見不容置疑的錯誤認識,將其視為“科學判斷”,從而盲目信賴,使審查流于形式。對鑒定結果稱謂的變更,使“鑒定結論”走下了神壇,還原了其普通證據的根本屬性,有利于強調司法機關的審查義務,在較大程度上弱化司法人員對鑒定意見的盲從意識;再次,是尊重司法權的應有之義。鑒定人的判斷僅是司法人員認定事實的參考依據,其并不能代替司法人員結合全部案情和證據對涉及專門問題的相應事實進行認定。即鑒定結果僅僅是司法活動的證據,是否采信,尚有待于司法人員根據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進行審查。對鑒定結果冠以“結論”稱謂混淆了鑒定活動的本質屬性,甚至在較大程度上造成了鑒定人鑒定權對司法權的嚴重侵犯。
(二)強化了鑒定人出庭作證。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強調鑒定人在特定情形下應當出庭作證,拒不出庭作證的,不僅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依據,而且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作證,情節嚴重的,還可處十日以下拘留,在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同時還完善了鑒定人保護制度。這些規定毋庸置疑極大地強化了鑒定人出庭作證義務,順應了刑事司法鑒定的需要。具體來說,由于鑒定技術和鑒定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性,鑒定意見作為刑事司法的重要證據之一,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經過有效質證才能作為認定案件的依據,是公正、高效、權威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鑒定人是司法鑒定的實施者,也是出具鑒定意見的主體,是最直接、最全面了解這些信息的人。[1](p30)因而,只有鑒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當事人、專家輔助人的詢問,闡明鑒定的過程和采用的方法以及相應的資質,才能保障法官對鑒定意見的科學性作出準確判斷。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鑒定人強制出庭作證制度,是審判階段規范鑒定的重要措施,不僅為改變司法實踐中鑒定人出庭率極低的狀況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為法官科學審查鑒定意見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有效保障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質證權。另外,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及故意虛假鑒定應負刑事責任的規定使得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更為科學、合理,較大程度上解決了司法實踐中鑒定人不出庭作證導致無法有效審查鑒定意見的痼疾。
(三)創設了專家輔助人制度。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創設了專家人輔助制度。專家輔助人,在國外通常被稱之為專家證人,本質上是當事人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協助其在庭審過程中進行質證。具體來說,該制度賦予了專家輔助人出庭協助當事人向鑒定人發問并就鑒定意見反駁的權利,保障了有專門知識的人有效參與刑事司法活動,通過其對鑒定意見的協助認證、質證或辯護,極大幫助了審判人員科學、全面審查和認定鑒定意見。由此,我國引入專家人輔助制度的最大意義在于,在較大程度上有助于實現鑒定領域專家間的較量,進而在較大程度上形成了對鑒定人的有效制衡機制,打破了鑒定人壟斷對專門性問題判斷的桎梏,避免了“科學”成為法官的主人或由平民法官利用生活經驗常識任意宰割“科學”的命運。同時,辯方申請專家輔助人參與訴訟,“有效彌補了其在科學方面專業知識匱乏和對鑒定意見質證經驗不足的缺憾”[2](p88),極大地提升了辯方訴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控辯雙方在鑒定方面訴訟能力嚴重不平衡的現狀。
二、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鑒定制度:不足與反思
(一)鑒定意見的內涵界定不明確、不合理。
“鑒定結論”到“鑒定意見”的演變,有著深刻的司法背景,但其內涵尚不明確。筆者認為這種變革應具有兩方面內涵:其一,厘清了司法活動和鑒定活動的關系,明確了鑒定活動的本質屬性和法律效力,即鑒定結果僅是一種證據,是鑒定人借助專業知識的主觀判斷,必須接受司法人員審查、判斷,而非天然具有不可辯駁的權威性;其二,強化了司法人員對鑒定結果進行審查的義務。對涉及鑒定事項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審查,是司法人員的法定職責,必須履行,因此其有義務利用專業知識對鑒定意見進行相應的審查,而不能借口“科學問題”將司法審查權讓渡給鑒定機構。但是,將鑒定意見擄下神壇的同時,必須避免過分削弱其權威性。畢竟鑒定系具有國家認可的相應資質的專業技術人員,運用高科技設備和先進技術對專門問題進行甄別的活動,而這些專門性問題往往是普通人運用生活經驗和常識不能進行有效判斷的,加之鑒定人處于中立立場,我們應當相信鑒定結果具有較大程度客觀公正性。
另外,新刑事訴訟法中關于“鑒定意見”內涵的界定尚有不足之處,即將所有專門問題的鑒定結果包括偵查機關自行作出的鑒定均稱之為“鑒定意見”缺乏合理性。筆者認為偵查機關為偵查而委托其內部鑒定機構進行的鑒定,因缺乏中立性,通常公信力較低,缺乏作為定案根據的正當性。如2009年杭州胡斌飆車案,公安機關偵查階段公布的“鑒定結論”載明事故發生時時速為“70碼”,深受民眾普遍質疑,最后不得不申請社會機構重新鑒定。[3]鑒于此,偵查部門鑒定應作為偵查技術手段之一,而不應納入鑒定意見范疇,這種鑒定結果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確表示認可且聲明放棄申請重新鑒定權時才能作為定案根據。
(二)鑒定人出庭作證的保障不充分。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十一條規定基礎上,對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規定進行了完善,包括出庭的程序性制裁后果即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以及對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特殊保護,使得這一制度更加具有合理性,但尚有不足之處,具體體現在:
一方面,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條件過于嚴格。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之規定,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其一,公訴人、當事人或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其二,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證。這種規定一方面極大限制了應當出庭作證案件的范圍,仍無法根本上解決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司法現狀。另一方面,強化了法院在鑒定人出庭作證方面的審查權,導致法院權力過大,忽視了當事人、或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法定質證權;
另外,沒有根本消除鑒定人不出庭作證的顧慮。司法實踐中鑒定人擔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打擊報復是其不愿出庭作證的重要原因。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了充分的鑒定人安全保障措施,一方面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等嚴重的暴力犯罪案件,司法機關應當主動采取法定的保護措施,除此之外,鑒定人及其近親屬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面臨危險的可以申請保護。這在較大程度上解除了鑒定人出庭作證的顧慮,但因擔心打擊報復僅僅是鑒定人不愿出庭作證的原因之一,對鑒定人出庭應得到的合理經濟補償沒有得到解決也是重要原因。
(三)專家輔助人訴訟地位低下。
允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質疑的機會,乃是構成鑒定意見作為事實認定依據的必要正當程序。[4](p102)因此,根據程序正義的內在要求,專家輔助人作為重要的訴訟參與人,其各種訴訟權利應當得到保障,其訴訟地位應被足夠重視。然而,2012年新刑事訴訟對此卻缺乏應有的立法尊重。加之,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對鑒定人相關信息和鑒定過程三緘其口”,[5](p12)鑒定意見的理論依據、檢材來源,以及鑒定程序和鑒定人資質,專家輔助人均無從知曉,無法在法庭質證時充分對鑒定意見進行“質疑”和“質問”,使得專家輔助人出庭作證制度功能發揮仍然受到較大的限制。這種局限主要體現在對其程序參與權保障不足,由于鑒定具有高度技術性和隱蔽性,專家輔助人在沒有充分了解鑒定相關信息情況下,難以有效輔助當事人訴訟。特別是辯方專家輔助人,知情權無法得到保障,質證的能力必然受到極大限制。另外,專家輔助人針對鑒定意見所提反駁意見,缺乏相應的證據效力,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僅將其視為當事人質證意見的一部分,導致法官裁判時,必然潛意識地傾向采納鑒定意見。這種背景下,辯方輔助人即便出庭顯然也難以與控方和鑒定人抗衡,進而使得刑事訴訟中的控辯雙方訴訟能力仍然嚴重不平衡,背離了現代刑事訴訟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立法宗旨。
(四)鑒定程序啟動權配置保留了強職權主義。
新刑事訴訟法第146條和192條規定,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他們提出申請,可以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重新鑒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可只告知結論部分,不告知其他內容。調查數據表明,實踐中,公檢法委托的鑒定、律師事務所委托的鑒定、企事業單位委托的鑒定、個人委托的鑒定、其他主體委托的鑒定分別占鑒定業務總數的59%、10.3%、4.1%、22.3%、3.5%。[6](p4)可見,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在鑒定程序啟動方面仍然凸顯了強職權主義色彩,即初次鑒定和再次鑒定的啟動權完全受控于公檢法等公權力機關。而當事人、辯護人及訴訟代理人僅享有補充鑒定和重新鑒定的申請權,且該權利的實現,需經過偵查機關或審判機關的同意,另外,其對鑒定過程的知情權也受到了極大限制。這種模式的弊端在于忽略了當事人的辯護權,導致控辯嚴重不平等。這是有罪推定在鑒定制度中的體現,立法者先入為主地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性為社會的破壞者,弱化其訴訟能力,防止其通過鑒定結果逃脫法律的制裁。這些弊端已經在多年的司法中暴露無遺,比較典型的案例如在2006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邱興華故意殺人案中,包括著名精神病臨床專家劉錫偉教授和鑒定領域的泰斗楊德森教授在內的數位法學專家和人大代表呼吁對邱興華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7](p4),其律師也提出鑒定申請,但均被檢察機關和法院予以否決,一二審法院均在沒有對邱興華進行精神鑒定的情況下對其作出了死刑判決。在2008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楊佳殺人案中,雖然司法機關啟動了精神病鑒定程序,但“由公安機關主導的單向型鑒定由于缺失辯方的參與,其公正性、客觀性和科學性仍然不能令人信服”[8](p110)。
三、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鑒定制度的再完善
(一)強化對鑒定意見的有效審查。
鑒定結果稱謂變革,反映了鑒定意見的本質屬性,同時對刑事司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須采取各種措施,強化對鑒定意見的有效審查。具體來說,包括:其一,提升庭審質證的地位和功能。鑒定結果稱謂的變革昭示著鑒定意見本質屬性的回歸,即鑒定意見不能自動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必須經過質證和法院的審查才能作為定案根據。這就要求必須彰顯庭審質證的重要性,在一定意義上講,法庭質證就是對鑒定活動成果的檢驗和驗收。[9](p162)因此,必須將庭審質證視為整個鑒定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核心環節,完善對鑒定操作規程、使用儀器和方法上的質疑機制;其二,嚴格區分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刑事法官往往將刑事技術鑒定視為司法鑒定的直接定案依據,被諷為公、檢、法“自偵自鑒、自檢自鑒、自審自鑒”的壟斷模式,這種做法極大弱化了司法審查權,也忽視了對辯方權利的平等保護。隨著鑒定“結論”走下神壇,這種狀況必須改觀。必須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通過對鑒定人資質、鑒定程序、條件以及鑒定依據的詳細詢問強化審查,在當事人特別是辯方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必須充分保障其申請補充鑒定和重新鑒定的權利;其三,盡快制定統一的鑒定意見采信標準。對鑒定意見的審查過程必然充斥著假設、推論,十分必要進行類型化歸納,總結出較為統一的標準。如鑒定人的資質、鑒定操作程序的規范性、鑒定依據的科學性等。美國1923年通過弗賴依訴合眾國案,確定首個專家意見證據的科學性標準——弗賴依標準(普遍接受標準)[10](p187),對我國鑒定意見審查標準的制定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當然,借鑒這些制度時,必須考慮我國自有的司法實踐和國情[11](p95),即適度提升弗賴依標準,使其逐步實質化,積極構建在我國能夠行之有效的審查標準。
(二)賦予鑒定人出庭作證保障性權利。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十一條規定基礎上,對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規定進行了完善,包括出庭的程序性制裁后果即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以及對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特殊保護,使得這一制度更加具有合理性,但仍應進一步完善相應的保障措施。如前所述,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之規定的鑒定人出庭作證條件過于嚴格,為提升鑒定人出庭率,應適度放寬。與此同時還應當充分保障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各種權利,包括合理的經濟補償權和訴訟程序權。國外立法均對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報酬權保障高度重視,如德國制定了專門的《證人、鑒定人補償辦法》,美國在《聯邦證據規則》中規定了專家證人報酬支付辦法,我國《司法鑒定收費管理辦法》等相關規范性文件對此明顯缺乏相應的保障,必須予以改進。因此,從根本上解決鑒定人不愿出庭作證的弊端還必須深入探索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或補助機制。就鑒定人的訴訟程序性權利而言,也是應當進一步完善,特別是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內容、對其詢問適用的規則應當明確,還應當賦予其人格尊嚴受尊重、依法提出異議、反詢問等各項保障性權利。
(三)充分尊重專家輔助人的訴訟地位。
專家輔助人被譽為刑事司法鑒定領域中的“技術顧問”[12](p163),是刑事訴訟中重要的特殊訴訟參與人。欲有效發揮專家輔助人的專業性輔助功能,明確并充分保障其在刑事訴訟中各種基本的程序性訴訟權利,至關重要的特別是應當尊重其鑒定程序參與權和庭審質證權。現代各國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主體地位均得到立法的認可[13](p91),對被追訴人知情權的保障是重要體現。從國外經驗看,均充分保障專家輔助人的知情權,如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第58條規定,專家輔助人在不影響鑒定人獨立開展鑒定活動的前提下有權參與司法鑒定的過程,并根據其知悉了解的內容提出意見,且相應意見應在最終鑒定意見中體現。可見,保障專家輔助人的知情權顯然是我國專家輔助人制度改革的關鍵,應當首先保障專家輔助人的鑒定參與權,對于鑒定結束后聘請的專家輔助人應當允許其考察鑒定樣本和檢材,以及查閱、摘抄和復制鑒定人進行鑒定活動的相關記錄,并就相關問題向鑒定人發問。另外,必須明確專家輔助人在訴訟過程中所提意見的證據地位,特別是對鑒定意見的駁斥,應通過立法賦予其相應的證據能力,甚至足以動搖法官心證的證明力。
(四)合理配置刑事鑒定程序啟動權。
司法鑒定活動是為司法機關提供訴訟證據的活動[14](p14),因而鑒定啟動權本質是舉證權和取證權,而不是準司法權,應當為控辯雙方所平等享有。因此,必須改革我國當前控辯完全失衡的鑒定啟動權配置模式。從國外的立法狀況看,無論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均十分重視控辯雙方鑒定程序啟動權的平等保障。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56條的規定,辯方與控方以及法院享有平等的鑒定程序啟動權。在德國,雖然鑒定啟動權專屬于法官和檢察官,但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68條第2款的規定,當事人擁有充分的程序參與權,即其提名的鑒定人在不妨礙法官指派的鑒定人工作的情況下參加勘驗和必要的調查。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均平等保障了控辯雙方平等的申請權和救濟權。在英美法系國家,由于刑事訴訟被視為國家與當事人之間的刑事糾紛,控方地位被當事人化,[15](p145-219)更加凸顯了鑒定啟動權的雙向配置,辯方在鑒定程序的啟動方面享有完全的“平等武器”。在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我國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仍然堅持的鑒定啟動權單項配置模式必須改革,筆者認為,在審判階段的鑒定應當委托偵查機關內設機構以外的社會鑒定機構進行,且當事人或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出申請的,法院應當同意。另外,當事人啟動鑒定程序后偵查機關應當予以配合,包括提供相應的檢材、樣品和檢驗對象。在偵查階段或提起公訴階段進行的鑒定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專家輔助人在不妨礙偵查工作的前提下參與調查和鑒定,并準許其在后續訴訟程序中以專家輔助人身份提供相應的意見。
[1]王進喜,李小愷.論《刑事訴訟法》修改對司法鑒定活動的影響[J].中國司法鑒定,2012,(9).
[2]鄒海燕,陸滌.論我國設立專家輔助人制度的必要性[J].中國司法鑒定,2012,(1).
[3]佚名.杭州警方就飆車案70碼說法向社會致歉[EB/ OL].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society/2/200905/0515_344_ 1159475.shtm l,2013-04-15.
[4]劉曉農,彭志剛.關于刑事鑒定的幾個問題——以《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視角[J].法學論壇,2013,(1).
[5]吳高慶,張進.論刑事鑒定意見的庭前開示程序[J].中國司法鑒定,2013,(2).
[6]李禹,陳璐.2010年度全國法醫類、物證類、聲響資料類司法鑒定情況統計分析[J].中國司法鑒定,2011,(4).
[7]陳學權.刑事司法鑒定的程序正義——邱興華案對中國刑事司法鑒定制度的啟示[J]中國司法鑒定,2007,(8).
[8]鐘朝陽.程序公正與刑事訴訟中的鑒定啟動權[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9,(1).
[9]胡占山.簡析新《刑事訴訟法》對司法鑒定工作的影響[J].中國司法鑒定,2012,(4).
[10]李強,馮興吾.刑事鑒定結論審查運用問題研究[J].河北法學,2010,(10).
[11]朱晉峰.刑事鑒定意見證據能力的程序保障探析[J].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3,(1).
[12]陳斌,王路.論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專家輔助人及其制度構建[J].湖北社會科學,2011,(1).
[13]肖輝.背景與意義——刑事被追訴人知情權的提出[J].河北法學,2005,(6).
[14]黃道誠.刑事鑒定若干問題研究[J].河北法學,2003,(4).
[15][美]米爾伊安.R.達瑪斯卡.司法與國家的多種面孔——比較法視野中的法律程序[M].鄭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勞志強
DF73
:A
:1003-8477(2013)07-0154-04
田毅平(1966—),男,西南政法大學應用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