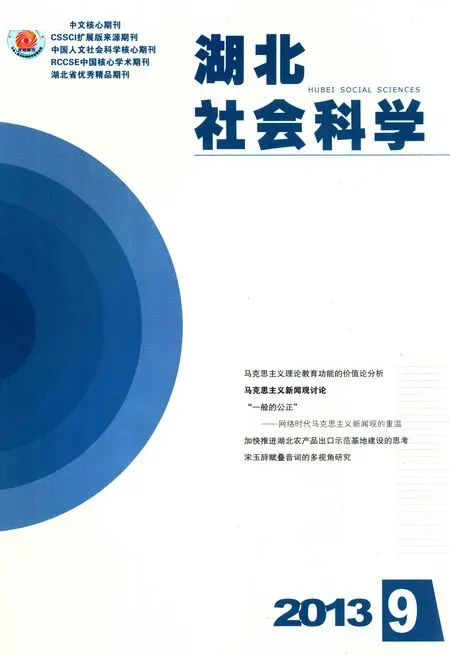論韓德讓與多爾袞身后迥異之原因
董馨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廣東珠海 519041)
論韓德讓與多爾袞身后迥異之原因
董馨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廣東珠海 519041)
遼圣宗時期的大丞相韓德讓和清世宗時期攝政王多爾袞,位高權重、顯赫一時,分別成為遼史、清史中不可回避的人物。韓德讓和多爾袞同樣在先帝駕崩的情況下擁立幼帝有功,同時在小皇帝即位后兩人都有攝政之權,統管國事,地位僅次于皇帝和太后。而且有趣的是兩人私生活方面的傳說更是版本眾多、流傳甚廣。
多爾袞;韓德讓;歷史背景;性格行為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不少少數民族建立了統一王朝,其中北宋時期與中原王朝對峙的遼政權以及中國最后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清朝是其典型代表。在兩朝的歷史中,曾涌現出不少杰出人物,而遼圣宗時期的大丞相韓德讓和清世宗時期攝政王多爾袞,位高權重、顯赫一時,分別成為遼史、清史中不可回避的人物。
韓德讓和多爾袞同樣在先帝駕崩的情況下擁立幼帝有功,同時在小皇帝即位后兩人都有攝政之權,統管國事,地位僅次于皇帝和太后。而且有趣的是兩人私生活方面的傳說更是版本眾多、流傳甚廣。嘗言韓德讓“有辟陽之幸”,[1](p175)多爾袞有“太后下嫁”疑云。有史籍載承天后私謂德讓:“則幼帝當國,亦如子也”,[2](p1011)第一歷史檔案管所藏順治間檔案封皮上有“皇父攝政王旨”的批紅字樣,而在他們身后,韓德讓“贈尚書令,謚文忠,建廟乾陵側。”[3](p1289)“謚文忠”是歷代王朝丞相最不易得、最為榮耀的謚號。多爾袞卻只是在死后曇花一現的殊榮之后被認為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謹告天地太廟社稷,將伊母子并所得封典,悉行追奪。”[4]又被鞭尸斬首,結局悲慘,雖然日后翻案,但終算不德善終。是什么原因使二人結局如此大相徑庭?恩格斯說過:“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因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件。”[5](p478-479)所以二人不同的結局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本文欲對這些原因做初步探悉。
一、歷史背景因素
想認清歷史事實的真相,必然要把歷史事件放在時代背景下去審視觀察。韓德讓和多爾袞所處的歷史大環境是分析兩人結局的最主要的參考資料。
1.二者擁立幼帝的過程。遼穆宗時期,好游戲,厭國事,每日酣飲,國人稱為“睡王”。他昏庸殘暴,不理朝政,引起人民不滿,后被殺。景宗即位,人心四至,但景宗“因風疾,多不視朝”,[1](p175)“凡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1](p1201)景宗病故,年僅12歲的梁王耶律隆緒即位,當時“母寡子弱,祖屬雄強,邊防未靖”,[6](p1201)承天后攝政當國,對內要應付舊勢力反撲,對外要防范宋朝新的軍事進攻,急需一名握有實權、才能卓越的大臣輔佐,又因為“時諸王宗師二百余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援助”。[6](p175)此時遼政權漢官勢力逐步增長,韓德讓是其中地位最突出的。蕭后于是依靠韓德讓和耶律斜軫,“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得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1](p175)實施上述政策后,人心漸定,政局始穩,所以《契丹國志》說:“帝登大寶,皆隆運力也”。而審視圣宗即位時的歷史背景,韓德讓擁立之功不可沒,而且他顯然是誠心實意輔佐幼帝,無可猜忌懷疑之處,因為他的鼎立支持,圣宗和太后才得以坐穩江山。
反觀多爾袞,崇德八年秋,太宗皇太極暴亡,因他身前集權的努力和滿洲貴族日益封建化,繼統危機出現。如早前朝鮮使臣所說:“彼諸王輩皆分黨,多有乖覺之士,汗死則國必亂矣……他日必有爭立之舉”。[7](p3627)這時有三個可能的即位者——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大貝勒代善。其中尤以多爾袞和豪格爭奪激烈,相持不下。兩白旗支持多爾袞,豪格掌握正藍旗,并有兩黃旗支持,在崇政殿商議皇位繼承人會議上雙方劍拔弩張,多爾袞發現形勢不利于己,便提出:“當立帝之第三子,而年歲幼稚……吾與……左右輔政,年長之后當即歸政”,[8]這一折中辦法獲得與會者同意。但是,從此處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多爾袞不是心甘情愿退出王位爭奪、擁立福臨的,而是看出自己無法操勝券,又不甘心豪格即位,才提出福臨,其中考慮原因很多,諸如福臨年幼,易于輔政,福臨母莊妃地位甚高,擁立帝子以打擊豪格,又或者還有后人揣測的多爾袞與莊妃的私情。主要都是多爾袞從自身利益考慮,提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這樣一來其擁立之心遠不如韓德讓單純誠懇,從開頭便埋下了猜忌的種子。
2.二人攝政期間。唯物史觀的觀點說“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9](p389)考察歷史事件要從是否順應歷史發展規律入手。韓德讓所處的時代,正是遼中衰的時期,契丹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必須適應歷史的發展規律。在周邊王朝已經高度封建化的條件下,遼王朝進一步封建化,是大勢所趨。同時面臨北宋西夏等周邊環伺的強敵,遼國把發展國力作為重要議題。我們可以看到承天太后的改革也是從內政和外交兩方面著手。而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主要原因,于是調和國內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成為首要任務。
契丹國家的建立是與漢族地主的支持分不開的。尤其是在占領燕云十六州后,大量的漢族地主進入了契丹的統治階層。但是民族矛盾還是相當的尖銳,像《冊府元龜》中記錄了不少有關人民群眾南奔的情況,還有“有使北者,見燕京傳舍化墨鴉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都表現了漢族人民對中原的思念。所以遼朝需要聯合漢族上層勢力擴大統治基礎、重用漢人、進一步效法漢人的一套統治經驗和方法。韓德讓出生高貴,世代為遼朝效力,同時又是少見的人才,歷史重任就選擇了他。我們還必須注意的一點是:韓德讓是一名漢人,即使他地位再顯赫,官職再高,也不可能有謀朝篡位的想法,一個外族的人是不會做遼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的。而且當時契丹貴族一直存在關于由誰來繼承最高權力的斗爭,爭取到漢人的支持對皇帝的意義就更加不凡了。
再看多爾袞,順治帝即位之后,關內明朝內部發生一系列動蕩,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建立了大順政權,不久攻陷北京,李自成稱帝,而與清軍對峙的吳三桂在一些原因的綜合作用下開關請清軍助攻農民起義軍,多爾袞率八旗勁旅,在山海關大敗李自成,一舉奪取了全國政權。當時他戰功卓著,聲譽和權力有進一步的發展,關內迎降的明朝舊臣甚至只知道有攝政王,不知道有順治皇帝。這樣的聲勢不得不引起小皇帝的懷疑和忌憚。歷來功高蓋主者皆不能擺脫此等命運,后他迎順治入北京稱帝,因其“助成大業……又輔朕登基……碩德豐功,封為叔父攝政王。”[10]實際權力掌握在他手中。此時,盡管清軍占領了北京附近,還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不在自己手中,占領地區人心不穩,多爾袞又繼續肅清反對勢力,為清朝統一全國奠定基礎。雖然他所做的都是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但是不可否認多爾袞的私心,他身居要職,對于未到手的皇位,不是沒有覬覦之心的,同時和韓德讓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本身是皇族,又是皇帝的叔父,擁有兵權,實力雄厚,況且少數民族中本來就有兄終弟及的傳統,多爾袞篡權的可能性就很大,于是皇帝一直以來對他的猜忌不滿便逐漸累積沉淀下來。
還應看到的一點是,雖然即位問題的爭斗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滿清貴族內部的矛盾并沒有隨之消亡,兩黃旗與兩白旗由來已久的矛盾也沒有得到解決。多爾袞的顯要權勢引來個方面的反對和議論,當時很多勢力不敢與他正面交鋒,但卻在等待他死后的全面反彈。
二、人物的性格行為因素
歷來的歷史分析中,我們都非常看中歷史背景因素,這當然很重要,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個人的性格和行為對于歷史事件的影響,這些是事件發生的偶然因素,如馬克思所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并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5](p393)對于韓德讓和多爾袞的不同結局,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比較,一方面是他們本人的性格作為,另一方面是他們的主人即皇帝的性格。
1.本人性格。韓德讓據歷史記載“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1](p1289)《契丹國志》中說他“智略過人”,“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他“總宿衛士,太后益崇任之”。[1](p1289)其崇信程度古今少見,但他并沒有用此作為飛揚跋扈、謀求私利的資本,而是為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忠心報國,勇于進諫,積極薦賢,總的來說能夠顧全大局,如《契丹國志》中記載,自他“為相以來,結歡宋朝,歲時修睦,無少間隙,貼服中外,靡有邪謀”。韓德讓知人善任,比如耶律烏不呂曾經頂撞過他,但他認為烏不呂才堪大用,仍推薦其做統軍使,承天太后問他為什么推薦對他不遜之人,他回答:“于臣猶不屈,何況其余”。他還主動密切與大臣的關系,“昉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已故度法修明,朝無異議”。[1](p1202)在他死后,連宋真宗都說“德讓頗智謀,專任國事……臣僚中未聞有比者”。[11]
韓德讓在擔任重臣的時候仍能嚴格自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少見的,很多權臣都恃寵爾驕,但作為最高統治者是不允許任何人漠視甚至踐踏自己的權威。最為漢族知識分子的代表,韓德讓為遼的封建化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寬厚的為人使他在朝中聲望甚高,一貫的言行為最高統治者分憂,使最高統治者滿意,自然寵遇更厚。
比較來看,多爾袞就不甚相同了。多爾袞自幼勤學苦練,屢建奇功,威望能力遠勝于他人,皇太極也對他說:“朕愛爾過于諸子弟”。[12]所以他一直自視甚高,成為輔佐幼帝的攝政王,隨清軍入關軍事進展的順利,他的權力欲也日益膨脹,再加上皇叔父的長輩身份,他益發嬌縱。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軍事大權,結黨營私,打擊異己,其同母兄弟阿濟格和多鐸都在順治元年被晉封為親王,分別統帥主力部隊進攻李自成大順軍和南明弘光政權,其親信剛林、祁充格在朝中主持政務,而濟爾哈朗因故數次被罰,順治四年七月,他的幾個侄子告發他,多爾袞趁機興起大獄,將濟爾哈朗降為多羅郡王,罰銀五千兩。[13]多鐸則被進為“輔政德叔豫親王”,取代了其地位,豪格在一度復爵后于順治五年(1648年)三月再次被羅織罪名,遭到幽禁,豪格“憂憤填膺……不數日竟絕粒而死”。多爾袞建立的王府“虎踞龍盤……與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其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潛擬至尊”,[14]而且獨攬大權,“凡一切政事及批查本張……擅作威福,竟以朝廷自居。”[15]這一切小皇帝看在眼里,眾人也看在眼里,如俗話所說槍打出頭鳥,多爾袞如此驕橫跋扈,擅越皇權,使皇帝對其積怨日深,他刻薄寡恩、猜忌多疑、賞罰任性、玩弄權術的性格使其越來越眾叛親離,以至于他一死其親信蘇克薩哈首先告發,終于結局悲慘。況且他樹敵不少,那些政敵在他當政期間被一一打倒,但無時無刻不伺機反撲,這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多爾袞在位時如是,被打倒亦如是。
2.皇帝的性格。耶律隆緒是遼代很有作為的皇帝,他“沖齡嗣位,睿智皇后稱制……帝壯,益習國事,銳意于治。”[14]他深受承天后的影響,深知緩和民族矛盾、聯合漢族地主階級的重要性,所以他對韓德讓一直很尊敬倚重。據史載,圣宗以其功大,“見則盡敬,至父視之”,并“日遣其弟隆裕,一問起居,望其帳,其下車步入”。[16](p553)他性格寬厚,高瞻遠矚,看待事情不致偏激,一向以大局為重,對韓的寵遇可以給契丹境內其他漢人以巨大影響,無形中也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特別是漢人中的上層分子,更是不愁晉身無路,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遼朝。
順治帝是位特殊的皇帝,他多愁善感,身體羸弱,他平時若早睡則終宵反側,愈覺不安,他常常自哀自嘆,“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軀,如何挨得長久?”由于幼年他便開始籠罩在皇父攝政王的壓力之下,形同傀儡,這造成了他極度敏感早熟的性格,這樣的性格使他對多爾袞的言行思慮更多,且又涉及個人利益和統治基礎,反應比一般人更為強烈。所以對這位驕橫的叔父反感更深,加之多爾袞為他選擇的皇后令他十分不滿,像他如此多情的人夫妻生活不睦,更加重了對多爾袞的怨恨。
三、其他因素和相關傳聞
1.傳聞方面。后世對多爾袞、韓德讓的事跡傳聞很多,尤其是他們與臨朝太后的關系,史學界爭論不休。姑且不論這些傳聞的可信程度,但事出有因,未必是空穴來風。
路振在《乘軺錄》中記載:“德讓出入帷幕無間然矣……每當弋獵必與德讓同穹廬而處。”[2](p1011)還有宋人言:“契丹主幼,國事決于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信用事,國人疾之”,[17]我們可以認為蕭后和韓德讓關系非比尋常。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六年,太后觀擊鞠,胡里室突隆運墜馬,命立斬之。”[1](p1290)他的炙手可熱甚至達到這樣的地步,還有自己的宮衛,在遼歷史上除了皇族只有他一人有宮衛,可見韓德讓的殊榮,以及太后寵幸的程度。在有關他的記載中,我們沒有看到太后對他有一絲懷疑和輕視,而是始終如一,傾心相待,“及薨……葬視一依承天太后故事”。[1](p176)終遼一世,不僅沒有受到毫發訾議,到后來反而敬禮有加,與蕭后對他的信任息息相關。
有關多爾袞和孝莊的故事眾說紛紜,這里僅舉一例。據說多爾袞位居攝政,于是讓范文程上奏稱他為皇父,曰:“王既子視皇上,則皇上亦當以父視王,可乎?”眾亦曰可,隨后又進一步建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為天子,使圣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郁之中,豈何以教天下之孝?”“王婦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無偶,宣請王與皇太后同宮,皇父攝政王其身份容貌皆為中國第一人,太后頗愿紆尊下嫁,群臣皆賀”[18]在這個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到一直是多爾袞在活動,而太后一直未露面,不禁引人疑慮,詔書中也沒有太后本人意愿。我們或許可以猜測多爾袞是以攝政王身份,通過群臣請求之法達到了逼娶太后的目的,孝莊有被迫下嫁的嫌疑。若與他們相關的兩個太后的情勢有別,就不能不對日后皇帝的想法產生差異。
2.思想觀念方面。此方面論述也與太后事件有關,即兩人所處時代的差異性。雖然兩人都處于少數民族建立王朝、封建化的過程中,但“封建化”的概念已有很大差異。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一般是生產方式以及相關上層建筑的漢化。遼與清的封建化的進程差異最大的就在于上層建筑中的文化層面。遼承唐制并借鑒宋朝經驗,思想觀念方面與唐較為相似,唐代觀念開放,男女禁忌不多,可以自由交往,對婦女的貞潔要求也不及后代嚴格死板,是封建道德史上相對放松的時代。而遼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有“妻后母報寡嫂”的風俗,對女人再嫁視為當然,在封建化過程中,唐代遺風也被一并吸收。清承明制,在道德的要求上是以朱熹的封建道德為準,婦女講究三從四德,貞潔觀刻板嚴格,加之明朝專制集權統治的進一步深化,清代吸收的漢文化與遼時在觀念和形式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對于太后下嫁,后人竭力掩飾,可見眾人對太后下嫁一事是個負面態度。
綜上所述,韓與多爾袞所處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歷史背景有異,兩人性格迥異,他們的主人亦性格不同,與同僚關系也大相徑庭,諸多因素的合力促使二人的結局截然相反。這又一次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關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理論的正確性。
[1]葉隆禮.契丹國志·耶律隆運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路振.乘軺錄[A].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77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脫脫,等.遼史·列傳第12·耶律隆運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清世宗實錄·卷53,順治八年己亥[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脫脫,等.遼史·景宗睿皇后蕭氏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7]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0.
[8]沈陽狀啟·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A].清初史料叢刊:第十一種[C].沈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83年內部刊行.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清世宗實錄·卷9,順治元年十月甲子[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2]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3]清世宗實錄·卷37,順治五年三月己亥[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4]清世宗實錄·卷53,順治八年二月己亥[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5]脫脫,等.遼史·刑法志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大平興國七年[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太宗雍熙三年正月[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8]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卷1)[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高思新
K246.1 K249
A
1003-8477(2013)09-0104-03
董馨(1981—),女,吉林大學珠海學院講師、教研室主任。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百人工程”骨干教師培養計劃項目[院發(2010)13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