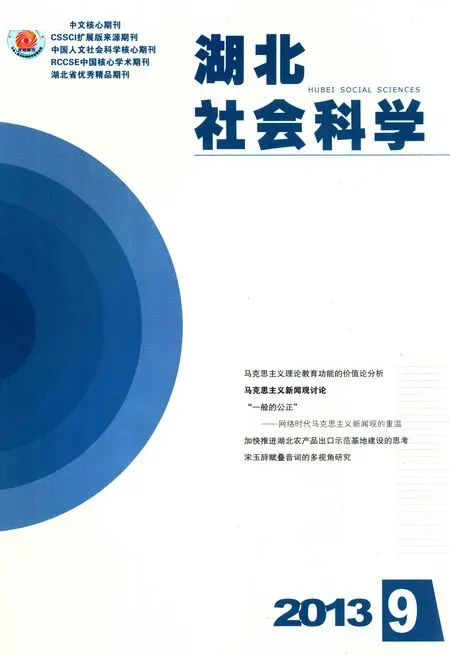海外華人新移民對崛起的中國國家形象認知
——以華人新移民的中國認同為視角
林逢春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廣東廣州 510642)
海外華人新移民對崛起的中國國家形象認知
——以華人新移民的中國認同為視角
林逢春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廣東廣州 510642)
憑借增長的經濟與文化影響力,崛起的中國對全球華人尤其是海外新移民產生了一種輻射源的作用。中國的壯大喚起了海外新移民的族群意識,促使該群體在融入居住國主流社會的同時,也密切關注祖籍國中國的發展動態和國家形象。以留學生和技術移民為主要代表的華人新移民對中國國家形象總體上持一種積極的評價;同時,他們從跨國行為者的角度,借助現代媒體等渠道對中國的內政外交表達了自身的觀點,鞭策中國塑造大國形象和民族尊嚴以滿足其成就“主流精英”的心理訴求。華人新移民對崛起中國的國家形象認知,使之在維護和優化中國形象以及為中國的發展建言獻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崛起;海外華人新移民;國家形象;認同
對于中國崛起的課題,近些年國內外學者從國際政治和傳播學角度研究中國崛起(或和平發展)與中國國家形象的成果頗豐。這些作品大體上從形象的內涵入手,運用相關的理論,探究國家形象對中國實現崛起的功能意義,或者是大國和平崛起視角下國家形象優化的路徑。①參見門洪華,周厚虎: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及其傳播途徑[J].國際觀察,2012年第1期;李格琴:大國成長與中國的國家形象塑造[J].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期;羅建波:論中國和平發展視野中的國家形象塑造[J].新遠見,2007年第9期等。對于同一課題,作為非國家行為體——華人散居者,基于其特有的屬性,尤其是伴隨著中國崛起背景下海外華人新移民出現的新趨向,不少學者開始從軟實力等理論角度思考海外華人(移民)在中國和平發展乃至構建和諧世界戰略進程中的特有功能。②代表作品參見陳云云,張晨輝:和諧世界視域中的華僑華人[J].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陳奕平:華僑華人與中國軟實力:作用、機制與政策思路[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陳遙:東南亞的軟實力與華僑華人的作用——國際關系學和華僑華人學整合的視角[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許梅:東南亞華人在中國軟實力提升中的推動作用與制約因素[J].東南亞研究,2010年第6期等。中國崛起所推動的華人新移民群體族群意識的上揚,使得該群體更關注中國的外交和國家形象問題,有些華人移民甚至呼吁和鞭策自我素質形象的提升以優化“中華形象”。③華人傾向于用“中華形象”一詞來表達自身中華文明跨國傳播的傳播策略和文化訴求,以避免陷入類似“中國形象”的政治學上的國家概念而招致爭議。參見曾筱霞,冰凌:中華認同與中華形象[DB/OL].中國新聞網,2011年09月16日,http:// www.chinanews.com/kong/2011/09-16/3333684.shtml.然而,或許是出于復雜的政治因素,海外華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評價,或隱含在華人認同的專述,或散見于僑務工作者和僑領的發言稿、海外華文傳媒評論或會議對話中,也未深入探究華人的中國認同與中國國家形象之間的內在機理。這使得國內繁多的華人研究作品中暫時未見系統的對華形象研究成果;④參見葉虎:海外華文傳媒與中國國家形象塑造[J].當代亞太,2001年第1期;[西]徐松華:海外華人和祖國榮譽——中國形象與25年來在西班牙的變遷[J].統一論壇,2009年第6期;[墨]劉可偉:中國30年改革開放對海外華僑華人觀念的改變影響深遠[J].統一論壇,2009年第1期等。而海外學者劉宏和丁勝則洞察到在中國崛起背景下華人(精英)群體涌現的族群民族主義趨勢、表現及由此出現的對中國外交和國家形象的互動關系。[1]另外,根據國內學者目前對“國際移民與國家形象”的研究成果,以新移民為主體的海外華人自身的形象及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將影響到中國的外交與形象。[2]本文以海外華人新移民的中國認同為視角,梳理和探析中國崛起背景下華人新移民對華形象認知的動向,以此探尋這種形象認知行為對中國大國崛起的功能意義。
一、移民與祖籍國國家形象的聯動關系
國家形象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自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是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的體現。[3](p23)在強化硬實力的同時,整合本國的軟實力資源,通過良好的聲譽釋放善意和穩定的預期,減少中國國力迅速增長對現有國際權力結構產生的沖擊及由此產生的猜忌心理,有效地向世界表達中國訴諸于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和全球責任。[4](p220)通過這種努力優化本國的國家形象,有利于中國在崛起進程中贏得國際體系下他國的認同與支持。
對于一個移民國家而言,國際移民成為遷出國國家形象的載體。國際移民從一踏進接受國伊始,他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個體的形象,更是整個遷出國的國家形象。移民給予接受國國民以直接的感性認知遷出國的機會,移民個體和群體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向接受國的國民傳遞著與遷出國的國家形象相關的信息。
作為重要的移民國家,20世紀70年代末移居海外的華人新移民以自己的言行傳遞著遷出國中國的形象符號等信息。本文論述的海外華人新移民,指涉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公民移居國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權或加入當地國籍的華僑或華人。該群體主要由留學生、技術移民、商務移民、家庭團聚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構成。由于非法移民是國際社會共同反對的對象,本文所談的新移民不包括該群體。這些新移民的言行舉動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對遷出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都會產生相當的影響。因為在遷入國民眾眼里,新移民的集體屬性(身份認同)比個人屬性(如姓名、籍貫)更為顯眼。作為遷入國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新移民個體素質修養和精神品質,自然受到所在國媒體和公眾的關注。新移民身上所附帶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行為方式也會給接受國原有的文化結構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華人新移民在居住國為謀生和發展的社會經濟行為,則影響到居住國的生存資源環境。受到沖擊的一方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會竭力捍衛本國和主體族群的文化和生存資源因而同新移民群體形成一定的張力。自此,遷入國因而容易對新移民的遷出國——中國的文化和政策取向表示關切。此外,移民還影響到遷入國對遷出國的整體認知,而這種認知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其對遷出國的言語描述及其互動。[5](p63-64)新移民總體文化素質較高,他們在中國實現一定社會化的基礎上才以改善經濟條件為目標對外移民。一方面,出于一種鄉土感情,他們總體上傾向于描述遷出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另一方面,老移民支持中國革命和匯款回祖籍國及僑鄉而引發“政治效忠”問題的出現,新移民更多是借助跨國專業性社團和新媒體等渠道聯動中國社會。入籍或取得居留權的新移民憑借知識技能融入居住國主流社會,并切實為當地的教育、科技等領域作出應有的貢獻。
可見,新時期華人新移民在居住國的努力及其公眾形象,尤其是該群體對祖籍國中國的形象認知,無疑成為中國在和平崛起進程中建構良好國家形象的影響因素。于是,了解新移民的對華形象認知及其表現,有助于我國在崛起進程中把握和設計好必要的國家形象戰略和僑務工作方向。
二、海外華人新移民的中國認同及其對華形象認知
認同(identity)一詞在中文語境中具有“身份”、“同一性”和“認可”等三方面的涵義。它一般指的是個人和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趨同過程。[6](p15)基于特有的跨國性和民族性,海外華人的認同因為復雜的社會化進程而有了多重維度。事實上,對于分布在海外各地的眾多華人,任何一個華人認同都是復雜多變的。對此,在分析華人對中國認同問題上,需要在解釋的整體性與復雜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王賡武教授以“多元認同”來處理此問題,他以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和階級認同來分析華人中國認同的動態變化。假定任何個人和集團在同一時間持有一種以上的認同完全正常。在該分析模型中,多元認同的過程有賴于相應的規范對華人所形成的約束力,在華人的互動和實踐中,以上四種認同分別對應政治規范、自然規范、文化規范和經濟規范。這些規范指導、支配和調節著華人行為的標準。兩種或兩種以上規范形成一定的協同效應并產生一種復合型認同。具體到各地華人,其多元認同的變異類型則千差萬別。但畢竟人類多樣化的認同總是歸屬于某個群體或組織,從認同的歸屬來看,政治認同和族群認同構成分析華人身份認同的兩大維度。[7](p69)不過,考慮到全球化背景下華人新移民順應國際移民浪潮以改善經濟地位的事實,跨國認同也應當作為當前華人新移民認同的重要維度之一。換言之,華人新移民的中國認同可以從政治認同、族群認同和跨國認同等三個維度加以考察。
循此邏輯,身居海外各地的華人新移民在確定最終的政治認同后,都力圖通過壯大華人經濟、踴躍參政、發展華文教育和加強華人社團功能建設等多方面的努力,逐步進入當地主流社會并提升其在居住國的利益地位。此外,新移民一般掌握兩種(以上)語言,在兩個(以上)國家地區擁有一定的關系網絡和事業基礎。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表現出行為上的跨界性、文化上的多元性、經貿的全球性,給人一種“既在此處又在別處”且“浮萍無根”的漂移狀態。一方面,基于經濟利益的工具理性,他們同全球范圍內同一階層(主要是中產階級)進行經貿往來,意欲憑借雄厚的技術和資本躋身所在國主流社會;一方面,伴隨中國崛起而來的拓展性海外利益及其優惠性的僑務政策,新移民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糅合因族群文化的親近感而激發的價值理性,同祖籍國中國以及同一階層的海外華人進行經濟與文化上的密切往來。美國華人服裝公司利用利維·斯特勞斯公司的轉包合同制度,在唐人街辦起服裝加工廠以承接美國商業相關業務,并逐步推動美國公司的升級;同時,利用中國大陸的優惠政策和傳統文化紐帶關系,在大陸建立了服裝加工廠,形成產業鏈并逐步拓展亞太地區的市場。[8](p185)如此一來,海外新移民形成并維系了多重的聯結祖籍國與居住國之間的社會關系進程,在此進程中他們建構了跨地理、文化和政治疆界的社會場域。[9](p11)這符合有關“跨國主義”的機制內容。居住國為新移民提供了政治、經濟權利認同與訴求的本源,而祖籍國中國的經濟文化影響力則激發了該群體族群認同的整體性上揚。在全球化背景下,有鑒于崛起中國所帶來的潛在收益和傳統的家庭紐帶關系,并且在中國官方的政策施動下,華人新移民在跨國經濟文化往來過程中運用了中華文化符號并聯通中國與居住國的經濟社會往來;同時,新移民造成了新華僑的生成,在力爭躋身北美、歐洲等發達國家與地區主流的生存競爭當中,祖籍國經濟與文化的興起支持了這些新移民維護自身地位的族群意識。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硅谷等地區的商務移民和技術移民以“太空人”模式穿梭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受到中國經濟高增長和優惠政策的吸引,他們將家庭留在美國,而將事業轉向中國大城市。利用雙語文化語言優勢,在美國在華跨國公司中擔當重要角色,或將美國先進的科技與管理經驗運用到中國上海、昆山等城市或僑鄉。出于家庭紐帶和事業的穩定,他們對太平洋兩側都有一種歸屬感,并關注和期待中國與居住國建立起一種穩定的雙邊關系。而由美國留學生和知識分子通過“美中教育聯合會”等組織,推動美中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像王紹光和劉亞偉等華人學者,深入中國基層,研究分稅制和基層民主,并向中國政府、知識界和民間傳達相關理念。支撐他們行為的動機信念是“既然來自中國,就有責任和義務為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健康發展盡力,使中國變得自由、民主、繁榮、昌盛”。[10]
新移民群體因而發展起了一種超越一國疆界,既接受居住國的政治認同,又沿著種族主義方向衍生并認同全球各國華人的跨國民族主義。①海外華人的跨國民族主義的相關屬性可參見吳前進:《冷戰后華人移民的跨國民族主義——以美國華人社會為例》[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Hong Liu.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4,2005這種跨國民族主義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華人新移民對中國的認同。新移民對祖籍國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源于該群體成員對族群(文化意識)的認同。而當前新移民所表現的族群認同究其實質是一種族群性的民族主義,所以,新移民對全球范圍內的海外華人以及祖籍國中國的認同程度深刻地影響到了其對華國家形象認知。基于政治認同問題,海外新移民以“中華形象”來表達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對于留學生、技術移民等逐步融入居住國主流社會的跨國華人,他們關心中國的發展狀況和國際形象,在各種與中國有關的紀念活動中也表現出一種自豪感,并期待中國的國家形象能夠持續優化,滿足其在居住國生存競爭過程中的自尊。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達到一個頂點。奧運圣火傳遞期間由留學生主體的海外華人新移民自發組織起來護衛火炬,并連同國內網民反對CNN網站對西藏“3.14騷亂”不實的報道和偏見。[11](p24-25)擁有知識和技術的新移民成為這股思潮的主體,他們不論居住地、不管何種身份,不約而同通過游行、新聞傳媒、網絡論壇等多種公開渠道來表達其對中國利益立場的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他們欣喜地看到了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連年保持高增長態勢,中國在走向世界的同時學習相關的國際規范規則,開始重視人權、信息公開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建設。對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們大多希望“大部制”改革能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一個范本。在國際社會上,中國因為抗擊經濟危機等多方面的努力而表現出更為自信和負責任。對此,華人對當下祖籍國的繁榮進步表現出一種自豪感!在中國官方“為國服務”的優惠政策感召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在中國與居住國之間的跨國聯系趨于頻密,并希望享有“雙國籍”,依托祖籍國和平發展所提供的條件環境實現自我發展。②相關資料參見“在日華僑華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值得期待”[OL].中國新聞網,2008年03月07日,http://news.qq.com/a/ 20080307/002945.htm;海外華僑華人認為中國展示出負責任大國形象[DB/OL].新華網,2009年3月9日,http://news.xinhuanet. com/misc/2009-03/09/content_10978641.htm;[墨]劉可偉:中國30年改革開放對海外華僑華人觀念的改變影響深遠》[J].統一論壇,2009年第1期等;劉宏:海外華人與崛起的中國:歷史性、國家與國際關系[J].開放時代,2010年8期,第88頁。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不少華人精英在僑務會議和華人媒體等公開場合將華人自身形象與“中華形象”糅合為一體,在自信之余還表現出一種自勉的行為心理。作為國際移民的重要一支力量,多年在居住國民眾的接觸和文化碰撞中,“生于新中國,長于紅旗下”的新移民,由于受到祖籍國社會化的影響,使之在跨國活動中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依然強烈。隨著中國的崛起,他們從祖籍國獲取的利益機會隨之增加;同時,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形象態勢則維系和支撐起華人新移民內心深處成就居住國主流精英的自我身份認知。[12](p24)由此,以技術移民為代表的在華人精英期待著中國能以負責任大國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以滿足其成就“主流精英”的心理訴求。為此,他們要以良好的公共形象出現在居住國社會。近些年,世界各地的新華人華僑不但反對那些影響中國形象、有損民族尊嚴的歪曲媒體聲音,還呼吁各地華人潔身自愛、提升自我素質形象。2011年9月17日至18日,南非華人自發投資舉辦的宣傳中國國家形象的大型圖片展“中國秀”,向南非華人華僑和民眾展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和成就。此次圖片展是海外華人首次以自發組織的形式推廣中國的國家形象。[13]難能可貴的是,越來越多的海外僑領在公開場合都表達了華人形象與中國形象的相關性。西班牙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徐松華就公開表示,海外華僑華人和祖國的榮辱息息相關,華人的舉止言行代表著中國的形象,呼吁華人華僑要高度重視該問題,并在生活和商務活動中踐行中華民族平等互利的理念,并在崛起當下采取理性謙恭的辦法處理與他國經貿的摩擦,以彰顯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良好形象。[14](p22)而墨西哥蒂華納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劉可偉也表示,中國的崛起和外交智慧,歷練了華人內心的正氣和大氣,升華了華人的人生觀。[15]
當然,由于海外華人新移民其教育背景、生活環境和價值觀的差異,不否認部分華人對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國家形象出現一些批評性意見。他們在關心和贊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同時,尤為關切中國的政治透明度。特別是一些華人精英,他們對中國前進中出現的社會不公平、腐敗以及環境惡化等問題進行了批判。基于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他們有時也會主觀地針對中國對某一事件的外交處理方式與結果表現出一種不滿。①參見Ding Sheng.Digital Diaspora and National Image Building: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Diaspora Study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J].Pacific Affairs.Vol80,2007-2008Winter一文,部分華人對1998年印尼排華浪潮中中國政府的反應,以及中國政府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關痛癢的批評表示不滿,他們認為這種外交方式致使中國外交形象“太軟”;同時也對中國出現的“黑磚窯”、食品安全和官員腐敗等事件持批評態度。
總之,以經濟高增長為主導的中國國力的綜合性提升,繪制出海外華人新移民內心深處中華民族復興的愿景。他們從中看到自身地位提高的發展機遇和心理動力,在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得到總體性提高的同時,也期盼祖籍國通過堅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等舉措解決中國大國成長道路上存在的問題,進而推動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在自強自立的民族主義感情驅使下,部分華人精英做出自我鞭策,期盼中華民族昌盛圖景和主流精英形象的共同展現。
三、華人新移民對中國崛起的功能意義:基于其對華國家形象的認知
海外新移民為海外華人社會注入新的血液,在經濟利益和民族主義作用下,該群體的中國認同及對其國家形象認知的新動向,使之在中國崛起的同時產生一種本土回歸運動:從中國方面看,基于華人移民客觀上承載著國家形象的事實及其發展新動向,近些年中國政府啟動僑務公共外交,希望借力華人振興中華民族文化和傳播中國善意的政策理念,進而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以支持中國的和平崛起。從海外華人新移民方面看,基于跨國民族主義而形成的對祖籍國的總體正面形象認知,他們維護并期待中國國家形象的進一步優化。
一是構建網絡虛擬社區,表達中國國家形象優化的方向。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基于相似的文化認同和民族情感,技術移民通過互聯網為核心的國際信息技術,建立起不同類型的網絡社區。在這個虛擬的族群性社區上,他們傳播和分享有關中國各個領域的信息,關注中國與其居住國關系動態。他們利用博客、聊天室等技術,拓展社交圈子以實現利益往來、抒發情感以維系宗親關系、交流知識和信息以增進對中外社會動態的理解。誠如約瑟夫·奈所言,全球信息化背景下那些掌握國際信息傳播能力的非國家行為體對一國政治的可信度和國家形象的影響力愈發明顯。[16](p117)技術移民為代表的新移民,他們參與中國事務的討論并從跨國行為者的角度提供自身觀點,還與中國國內網民一道通過信息溝通、對話和辯論而鞭策中國的內政外交及其國家形象走向優化。旅美學者薛涌被認為是中文世界里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他在博客上評論中國事務,并從國際視野中為中國的形象優化提供了一些建設性意見。而鳳凰博客則開設了“海外華人圈”,成為海外華人博客的集聚地之一。這類博客聯動中國網民,他們所傳播的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理念也漸漸為中國學界和網民所接受。[17](p16)這類新移民通過信息溝通和文化理念的交流,激勵中國國家形象的進一步優化。
二是華人精英自發組建智庫,為崛起中國建言獻策。在加強美國華人學者的支持體系的同時,中國旅美社會科學教授學會(ACPSS)也以“支持中國的改革和對外開放”為目標。該學會凝聚了美籍華人學者,定期在兩岸三地主辦研討會,深入研究中國的現代化和中美關系問題,為中國學者在中美戰略對話中作出了貢獻。[18](p228-234)而香港亞太研究所根據各階段中國發展的主流問題,每年召開一次涵蓋海外華人學者專家的學術研討會,為中國在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外交定位和國家形象塑造等方面獻言獻策。基于華人精英的開放性、專業性和獨立視野,由華文媒體和華人專家組成的海外華人智囊團通過定期的“會診”及其獨特見解,對大陸決策層和智庫產生了間接性的影響,進而對崛起中國起著一種補充性的助推作用。[19](p28-29)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一些新移民的某些敗德行為和海外新老移民的摩擦,尤其是冷戰結束后海外華人新移民在當前仍屬民族國家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下,跨國民族主義趨向正在令一些移民接受國的政府、公眾和媒體懷疑和渲染移民群體背后的移民遷出國政府的企圖,其公眾形象也容易導致居住國民眾對祖籍國中國國家形象的聯想和猜疑。可見,如何協調民族主義與跨國主義無疑成為當前中國僑務工作的重要問題領域。
四、結語
海外華人新移民在中國崛起的輻射下所表現出來的跨國民族主義,使之在融入居住國主流社會的同時,也從總體上擁護支持中國的國家形象,因而能夠在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有所作為。鑒于此,中國應該在崛起的征途上深入實施僑務公共外交,根據海外華人社會的新動向對海外華人群體進行細分,尤其是要明確海外華人新移民的屬性,規劃僑務公共外交的推進策略。切實發揮新移民在僑務公共外交戰略中的中堅作用,尤其是借助留學生與技術移民為代表的華人精英在國際信息技術領域中的優勢地位,在挖掘和凝聚中華民族核心文化價值的同時,引導和攜手華人精英傳遞中國的和合文化理念,消弭國際社會上五花八門的“中國威脅論”;同時,通過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將順應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文明潮流,致力于健全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培育民間組織良性發展的土壤,借此贏得海外華人對我國僑務公共外交的認同與配合。通過多方面努力實現兩者間社會資本的互利性、價值觀共享性和文化共榮性,以共同的文化紐帶攜手建構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家形象,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注入持久的動力。
[1]Hong Liu.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4,2005;Ding Sheng.Digital Diaspora and National Image Building: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Diaspora Study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J].Pacific Affairs.Vol80,2007-2008Winter;Wanning Sun.Motherland Calling:China’s Rise and Diasporic Responses[J].Cinema Journal49,Number 3,Spring 2010.
[2]強曉云.試論國際移民與國家形象的關聯性——以中國在俄羅斯的國家形象為例的研究[J].社會科學,2008,(7).
[3]管文虎.國家形象論[M].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
[4]李正國.國家形象構建[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5]強曉云.試論國際移民與國家形象的關聯性——以中國在俄羅斯的國家形象為例的研究[J].社會科學,2008,(7).
[6]周大鳴.論族群與族群關系[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2).
[7]柴玲.論海外華人的中國認同[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0,(1).
[8][美]陳錦江.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美籍華人企業經營網絡和跨太平洋的經濟聯系[A].孔秉德,尹曉煌.美籍華人與中美關系[M].余寧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9]吳前進.新華僑華人與民間關系發展——以中國—新加坡民間關系為例[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7,(6).
[10]Kellogg,Ryan P.China's Brain Gain?Attitudes and Future Plan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J].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Jan2012,Vol.8 Issue 1;Boudreau. John.Overseas Chinese return to start companies[N].San Jose Mercury News(CA),10/29/2009.
[11]王家駿,蔡逸楓.民族主義新勢力[J].鳳凰周刊,2012,(13).
[12]Pei-teLien.ChineseAmericanAttitudetoward Homeland,Government and Politics:A Comparison among Immigrations from China,Taiwan and HK[J].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Vol14,2011.
[13]非洲華人首次自發展現中國國家形象[DB/OL].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5686136.html,2011-09-18.
[14][西]徐松華.海外華人和祖國榮譽——中國形象與25年來在西班牙的變遷[J].統一論壇,2009,(6).
[15][墨]劉可偉.中國30年改革開放對海外華僑華人觀念的改變影響深遠[J].統一論壇,2009,(1).
[16][美]約瑟夫·奈.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M].錢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17][新加坡]周兆呈.新空間新網絡新角色——博客對海外新移民與中國互動的影響[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7,(4).
[18][美]吳寧華.改善大陸社會狀況和美中關系:四個由華裔美國人領導下的跨國協會個案研究[J].孔秉德,尹曉煌.美籍華人與中美關系[M].余寧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19]王文.解密海外華人智囊團——海外華人智囊團建言中國崛起[J].華人世界,2007,(1).
責任編輯 申華
D634
A
1003-8477(2013)09-0050-05
林逢春(1981—),男,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講師、經濟師。
國務院僑辦僑務理論研究廣東基地課題“僑務公共外交:理論基礎、作用機制與政策思路”(GDQW20121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