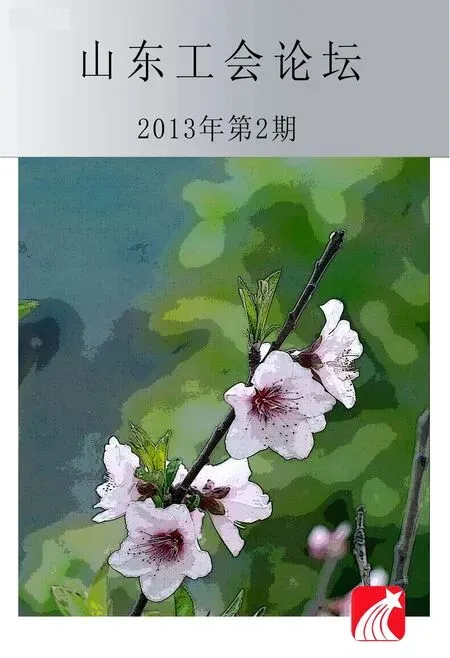從比較法的視角看中國侵權法的價值與完善
孫曉蓉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北京 100088)
【法學新論】
從比較法的視角看中國侵權法的價值與完善
孫曉蓉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北京 100088)
《侵權責任法》是在借鑒外國侵權行為法和總結我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頒布的,在救濟權利、填補損害這一功能定位的指導下,我國《侵權責任法》在體系建構、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賠償責任等多方面制度的設計上都體現了對民事權益的全面保障。隨著社會生活的現代化和復雜化,各國侵權行為法都有了一定程度地發展,以加強對私權的保護。以義務為切入點構建侵權體系更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對侵權法提出的新的要求,在此基礎上,筆者通過對外國侵權法的比較研究,為《侵權責任法》的完善提出建議。
救濟法;利益衡量;民事權益
一、侵權法的價值理念:對私權的全面保護
(一)權益與自由的價值平衡
王利明教授指出:“在近年來我國的法治建設過程中,民事立法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對各種私權的確認,即通過頒布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等法律來不斷確認民事權益;另一方面,通過頒行《侵權責任法》,對已為法律所確認的民事權利給予充分的保護,提供相應的救濟。”與物權法一樣,《侵權責任法》的核心在于保障民事主體的私有權益。在大陸法系的民法典中,侵權法都是債法的組成部分,最為典型的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其僅僅把侵權行為作為債發生的原因之一進行了規定,與合同之債、代理權授予之債、無因管理之債和不當得利之債相并列,并沒有占有很大的立法空間。而在英美法系的民法立法體系中,侵權法與財產法、合同法等處于同等地位,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歷時八年,在中國誕生了世界成文法中第一部以侵權法命名的法律,這在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立法中具有開創性的重大意義。
我國的《侵權責任法》是對民事主體的各項民事權利在受到侵害的時侯進行救濟的法。“法的價值是標志著法與人的關系的一個范疇,這種關系就是法的存在及其屬性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或積極作用、效用。”[1]對侵權責任法價值功能的不同認識,直接關系到侵權責任法的體系構建、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賠償責任等多方面制度的設計。王利明教授認為,侵權法的主要功能是為受害者提供救濟,更確切地說應當是“補償”,而“填補損害”功能的適用要在以損害由受害人自我負擔為原則、以加害人負擔為例外的背景下而展開,并在著重于維護受害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兼顧加害人的行動自由。
任何一部侵權行為法都承載著需要協調的二元價值目標,即民事權益的維護和行為自由的保障。與此相適應,它的任務就在于,以社會現實需要為出發點,在權益保護和自由保障之間不斷尋求平衡。“一種法律秩序在何時、在什么條件下將已經發生的損失轉由他人承擔,這取決于很多因素,特別是取決于在該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和傳統習慣。”[2]。
(二)《德國民法典》中的侵權行為法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者在經濟自由主義的大環境下,深受康德自由哲學的影響,從而在侵權行為法上更多地關注社會成員的行為自由。為了能夠充分保障行為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自我發展,立法者所確立的侵權行為法的模式即是:只有該行為在侵犯了法律所明確列舉的絕對法益時才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其他情況則要滿足更加嚴格的條件。從具體法條來看,《德國民法典》設置了一個小的侵權責任的一般條款,其823條第一款將侵權行為定位為“對絕對權利以及相類似權利的侵犯”;同時,《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二款以及第826條分別規定了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的法律而損害他人以及違反善良風俗的故意損害所應承擔的責任。這三個“小的一般條款”以“符合事實構成、違法性及過錯”這三個要件,描述了傳統侵權行為法律規范的基本內容,作為法官判定承擔侵權責任的基礎。又因為事實的構成要件可以被拆分為行為、因果關系和損害事實這三個方面,所以德國侵權行為實際上是由四要件構成,即違法性、過錯、因果關系以及損害結果。通過分析可知《德國民法典》將“違法性要素”從過錯概念中剝離出來,將之確立為獨立于“過錯”的侵權行為的要素,由此可見,德國民法典對個人的行動自由的強調強于對社會安全的維護,因此其在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的立法上注重限制對侵權責任的適用。
德國的這種立法設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概念法學方法論的影響。“概念法學認為成文法典一旦制定出來即可自給自足,法典為人們交往提供了普遍的結構,并足以解決各種各樣的糾紛。法官只需要根據適當的邏輯推理,就可以從現有的由概念構成的法律條文中得出正確的判決,而無需求助法律之外的東西,也無需考慮法律的目的、公平正義的理念和社會的實際需要。”[3]這種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方法突出強調了法律的穩定性這一基本特征,為人們提供了確定的行為模式。但是隨著社會生活領域的不斷拓展和時代的進步,當時立法者所構建的理論上極為完美的侵權行為法模式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時顯示了它力不從心之處。侵權責任法作為民法中公認為最具有演進性和活力的部門,其因與所處時代的公共政策和道德習俗等具有密切關聯而富有濃郁的時代氣息。對于這樣一個處于快速演進的法律部門來說,“侵權法的晚近發展讓我們深刻感受到這一制度的諸多不適;侵權法不得不去適應社會的變遷和賠償損害的新要求”。[4]與此同時,概念法學的觀點也受到了之后興起的利益法學派的猛烈抨擊。“法官僅依靠邏輯結構不能令人滿意地處理生活的需要。立法者必須保護利益……法律和生活所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法官——作為思想協助手協助立法者,不僅注意語句和命令,而且考慮立法者的意圖,并親自檢查有關的利益,表達法律的價值,即使在立法者尚未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亦是如此。”[5]從而,才會有后來德國侵權行為法的突破和發展,如一般人格權,純粹經濟損失等概念的產生。《德國民法典》將過失責任限定在第823條第一款所特別列舉的受保護利益的范圍之內,但在不斷地發展中德國立法者希望通過將民法典第826條中“故意”的概念延伸至最大限度將過失責任擴張至純粹經濟損失。從人格利益的方面分析,在德國法上,個人名譽、榮譽和隱私的保護得到了明確的承認。一般人格權在《德國民法典》中的侵權法部分基本無體現,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才被德國法院通過判例在司法實踐中發展起來。
(三)法國的侵權法
在成文法國家,同樣采用小的一般條款的典型國家是法國,但是在價值取向上卻與德國侵權法截然不同。《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規定:“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錯而致損害發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責任”。第1383條規定:“任何人不僅因其行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且還因其懈怠或疏忽大意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因此張新寶教授認為“法國民法主張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和過錯三要件”。由于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響,法國將“違法性要素”內置于過錯概念中,構建起開放式的過錯侵權責任法體例。這樣的體例高度強調社會安全價值,賦予法官極大地自由裁量權,從而能最廣泛地救濟受害人并填補損害。但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法國侵權法的這一體例招致了“不能充分保障行動自由”的質疑。此外,在法國法中,“違法性要素”是從違反客觀法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例如,2005年的法國《債法改革草案》就將過錯定義為“違反法律法規所確立的行為規則或者未盡到謹慎勤勉的一般義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對行動自由的保護,但是從違反“客觀法”角度闡釋的違法性,所指的只能是廣義上的“法”,所以《草案》的這一體例仍然是以社會安全價值的保障為核心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國侵權行為法所保護的范圍具有極大地開放性,可以滿足社會不斷發展對侵權法提出的新要求。
(四)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價值取舍和制度構建
與《法國民法典》對侵權行為的價值衡量相類似,我國《侵權責任法》在立法中始終貫徹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其保護范圍具有極大的寬泛性。但是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我國《侵權責任法》區別于德法兩國立法,在借鑒了埃塞俄比亞立法模式的同時結合我國實際需要進行了新的發展。《侵權責任法》第二條直接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緊隨其后列舉了生命、健康、姓名權等18種人身、財產權益。這一條文作為侵權責任大的一般條款,確定了《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即所有應當依法保護的民事權益。此外,對于將來可能發生、目前沒有預料到的特殊侵權責任預留了法律適用的空間。與此相配合,《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一款作為侵權責任小的一般條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由此為一般侵權責任提供了請求權基礎。這兩者相互協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小搭配的雙重侵權責任一般條款體制。在總體概括的基礎上,我國立法者借鑒英美侵權法侵權責任類型化的經驗規定輔之以幾種特殊侵權的類型,如網絡侵權、醫療損害侵權、環境污染侵權、高度危險責任、飼養動物損害責任以及物件損害責任等。這種立法體制不僅克服了《德國民法典》侵權行為法體系過于封閉的不足,又避免了以《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為代表的一般條款模式過于抽象的不足,成為純粹的侵權責任法保護客體的范圍標準,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侵權責任法》的彈性和包容性,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適應不同時期對私權保護的需求。
從大陸法系的民法來看,許多國家的民法典中僅僅規定了單一的過錯責任原則,而對于嚴格責任都規定在特別法之中,例如德國、日本等國家。但我國選擇了多重歸責原則,即通過92個條文確立了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以及嚴格責任相結合的現代新型侵權法體系,這與分別制定于19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侵權責任法部分(共5條)、20世紀初的德國民法典侵權法部分(共31條)相比,內容大為充實,對私權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護。從責任形式方面來看,《侵權責任法》為公民的私權利提供了全方位的、更加充分的救濟。我國《侵權責任法》第15條一共列舉了8種責任形式,其中包含了物權請求權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也涵蓋了“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債權請求權。此外,《侵權責任法》第一次在第22條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并通過第47條規定了懲罰性賠償。雖然具體操作中量化的標準還有待于明確,但不難看出,《侵權責任法》從保護人身權益到保護財產權益、從過錯責任原則到無過錯責任原則、從一般侵權到特殊侵權、從責任認定到責任方式、從自己責任到替代責任、從物質損害賠償到精神損害賠償、從實際損害賠償到懲罰性賠償等諸多規范,都十分充分地體現了重點保護民事權益和全面救濟受害人的基本立法理念。
二、侵權法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一)責任承擔基礎——從權利向義務的轉換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德國民法典》從“權益侵害”角度去定義“違法性”,這種立法設計必然會導致以受侵害權益的不同為區分依據,構建起“三段式”的“小概括式”的過錯侵權責任體系。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一般性條款的路徑也是由“權利”導向“不法”進而最終導向“責任承擔”這一法律后果。不可否認,權利始終是民法制度構建的核心。縱然我國立法工作者在《侵權責任法》第二條規定了外延極為豐富的18種民事權利,試圖通過法益損害、行為可歸責性、不法性、過錯這四個循序漸進的步驟的判斷來確定是否承擔侵權責任,但在飛速發展的當今社會,仍然無法達到“充足”的程度。“民法作為維護和促進私人利益的法律,其自由運動的形式并不是完全定格在權利技術上,因為至少在債的關系上,債務更應當成為決定性因素,那種將個體所能遇到的所有私法狀態都歸結為權利體系的觀點具有片面性。”[6]權利不僅僅是作為承擔責任的一種媒介,更是法律維護正義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近現代侵權法通常只是將權利受害作為一個或有或無的條件,而主要在于強調侵權構成歸于某種更為廣義的法定義務之違反、某種程度主觀不法的存在、因果關系、損害等因素以及強調損害賠償義務的直接發生性。”[7]因此,更加合理的解釋應當是從義務的視角來審視當今世界各國侵權法的發展和完善,通過“義務”這一橋梁來達到權利保障的最終目的。
縱觀《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體系,立法者在規定特殊侵權行為的多個具體條文中就體現了由權利向義務為歸責基礎的轉換。如《侵權責任法》第37—40條所明確規定的公共場所管理人和群眾性活動組織者的安全保障義務、教育機構的安全職責,并且通過第七章對醫療損害的規制明確了醫院等醫療機構的安全注意義務。這些條文的制定不僅充分體現了我國立法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完善,更適應了我國國情的現實需要。
(二)我國《侵權責任法》在制度構建上的完善和建議
但是,《侵權責任法》中這些以“義務”的違反為責任承擔切入點的規定僅僅體現在特殊侵權類型中顯然是不夠的,特定類型化的立法模式使得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只能適用一般侵權責任條款的過錯責任原則來判斷其是否侵害了《侵權責任法》所列各項人身、財產權利,從而可能最終導致法律無法對此行為作出規制。縱觀世界各國民事立法,可以發現荷蘭和英格蘭侵權行為法的規定恰恰彌補了這種缺陷和不足。《荷蘭民法典》認為損害之結果可歸責于行為人時,即可成立侵權,至于該可歸責性的判斷不僅可以以制定法為依據,也可以以善良風俗以及社會的一般行為準則為依據。在普通法系國家,英格蘭法中的侵權責任的成立也并不是從構成要件來考慮,而是通過其是否構成了各種有名的侵權類型和過失侵權來判斷。其中,“過失”這一概念在英格蘭侵權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有名侵權被認為是聚合在一個有名侵權制度下的特定化訴因的話,那么就相對清楚了:實際實施的某種侵權,在普通侵權法中也是最重要的侵權,就是過失,而且它又符合一種有名侵權的要求。”[8]但是與各種有名侵權不同的是,它強調對一種一般注意義務的違反,即一個普通的理智的人合理預見和合理注意的標準。通過對“過失”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出普通法系的侵權行為是與“義務”這一概念密不可分的。我國《侵權責任法》在制定時主要是各種特殊侵權類型參考了英美法的具體規定,而沒有以一般性的條款對這一責任基礎進行闡釋。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變遷,權利已經明顯無法為侵權行為劃定明確、全面而合理的界限。“侵權法的靈活性和一般性能減緩主觀權利內在的剛性和特定性,由此侵權法具備有用和多重的重要功能”。[9]例如,在人們的行為自由和社會正義之間,加害人一方的行動自由可能與受害人一方的民事權益發生沖突,張新寶教授指出,這一矛盾上升到法律的層面,在宏觀上就表現為將來的不特定的受害人權益保護與不特定的潛在加害人行為自由維護之間的沖突,而從“義務”的角度可以達到某種相對平衡的效果。“義務”并不僅限于制定法上的明確列舉,也不是大而化之的全部道德義務和責任,它隨著社會環境形勢的變遷而不斷為人們的交往活動提出新的要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現代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在這些“有用和多重的重要功能”之中,《侵權責任法》的預防功能成為救濟權利中相當突出的一環,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侵權法的立法目標和價值走向:侵權責任法應當不再單純是回溯既往地彌補過去已經發生的損失,而是要“向前”積極地預防未來的損害;侵權法不應當是被動、消極地去填補受害人的損害,而更多的是提前主動介入到我們這個“風險社會”的一切“風險源”之中。從這一角度來說,筆者認為,在侵權法中有必要規定一項概括性義務條款,來涵蓋社會生活中可能發生的違背公平正義和公序良俗的種種現象,這是我國《侵權責任法》在未來的發展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嚴存生.法的價值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3.
[2][德]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齊曉琨譯.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
[3][5]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8.109.
[4][9]RevuetrimestrielledeDroitcivi,l2007,JanvierMars,p229233、251.轉引自石佳友.論侵權責任法的預防功能[J].中州學刊,2009(4).
[6][法]雅克·蓋斯坦等,陳鵬等譯.法國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9.
[7]龍衛球.債的本質研究——以債務人關系為起點[J].中國法學,2005,(6).
[8][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張新寶譯.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上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35.
(責任編輯:滕元良)
Seeing the Value and Perfection of China's Tort Law from the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Sun Xiaorong
the“Tort Liability Act”is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oreign tort laws and summarizing Chinese practical experience.Under the guidance of feature positioning,relieving rights and filling damages, our“Tort Liability Act”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in multifaceted system design,such a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imputation principle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compensation liability,etc.With the modernization and complication of the social life,the tort laws in countrie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Obligations as the entry point,the construction tort system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development to the tort law,and on this basis,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oreign tort laws the author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erfection of“Tort Liability Act”.
remedy law;balancing of interests;civil rights
D923
A
1008—6153(2013)02—0040—04
2013-03-09
孫曉蓉(1988-),女,山東濰坊人,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專業2011級碩士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