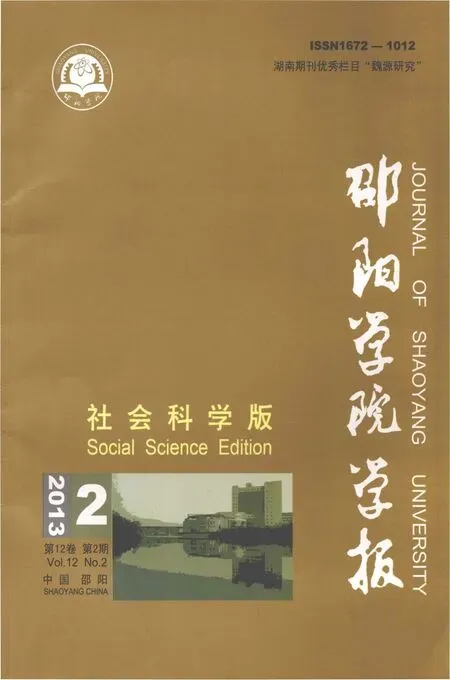《爵士樂》的敘事藝術
唐志欽
(邵陽學院 外語系,湖南 邵陽 422000)
《爵士樂》[1](Jazz[2])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妮·莫里森繼《寵兒》之后于1992 年發表的一部后現代主義小說力作。它是一曲19 世紀末至20世紀20 年代的黑人情感悲劇,寫的是美國黑人如何在白人社會中建立起一種生活方式的故事。小說的情節并不復雜:為了逃避貧窮和暴力,黑人喬與妻子維奧萊特從南方鄉下來到北方大都市謀生。但年過半百的喬竟愛上了年僅十八歲的女孩多卡絲,后又因多卡絲移情別戀而槍殺了她。知情后的維奧萊特則拿著刀子大鬧葬禮。
就這樣一個似乎有些俗舊的三角戀、婚外情故事,被莫里森的如椽之筆書寫成一曲哀婉曲折、催人淚下的悲歌。揭示了美國黑人身份失落后的文化不適癥及精神的疏離和自我的異化,折射出美國黑人的傳統價值觀和新城市價值觀的沖突。但小說更能吸引人更為人稱道的卻是它文本的“有意味的形式”——其高超的敘事藝術和技巧。正如黑人評論家亨利·蓋茨在《表征的猴子:美國非洲裔文學批評理論》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這部小說引人入勝之處不只是情節的安排,而是在于故事的敘述。”[3]筆者擬從敘事結構、敘事視角及敘事語言等三方面來探討其敘事藝術。
一、敘事結構
《爵士樂》的敘述結構獨特。它顛覆了傳統小說的內部形態和結構,呈現出后現代特征。其結構不僅是為了增強意義而設計的,它本身就構成內容,結構生成意義。它是按爵士樂的章法“演奏”出一個爵士時代的故事。就像是拉格泰姆(Ragtime)的切分音法一樣,小說被切分成沒有標題和序號的十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僅以一頁空白分隔,恰似爵士樂演奏中的緩沖與停頓。故事在敘述時間上來回穿梭,漾溢著爵士樂的基調和樂觀。第一部分為20 世紀20 年代,主要人物之一多卡絲已死亡,喬的妻子維奧萊特從多卡絲姑媽愛麗絲·曼弗萊德要來了相片,并以追述她“坐大街”和“偷小孩”之事來說明她精神狀態,已出現了敘事者所稱 的“裂紋”(crack)。第二部分時間閃回到了20 年前,回憶1906 年喬和妻子維奧萊特從南方來到紐約及二十年后和多卡絲在“那個十月的午后”初次相遇和租房幽會的情景。第三部分以1917 年東圣路易斯的種族騷亂為開始引出多卡絲的身世,提及她“五天之內參加了兩次葬禮。接著時間又跳回到1926年3 月,重述維奧萊特向愛麗絲索取遺像的場景。第四部分寫維奧萊特從愛麗絲家出來后坐在雜貨鋪里回憶自己的身世,并想到了童年時代母親因家園被毀精神失常并投井自殺的情景,以及外祖母特魯·貝爾前來撫養他們兄妹幾人的情形。第五部分寫喬的大半生經歷,從1873 年他的出生到50 歲槍殺多卡絲的七次重大變化。第六部分也是從1873 年開始寫的,講述維奧萊特的外祖母特魯·貝爾所伺奉的白人小姐與一個黑人的私生子戈爾登·格雷在尋找生父的途中遇到了一名臨產的瘋女人。那個瘋女人就是喬的母親。第七部分時間是1926 年1 月1 日,喬在紐約尋找離他而去的多卡絲,并回憶起當年尋找母親的經過。第八部分是多卡絲臨死時的獨白。第九部分寫多卡絲的生前好友費莉絲到維奧萊特家中做客,兩個孤獨的女人互相接納。第十部分結尾,敘事者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進行逐一交代。
《爵士樂》的敘述結構,體現了莫里森的創作理念。“我希望這部作品能夠展示音樂的智力、感性、無序;展示它的歷史、它的流變,以及它的現代性”(序)。正因為這別樣構架,文本缺少一個相對緊湊的因果關聯,缺少環環相扣的整體發展線索。在閱讀過程中需要充分調動讀者智識和認知的能量。如維奧萊特以上門為女人、尤其是妓女做頭發為生,她從顧客的頭發聯想到她的外祖母曾經伺奉過的小男孩的頭發。這一聯想的原由和意義在后面的第四部分陷入沉思的維奧萊特和第六部分戈爾登·格雷尋父記才出現[4]。第一部分中提到維奧萊特“一屁股坐在了大街中央”[1](P16),“在大庭廣眾之下發瘋的事”[1](P21),而對于這一怪異行為的解釋,卻來自第四部分。小說第二部分提到喬告訴情人多卡絲他尋找母親的這個片斷的疑團在第七部分才被解開。
雖然莫里森以音樂的切分構建其小說的若干片斷,凸顯其后現代碎片化特征,但每部分是上下呼應,首尾相連,以頂針修辭式的結構形式,呈現出敘事的回旋和銜接。例如,第二部分的結尾是:“從冰冷變得炎熱,又變得涼快。”第三部分的第一句話是:“就像七月的那一天。”第三部分的結尾是“……清晨,坐在熨衣板旁戴著帽子的女人”,第四部分即以“帽子,沿著前額向后推去……”開頭。而“春天”、“城市”出現在第四部分的結尾與第五部分的開頭。第七部分的最后問句是:“她在哪兒?”第八部分的第一句是:“她在這兒。”第九部分以“能減輕痛苦”結尾,第十部分則用“痛苦”一詞開端。
《爵士樂》的敘述結構完全摒棄了傳統線性以故事、情節為核心的結構模式,而是呈現出一種循環的、流動的樣態,猶如循環主題與變形樂句等法則結合而成的爵士樂,充滿了托馬舍夫斯基所說的“節奏的韻律”(rhythmic impulse),令讀者猶如置身于20 年代哈萊姆爵士樂師即興演奏的旋律之中。這種極富詩意和樂感的架構,運用了多元碎片化結構以及復調性、對話性、間離效果等現代敘事手段將故事情節、人物經歷切成一塊塊內容,精心拼接。表面上雜亂無章、支離破碎的龐大結構被嚴謹地組織起來,并被莫里森“用現代小說幾乎所有的文字手段將每一個碎片安放妥帖,焊接牢固”[5]。這種嵌入、倒置、循環的敘事結構“馬賽克”,顛覆了讀者傳統的線性閱讀習慣,挫敗了讀者對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一種先在的閱讀期待,打破了章節設置的常規做法,從而開辟了文本的多重敘事空間,增強了敘事力度,使多種解讀成為可能。
二、敘事視角
《爵士樂》的敘述視角有著豐富的變化。基于蓋茨的黑人方言理論,敘述視角的不同構成了說話主體的互換,造就了聲音的多元化。故事的開始,敘事者是第一人稱敘述的不可靠的旁觀者,是一個“饒舌、聰明、沒有給出名字的哈萊姆區人”[6]。“嘁,我認識哪個女人”[1](P1)開始了小說的敘述。這種黑人表達話語的敘述聲音(the narrative voice)似乎無所不知,能出入人物內心世界,能賦予人物聲音:喬、維奧萊特、在東圣路易斯暴動中身亡的她的雙親、多卡絲的阿姨愛麗絲等。但她的語言又充滿了非連續碎片式的即興闡發和想象編造。這種即興式的黑人口語是黑人話語權擁有的體現,向讀者傳遞著黑人文化傳統挑戰了美國主流話語和文化權威的信息,顯示出美國黑人集體聲音的力量。
表意的聲音(the signifying voice)主要體現書中人物充滿自由聯想和福克納式回憶的內心獨白。這是利用轉喻(trope)、隱射(innuendo)、重復(repetition)、區 分(the play of difference)、命 名(naming)、迂回表達(circumlocution)等非裔美國修辭策略傳達出“合聲”(double-voiced)的話語模式,表達敘述意圖。小說中維奧萊特回憶母親自殺時“不會忘記她縱身墜下的那個地方——那么狹窄、漆黑一片”[1](P101),“那一口井吞噬了她的睡夢”[1](P101)。表意的聲音訴說的不僅是母親自殺的慘劇,還有民族的創傷。這一創傷使得維奧萊特由于恐懼而多年不敢生小孩,以至于后來上演偷小孩的一幕。喬在槍殺多卡絲的路上,回想起當年去巖洞找他母親的情景。“她在哪里?”[1](P184)她既指多卡絲,又指他母親。他之所以愛上多卡絲,多半從多卡絲身上能找到他母親的蹤影,以至于當多卡絲要別他而去時,他無法容忍而付諸暴力。
最典型的表意之聲可以說來自作家本人。莫里森從20 世紀70 年代她為之寫序的《哈萊姆死者之書》的歷史檔案中吸取材料,激發靈感。經過十多年的醞釀構思,成就了《爵士樂》這一杰作。她這一把真實事件整合到虛構文體中的做法,模糊了歷史和事實的界限,以美國的黑人生活為主要內容來表現百年來美國黑人社會的演變和發展,從而表達了對美國主流傳統對非裔文化記憶中的不公正敘述的抗議。使主流大寫歷史解讀成多樣化小寫的歷史成為可能,為更真實地建構非裔文化傳統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反應的聲音(the responsive voice)出自于那個說“我完全知道她是什么感覺”和“祝她好運,咱們走著瞧”[1](P3)的喋喋不休的敘事者而變成的說“我必須是那祝他順遂的、說出他名字的語言”的理論家之口。她是敘述權威的小說家,即小說內的小說家。由于她的出現,小說文本打上了元小說的印記,呈現出典型的后現代小說特色。她不僅隨時暴露自己虛構的痕跡,還常常對自己的表現進行評判:
“我得說,這很冒險,要是你想弄清楚任何人的精神狀態的話。不過找這個麻煩是值得的,如果你像我一樣——好奇、有創造力而又消息靈通……我也不知道,雖說要想象那一幕幕并不難。”[1](P145)
在第六章里,敘述者以為戈爾登·格雷冒雨把臨分娩的瘋女人送進小屋,目的是要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便隨后捫心自問:“我在想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他想象得那么糟?[1](P169)“我真是又粗心又愚蠢,等我(再一次)發現自己有多么不可靠,我簡直是怒不可遏。”[1](P169)
《爵士樂》由于敘述主體的分化和視角的不同導致多種聲音的出現。“敘述的聲音”著重傳達外在信息,“表意的聲音”旨在凸現深層內蘊,“反應的聲音”則使說者和聽者形成對話性的互為影響,使聽者積極參與文本的建構。這三種互為區別又有交叉的聲音形成的多聲交融,使敘述文本呈現出一種多元復合的戲劇張力,成為爵士樂風格的合奏曲,你吟我唱,此消彼長,極富樂感和詩意。同時使小說的虛構世界與社會現實、歷史與現世小說糅雜在一起,模糊了文學藝術與現實生活的界限,“強調讀者對作品的參與,要求讀者自覺地游離于藝術與生活之間,并且主動地闡釋其多重性的價值認識”。[7]
三、敘事語言
莫里森曾將語言比作“手中之鳥”,語言的前途掌握在使用者之中。作為一位語言駕馭高手,莫里森“深入地探索了一種她期求脫離種族羈絆的語言”。她的小說語言吸取了黑人口頭文學的傳統,看似簡單卻幽默、機智,那是經過精雕細琢之后不留痕跡的文學語言,“向我們展現了詩意的璀璨”。
《爵士樂》中的語言具有爵士樂即興演奏自由發揮的特點,激蕩著爵士樂風格。猶如文字彈奏出的一曲爵士樂,極富有樂感,
“他說:為什么?
“我說:因為……因為……因為……
“他說:因為什么?
“我說:因為你讓我惡心?
“惡心我自己,也惡心你。[1](P199)
小說中經常出現這種結合爵士樂的一問一答形式的語言進行小說敘事,這種即興演奏和參差不齊的節拍,以及深沉的情感表達,增強了小說的敘事的節奏和速度,強化了主體的演繹。
“那個維奧萊特不是什么披著我的皮、使著我的眼睛,在城里奔波、滿街亂跑的人,狗屁,不,那個維奧萊特就是我”“在他的大腿、他的大腿、他的大腿、大腿、大腿上打著拍子”[1](P99)這些生氣盎然富有律感的語言正像爵士樂獨有的節奏美和即興創作之美,擁有質感和張力,誘發讀者的情感起伏和審美情趣。
語言句式的多樣化也是《爵士樂》的一大亮點。圓周句、倒裝句、設問句長短句錯落多姿,異彩紛呈。在莫里森的筆下如行云流水,運用自如。這些形式詭譎極富表現力的語言表達句式契合了變化多端的內容和跌宕起伏的情節,完美詮釋了小說主題意蘊,真正做到了形式和內容的高度統一。
《爵士樂》語言的最大特色就是處處布滿隱語(metaphorical reference)。又以此為象征和比擬來演繹主體深化主題。書名便是是個很有啟發性的隱喻。《爵士樂》不是一部關于爵士樂或者取材爵士樂的小說。小說以來自19 世紀美國南部的黑人民歌爵士樂為題,是借用了這些音樂上的手法來展現爵士樂時期的黑人歷史,是黑人生活和命運變化的一種隱喻,更成為非洲裔美國黑人所特有的生存境遇的一種隱喻。《爵士樂》中人物名稱也是如此。喬·特雷斯給自己取名字的根據是,他聽到父母“毫無痕跡”地消失的故事后,認為自己就是他們消失時留下的“痕跡”(Trace)。維奧萊特(Violet)意為紫羅蘭也是暴力(Violent)的諧音。喬的母親瓦爾德(Wild)就是瘋狂、野蠻的意思,是一個自我放逐、脫離了社會生活的瘋女人形象。
小說中維奧萊特反思自己,調整自己的價值觀,她設法了解死者的情況并和她姨媽成了朋友。這一隱喻揭示莫里森的道德世界:“用你所剩的一切去愛,一切,去愛。”[1](P118)昭示著擺脫白人對黑人的“精神奴隸”和黑人抗爭并取得和解的可能。從而走出一條自我救贖獲取重生之路。
總之,進入莫里森的小說就是進入了一個字詞和用語的彼此戲弄的“語言的快樂宮”(the funhouse of language)。書中的人物把語言當成“精細復雜的、具有可塑性的玩具,是設計來給他們玩的”(伍德,2003)。“這語言魅力無窮,光芒四射,就像一個珍藏在箱子里的晚會手袋!”(序)隨處可見的“戲妨”、“口語”、“呼叫”、“應答”、“重復”、“即興”、“停頓”解構了白人正統語言規范的同時也體現了莫里森熟捻的后現代創新手法和技巧。
《爵士樂》小說獨特的敘事結構、多樣的敘事視角和生動的敘事語言是莫里森把音樂移植到小說創作中取得成功的典范。小說“借爵士樂即興演奏的方式敘述,推動故事的進展,令讀者猶如置身于上個世紀20 年代紐約哈萊姆爵士樂師即興演奏的旋律之中。”(Preface)“呈現一種多元復合的戲劇張力”[8],被譽為“吟唱布魯斯的莎士比亞”、“令人驚奇的詩劇”。難怪《爵士樂》連同她的《秀拉》、《所羅門之歌》、《寵兒》等4 部作品當選為20 世紀美國百部最佳小說,莫里森也被評為當今美國最受歡迎的黑人女性作家。
[1]托妮·莫里森著.爵士樂[M].潘岳,雷格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2]Morrison,Tony.Jazz[M].Plume,1993.
[3]Henry Louis Gates Jr.,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ory of African Litery Criticism [M]. New York: Oxfort Press,1988.
[4]劉向東.〈爵士樂〉的敘事特點及意義[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4) :4.
[5]雷格.二十世紀文學精選:寵兒[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6]邁克爾·伍德著. 顧鈞譯. 論當代小說: 沉默之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7]藍仁哲.一部后現代主義的先驅元小說[J]. 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2) :1-5.
[8]毛信德.美國黑人文學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說創作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