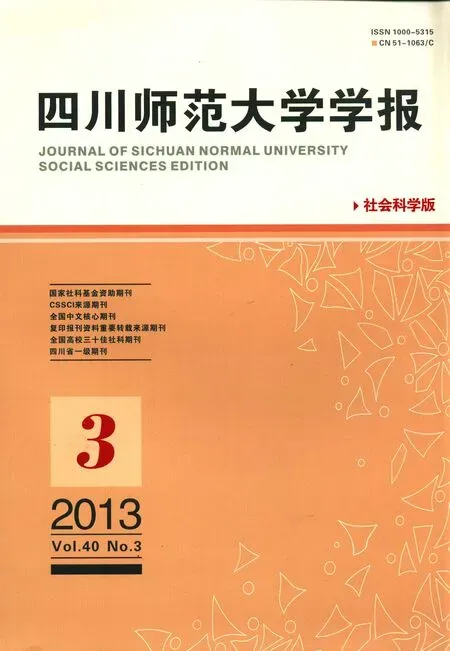視野下移中的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
王 瑩 瑩
(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長春130024)
視野下移中的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
王 瑩 瑩
(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長春130024)
學術視野的下移 促使歷史研究從精英走向大眾 將生活史研究引入到教育歷史的研究中 以扎根基層的農村教師為研究對象,以農村教師的家庭、學校、社會生活的演變為主要研究內容,運用文獻分析、田野考察、口述史、教育敘事等多學科的方法與途徑,進行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有利于還原歷史的多元風貌,拓展教育史研究的領域,可成為未來教育史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
農村教師;生活史;微觀史學;教育史研究
近年來,由于學科間的交叉與滲透,研究視野下移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特別是探討方法論的重建成為西方新史學的發展趨勢之后,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歷史研究出現了人類學轉向,歷史學家逐漸擺脫傳統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史學研究“回到平民,回到日常,回到連續”[1]361,研究重點逐漸從傳統的政治史轉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不僅研究著名人物的歷史,更要研究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普通民眾的歷史,主流話語范圍之外的其他聲音得以展示和認可。同時,“教育實踐是教育的日常生活形式,是實踐活動者經歷的內心體驗”,這要求我們的教育研究“回到教育的日常生活世界”,“恢復教育實踐的復雜性、豐富性和生命性”[2]。視野下移的教育史研究要求加強日常生活教育的研究,從而使得教育研究回歸實踐品性成為可能。
由于中國社會的鄉土性,農村社會變遷始終是中國歷史變遷的主體內容,困擾中國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在這個不可逆轉的進程中,農村教育的現代化應成為農村現代化的先導。農村教師是農村教育的主導者,他們通過促進農村居民特別是農村學生的發展,將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一個小學生之好壞,關系全村之興衰。國家設立小學,是要造就國民以謀全民幸福。因此,全民族的民運都操在小學教員手里。”[3]219毋庸置疑,農村教師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隨著“三農”問題的日益突出,農村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國內農村教育研究已經起步,然而學術界對于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農村教師的研究——還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歷史的反思則更為缺乏,這對于農村教育的研究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研究農村教師的日常生活史,從一個個曾經被歷史忽略、然而并非沉默的小人物身上,還原出鮮活的歷史場景,成為現實研究的迫切需要。
一 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溯源
生活史學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于德國和意大利,是人類學影響下產生的一種新的研究趨勢,在意大利被稱為“微觀史學”(micro history),最早由意大利史學家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提出并踐行,由他撰寫的《乳酪與蛆蟲——16世紀一個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就是微觀史學的代表性作品[4]。微觀史學“以在本質上縮小觀察規模、進行微觀分析和細致研究文獻資料為基礎”[5]99,它通過各種各樣的線索、痕跡,對歷史上那些具體的、個別的人物或事件進行細致考察,進而發現“大題目”旁邊往往被人忽略的東西,來獲得通向關于過去的知識的門徑。微觀史學的真正價值在于它背后所體現的全新史觀,在微觀史學家看來,16世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的一個磨坊主的生活,同那些精英人物、重大事件一樣可以在歷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僅在學術界受到關注,而且走出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進入社會視野,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一)研究對象微觀化。它追求生動立體地再現千姿百態的日常生活,并探究其發生和變化的機制,村落、街區乃至個人常常被視為最合適的研究對象。但研究對象的微觀并不意味著結論意義的“微小”,以小見大是生活史學的主旨。(二)學術視野下移。從以往的關注精英到關注大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在小人物群體中探尋歷史動因。(三)研究內容包羅萬象。衣食住行、人際交往、職業與勞動、焦慮與憧憬、災變與節慶等都屬于生活史的研究內容;而日常行為所牽涉的所有制關系、財產繼承、人口變化、家庭關系、親族組織等等,都可以作為背景進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圍,把日常生活作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機結合的結點。(四)他者的立場。生活史學家不贊成對歷史上的生活方式妄加評判或濫施同情,主張站在歷史當事人的位置上,不僅要身臨其境,而且要心在其中,“設身處地地感覺和體會”[6]。
由當代法國兩位重要的史學家杜比(Georges Duby)和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總其成的《私人生活史》(5卷本)是生活史研究的經典著作,為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這套書網羅了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等國的72位著名史學家參與,自1985年開始編纂,歷時12之久,以歷史年代為縱軸,從大量的繪畫、日記、文學作品以至出土文物中搜尋點點滴滴的歷史資料,以學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從古代到現代人們的日常行為與生活方式,包括他們的思想、情感、身體、態度與看法、習慣與居所、原則、標志和印象等,為我們講述私人生活的演變歷史,力圖為我們還原私人生活的本來面目,給我們展示出了一幅鮮為人知的私人生活長卷。當然作者沒有僅僅停留在對私人生活的表相的描述上,而是從經濟發展的影響到文化傳統的浸潤,從私人權力的變遷到公眾社會的發展,從衣食住行的變化到風俗習慣的形成,從生老病死的規律到宗教信仰的日漸衰退,從兩性關系的此消彼長到血親家族的不斷解體,用自己嚴密的邏輯論證,條分縷析,注重從哲學、宗教、心理等深層次上對私人生活的表相加以解釋,為我們找出引起私人生活演變的真正原因,探尋主導私人生活變遷的背后力量,從而使微觀的個人或家庭世界與宏觀的國家社會之間精微復雜的互動脈絡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在史料運用方面,引用的歷史資料有雕塑、繪畫、賬簿、日記、回憶錄和官方文件等,種類繁多,來源廣泛,尤其是把歷史圖像當作證據,以視覺資料為論述起點,帶給讀者許多以往單獨依靠文字來敘述歷史的著作所無法給予的信息。這種歷史寫作的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也很快被史學界效仿。
我國學者對日常生活史學的關注發端于20世紀20年代,按研究方法劃分,經歷了初創時期的民族風俗志式描述階段、隨后的經濟-社會史研究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經濟-社會史研究階段和當前在多學科交叉綜合的趨勢下走向獨立化與多元化的四個發展階段,研究動向主要集中于身份認同、個體與群體的生存經驗、民族主義想象及婦女史與性別史研究等層面[7]。期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曾經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書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城市生活長卷叢書,也涌現出像陳存仁的《銀元時代生活史》和《抗戰時代生活史》這樣的著作。然而,生活史在自成體系的同時也面臨著潛伏的危機,“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專注于描寫中下階層的生活細節,殊難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形成一個新的典范……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狹窄,不厭其煩地詳細敘述各種瑣碎事物,卻不能從中說明其歷史意義,歷史學家的工作只剩下在舊報紙雜志堆里尋找人們茶余飯后的閑談、再將之拼湊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8]。因此,為了避免生活史的研究流于瑣碎的敘事,應當構建個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橋梁,將個人的生活放置于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產生更具有穿透力的問題意識。
近年來,教育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問題日漸受到界內學者的重視,傳統的治史視野和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漸顯出不能滿足現實和學科發展需要的跡象,要求引入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有關理論。隨著史學研究視野的下移,教育史的研究對象已經不僅僅局限于以往少數的上層精英,而逐漸面向普通大眾,一向被排斥在史家著作之外的社會邊緣人物的活動逐漸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過去那種只重視精英教育、正規教育的狀況隨著對下層民眾教育和民間教育的關注而有所改觀。卜玉華的《回溯與展望——中國中小學教師發展的世紀轉型》對建國后社會大轉折時期的人民教師和群氓時期的革命教師的生活狀況和職業素養進行了分析。她研究中的教師生活是教師的基本的生存狀態,大致包括身份、地位、職業聲望、職業生活等,通過一些帶有一般性的問題分析,加上具有典型性的教師個案的描述和分析,來呈現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教師發展圖景[9]。雖然并非針對農村教師,但具有普遍意義,在研究思路上對教師生活史研究的進行也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劉云杉的《帝國權力實踐下的教師生活形態——一個私塾教師的生活史研究》通過對清末一位塾師長達四十余年的日記所做的文獻研究,彰顯了科舉廢除前后一位私塾教師所體受的文化、國家、社會的種種權力,以此透析士紳與國家的關系[10]143-173。華東師范大學丁鋼教授和黃書光教授分別指導的博士司洪昌、張濟洲都在其博士論文中采用了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及有關理論,東北師范大學袁媛的博士論文《熱鬧而寂寞的鄉村教化:基于建國后石村社會教育歷史人類學考察的研究》也運用了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并綜合運用了口述史和教育敘事。在這些研究中也涉及到對教師生活的研究,為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諸多可鑒之處。但上述研究或著眼于學校教育,或關注農村的社會教育,運用微觀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專門針對農村教師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幾乎仍是空白。
二 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的要素
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對象理所應當是實實在在的“人”,是中國最基層的農村教師。法國年鑒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說過:“我們永遠別忘了,歷史的主體和客體乃是人,乃是如此豐富多彩的人,他的復雜性,無法用一條簡單的公式來表達。”[11]27因此,要了解人類全部的生活,就必須以“人”為其研究的基點。當然,歷史不僅僅是由王侯將相和英雄人物所書寫,農村教師是農村教育的主導者,默默無聞地為農村教育的發展貢獻著光和熱,農村教師的生活史應成為農村教育史乃至整個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內容應該包括農村教師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據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以具體化的、客觀化的和體制化的三種形態存在,在個人一生的各個階段、各個情境之下影響著行動和思想,貫穿于個體社會化的整個過程中[12]192-201。家庭和社會的耳濡目染有助于增強個人的具體化文化資本和客觀化文化資本,學校教育主要是有助于積累個人的體制化文化資本。同時,在家庭、社會和學校中獲得的各種文化資本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在家庭和社會中獲得的具體化文化資本有助于在學校教育中獲得更多的體制化文化資本;在接受學校教育,爭取獲得體制化文化資本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具體化文化資本和客觀化文化資本的增加。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貝林(Bernard Bailyn)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曾經對教育史研究范圍僅僅局限在學校正規教育范圍內的現象進行批判,他認為這樣不僅不能全面地審視教育,也無法評價教育任務的多樣性和重要程度,無法判斷教育在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13]9-15。農村教師不僅僅是作為農村教育的主導者而存在,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同時也可能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子女,衣住行、食色性也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內容不應僅僅局限于他們的專業成長和職業發展,還應該包含他們的社會聲望、經濟生活、家庭和社會生活等。只有將農村教師視為一個“人”,他們的形象才更加的立體和豐富,不至于淪為社會發展的注腳。以他們的生活為結點,我們才能更立體地觀察農村和農村教育的發展,深層次地發現農村教師與村落、地方乃至國家之間的互動,系統分析研究農村教師生活嬗變歷程及其與國家、地方的政治、經濟特別是農村教育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農村教師的生活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問題,并探索農村教師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在研究的史料和方法上,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應力求突破藩籬,采用多學科的方法。但對任何歷史研究者來說,文獻分析法都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基礎的方法。其中不僅包含對已有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和再利用,也包括新資料的挖掘、整理,以最大可能地接近歷史原貌。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同樣需要盡可能多地占有反映中國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教師生活的有關歷史文獻,并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對研究的內容加以分析說明。
對于生活史研究來說,史料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十分必要的。由于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面向的是基層的農村教師,他們既沒有提出著名的教育思想,也沒有引領重大的教育變革,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中,他們依舊屬于“沉默的大多數”,教育史料中少有關于他們的個人記載,他們在教育世界中的真實經歷和心靈顫動都被簡化為冰冷的統計數字。因此,除了國家和各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規和統計數據等官方資料外,他們個人的檔案、地方檔案、口述資料、私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相關的史料更應該設法搜集和保存。然而筆者在調查中發現,相當一部分的農村教師作為村里的文化人,或出于清高、“恥談錢”,或出于隱私、“諱言錢”,他們對日常經濟生活的記載很少見,能找到的資料也很零碎,幾乎無人整理。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任教的教師大多已去世,現存者也已年邁,若不抓緊時間調查,恐這部分珍貴史料再難見天日,迫切需要我們開始搶救性的口述或影像訪談。因此,借鑒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深入到農村教師的生活中去,便成為一種十分有效的手段。通過田野考察,對當事人的口述資料進行采集和整理,還需要對其真實性和可靠性做進一步的考證。最理想的方式是通過文本和口述資料的相互印證,充分利用反映農村教師生活的書信、文學作品、影像乃至網絡博客等資料,以及從他們的親友、學生那里獲得的材料,利用圖文、影像證史的方法,共同印證其生活歷史的真實性。
在研究成果的呈現方式上,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應該注重敘述的運用,教育敘事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正如首先將敘事研究引入中國教育史學界和教育研究領域的丁鋼教授所言:“我們嘗試教育敘事研究和之所以提出‘教育敘事’,并不是為了勾勒一種教育批評,乃是為了接近在中國教育空間里發生的各種‘真相’,在其中,有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思想、聲音與經驗,它們會聚在一起,構成了等待我們去考察的教育事件,而這些事件的流動性及其復雜意義常常只有通過敘事方式才能表達出來,尤其是事件中的個人‘生命顫動’的揭示,也許教育敘事的理論方式是最為合適的方式。”[14]24教育敘事并非單純為了敘事而敘述,而是通過所敘述的事件和人物揭示其社會與文化意蘊,使研究保持較高的學術價值。通過敘事,以通俗而生動的語言和鮮明真實的形象爭取廣大讀者,以生動的描寫代替抽象的分析,以溫情代替冰冷枯燥的理論,也讓農村教師的形象更加鮮活和豐滿,這也有利于教育文化傳播的大眾化,打破“學術自封”的壁壘,為教育史學科的研究與發展注入新的血液。
三 農村教師生活史研究展望
“人研究歷史不僅僅是研究一種政治制度史,研究政策的得失,更主要的(是)對人的生活、生命的一種理解,是研究人的生命史”[15]。回歸生活世界是現代哲學的重要導向,隨著學術視野的下移,歷史研究已經從“閣樓”走向“地窖”,從“精英史”到兼顧“大眾史”。我們將研究的視角轉向社會基層,“從書面歷史的宏觀模式中解脫出來,返回到該歷史的基礎”,轉向當下熱騰騰的歷史(history while it’s hot)①,轉向生活和工作在農村的教育工作者,“把教育從其制度的避難所中解救出來,帶回到世界里去”[16]12。這也要求我們深入到農村教師的生活中去,全面掌握第一手的資料,透過個體生活的微觀研究,把握個體、家族、社區、國家之間的關系互動,解釋學校與家庭、社會之間各種復雜的關系,這樣才能真正的還原歷史的多元風貌,把握教育和發展的脈絡。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教師的生活史轉換了教育歷史記載的對象,拓展了教育歷史研究的領域,應成為未來教育史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
在研究農村教師生活史的同時,要注意兩個基本問題:其一,材料問題。這不僅是研究農村教師生活史,也是所有有關底層社會的研究所涉及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特別是當研究年代久遠的歷史時,我們是否可以掌握足夠的史料來撰寫“自下而上”的歷史?由于研究者無法進行口述訪問,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又不會為自己的生活留下記錄,只能依賴精英分子留下來的記錄時,生活史的研究應該如何進行?社會底層能否為他們自己說話?當然我們可以盡量地挖掘他們自己生產的史料,如日記、傳記等,但我們同時需要思考:這樣的材料又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情境中誕生的?其二,對材料的詮釋問題。雖然對農村教師日常生活的細致描寫,對研究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研究者僅專注于此,便很難超越已有的研究。當我們不只將農村教師的生活作為佐證我們論點的材料,而是當成一種幫助我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的工具,那么農村教師生活史的研究就有可能成為我們研究教師問題、研究農村問題的新的典范,不僅利于我們發現新的問題,而且能夠幫助我們重新反省已有的研究。
注釋:
①此說法來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一批口述史學家。早在二戰期間,戰場上的硝煙還未散盡,一批史學家就立即開展“后戰斗訪談”,重新建構當日戰況。參見:“History While It’s Hot”,載于1943年10月30日出版的Saturday Evening Post,Vol. 216,Issue 18,p.82。
[1]張小軍.歷史人類學:一個跨學科和去學科的視野[C]//清華大學歷史系,三聯書店編輯部.清華歷史講堂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2]鄔志輝.論教育實踐的品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4-22.
[3]華中師范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5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Ginzburg C.The Cheese an 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M].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
[5]Levi G.On Microhistory[C]//Burke P.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
[6]劉新成.日常生活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N].光明日報,2006-02-14(12).
[7]胡悅晗,謝永棟.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J].史林,2010,(5):174-182.
[8]連玲玲.典范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J].新史學(臺北),2006,(4):254-281.
[9]卜玉華.回溯與展望——中國中小學教師發展的世紀轉型[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
[10]劉云杉.帝國權力實踐下的教師生活形態——一個私塾教師的生活史研究[C]//丁鋼.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3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11]轉引自:(瑞士)雅各布·坦納.歷史人類學導論[M].白錫堃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2](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Bailyn B.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Needs an 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M].Chapel Hill,Virginia: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
[14]丁鋼.教育敘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N].中國教育報,2004-02-19(8).
[15]許斌,定宜莊.一個口述史學者的口述——定宜莊博士訪談[J].黑龍江民族叢刊,2003,(5):83-87.
[16](英)保爾·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M].覃方明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Teachers’Life History with Downward Vision
WANG Ying-ying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4,China)
The focus of edu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changed from the elite to grassroots with downward vision.Research on life history of rural teachers introduces life history into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y.Taking teachers who live and work in rural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ir family,school and social life,research of rural teachers’life history will be benefit to recreating the original scene of histor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field study,or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narrative.Meanwhile,it provides new ideas to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Life history will be one of the prevailing trends in the future.
rural teachers;life history;micro-history;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G451
A
1000-5315(2013)03-0072-05:,。,
[責任編輯:羅銀科]
2012-12-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建國后農村教師生活樣態研究——D村教師生活史”(編號:10ssxt111),“聯校教育社科醫學研究論文獎計劃”2011-2012年度課題“建國后農村教師生活樣態研究——基于D村教師生活史的考察”(編號:JY1102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王瑩瑩(1984—),女,河南南陽人,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