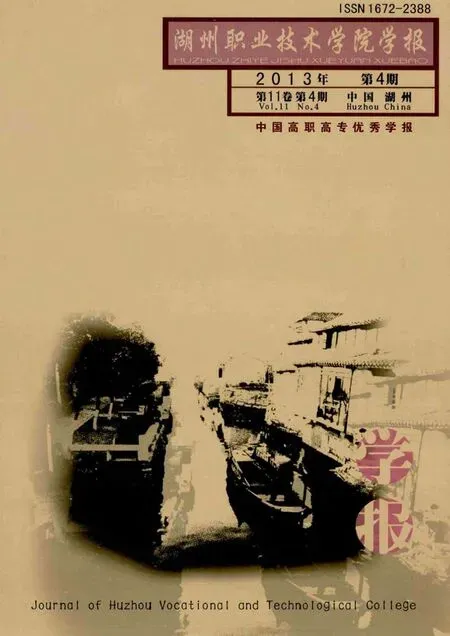中國音樂起源新論*
黃 昌 海
(衢州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中,音樂起源于大自然的恩澤。《禮記·樂記》這樣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1](P160)
這里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就是指地氣上升,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產生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等各種諧調的自然現象。音樂就是天地之間這種和諧景象的摹寫。 “圣人作樂,所以象天地之和”這種中國古代音樂美學的最高境界,體現了中國古代“樂與天通”的音樂起源論。與此相仿,《呂氏春秋》中也有“音樂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的描述。但這種抽象的結論并沒有道明音樂起源的線索。
對于歷史的考證,原本屬于考古學家、人類學家的職責范圍,現在擺在了音樂學家的面前。它給我們一個啟示:透過考古學家高度倍數的鏡片對各種出土文物的凝神默想,我們可以跨越世紀的阻隔,透過浩如煙海的歷史塵埃,嘗試用一種描述性和經驗式的方法去探尋人類初原時期與音樂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關的活動履跡。
一、音樂的源流概要
在我國,據考古發現,山頂洞人已經懂得裝飾,并開始學會用符號來象征人的觀念和情感態度,并能有意識地在死者身旁放置隨葬品、裝飾物,在尸體身上撒上紅色的石粉,而且這種現象不約而同地存在于世界各個地方。許多古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都認為,這種現象已包含著或提供了某種觀念含義,它源于人的靈魂意識,而這種靈魂意識則是由“巫”來實現的——這也是人類最早的藝術源頭之一。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紅”色象征著血液和生命,死者涂上紅色的石粉,就意味著賦予死者新的生命。所以,紅色就帶有了其社會性的巫術禮儀的符號意義,并伴生了朦朧美的意味。
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仰韶先民的甕棺底部都有一個孔,意在讓死者的靈魂自由出入,這是原始人類靈魂意識的物態化的反映。現在,世界各國仍然保留著的招魂儀式,大概也就是這種靈魂意識的繼承。
從我國浙江余姚縣河姆渡和河南舞陽縣、賈湖縣賈湖史前文明遺址的挖掘中,分別發現了八千多年前用禽類肢骨制成的骨哨,特別是河姆渡遺址發現了一百多支品種各異、音色也各有特征的骨哨。在德國南部的布勞保峪勒還發現了一支三萬五千年前的骨笛。而在仰韶文化遺址也曾出土多件陶塤。它們形如橄欖,中部圓形,兩頭橢圓,頂端有一個吹孔,另一吹孔貫穿兩端。這些出土的遠古樂器經考古學家放射性探測后,被斷定為均制作于距今六千至八千年左右。這種分布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遠古音樂現象,使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音樂史家無不感到驚訝。我們的先民對于音樂的認識和使用,遠在他們創造文字之前。他們所從事的音樂活動比我們今天所能了解的要豐富得多。他們在當時意識水平的基礎上,極大地開發和積累了對音樂功利性的認識能力。這些大量出土的遠古樂器,以一種物態化存在的事實,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遠古先民原始文化中音樂意識形成的源流,并對我們研究史前音樂史具有重大意義。
二、音樂起源的勞動說
一種社會文化的出現不是先民夢中想象出來的,它往往與自然現象及人類的勞動生活相關聯。遠古人類幾乎在同一階段的相當范圍的地域空間內對音樂產生了認識。人類產生對音樂的認識不是孤立的人類文化進化現象,而是人類在與大自然的交合中產生的必然現象,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與大自然構成的必然關系。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在一種“前藝術”的文化中,必定蘊藏著人類文化心理的許多秘密,有著某種人類共有的規律性的內涵。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原始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這種人類所獨有的音樂形態,一方面豐富了他們所需的物質條件,同時也強化了他們的聽覺感知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人類音樂創造對象化的產物。
同時,大量實證表明,與勞動緊密相關的原始樂舞同原始人類的生活具有直接的關系。
就音樂的構成來看,形成樂音動態形式的基礎是節奏。這種原始樂舞中的節奏意識是強化人對節奏感知力的重要來源。
那么,原始人類最早的節奏意識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在集體性的勞動中,某種約定俗成的習慣動作,使他們感到好奇,如共同把獵物抬回家時,必然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杭育、杭育”聲。在兩千多年前,古籍《淮南子》對這種勞動號子即有記載:“今夫舉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動力之歌也。”[2](P3)這種勞動中產生的協調律動,就演變成了一種固定的節奏意識,使原始人從中感到了愉悅。而要把勞動中力量的實際使用所引起的愉悅再度體驗的愿望,則促使了再現某些動物動作和勞動動作的舞蹈的出現。僅從云南現存的各種少數民族傳統舞蹈中,就可發現這種原始樂舞的胎記。如佤族木鼓舞,便是勞動場景的生動再現:蒙羊皮的大鼓二至三行順序擺開,每只鼓的鼓尾站一人,鼓前站兩人。眾多女子成雙起舞,應和鼓點,陣容宏大,聲勢熱烈。舞蹈表現的內容是從栽秧到收獲的全過程,耕田、撒秧、拔秧、綁秧、送秧、分秧、栽秧、割谷、捆谷、打谷、背谷等――再現于舞中,共計十三套鼓點。每套鼓點各異,其間還有不知名的鼓點,使栽秧鼓譜復雜多變而豐富,跳鼓者瀟灑優美。時而敲鼓,時而用鼓槌交叉碰擊,發出悅耳的節奏,再加上那種陶醉自若的舞姿,令觀眾的思緒隨著鼓點去追憶那遠古人類的生活場景。
節奏意識的起源必與舞相聯系,而節奏又是產生音樂的基礎,所以,這種與舞相生相伴的音樂舞蹈,被后人稱為樂舞。
勞動中的節奏是產生音樂的起源之一。如云南韶通的苗族蘆笙舞,在他們舉辦活動時,少則十來支、多則上百支,大大小小的竹簧笙聚集在一起演奏,它們沒有統一的律制,也沒有統一的調性,只有相同的節奏,眾人聚在一起“齊聲高奏”。那恢弘的氣勢,新奇的音響,充分展現出遠古先民特有的表達方式。而云南滄源佤族的傳統木鼓樂舞,在木鼓的敲擊伴奏和“歌唱”中能使舞者體驗到情感的升華,還會使舞者達到迷狂狀態,不到精疲力竭不會停下。于是,云南民間有“從早跳到太陽落,只見黃灰不見腳”的民謠來比喻這種癡迷。這種樂舞形式就是一種非常久遠的文化樣態。
三、音樂起源的巫術說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在世界各民族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都經歷過巫術時代。著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無論怎樣原始的民族,都有宗教與巫術。”[3](P3)而巫術的主要功能在于“人可以通過某種方式達到影響自然以及他人的目的便產生了巫。”[4](P226)這說明,當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還很粗淺,而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還相當幼稚時,便會去尋找一種神秘的力量,以便支配自然。這時,巫術就應運而生,并由此建立起一種確保自我的保護機制。
巫術在原始社會里具有超常的社會功能。在《說文解字》中就有這樣的解釋:“巫,祝也,能齊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在原始人的意識里,巫的一切言行都是受了天地之托,神力無限,能代表鬼神的旨意。因此,巫師集部落宗教、生產以及藝術的知識于一身,他們是“智、圣、明、聰”的化身,而且她(他)們常常就是部落的領袖,被奉為神的使者,能對靈魂、風雨雷電、大漠山川等自然中的神秘現象做出權威性的占卜和解釋。
巫術的存在與我們所要討論的話題極為密切。巫師除了具備上述神通廣大的能力外,還是“歌唱家和舞蹈家”。她的所有占卜都與歌唱、舞蹈相聯系,于是才有古書中記載的遠古傳說:“川石拊石,百獸率舞。若國大旱,則帥巫舞?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這些都是巫師在社會生活中遠古身影的再現。這種巫術的禮儀活動不單在遠古的中華大地存在,在南美、澳洲,人類文化學家也發現了幾乎與之一致的活動,如在他們現今的土著文化遺存中,剽牛要先跳舞、唱歌,以示對牛神的安慰。非洲部落的人出獵前都有占卜和歌舞的儀式。歌舞和巫術是合二為一的,它們與其部落、氏族的命運興衰息息相關。
巫術在文學中的反映是神話傳說,在音樂中的反映是詩、歌、舞三位一體的原始樂舞的基本形態。在《楚辭·九歌·東君》篇中就有“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和篇”,說的就是詩歌、音樂和舞蹈緊密相連,三者合為一體的文化形態。
原始人在巫術的幻覺中,常常通過樂舞宣泄達到與外部世界的和解,以求得內心的平衡。
人類許多古老的文明能傳到今天,很大的程度上歸功于巫的存在,是巫師們在各種節日、集會、祭禮、婚喪等活動中一代又一代地傳唱下來的。所以,何曉兵教授稱巫師是“人類第一批傳道解惑的知識分子”。
巫師作為介于人與神的中介,他們的言與行都不能同于凡人,語言要用音樂這種“神的語言”,動作要用“神的肢體動態”,才能達到與神溝通的目的。只有音樂中那富于強烈情緒的感染力,才會使原本冗長的講述變得生動;音樂與人聲語調和生活節奏絲絲入扣的配合,才加強了聽眾的記憶力。所有對洪荒時代的遙遠回憶,對空有輪回的追問和應答,都被巫師化為部族都能聽懂的故事。最終,部落的精神形態、生產經驗的積累,以及相關的行為規范,才得以在星空下的篝火旁、在同天地交感的幻覺中代代流傳。
因此說:“后世的一切藝術、科學、哲學都誕生于原始樂舞的搖籃之中。”[5](P89)并且,正是音樂這一最古老的人類文化形態,陪伴著我們原始先祖從“獸”徹底進化為“人”,從蒙昧走向智慧,從野蠻邁向文明。
李澤厚先生激動地寫道:“后世的歌、舞、劇、畫、神話、咒語……在遠古里是完全揉合在一個未分化的巫術活動的混沌統一體之中的……想當年,它們都是火一般熾熱虔信的巫術禮儀的組成部分或符號標記,它們是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語的凝化了的代表。”[6](P11-12)
巫師作為人類的“第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對于音樂的把握、運用,早已在我們不能認知的年代擴大了原始人的聽覺感知力,并埋下了審美的種子。自巫術存在的那一刻始,巫師們從事的每一次禮儀活動,就是一次遠古音樂形態的活化,都是一次原始人類音樂聽覺模式的重建和人類審美意識的催生,更是音樂作為一種載體賴以生存、傳播和發展的重要依托。
巫術,它作為遠古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觀念形態,它的存在本身也只是一種意識物態化的符號,它不是藝術起源的全部動因。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它又是審美文化的母體。
在人類的初原時期,樂舞之于巫術也只是作為巫師手中“宣唱法理”的一件道具而已。在原始宗教禮儀中,樂舞的表演對原始人“與其說是一種藝術,不如說是一種力量,一種支配與征服其他物類,控制人類命運的力量。音樂這種功能只存在于巫術儀式中才能得以體現”。[7](P517)
原始時代藝術的“含義”與“代表性”,是指巫術的一種象征性。也正是文化本身的社會意義,直到近代,許多原始民族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技或政治,卻無一沒有音樂,這其中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四、音樂起源的模仿說
人類社會能擺脫原始社會大踏步地走向現代,靠的是善于思考的大腦和靈活的雙手。因此,音樂起源于模仿是音樂起源于勞動與巫術之后的必然命題。模仿與勞動是人類通過社會實踐來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的最直接的兩條途徑。
生產力的低下,認識的貧乏,使原始人對自然界懷著一種神秘的恐懼和崇拜心理。正是由于無知而引發疑問,疑問而引發想象,而想象則引發出了模仿。
我們可以肯定,史前先民在制作這種模仿鳥獸的哨音時,一方面開發了人類最早的音樂聽覺感知力和雙手的靈巧性;另一方面又從這種鳴響中獲得了聽覺的愉悅,并在這種創造性的勞動中認識到自己主體存在的價值力量,從而使這種模仿行為擺脫了簡單的勞動性質,而帶有一種內心審美體驗的意義。
早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就對音樂起源于模仿進行過研究,并有許多的論述。他們認為:“藝術起源于人對自然的模仿”,“人從模仿中學到知識”,“音樂源于模擬”,這就從根本上肯定了模仿產品的本身就是人類文化進化的產物。
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茨指出:“人們在開始能夠編出流暢的歌曲而給聽眾以享受的很久以前,就學會了用口模擬鳥類嘹亮的鳴聲,最早教會居民吹蘆笛的,是西風在蘆葦空莖中的哨聲。”[8](P22)
在眾多的原始樂舞中,人類無一不是將勞動中的習慣動作活化于舞蹈之中,或模仿勞動的過程,或模仿自然中各種動物的動作、叫聲。人類在這種模仿中獲得審美的愉悅,演繹出今天音樂的雛形。
節奏是構成音樂的基本要素,在原始樂舞中,節奏性樂器是最早與樂舞相聯系的節奏工具。故,作為一種節奏性工具,它的出現雖然并不與舞聯在一起,但又與樂舞相關聯,它是最早與樂舞融為一體而具備了樂器功能的。
下面,我們來看看鼓的產生:雷是一種威力巨大的自然現象,它能帶來狂風暴雨、洪水災害,能引起森林大火,擊斃人獸。原始人類對此感到無比驚恐。他們看到其他人群和各種獸類常被雷聲嚇得四處奔逃,就對雷鳴產生了迷信和崇敬,希望自己也能通過什么辦法發出雷鳴,借以嚇退其他部落的掠奪,并可在圍獵時使用。為了達到模仿的目的,原始人類開始尋找雷獸。在他們“萬物有靈”的心理看來,雷鳴一定是某種兇猛的動物發出的聲音,因此,史籍中有“雷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如雷”[9](P248)這樣根據傳說的記載。鼓在非洲是一種非常普及的樂器。布隆迪人的鼓在制作上還模仿母體的形態,同時表現出一種生殖崇拜。在布隆迪人看來,鼓的每個部位都與母體的每個部位相對應:整個鼓面是嬰兒安睡的懷抱,固定鼓面的釘帽是母體的乳頭,加固鼓面的皮條是母體的冠帶,鼓身是母體的腹部。我國云南傣族的象腳鼓,也是典型的帶有模仿性質的樂器。我國古籍有“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的記載,表明朋友相聚,在“鼓瑟鼓琴”中獲得愉悅。
無論是原始人類模仿雷聲制成了鼓,還是模仿鳥鳴制成了鼓哨,模仿黃鶯唱出了悅耳的歌,這些歷史都為我們揭示了遠古初民在審美聽覺上已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形態的心理結構,從而才使各類具有擬音特征的樂器從初級的模仿發展到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創造,從單音意識發展到二度音、三度音,直到今天變化無窮的七音十二律的各種組合。人類音樂文化的這種發展進步本身,也反映著原始人類通過勞動發展自己、改造社會所經歷的實踐過程。這也是音樂文化的發展在特定物質條件下的一個必然過程。縱觀人類音樂發展的歷史,它們無不帶有這種姍姍學步的痕跡。
現代“格式塔”心理學研究的深入與認識的提高,為“音樂模仿說”提供了更多可供借鑒的理論依據。
無論是“寫實”模仿或“抽象”模仿,它們都在作曲家的琴弦上幻化為動人心弦的樂音。從音樂的整體發展過程來看,它們兩者是相互結合、相互參證、相互促進的,共同構成了人類音樂文化壯麗雄奇的音響之流。從古到今,世界各民族的藝術正是在一種文化傳統和象征體系中形成了獨特的符號意義。正如人類學家吉爾茲說的那樣:人類文化的基本特點是符號的和解釋的。如此,不同國度、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各種文化才能在悠遠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里既相對獨立又彼此交融,各民族文化多元并有的格局才能逐漸形成。惟其如此,一部人類音樂的發展史才成為一部充滿隨人性之騷動而起伏,并因之形成了各民族藝術風格獨立、流派紛呈、多彩多姿的音樂風格史,也是人類自由理想的追求史。
參考文獻:
[1] 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2] 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
[3] [英]馬林若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和神化[M].北京: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1986.
[4] 方 坤.民族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5] 何曉兵.音樂與智力[M].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5.
[6] 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7] 修海林,羅小平.音樂美學通論[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9.
[8] 何乾三.西方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論音樂[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9] 馮國超.山海經·海內東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