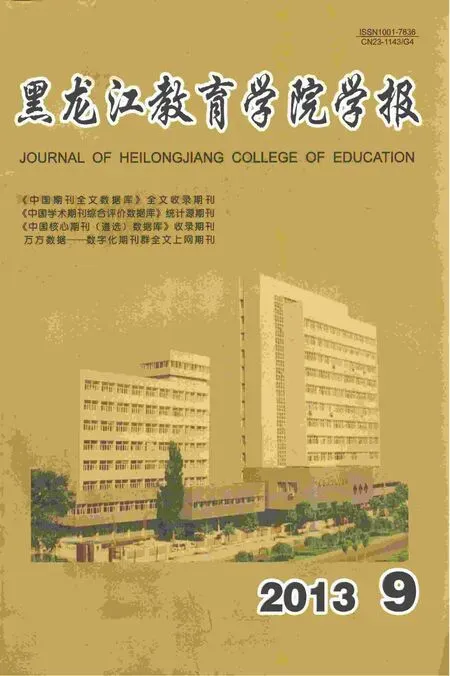川端康成作品“悲而美”藝術風格的形成原因
李方媛,葛曉昱
(黑龍江東方學院,哈爾濱 150086)
何乃英的《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中寫道:“從川端康成關于自己小說藝術風格的論述來看,從他各個歷史時期、各種不同題材有代表性的小說創作來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美而悲是他的主導的藝術風格。”[1]每一位作家在其作品藝術風格的形成過程都有一定的內因與外因。成長環境是外因,經歷與遭遇及所受到的某些思想的影響稱之為內因。川端康成一生的作品都沒有離開“悲而美”的風格特色,這位偉大的作家“悲而美”的藝術風格形成的原因可以從三方面去探求。
一、孤寂的童年及內向的性格
川端康成的童年是苦澀、孤寂的。充滿了孤單與死亡氣息的童年造就了他敏感內向的性格。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家族,親人在他成長過程中相繼離世,給他成長的道路上蒙上了一層陰影,造就了他“悲天憫人”的性格。
川端康成在《獨影自命》中寫道:“在祖父去世之前,祖母在我八歲時去世,母親在我四歲時去世,父親在我三歲時去世了。我唯一的姐姐寄在伯母的家里,在我十歲的時候死了……這種孤兒的悲哀從我的處女作就開始在我的作品中形成了一股隱蔽的暗流,這讓我感到厭惡。”[2]16
《獨影自命》中這段獨白,不僅說明了川端康成悲慘的身世與遭遇,也包含了他對孤獨無助的童年的深切體驗。可見童年的生活深深地影響著川端康成,童年的不幸與悲涼也在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刻下了烙印。他的早期作品多數描寫的是孤兒生活的體驗、失戀的痛苦,社會下層人的生活,例如《招魂節一景》、《篝火》、《淺草紅團》、《伊豆舞女》等。
川端康成有著根深蒂固的“孤兒根性”,小說《伊豆舞女》便體現了這一點。川端康成1918年去伊豆半島旅行途中,在天城嶺邂逅了一個小舞女,以這次刻骨銘心的經歷為內容創作了《伊豆舞女》這部小說。小說中的“我”和川端康成一樣是一個孤兒,在旅途中,與14歲的小舞女產生了朦朧的戀情,舞女對“我”的贊美與喜歡,讓“我”擺脫了與生俱來的“孤兒根性”,心靈得到了凈化。小說表達了單純朦朧戀情的“美”的同時,也對舞女等社會下層人的苦難生活懷有深深的同情,表達了“悲”的思想。
此外,內向的性格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由于身世坎坷,形成了孤僻內向敏感的性格,雖然父母去世后,有著祖母和祖父的愛,但是由于家族落魄,住的房子破舊不堪,祖孫三人的生活頗為陰郁與寂寥。由于川端康成是早產兒,身體異常虛弱,祖母對他的愛幾乎達到盲目的程度,甚至怕感冒讓川端康成留著女孩子一樣的長頭發,隔代的愛代替不了父母的愛,在這種盲目變態式的“愛”的包圍下,隨后又經歷了祖父母的相繼病逝,使他對死亡充滿了恐懼。
孤獨的童年和內向的性格,是川端康成作品“悲而美”的藝術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化的淵源及戰爭的傷害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影響著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他最喜歡《源氏物語》,認為《源氏物語》是日本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源氏物語》是平安王朝時期文學的代表作,將自然和感情融入到作品中,充滿了“無常感”,川端康成作品繼承了這種“物哀”思想,作品《古都》描繪了一年四季古都美麗景色的變化。在這美麗的景色的四季交替中,孿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身世故事交織在景色中,達到“物我一如”,自然與人交融在一起的效果。
日本人崇尚大自然,對于春夏秋冬的各個季節的變化,感受深切。川端康成生在大和民族,對于自然的變幻感受更加靈敏。他大部分的作品都以自然為背景,融入人情,把更多的筆墨傾注于情景交融之中。《雪國》中就是通過對雪國旖旎的風光的描寫為背景,以島村和駒子的感情為主線,表達了“世事無常”的思想,景物的“美”,襯托了愛情之“悲”。
“在遙遠的山巔上空,還淡淡地殘留著晚霞的余暉。透過車窗玻璃看見的景物輪廓,退到遠方,沒有消逝,但已經黯然失色了。盡管火車繼續往前奔馳,在他看來,山野那平凡的姿態越是顯得更加平凡了。由于什么東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內心反而好像隱隱地存在著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3]這是《雪國》中的一段景物描寫。川端康成善于捕捉瞬間美。通過對景物的描寫,襯托了主人公內心淡淡的哀愁,朦朧又含蓄。
川端康成中年時,恰恰是日本法西斯分子發動戰爭時期,處在戰亂中的川端康成沒有像其他作家那樣投身于戰爭中,對戰爭采取了一種“超然”的態度,在《獨影自命》中寫道:“我是一個沒有受到什么戰爭影響的和損害的日本人。我的作品在戰前、戰時和戰后既沒有突出的變化,也沒有明顯的斷層。作家的生活也好、自己的私生活也好,都沒有那樣清晰地感覺到因為戰爭而帶來的不自由。另外,不用說我也不曾有過對日本像神一樣的狂熱和盲目的愛。我只不過經常地懷著孤獨的悲哀為日本人感到悲傷。因為戰敗,這種悲哀滲透進了我的骨頭。但反過來它又使我的靈魂獲得了自由和安定。”[2]3
盡管川端康成一再強調戰爭對他毫無影響,但是日本戰敗后,隨著外來文化不斷地侵蝕日本傳統文化,川端康成對于傳統文化的衰落憂心忡忡。與其說不在意戰爭,莫不如說對于戰爭他內心是排斥否定的。同時,正是由于戰爭使他在文學道路上堅定了追求日本傳統美的想法。
文化的淵源和戰爭的影響使川端康成的文學創作堅定了方向,走向成熟,是“悲而美”藝術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佛教的因緣及傳統美的追求
川端康成在小說《抒情歌》中,把佛教“輪回轉生”思想,稱為“無與倫比的可貴的抒情詩”[4]。佛教的眾多思想在其他作品中均有體現。佛教是其小說“悲而美”藝術風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日本是佛教的國度,佛教于公元6世紀傳入日本后,受到了天皇、貴族的擁護,經過演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佛教,此后又逐漸走進了日本人的生活,融入到日本文化中。
佛教講究“萬物一如,輪回轉生”、“虛無”、“無常”、“生來即苦”,川端康成把佛教看成是一首可貴的抒情詩,諸多作品中蘊含了佛教思想。《雪國》結尾處描寫了葉子的死亡,美到極致,蘊含了佛教“輪回轉生”的思想;《伊豆舞女》表達了佛教“生來即苦”的思想,對于舞女苦難的生活表達了深切的同情;《招魂節一景》結尾處涂上了佛教“虛無”的色彩;《睡美人》表面描寫了老人抓住人生最后一段時光來放縱自己,實際表達的思想是如何得到拯救的主題,蘊含佛教救世的思想。
“萬物一如,輪回轉生”思想讓川端康成看淡了死亡的恐懼,幻想親人的離世是去了天國,而并非死亡消逝;“無常觀”融入了日本古代傳統文學中,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多有體現,使川端康成在思想上認為“萬物無常”,使他的作品蒙上了“悲”的色彩;此外,“虛無”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總是與“美”聯系到一起,《雪國》中的虛實景物描寫及葉子人物的塑造等。
此外,川端康成對日本傳統美的繼承與發展,是他作品走向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致授獎辭時,對川端康成的文學成就做出了如下總結:“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藝術手法,表現道德的與倫理的文化意識;其二,在架設東西方文化橋梁方面做出了貢獻。”[5]
《雪國》、《古都》、《千羽鶴》這三部作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除了因為作品中蘊含神秘的宗教色彩之外,傳統美的繼承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我把戰后自己的生命作為我的余生。余生已不為自己所有,它將是日本美的傳統的表現。”[2]3
川端康成在諾貝爾獎的獲獎演說《我在美麗的日本》中,開篇引用了道元禪師的一首和歌《本來面目》,“春花秋月杜鵑夏,冬雪皚皚寒意加。”[6]川端康成在獲獎辭中引用了許多古典詩詞,來抒發對自己的民族的美的體驗。系統地闡述了日本文學的傳統美,這成為川端康成文學中的日本美論,也構成了他的獨具特色的美學理論體系,使川端文學獨放光彩。
總之,一個作家作品的藝術風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與該作家的經歷和遭遇為前提,所受思想的影響為內在條件,形成的獨立完整的風格特色。川端康成“悲而美”的藝術風格使他的作品在整個日本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占有重要的文學地位。
:
[1]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281.
[2]川端康成.獨影自命[M].金海曙,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3]川端康成.雪國[M].葉渭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4.
[4]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G].葉渭渠,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162.
[5]葉渭渠.冷艷文士川端康成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社,1996:325.
[6]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散文(下)[M].葉渭渠,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