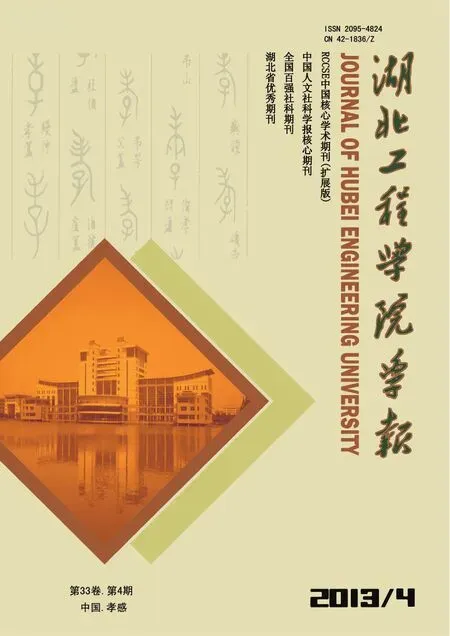存在的苦難:《走窯漢》的生命景觀
劉成勇
(周口師范學院 中文系,河南 周口466000)
劉慶邦的《走窯漢》于1985年9月發表于《北京文學》,這篇小說引起了林斤瀾的注意,認為是一篇使作者“走上了‘知名的站臺’”的作品,將它推薦給汪曾祺,汪曾祺鼓勵劉慶邦“按走窯漢的路子走”。[1]于是,沿著《走窯漢》的路子一路走來,劉慶邦成為當今短篇小說創作的代表性人物。今天看來,這篇小說與此前的創作相比呈現了如下幾方面的變化:注重人性的表現、想像的作用和故事情節的完整。其中對“人性”的探索成為劉慶邦一以貫之的文學母題,也成為解讀其作品的常規視角。但對于馬海州這一人物,從“人性”入手會出現價值判斷的悖論。有論者認為,“馬海洲的報復張清,就不僅僅是捍衛妻子的貞潔,而是在捍衛他理應享受的與地面上普通人一樣的權利。其正義性質是不言而喻的”[2];也有論者認為,“馬海州屬于惡魔型的人物,也是民間復仇故事中最為邪惡的一種,他把人間陰暗的心理發揮到極致”[3]。“人性”是復雜的,對馬海州一正一反的評價正說明了這一點。問題是,這兩種看法針鋒相對,又都具有說服力,對“人性”進行價值判斷陷入了社會道德的泥淖。這可能會與劉慶邦“不動聲色的敘述中,既看不出他的褒貶,更不去做什么評判”[4]的將生活本來面目冷靜呈現的敘事倫理不一致。就敘事倫理而言,劉慶邦“更愿意從存在的角度和文學的角度看取煤礦生活”[5],這說明在“人性”的后面還有一個更高的敘事法則統率著劉慶邦的小說創作,這個法則就是生命本身,是生命在文學作品中的美學顯現。
人性既包括社會屬性,也包括自然屬性,對人性的甄別與判斷屬于道德理性范疇。歷史地看,人性是一個隨社會、時代等外在因素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的變量因素,正因如此,“文明”的產生、發展和升華才有了可能,“拯救”才會含有信仰的力量緩解存在的焦慮而不僅僅是虛幻的名詞術語。與之相比,具有本體意義的是生命,這是任何存在都無法改變的事實,也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先行到死”的人生結構中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實。劉慶邦在作品中探討了各種各樣的人性,但人性并非是其作品內容的全部,像《鞋》《梅妞放羊》等這些“證美”小說更多的是展示一種生命的情態。有時候,他甚至反對從人性的角度解讀其筆下的人物。針對論者對《紅煤》的闡釋,劉慶邦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把《紅煤》說成是寫陰暗面或者是丑惡的東西。我自己覺得我對宋長玉這個人物,還是以理解和悲憫的態度來塑造他。”[6]劉慶邦的這種說法表明他并不是從“人性”的角度去看宋長玉的,理解和悲憫的基礎是宋長玉的生命存在。有論者認識到“生命”在劉慶邦文本中的意義:“他從人生的自在的精神形態和生命情狀來思考人的生命過程中無意識的力量。……他對人生命運的幽遠深長的描繪,更多的是從人的精神救贖和自審的意義來認識的,因而更接近現代文化中生命哲學的理解。”[7]如果從生命哲學的角度來解讀《走窯漢》,也許比較能契合劉慶邦的創作意圖和審美理想。
馬海州是一名普通的挖煤工人,他和妻子小娥在礦山度蜜月。新婚燕爾無疑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時光,更何況妻子又是那么的漂亮:“粗腿,胖手,細腰,白臉兒,特別是那一雙眼睛,純潔清澈,露出孩子的稚氣和嬌憨。”小娥的美讓馬海州“愛不釋手”,“他們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淚”,“不到臨下井的那一刻,馬海州決不離開妻子”。對小娥愛得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馬海州下井干活時也不許小娥出屋,叮囑她“無論誰叫門也不許開”,并且常常是“匆匆離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推推門看是否真的鎖上了”。馬海州的小心翼翼不是多余,他擔心小娥受到傷害,尤其是來自于“性”的傷害。這不是沒有可能,“礦工們常年在沉悶、陰暗的坑道里勞作,對于他們來說,最值得珍愛的莫過于女人,而最最可恨的是,當他們在地底下揮灑汗水時,人家在地面勾引他們的老婆,說實在的,誰都有這個擔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小娥的呵護就是對自己生命完美的呵護,在礦工們的心中,妻子“除了‘物質的意義’,更重要的還是象征歸宿的‘精神的意義’”[8]。
馬海州的擔心還是成為現實。黨支部書記張清用一個“不知使用了多少次”的薄鐵片撥開小屋的暗鎖,以“做貢獻”和“遷戶口”為名侮辱了小娥。來自原始本能的性愛禁忌激勵馬海州捅傷張清,讓張清付出了血的代價,但他本人也因此觸犯了法律。幾年的牢獄生活并沒有銷蝕掉馬海州的復仇意志,出獄之后的他并沒有放過張清,而是繼續著自己的復仇行為。只不過這一次他改變了策略,以“靈魂拷問和精神逼迫”[9]作為復仇的方式。復仇行為始終引而不發,卻又能讓對方時刻感受到生命威脅的存在。這是比肉體傷害更為殘酷,也更加瘋狂的精神暴力的施虐。精神暴力以語言和身體為中介直逼對方靈魂深處。一方面,馬海州不斷翻檢出與“那件事”有關的語言符碼,讓張清一次次進入到難堪的歷史場景中去。小娥給眾人散煙,沒有給張清,馬海州提醒她:“為啥不給張書記,他不是要給你遷戶口嗎?”他稱張清為“張書記”,這讓張清感到諷刺,感到惱火,又感到害怕:“他們雙雙來到二樓張清門口,粗的聲音:‘張書記!’細的聲音:‘張書記!’他倆一遞一句喊著,節奏把握得很好,顯得不急不躁,彬彬有禮”。他拿著薄鐵片向張清詢問捅門的用法,在張清跟前抓著小娥的乳房說“想跟書記學點見識”。另一方面,他又利用自己身體上的優勢,對張清造成一種空間感受上的壓迫和進攻。小說中處處突出馬海州身體的強健:“大骨架”“高眉骨下深藏的眼睛”、“馬熊一樣寬闊的脊背”、“鱷魚皮一樣粗糙的臉”,這些外形特征顯示馬海州是一個充盈著強悍而旺盛生命力的人。與之相比,張清的身體是模糊的,羸弱的。因為身體的弱勢,張清經常處于“被看”的境遇。洗澡的時候,馬海州“老是瞅他身上那塊地方”,或是“兩眼直直地盯著那塊傷疤,像是在欣賞他所創作的一幅杰作”。這讓張清窘迫且憤怒,“他咬著牙,把拳頭握起來晃著,做出一種類似瘋狂的舉動”。這樣的舉動只會讓馬海州更加愜意,感覺到復仇成功帶來的快感,“嘴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張清終于抵不過靈魂的不堪重負,跳下煤窯結束了生命。
馬海州真的取得了勝利嗎?在對張清精神施虐的同時,他也在反芻著痛苦的人生況味。他一次次讓小娥講那件讓他“一想起就心如刀攪”的事,“越問越細,連當時那個壞蛋的兩只手各放在什么部位都問到了”。在小娥講完之后,馬海州又大發脾氣,責怪小娥不該講這些。每一次的講述都讓馬海州的靈魂撕裂,每一次的講述都是心靈的自我戕害。劉慶邦說過:“人類的生命的韁繩是無形的,它往往是一項事業,這項事業就好比是一條韁繩。它通向生命,連結生命,引導生命,并緊緊地拴住生命……”[10]“性”就是馬海州生命的韁繩。執著于“性”讓他的生命簡化和窄化,失去了應有的高度和厚度。復仇過程中,他不僅傷害了自己,也給他人帶來傷害。當張清和小娥離開這個世界之后,“性”的困擾也隨之而去。雖然馬海州還活著,但他的生命卻陷入無盡的萎頓和頹廢之中,存在的虛無帶給馬海州的將會是比痛苦更加難以忍受的生命形式。
小娥是無辜的,但她卻成為雙重受害者,先是張清對她身體的侮辱,后來又有馬海州對她靈魂的撕裂。“出了那件見不得人的事以后,小娥本想一死了之”,有了馬海州的那句“不許你死”,小娥屈辱地活了下來。身體的失貞讓“她仿佛成了一只妖魔鬼怪,連三歲的孩子都朝她投瓦塊”。大年初一,有人在她門上掛了一只“爛幫露底的破鞋”,她把破鞋燒了,第二天又掛上一只,“凡此種種,小娥都默默地忍受下來了”。丈夫出獄,小娥匆匆到礦山相見,得到的卻是冷冷的一句話:“我以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小娥年紀不大,不過二十多歲,正處于人生最美好的階段。經過“那件事”以后,她以對身體體征的遮隱躲避不堪回首的記憶:“黑棉襖,黑棉褲,黑棉鞋,頭上頂著黑毛巾,一身農村老太太打扮”。但這種“修女”式的打扮并不能消除小娥的性別體征,她的身體一次次被馬海州用作向張清實施精神暴力的武器。在馬海州的命令下她不情愿地向張清遞煙,和馬海州一起到張清的房門前一遍遍地喊著“張書記”。在張清背后,響起的是馬海州“寬厚的嘴巴嘬在臉蛋上的啵啵聲”,在張清面前,“馬海州把低頭站著的小娥輕輕攬在懷里,胳膊搭在她脖子上,大手在鼓起的乳房上抓著”。最讓小娥難以忍受的是她一次次地為馬海州復述“那件事的始末”,還“不敢不講”,而每一次的講述都是對靈魂的自我閹割。小娥的命運不僅代表著歷史性的女性生存遭際,也反映了身心俱疲的存在者對柔弱生命的默默承受,喪失反抗的生命讓人看到了救贖的艱難。
馬海州是深愛著小娥的,即使出獄之后也沒有改變。張清的死讓他無動于衷,聽到小娥的死卻讓他“呼地站起來”。小娥的死也許是他意想之外的事。可是設想一下,小娥不死,兩人今后的生活就一定幸福嗎?只要小娥存在,她身上銘刻著的性的恥辱就會讓馬海州痛酸楚苦,他對小娥的愛中摻雜了更多變態的成分。馬海州只注意到自己情緒的發泄,卻忽略了小娥也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她也有著自己的精神和靈魂。相愛不見得相知,馬海州和小娥之間的關系也許印證了“他人就是地獄”的存在主義命題的普遍性。
張清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壞人”,在礦上他不知糟蹋過多少女性,從這一點來說,他是死有余辜。但在通往死亡的過程中,張清的生命歷程讓我們看到了驚悸不安中的生命的可憐與卑微。從馬海州釋放回隊,張清“就感到一種潛在的危險,時時威脅著他的生命。他開始做噩夢,時常半夜里驚醒”。馬海州身上跌落的一把刀子能讓他“眼前一黑,差點一頭栽倒在地上”。在馬海州盯著他胸上的傷疤看時,傷疤開始痙攣地抽動。他的舉止越來越不正常,“老是犯愣”,買回來一碗飯,“一口未吃就扣在泔水缸里了”。有人“在他身后無意中咳嗽了一聲,他竟嚇得一下跪在地上……”張清的這種神經質的表現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他們都對命運充滿著未知的驚恐與焦慮,只不過格里高爾的威脅來自生活,而張清的威脅來自生命。張清的命運似乎出現過轉機。在他被冒頂落下來的碎煤埋住的時候馬海州將他救了出來,這讓張清因愧疚、感激而做出了真誠的懺悔:“海州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我對不起你,不是人……”張清以為馬海州救了他的命就是原諒了他,但沒想到的是登門道謝換來的是更為銳利的精神打擊。就在當天晚上,馬海州向他“請教”薄鐵片的用法,“想跟書記學點見識”。希望得到原諒的僥幸心理破滅,張清陷入到了最后的瘋狂中,“抄起一把椅子”,“把椅子打在暖水瓶上了,打在電話機上了,打在柜子上了,他像發了瘋一樣,掄開椅子,把屋里所有的東西都打得稀爛。而后一頭撲在床上‘哞哞’地哭起來”。幾天后,他跳窯自殺。也許這并不是馬海州想要得到的結果,否則的話,他完全可以在張清被埋時袖手旁觀,讓張清死于非命。事實上,第二次的復仇,馬海州不再以肉體的毀滅作為最終目的,他就是要從靈魂入手一點點摧毀著張清的生命意志。如果張清不死,這種折磨將持續下去。所以張清的自殺對于其生命來說,應是一種從永恒苦難中的解脫,張清僅有的一點活下去的希望被掐滅,這讓人在對他作出道德譴責的同時,對生命存在有了悲憫的理解。
劉慶邦鐘情于煤礦題材,他的處女作《棉紗白生生》、第一部中篇小說《在深處》、第一部長篇小說《斷層》以及這篇成名作《走窯漢》寫的都是煤礦生活。煤礦生活為什么如此讓劉慶邦樂此不疲地涉足徜徉?劉慶邦對此做出過解釋,一個原因是與自己九年煤礦生活的“煉獄”般的經歷和情感有關,還有一個原因是煤礦生活與文學有緊密聯系。他的煤礦小說寫得嚴酷、慘烈,他不太同意論者認為的自己將苦難都給予了煤礦,但事實上苦難還是占據了煤礦生活很大的戲份,或者說苦難已經構成了煤礦生活的底色。在劉慶邦看來,苦難不僅是一種社會學判斷,更是一種生存判斷。[5]社會苦難雖然不能消除,但有可能在科學進步、社會幫助甚至是主體努力的綜合作用下消解。生存苦難來自于人類靈魂深處的困擾,是與存在同在的生命基因。無論是馬海州生命的強悍,還是小娥生命的軟弱,或者是張清生命的卑微,苦難之于他們如影隨形。由于生命缺乏更為自覺的超越意識,他們只是被動地承受存在的苦難,這就不能不給生命本身蒙上一層絕望的陰影。如何超越,對于寫作《走窯漢》時的劉慶邦來說也許是一種困惑,或者是一個無法猜破的人生之謎。但無論如何,三個痛苦而焦灼的靈魂呈現了一種人類生命的獨異景觀,這或許是在“人性”之外《走窯漢》所具有的更深層次的意蘊。
[1]劉慶邦.把自己站成了獨特的風景[M]∥文匯報“筆會”編輯部.鄉村舞會2009“筆會”文粹.上海:文匯出版社,2010:186.
[2]雷達.季風與地火——劉慶邦小說面面觀[J].文學評論,1992(2):16-22.
[3]陳思和.在柔美與酷烈之外——劉慶邦短篇小說藝術談[J].上海文學,2003(12):18-20
[4]何志云.強悍而悸動不寧的靈魂——讀劉慶邦的小說創作[J].當代作家評論,1990(5):31-35.
[5]楊建兵.“我的創作是誠實的風格”——劉慶邦訪談錄[J].小說評論,2009(3):26-30.
[6]劉慶邦.“獨頭掘進”寫礦工[EB/OL].(2006-03-24)[2013-03-20].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2496/42501/4235667.html.
[7]王必勝.我讀劉慶邦[J].文藝爭鳴,1992(6):53-55.
[8]羅強烈.《走窯漢》《漢爺》:劉慶邦的方式[J].文藝爭鳴,1992(6):56-57.
[9]劉慶邦.短篇小說的種子[M]∥劉慶邦.從寫戀愛信開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108-117.
[10]徐迅.兔子,跑吧——說說慶邦[J].時代文學,2002(3):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