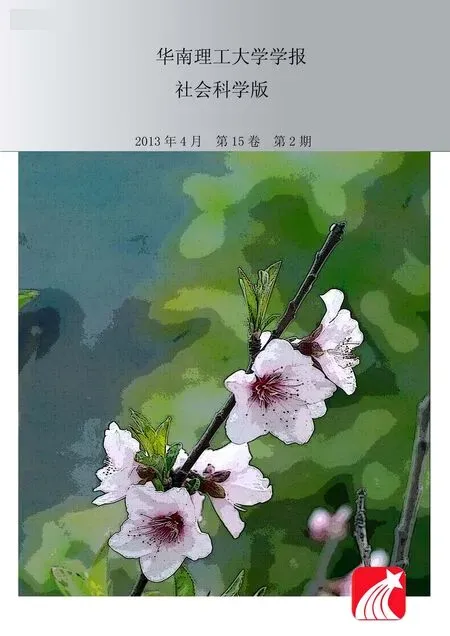傳統儒家個人品德理論探微*
——基于《論語》《孟子》《荀子》等儒家經典文本的詮釋
黃 聘
(中山大學 社會科學教育學院,廣東 廣州510275)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就強調修身養性、以德養人、以德治國,特別是作為中華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縱觀中國倫理思想史,自孔子以來,傳統儒家思想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個人品德修養資源。思想家們在個人品德的社會意義、主要內容、心理結構、修養途徑、外部條件等多方面均達成了不同程度的共識,因而也構成了一整套內容豐實、邏輯嚴密的個人品德理論和實踐體系。本文試在解讀《論語》、《孟子》《荀子》等儒家經典文本基礎上,對其進行系統梳理和意義闡釋,旨在為加強當代公民道德建設提供理論借鑒。
一、個人品德的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便是修身之學,修身養德不僅是儒家道德的核心,也是實現其人生理想的基礎所在。通過對儒家經典文本的窺探,我們可以證實這一點:
(一)《大學·中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可以說,傳統儒家將個人品德的養成和培育提高至社會生活的核心位置。在儒學經典《大學》開篇中便寫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1]23開宗明義,便以“明明德”、“親民”、“至善”分別指出了個人品德的社會地位、養成方式和價值旨向。而怎樣實現這一價值理想,促使道德人格的養成?儒家隨后便給出了清晰明確的答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1]16顯然,在儒家看來,人必須提高道德的自覺性(“修身”、“養心”),這是體現人的價值自覺和尊嚴的活動。
(二)《論語·里仁》:“德不孤,必有鄰”
在不同場合,孔子都曾表達人們修德的重要性,他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2]94“德不孤,必有鄰”。[2]105對于執政者來說更是如此:“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172“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6]在孔子看來,執政者的道德修養如何,直接關系到國治、天下平的道德理想的最終實現。因而執政者必須嚴以律己,做到以德感人,以德教人,以德正人。
(三)《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德性思想,在人性本善的立論基礎上,他提出了個體品德修養的內在依據。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261“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3]79在孟子看來,“仁義禮智”作為人的一種天賦屬性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然而,對于普通人來說,這些美德又極其容易喪失。據此,他認為人們自我修身的關鍵就在于把原有的優良品德尋找回來,用他的話來說即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271“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3]301
(四)《荀子·強國》:“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
荀子在人性論主張上與孟子恰好相反,他明確認為,人性本惡。其具體表現是:“人生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如果讓上述惡的本性不加約制,任期發展,必將導致“爭奪生而辭讓亡焉”,“殘賊生而忠信亡焉”,“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4]258因此,荀子認為必須對人性中的惡性加以改造。他提出“化性起偽”這一命題,認為后天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偽”,使“涂之人皆可為禹”。他認為,對于社會中的人,若能用禮義“教誨之,調一之”,則“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4]166雖然與孟子的人性主張相反,荀子在品德之于個體的意義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4]85又說:“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4]169顯然,與孟子主張“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196一樣,荀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有道德生活。離開了道德生活,人同禽獸就沒有什么區別。值得一提的是,荀子還著有專門的《修身》篇,用來教導人們“注錯習俗”、“積善成德”。
從以上例舉,我們不難發現:儒家諸子均十分重視個人品德的重要意義:對于一般人而言,品德既是人獸之別,又是立身之本。對于執政者來說,品德既是治國之基,亦是平天下之要。無論是孔子的性近說,孟子的性善論還是荀子的性惡論,都無一例外地凸顯品德修養之說的重要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二、個人品德的主要內容
從經典文本來看,儒家諸子在個人品德的主要內容(即德目)上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但總體而言,各有偏重,因而形成了以不同德目為核心統攝的德目范疇和德目序列:
(一)孔子:“仁”為核心的德目體系
孔子以“仁”為最高的道德原則,以孝悌為基礎,以智、仁、勇三者并舉,以“圣”為最高人格,提出了義、禮、忠、恕、孝、悌、慈、愛、溫、良、儉、讓以及恭、寬、信、敏、惠等具體德目。這些具體德目散見于《論語》的各篇目之中:“主忠信”。[2]13“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馀力,則以學文”。[3]11“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3]53“君使臣以禮,臣使君以忠”。[2]74“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2]255“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狄夷,不可棄也”。[2]360“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2]409“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434“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2]478“君子義以為上”。[2]498這些德目構成了一個系統的道德范疇體系,在此范疇體系中,“仁”是最高德目,以“仁”為統帥,其它德目有的屬于道德規范(如“禮”、“讓”等),有的則屬于道德精神范疇(如“仁”、“義”等)。它們的構建,為人們遵循社會道德規范、發揚社會道德精神提出了具體要求。
(二)孟子:三大層次的道德序列
孟子繼承孔子,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告子上》等著中,首次明確提出道德的序列。他分別說道:“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賦稅,深耕易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3]11“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3]124“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261張岱年先生曾將此概括為三個序列:“一、孝悌忠信;二、五倫;三、仁義禮智。”“孝悌忠信”是初步的道德;“仁義禮智”是主要道德原則;五倫則是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講的。[5]9-10孟子關于仁義禮智的學說,對于漢宋的倫理學史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荀子:“禮”為重心的德目范疇
在具體德目排序上,荀子不同意孟子的見解,他特別強調禮的重要,并以禮為“道德之極”,將禮與仁、義并舉。在《荀子·大略》、《荀子·禮論》中,他指出:“禮之于正國家也,如權衡之于輕重也,如繩墨之于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4]301“禮者,人道之極也”。[4]208類似這些論述,都鮮明地突出了“禮”對于人們立身做人、對于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作用。除“禮”之外,荀子比較注重“誠”德的堅守(所謂“致誠”),在《荀子·不茍》中,他說道:“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4]21把“致誠”作為修身的原則,這對于啟迪人們在修身中堅持“慎獨”,嚴以律己,無疑具有其特殊意義。總的而言,荀子所倡揚的德目雖有所側重,但其提出的個人品德修養內容并未出孟子左右。至漢代董仲舒,“三綱五常”成為統治階級道德的基本公式,個人品德的修養亦在此范圍內進行,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后來韓愈、程頤、朱熹等人都從不同程度上肯定并認可了“仁、義、禮、智、信”作為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這些道德規范流傳至今,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思想行為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三、個人品德的心理結構
知、情、意、行是個人品德的四大心理結構。儒家經典中雖然沒有關于個人品德的心理結構的專門論述,但在孔子、孟子等諸多道德教育思想的言論中,我們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個人品德的這幾種成分和結構:
(一)品德之“知”
“知”,即道德知識的學習。孔子認為,道德品質的形成首先在于道德知識和道德規范的學習。在《論語》開篇《學而》中,他就鮮明提出“弗學何以行”,“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2]2顯然,與同時代的亞里士多德注重“知識即美德”一樣,孔子也十分強調道德知識和道德學習的重要性,他將“學”作為做“君子”和自立的先決條件和個人得以立身社會的基礎。他認為離開了基礎的道德認識,是不可能形成優良的個人品德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曾說過“篤信好學,死守善道”[2]217。而“學”什么呢?孔子認為要學“道”、知“道”、適“道”。他說:“君子學以致其道”[2]65,“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2]441,“朝聞道,夕死可矣”[2]92這里的“道”就是對道德知識、道德規范的學習,只有學“道”、適“道”,才能做到“知者不困”。孟子也十分重視道德知識和規范的學習,他說“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3]117明確指出學習的目的就在于明人倫、通禮義。荀子專門作《勸學篇》,在開篇首句便點名了道德學習的重要性和持續性:“學不可以已”。[4]1
(二)品德之“情”
“情”,即道德情感的培養。“道德情感是人們按照一定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去理解、評價周圍人和事時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它對個人品德的形成、發展起催化、強化的作用,是加強道德認識、堅定道德信念、錘煉道德意志的催化劑,是道德行為的推動力”。[6]23孔子十分重視道德情感及其教育培養,在《論語·泰伯》中,他說道:“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2]212“興于詩”意思是說詩可以激發道德情感,“成于樂”是說音樂可以陶冶道德情操。同樣,荀子也特別重視音樂教育對于個人品德培養的作用,他認為音樂不僅可以抒發人的感情,陶冶情操,而且可以改善人際關系,純化社會風氣。
(三)品德之“意”
“意”,即道德意志的鍛煉。一般而言,道德意志是人們在踐履道德原則和規范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自覺克服一切困難和障礙的毅力。道德意志是促使個體品德行為反復出現并能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曾提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2]442,其意是說即便認識了“仁”這一道德規范,如果不能守住并保持它,即使認識了也會喪失。換句話說,道德規范只有由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信念,才能對道德行為發生指導和約束作用。因此,必須注重道德意志的鍛煉,這一點孟子亦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3]299只有加強道德意志的鍛煉,才有可能把人培養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138的人。荀子也指出,個人在修身過程中,不應因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身持守的道德意志。
(四)品德之“行”
“行”,即道德行為的踐履。道德行為是人們在一定的道德認識、情感和意志的支配下,在實踐活動中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則、規范的實際行動。道德行為的形成和長期履行是個人品德形成的關鍵階段和重要標志,道德知識學習、道德情感培養、道德意志鍛煉只有轉化為個人長期自覺的道德行為和道德習慣,個人品德才得以真正實現。孔子十分注重“行”。在《論語·學而》中,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2]11又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2]163在他看來,道德并非空談虛言,它首先是實際行動。孝敬父母、尊敬兄長、謹慎守信、愛人親仁,這些實際行為就是道德的具體表現。他認為一個人要言行一致,這是個人品德的基本要求:“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2]118之后,《荀子·儒效》作了進一步發揮:“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4]73在古代,遵循道德原則而行動,謂之“身體力行”,謂之“躬行實踐”。“身體力行”意謂在個體身上體現道德原則,“躬行實踐”意謂將道德原則在生活中實現出來。
四、個人品德的養成途徑
眾所周知,儒家個人品德修養的價值理想和價值目標是:“內圣外王”和“君子人格”。而如何實現“內圣外王”和“君子人格”?儒家經典中蘊含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個人品德修養理論和方法。
(一)好學慎思
個人品德的培養首先離不開道德規范的學習,不學習,便不懂得為人的規矩(“道”),也就不懂得善惡是非。因而道德學習構成了修身之基礎。孔子非常強調道德學習的重要性,在《論語·陽貨》中,他提出:“好仁不好學,起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2]481顯然,在他看來,一個人如果愛好仁義卻不好好學習,那么他會容易被人愚弄;如果愛耍點小聰明卻不知道好好學習,那么他會輕浮而無根基;如果講信用卻不好好學習,那么他會容易被人利用反而傷害自己;如果性格耿直而不好好學習,那么他說話會尖刻而刺痛別人;如果性子勇猛卻不知好好學習,那么他容易作亂闖禍;同樣,如果性格剛烈而不善于學習,那么這種人就容易莽撞妄為。在學習道德知識基礎上,孔子指出個體需要慎思,才能達致“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君子境界。因而他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2]465即君子有九種要思考的事:看的時候,要思考看清與否;聽的時候,要思考是否聽清楚;自己的臉色,要思考是否溫和;容貌要思考是否謙恭;言談的時候,要思考是否忠誠;辦事要思考是否謹慎嚴肅;遇到疑問,要思考是否應該向別人詢問;忿怒時,要思考是否有后患;獲取財利時,要思考是否合乎道義準則。
(二)自省慎獨
在個人品德的形成上,儒家不但強調學習,更強調自省。自省是指從思想意識、情感態度、言論行動等各個方面去深刻認識自己、剖析自己。從而及時發現和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提高自己遵守道德準則和規范的自覺性。《論語·學而》中有:“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2]7《論語·里仁》有“見賢而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2]99在孔子看來,自省就是反觀自身的精神性反思活動。倘若只有學習,而沒有聯系自身品行的反省,這樣無助于個人品德的提升。對此,孟子也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3]23這里的“誠”也就是反省自責而達到為己之善。“自省”的最高境界可視為“慎獨”。“慎獨”是中國倫理思想史上一個古老的、特有的修養方法,是儒家對個人內心深處比較隱蔽的意識、情緒進行管理和自律的一種修養方式。最早見于《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1]132“慎獨”,就是指在獨處無人注意的情況下,自覺按一定的政治、道德準則思考行動而不做壞事。在此,“慎獨”強調的是道德主體內心信念的作用,體現了嚴格要求自己的道德自律的精神,指出了一個人自覺實踐道德行為的意義。[7]81如果說,自省還是通過外在規范來約束個體行為的話,那么慎獨則是依靠主體的道德自覺性來達到“隨心所欲不逾矩”的目的。
(三)知行合一
這是儒家個人品德培養的重要特征。《論語》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2]2“時習”即經常練習、經常實踐的意思。孔子一貫重“行”,他明確主張對人的道德評價必須兼顧“言”和“行”兩方面并更注重后者:“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2]34孟子繼承和發揚孔子的“力行”思想,強調要想獲得卓越的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必須自覺地接受各種嚴酷環境的磨練和艱難挫折的考驗。同時他認為理想人格的造就全在將自己的天賦善性推己及人。同樣,荀子提出了“學至于行之而止矣”的重要命題,認為“學”的最終目的在于“行”。《中庸》有“力行近乎仁”,同樣也是強調道德實踐的重要性,強調道德學問不是外在的知識,道德學問必須同道德實踐相結合,同自身為人處世相結合,才是真學問。
(四)推己及人
儒家的個人品德修養學說顯然沒有停留于內省慎獨道德修養的基礎層面,它進一步要求“推己及人”,在社會關系中通過人際互動形成個人品德。孔子曾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2]365在《論語·憲問》中,他明確表達了修身并非潔身自好和獨善其身這一形式,而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165而道德德目,如孝、悌、慈、忠、信、義、親等,都要在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關系中才能體現。這便也是孔子“仁者愛人”的精髓。為貫徹“仁者愛人”,儒家有兩大修養方法:“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法和“中庸之道”的貴中尚和法。
首先,“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法是指儒家提倡人們在社會活動中以“忠恕之道”去實現“愛人”。所謂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實行“忠恕之道”要求人們必須具有仁愛和奉獻之心。如果一個人沒有一點仁愛、奉獻之心,那他就不會去“立人”、“達人”;同時,“立人”、“達人”的過程,又是強化仁愛與奉獻之心的過程。同時,實行“忠恕之道”,必須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善于體驗自己的情感和需要,并在此基礎上去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要,以免做出有損他人之舉。孟子的“舉斯心加諸彼”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實行“忠恕之道”的心理換位法的典例。
其次,“中庸之道”的貴中尚和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原則,也是個人品德培養的重要方法。《中庸》載:“喜恕哀樂之末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32它的基本要求是人們的道德行為必須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要適度,恰到好處,使各方面能各得其所,不能片面,走極端,否則,善意也會成惡果,有損仁德的實現。
五、個人品德的外在條件
傳統儒家十分重視教育、環境等外在條件對個體道德品質的影響作用。同樣,以人性論為前提,儒家諸子分別論述了后天環境與教育對于個體道德品質養成的影響。
(一)《論語·陽貨》:“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的命題,說明人們與生俱來的天性本來是相近的,但因為后天環境習染的不同,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對此,孔子舉例說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2]246此外,孔子提倡擇友、擇處,也是其環境對人的品德形成作用思想體現。關于擇友,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2]459關于擇處,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2]457毋庸置疑,孔子擇友、擇處的目的就在于創造一個有益于道德修養的環境,以便“就有道而正焉”。
(二)《孟子·滕文公上》:“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孟子、荀子所持“性善”、“性惡”論雖然在道德起源問題上認識不同,但均強調后天生活中環境和教育對人的道德發展之重要影響。在孟子看來,由于不良環境的“陷溺”,人們固有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觀念會逐漸喪失。他認為教育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存養”、“擴充”和發展先天的“善端”,如果沒有教育,先天固有的“善端”被不良環境“陷溺”而喪失了,人就會變成禽獸。[7]83因此他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3]117在此,孟子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道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學校在道德教育上發揮著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在此也彰顯出孟子“性善”論的可貴之處:孟子并未肯定人“性善”的永久性,要“擴充”、“存養”和發展“善端”,既離不開自身的修養努力,也必須創造良好的環境進行熏陶和教育。
(三)《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故而人的善德是后天通過教育學習所習得的,因此他認為教育可使“博學,積善而化性”。[4]97荀子與孔子一樣,同樣強調良師益友的榜樣作用。他說“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于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4]267在他看來,不同的環境鑄造出不同品格的人。他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又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4]75由此可見,雖然個人品德形成的關鍵在于個體的主體認識、情感、意識等內因的作用,但諸如環境、教育的外部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六、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以上儒家經典的解讀,不難發現,傳統儒家在不同的人性論基礎上形成了系統化、理論化的個人品德理論體系,在社會意義、主要內容、心理結構、方法途徑、外部條件等方面顯示了其獨特的倫理特征和民族風格,直接塑造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倫理精神和價值人格。毋庸置疑,回顧和借鑒儒家個人品德思想資源中的積極形式和內容,對于強化當代中國公民道德建設和學校道德教育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現實意義:儒家個人品德理論本身體現了傳統中國對道德價值的重視和個體修身的青睞,這既是傳統社會政治倫理建構和宗法社會秩序維護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道德作為“人獸之別”的重要標準,它本身所蘊含的倫理精神在任何時代都值得堅守:道德是每一個歷史時代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結方式,道德關系到每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根本利益和幸福。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樹立正確的道德意識,自覺遵守社會的道德規范,并堅定有力地拒絕道德虛無主義。同時,儒家個人品德內容中的“仁愛”精神、誠信品格、重義情結、勤儉意識等在功利主義價值觀大行其道的消費社會中無疑面臨著被瓦解的風險,但恰恰這些倫理品格積淀和形塑了中華民族傳統中最富價值的精神財富,在新時代的今天,這些道德品格又以新的形式展現在社會生活中,并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榮辱觀),這充分反映了儒家個人品德理論強大的理論生命力。最后,傳統儒家主張個體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慎獨等內在修養方式和推己及人、躬行實踐的外在方式(即“內圣外王”)達致理想人格的方法路徑即便對于當代社會的道德建設和學校道德教育的開展仍然頗具參考價值,對于現代公民文明修身和實現自身全面發展亦有著重要意義。當然,需要指認的是,儒家個人品德理論是與傳統社會特殊的經濟基礎、政治秩序、文化心理和社會結構相契合的,展現出的是其與傳統相符合的倫理特征和要求,因而它自身具有不可否認的矛盾性和局限性。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儒家個人品德理論必然面臨著被解構和重構的任務,這既是儒家個人品德理論自身局限的結果,也是它走向現代性社會并重獲新生的機會。在挑戰和機遇并存的雙重境遇中,我們相信,經過時代化改造后的儒家個人品德在煥發出傳統倫理精神風采的同時也會對當代倫理生態的改善和人類精神家園的建構作出不可磨滅的理論貢獻。
[1]朱熹. 四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83.
[2]來可泓. 論語直解[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3]徐洪興. 孟子直解[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4]章詩同. 荀子簡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張岱年. 中國倫理思想研究[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6]劉祎. 試論儒家德育過程論思想[J]. 新疆社會科學,2006(2):87 -92.
[7]王易、劉致丞. 試析儒家的個人品德養成論[J]. 道德與文明,2009(5):81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