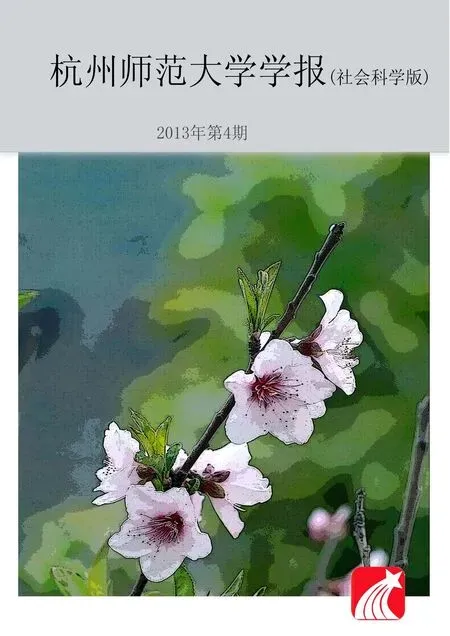中國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
吳 震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中國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
吳 震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對圣人概念作一觀念史考察,頗有意義。上古時代圣人概念的原本意思是指聰明睿智之人,然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圣人概念具有了雙重涵義:既指道德上的完美人格,又指政治上的杰出人物。戰(zhàn)國以降,孔子被圣人化,并表現(xiàn)出圣人神圣化之趨向。及至宋明時代,在“圣人可學而至”的思想口號的廣泛影響下,圣人之學及圣人之道成了儒家文化的象征,儒學也就成了成圣之學。及至陽明心學的時代,滿街都是圣人的觀點導致了圣人的徹底內在化,圣人成了人心良知的象征符號而不再神秘,并開始走向世俗化。在這一思想演變的歷程中,儒家圣人觀所蘊含的“超凡入圣”如何可能之問題亦值得省思。
圣人;圣王;孔子;孟子;王陽明;超凡入圣
眾所周知,自宋代出現(xiàn)新儒學運動以來,道學(或稱“理學”)家們就將歷史上以孔孟為代表的傳統(tǒng)儒學視作“圣人之學”或“圣學”來加以推崇,*程頤《明道先生墓表》,載《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40頁。另據(jù)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圣學”一詞僅見《論語集注·堯曰》引楊時注,而“圣人之學”則有3次,見《論語集注》之《里仁》《憲問》及《孟子集注·盡心下》。與此相應,圣人不僅是道學家應當努力實現(xiàn)的最高理想人格,而且還是士人學子乃至于普通民眾都應自覺努力追求的一種精神境界。那么,究竟何謂“圣人”?“圣人”概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又經(jīng)歷了哪些演變?本文以儒學思想史作為考察的焦點,從先秦時代談起,然后稍涉宋明新儒學,試對“圣人”問題作一觀念史的考察,最后筆者指出“人雖有限而可無限”——即“超凡入圣”如何可能的問題值得引起我們認真省察。
一 “圣”之涵義
顧頡剛曾指出:從語源學上看,“圣”字之意最初很簡單,只是聰明人的意思,從文字學上看,金文中“聖”字省作“耳口”,為會意字,加“壬”為形聲字,意指“聲入心通”或“入于耳而出于口”,都是聰明的意思。[1]這一點亦可由字書及傳統(tǒng)注疏得到證實,例如《說文解字·耳部》:“圣,通也。從耳,呈聲。”段注:“凡一事精通,亦得謂之圣。”[2]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得更清楚:“圣者,通也。從耳,呈聲。按,耳順之謂圣”,“春秋以前所謂圣人者,通人也。”[3]又如《古文尚書·大禹謨》《孔傳》謂:“圣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周禮·大司徒》鄭注謂:“圣,通而先識。”要之,從文字學上講,圣字原義為通,有聰明睿智之意。這個看法得到了當今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例如邢義田《秦漢皇帝與“圣人”》,載其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0頁;吉川忠夫《真人と圣人》,載《中國宗教思想》第2冊,東京:巖波書店,1990年,第179頁。
其實若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圣字最早在中國上古時代的巫覡文化中就已出現(xiàn)。據(jù)《國語·楚語下》所載觀射父論巫覡:“其智能上下比義,其圣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這里用了聰明圣智四個詞匯來表達巫覡具有異乎尋常、超出常人的感覺能力。這種能力也可以用聰明或通明來表示。
在主要反映商周歷史的《尚書》中,圣人也主要是聰明的意思。其《多方》篇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這是說圣人與狂人只在一念之差,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超人。《洪范》更有一句名言:“思曰睿”、“睿作圣”,此“圣”字即通明之意,《孔傳》謂“于是無不通謂之圣”。此外,《冏命》“聰明古圣”,《說命》“惟天聰明”等等說法,也是表明圣的意思就是通明或聰明。《詩經(jīng)》中的“圣”字之意亦類此,如《小雅·正月》“具曰予圣人”,《毛傳》謂“君臣俱自謂圣也”;《小宛》“人之齊圣”,《鄭箋》謂“中正通知之人”;《小旻》“或圣或否”,《毛傳》謂“人有通圣者,有不能者”。由這些《傳》《箋》來看,圣人可適用于君臣,意指“中正通知之人”而已。*以上有關《詩經(jīng)》文獻,轉引自上揭邢義田論文,載《天下一家》,第50-51頁注3。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了“九思”的概念,首先二思便是聰和明:“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曰明,聽曰聰。……”(《論語·季氏》)這顯然是沿襲《尚書·洪范》“視曰明,聽曰聰”而來。要之,圣人的意思大抵是指聰明,而聰明的原意與耳目器官有關,主要指聽覺或視覺的能力出眾,在《尚書》及《論語》當中,聰明則更多地與“思”的能力有關,這是商周至春秋末期歷來就有的一個說法。再如略晚于孔子的墨家更是喜歡使用圣人或圣王的概念,*有學者統(tǒng)計“圣王”一詞在《墨子》一書中的出現(xiàn)次數(shù)竟達121次之多,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論語》未見一例,而《孟子》僅見一例,參見吉永慎二郎《戰(zhàn)國思想史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591頁,轉引自鄧國光《圣王之道——先秦諸子的經(jīng)世智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57頁。按,圣王是指有位之圣人,而作為“素王”的孔子并不適用這一稱呼。在其論述當中,也有不少是以聰明來定義圣人或圣王的。這里僅舉一例:“故惟毋以圣王為聰耳明目歟?”(《墨子·尚同下》)這個說法仍然保留了以耳目器官表示聰明的意思。事實上,這層意思直到漢代仍然通行,例如《白虎通·圣人》:“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聲也。”
總之,在中國上古時代的春秋時期,人們把圣人主要想象為一種聰明人,而尚未有神圣的意思(這層意思的轉出要等到戰(zhàn)國時代),這是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但也不難理解。古人以聰明代表一個人能敏銳感覺事物和認識世界的能力,認為這種人才有資格被奉為圣人或者作為圣人君臨天下。上面引述的《尚書》及孔子和墨子的說法都表明了這一點,強調領導者必須有耳聰目明、思維敏捷的特殊能力才能勝任。這種以聰明論圣人的說法在儒家文化中可謂影響深遠、根深蒂固。孔子將人分為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其實也反映了這個觀點。及至后世由于受佛教影響,宋明理學將“上人”稱為“上根之人”,如王陽明(主要是指顏回和程明道,而非指圣人),此不贅述。[4](卷下,第315條)要之,聰明智慧是圣人之所以成為圣人的重要條件之一,這是商周以來及至春秋思想史上的一個傳統(tǒng)觀點。*相傳為子思之作的《中庸》亦云:“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也把聰明智慧看作是圣人的一項必要條件。另按,據(jù)邢義田,《尚書》及《詩經(jīng)》中的“圣”或“圣人”原來并沒有什么神圣的意思,圣字神圣化,是到戰(zhàn)國時代才開始出現(xiàn)的一種趨向,主要以孟子、荀子、韓非子等為代表,他引用朱駿聲的一個觀察:“春秋以前所謂圣人者,通人也”,“戰(zhàn)國以后所謂圣人,則尊崇之虛名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轉引自上揭邢義田論文,載《天下一家》,第50-51頁注3。
二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但是,在中國思想史上,一說到“圣人”,人們立即會聯(lián)想起孔子。那么,圣人一詞在《論語》中究竟是怎么被表述的呢?
孔子曾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這三畏是否有層級高低之分,并不十分清楚,總之,圣人是可畏的對象之一。這個圣人大抵是指古已有之的人物存在,而且是有言論流傳下來的。但《論語》一書明確提到的圣人并不多,除堯、舜、禹以外,偶爾提及文王和武王。根據(jù)《中庸》的記載,孔子除了“祖述堯舜”以外,還“憲章文武”,這是說孔子在文化立場上,一切以堯舜為準則為榜樣,同時還努力表彰文王和武王的豐功偉績。可見,孔子所說的圣人是古圣人,而不是當代的活圣人。所以,孔子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孔子其實是在感嘆這世上已經(jīng)不存在圣人了。換言之,在孔子的心目中,圣人是儒家終極的理想人格,其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有兩次提到堯舜時,似乎認為這兩位圣人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仍然有所不足而沒有做到十全十美: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
從“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一直到“修己以安百姓”以及能做到“博施濟眾”,這才稱得上是圣人,但是堯舜猶以為自己在“安百姓”及“博施濟眾”這兩方面做得還不夠完善。*此處兩句“堯舜其猶病諸”,可依朱熹《論語集注》的解釋來理解:“病,心有所不足也。”顧頡剛以為這兩段話表明孔子認為堯舜還稱不上真正的圣人(見參考文獻第[1]條顧頡剛論文,第87頁)。這個解釋可能有點過度了。這表明在孔子的觀念中,圣人確是很難做到的。所以孔子自己曾嚴肅表明:“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述而》)拒絕承認自己是圣人,甚至連“仁”都還沒有完全做到。
然而,在孔子周圍,卻有一種聲音以為孔子是當世圣人,據(jù)魯國貴族孟僖子的臨終之言,曾有這樣一段描述: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杜預注:“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孔穎達《正義》:“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圣人之后也(杜預注:“圣人,殷湯。”),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臧孫紇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后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四《左傳·昭公七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刊阮元校刻本,第2051頁。按,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卷二十:“曰圣人,曰圣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而言。”“弗父、考父為圣人者,圣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圣。”引自上揭顧頡剛文,第84頁。
由此可見,孔子生前似乎已有圣譽之享了。
但是孔子堅持圣人名譽是不敢當?shù)摹@纾斕自?jīng)問子貢,你的老師是圣人嗎?何以這么多才多藝?子貢答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意謂孔子乃是天生的圣人而且又多才多藝。對此,孔子的回應是:還是魯太宰了解我,我小時候出身卑賤,故而懂得一些本事而已(《論語·子罕》)。可見,孔子對于子貢稱其為圣人的說法仍是堅持否認的。
不過,在孔子死后不久,情況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在其弟子當中開始出現(xiàn)將孔子圣人化的動向。據(jù)孟子記載,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這三個說法不僅都將孔子直接說成是圣人,而且還極盡贊美之能事:孔子才是自生民以來的天下第一號圣人,甚至超過堯舜。而孟子在孔子圣人化“運動”中也有重要貢獻,他稱孔子為自古以來堯舜事業(yè)的“集大成者”,且贊美孔子為“圣之時者”,可以說,孔子被確認為圣人,無疑是孟子的功績。當然從文獻學上看,孔子圣人化的完成則應當以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的一段話作為標志:“孔子布衣,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按,在漢代揭示的各種“圣人名單”中,例如《韓詩外傳》《新序·雜事五》《白虎通·圣人》《漢書·古今人表》等,孔子均穩(wěn)居殿后的位置,參見上揭邢義田論文《天下一家》,第68-73頁。
總之,在春秋末期,孔子的圣人觀主要是指能夠治理天下的一種政治理想人格,它是遙不可及、高不可攀的。孔子既不輕許他人為圣人,更不自認為是圣人,其立場毋寧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恢復周禮的社會秩序,其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便是孔子對圣人之治的美好向往。至于“圣人”概念有哪些確切內涵,是否已有這樣一種思路:即將德性視作圣人的必要條件,這在孔子并沒有給我們更多的描述或說明。盡管在西周時代,“圣”作為德行之一就已出現(xiàn),例如《周禮·地官·大司徒》列舉的“鄉(xiāng)三物”中,“圣”已構成“六德”之一,與仁義知忠和并列,而在《左傳》這部經(jīng)過孔子整理的史書中,“圣”也作為十六德之一而出現(xiàn)(《文公十八年》),[5]但在《論語》當中,我們卻看不到孔子從德行的角度來探討“圣”字涵義的任何闡述。事實上,將圣人與德性(或德行)聯(lián)系起來進行探討則有待于孔門弟子,特別是從子思到孟子這一系的所謂思孟學派對此問題似有特別之關心。
三 楚簡《五行》篇與圣人
如所周知,在以往很長一段時期內,由于受史料的局限,人們關于先秦儒學史的考察,大多被限定在孔、孟、荀三人身上。然而自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分別從地下發(fā)現(xiàn)馬王堆帛書以及郭店楚簡中存在大量儒家文獻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們的先秦儒學史有了很大的改觀。一個通行的觀點認為,郭店楚簡中的儒家文獻成書于公元前3世紀以前,與孟子卒時大致同時,其中部分成書年代顯然要早于孟子,如楚簡《五行》篇的經(jīng)文部分大致可以推論是子思的作品,而帛書《五行》的說文部分則是孟子的作品。因此《五行》篇的問世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孔孟之間儒學史的空白。[6]以下,我們主要就楚簡《五行》為參照,來探討孔孟之間有關“圣”之觀念的演變。
郭店楚簡《五行》第1章是一篇總綱性的文字,其中羅列了仁、義、禮、智、圣作為“德之行五”的“五行”,其云:
圣形于內謂之德之行,不形于內謂之行。[7](PP.78-84)
意謂圣作為一種德行,它是內在化的存在,如果不是由內向外來展現(xiàn)自身(“不形于內”),那么就稱不上德之行,而只是“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圣”作為一種德行而被強調,而這樣的說法在《論語》中是看不到的,這應該是自孔子至孟子之間,儒家對“圣”之問題的一個理論發(fā)展。
關于“圣”之德行,楚簡《五行》經(jīng)部尚有一些重要表述:
聰則聞君子之道。聞君子之道則玉音,玉音則形,形則圣。(第7章)
未嘗聞君子道,謂之不聰。……聞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謂之不圣。(第15章)
見而知之,智也。聞而知之,圣也。(第16章)
聞而知之,圣也。……知而行之,義也。……見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禮也。圣智,禮樂之所由生也。(第17章)
聞君子道,聰也;聞而知之,圣也。……見而知之,智也。(第17章)
此處出現(xiàn)了聰明、聞見、圣智三對主要概念。智的問題,暫且不論。就圣而言,由上可知,首先圣具有“聰”的特征,顯然這是源自上古以來的看法;其次圣是“聞而知之”而不同于“見而知之”;再其次,“聞”的對象是指聞君子道而且知君子道。所謂君子道,當是指上層統(tǒng)治者的治國之道。至此可以看出,“圣”不僅具有聰明、聽聞的感覺能力,而且還具備治國之道的能力,這樣的“圣”顯然具有政治上的品格特征,類同于先秦時代的“圣王”概念(詳見后述)。
我們知道在先秦,存在“思孟五行說”這個說法,即荀子的一句著名評判:“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荀子·非十二子》)上引楚簡《五行》有子思“玉音”這一概念,此與孟子“金聲玉振”之說極為相似,應當說孟子的“金聲玉振”說,乃是唱和子思“玉音”之說的結果。現(xiàn)在我們果然在楚簡《五行》經(jīng)部中發(fā)現(xiàn),子思有一段論述與孟子的“金聲玉振”說極為相似,而且這一論述與圣人觀念密切相關,很值得注意。先來看孟子的一個說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孟子·萬章下》)
而楚簡《五行》經(jīng)部則是這樣記載的:
君子之為善也,有與始,有與終也。君子之為德也,有與始,無與終也。金聲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聲,善也;玉振,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聲而玉振之。(第10-11章)
這是說,善者人道,屬于人的行為,故有始有終;德者,天道,故有始而無終極。在“金聲玉振”這一典故中,“金聲”表示開始,“玉振”表示終極。按照這里的敘述,金聲相當于君子為善,玉振相當于圣人為德。而能收到“金聲玉振”之效者唯有圣人。這與上述孟子“終條理者,圣之事也”的觀點若合符節(jié)。
顯然,善屬于人類社會的原則,是人之道,這一點容易理解,但為何說德是天道呢?一種解釋是,德是天道所賦予的,這是用天賦說來進行解釋,然而這個解釋可能并不貼切。依《五行》之意,“德,天道也”應當是指有始無終的德具有天道的屬性,圣人知天道,故能隨順天道而行之,故該句之意是指,德合于天道,而不是說德出于天道。[6](P.125)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以《五行》又說:“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義也;行之而實,德也。”(第17章)意謂圣人能把握天道,并能按照天道而行,做到誠實無欺,這就稱得上有“德”。至于德是否出于天道這一根源性問題,《五行》對此似乎并未展開自覺的討論。
由此,我們可以獲致一個基本的了解,在思孟學派的著作《五行》篇中,圣是“有德者”且是“為德”者而不僅僅是“為善”者,圣與“德行”緊密關聯(lián),被賦予了道德人格的色彩而不僅僅具有聰明的特征,同時,作為“知天道”的“圣”顯然在五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突出地位。
值得重視的是,楚簡《五行》“聞而知之,圣也”的說法,竟然在《孟子》一書中也有反映: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孟子·盡心下》)
這里把湯、文王和孔子贊為“聞而知之”,顯然與《五行》思想有繼承關系,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將圣人規(guī)定為聞君子道而知君子道,或許正是思孟一派的固有主張。而在“圣人知天道”這一點上,楚簡《五行》特別以文王為典范,如曰:“圣人知天道也。……文王之示也如此。‘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此之謂也。”(第17章)有學者指出,若要在行為上實現(xiàn)《五行》所列的五種德行,恐怕歷史上只有一人,此即楚簡《五行》第17章以及帛書《五行》第27章出現(xiàn)的“文王”。[8]而在《孟子》的場合,除文王以外,又加上了孔子。
在“圣”的問題上,郭店楚簡除了《五行》有較多討論以外,在其它一些楚簡儒家文獻中也頻繁出現(xiàn)相關論述,這說明“圣”的問題在當時已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在主要講述選賢任能之道的楚簡《六德》中,圣與智作為一對概念出現(xiàn):
何謂六德?圣智也,仁義也,忠信也。……作禮樂,制刑法,教此民爾,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7](PP.130-131)
首先,圣智是六種德行之一,其次,圣智所具有的作用很重要,能夠制作禮樂、刑法,并能以此教育人民而使人民的行為保持正確的方向。楚簡《成之聞之》則曰:“圣人之性與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志。”[7](P.122)意謂圣人之性與中人之性,生下來是差不多的,沒有不同的走向。在主要討論治國為政之道的楚簡《尊德義》中有這樣一句:“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7](P.139)這里的圣人,意近圣王,是指具有治國之權的君主。另在楚簡《唐虞之道》中出現(xiàn)了“先圣”與“后圣”這對概念,其云:“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親也;……先圣與后圣,考后而甄先,教民大順之道也。”[7](P.95)此圣人亦指圣王。
總之,在上述這些郭店楚簡儒家文獻中,除了《五行》一篇明顯屬于思孟學派之論著以外,其余各篇目前還不十分清楚學派屬性,但是它們大多從政治或道德的角度來談論圣人或圣人之道、圣人之德,這是非常明確的事實,這充分顯示在孔孟之間圣人問題確乎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議題。
四 孟子:圣人神圣化
由春秋至戰(zhàn)國,圣人觀念到了孟子那里,開始發(fā)生重要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圣人的神圣化,便是由孟子完成的。首先,孟子在儒學史上可謂是將孔子圣人化的一員得力干將,他雖然稱伯夷、伊尹、孔子等都是“古圣人”,但強調孔子才是真正的集古圣人之大成的圣人;其次,孟子十分感嘆自孔子以降百多年來,竟再也沒有繼起的圣人出現(xiàn)(《孟子·盡心下》),這表明歷史的發(fā)展是有斷層的;再次,基于這樣的歷史觀,孟子為了興起絕學,他坦然自陳愿學“孔子也”(《公孫丑上》),隱然以繼任孔子為自我期許,換言之,他是以重振圣人之學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的。只是他在口頭上絕不承認自己已是圣人,所以當孟子的學生公孫丑問老師,說您已是圣人了吧,孟子回答說: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人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公孫丑上》)
這是說,連孔子都不敢自居圣人,不要拿“圣人”來吹捧我。
盡管如此,孟子卻贊賞孔子是“圣之時者也”(《萬章上》),比“圣之清者”的伯夷、“圣之任者”的伊尹以及“圣之和者”的柳下惠顯得更為高明。更重要的是,孔子是歷史上古圣人的“集大成”者,而“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萬章上》)。可見,其認孔子為圣人,是十分佩服和景仰的。
孟子并不停留于對圣人的形象描述,他還第一次對圣人提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一是“圣人,百世之師也”(《盡心上》),一是“圣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這是說,作為圣人須具備兩項條件:一是在政治教化上,具有人師的資格;一是在人倫道德上,具備最高的人格。很顯然,后來孔子被封為萬世之師、天下楷模,這個說法的始作俑者便是孟子。特別是,孟子從道德的高度來贊美圣人的道德人格為至高無上這一觀點的出現(xiàn),使得原本圣人只是聰明人的涵義演變成了圣人乃是完美道德人格之象征的涵義。
除了從道德的角度來理解圣人以外,孟子還從政治的角度,試圖對圣人的涵義作出一番新解釋。他指出:“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滕文公下》)這里的“圣人之道”的概念值得關注。孟子的意思是說,堯舜之后,社會秩序已經(jīng)開始失落,以堯舜為代表的圣人之道也已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則是各國的暴君,使得天下的社會政治陷入一片昏暗。由此可以看出,圣人之道是否存在,是決定社會政治是否有序的關鍵因素。那么何謂圣人之道呢?
在孟子看來,圣人之道所推行的政治其實就是仁政王道。孟子從歷史的角度非常明確地指出: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guī)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離婁上》)
所謂“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也就是堯舜推行的平治天下之道,最后“仁覆天下”,就是堯舜之道——仁政的最終實現(xiàn)。可見,圣人不僅僅是道德高尚的人物,而且還是治理天下的能手,圣人能將自己的“仁心”推行天下,從而使得天下蒼生無不受到“仁心”的滋潤,這就是圣人作為圣人在政治上的應有之作為。
然而在圣人問題上,孟子提出的更為重要的一個觀點則是:
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
這一觀點在幾千年儒學史上的影響可謂極為深遠。不用說,這一觀點顯然與孟子的性善學說有著密切的理論關聯(lián)。在孟子看來,人性皆善,這是學界眾所周知的說法,不必在此贅述。正是由于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堯舜之本性與普通人之本性是一樣的,原因在于不論是圣人還是普通人,在根本上屬于同類的存在,孟子堅定地指出: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告子上》)
又說:“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離婁下》)這兩段話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堯舜與人同,正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依據(jù)所在。那么,這個所謂的“同”,又有何具體所指呢?這就會令我們想起孟子的另一段名言: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上》)
圣人與我們相同者,正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理義”。從道德上講,所謂“理義”,就是仁義禮智,亦即人的四種本性,而這四種本性又是“根于心”的根本存在,故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盡心上》)。
由上可見,孟子賦予圣人以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地位,同時圣人又是能夠實施仁政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堯舜,實現(xiàn)圣人這一理想道德人格。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這一觀點的提出,既豐富了儒家的人性學說,同時又為儒家圣人之學奠定了基本方向。
五 荀子:圣人與圣王
在先秦儒家,對“圣人”特別是對“圣王”有更多討論的無疑是荀子。例如我們首先可以看到荀子利用孔子之口,對圣人做了這樣的描述: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圣矣?”孔子對曰:“所謂大圣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篇》)
孔子是否說過這番話,并不重要,對于我們來說,這是理解荀子心目中的圣人形象非常關鍵的一段描述。在荀子看來,圣人幾乎是無所不能的,既能對“大道”了如指掌,又能應變不窮,掌握天下萬物之性情。其實可以說,這正是荀子自己對圣人的一個基本規(guī)定。此外,荀子對圣人及圣王還有這樣一些描述:
圣人者,人道之極也。(《禮論篇》)
圣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正論篇》)
曷謂至足?曰:圣也。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為天下極矣。(《解蔽篇》)
圣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厘。(《儒效篇》)
以上是說,圣人不僅是道德上的完人,內心充滿仁義,言論與行為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還是制定規(guī)章制度的能人,圣人本身就是衡量天下萬物的標準。從這些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荀子,圣人主要含有雙重涵義,既有道德層面的涵義,又有政治層面的涵義,也就是說,圣人不僅是人們的道德楷模,更是社會制度的制定者。其實,在后一層意義上的所謂“圣人”,其意思更接近于先秦時代的“圣王”這一概念。
根據(jù)學者的統(tǒng)計,“圣王”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論語》未見,*然據(jù)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其載孔子釋《易·晉卦》,見“圣王”一詞,見趙達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二三子問疏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年,第211頁。《孟子》僅見一例,到《荀子》那里才開始大量出現(xiàn),共達37次,*參見注②。鄧國光指出圣王一詞普遍用于春秋時期,而戰(zhàn)國諸子幾乎都說圣王,見《圣王之道——先秦諸子的經(jīng)世智慧》,第158頁。這是先秦儒書中有關“圣王”一詞的最多記錄。所謂“圣王”,無非是指圣明君主,亦即后世所謂的“圣君”,例如堯舜作為一國之君主,同時又被封為圣人。然而孔子雖被后世封為圣人,但他只是“素王”,故稱不上“圣王”,所以荀子稱孔子是“圣人之不得埶(勢)者也”(《非十二子篇》),意謂孔子雖無權勢,但仍不失為圣人。那么,荀子何以那么重視“圣王”呢?這顯然與荀子思想非常重視禮儀等社會制度建設的政治關懷有關,由此,他對圣人問題的考察就不盡同于孟子,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表面看來,荀子“涂之人可以為禹”(《性惡篇》)的命題與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意思非常接近,強調的都是人人都可成圣的觀點;但是孟子此說的理論依據(jù)在于性善說,這一點已如上述,而在荀子,他主張性惡,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那么,性惡說何以推導出人人皆可成圣的結論呢?其實,荀子不是從人性論的角度來推論的,他是從人心皆有“知”的能力這一角度出發(fā)來得出上述結論的。荀子指出:
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性惡篇》)
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荀子是說,“涂之人”即普通百姓具有了解和實行“仁義法正”的資質和能力,因此只要專心致志、積善力行,即可成圣。這意思是說,圣人是可以通過行善的積累工夫而最終實現(xiàn)的。這一觀點的關鍵在于,唯有通過行為實踐——即積善才能實現(xiàn)圣人境界,所以荀子強調:
途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圣人。……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積也。(《儒效篇》)
荀子認為圣人雖然是“可積而致”的,但是人們往往不能真正去做,所以“可以”成圣,并不等于“必然”成圣,“可以”是指成圣的可能性,其最終實現(xiàn)端賴于實踐,這就好比人的腿可以行走天下,但未必意味著現(xiàn)實中的每一個人都能遍走天下,他指出:
故涂之人可以為禹,則然;涂之人能為禹,則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嘗有遍行天下者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性惡篇》)
由此可見,“涂之人可以為禹”并不一定要由性善說推論出來,相反,在荀子看來,人性惡亦可推導出這一結論。荀子指出:“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圣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惡篇》)又說:
古者圣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解蔽篇》)
這是說,正是由于人性惡,所以圣人出來制定禮義法度,以便人人都能遵守禮義法度,從而導向于善。
不過,禮義法度與人性無關,而與圣人作為有關,荀子指出:
凡禮義者,是生于圣人之偽,非故生于之性也。……圣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惡篇》)
為什么這么說呢?這是因為在人性問題上,荀子有一個重要觀點: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篇》)
也就是說,荀子從“性偽之分”的角度,來論證圣人的行為(偽)才是禮義產(chǎn)生的根源,至于“性”則是自然如此的,是“不可學、不可事”的。
總之,荀子所謂制定禮義法度的圣人,更接近于圣王。荀子認為,涂人百姓只有通過學習和實踐圣王所制定的禮義法度才有可能成圣,在這一過程中,涂人的行為固然重要,同樣,圣人的“偽”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更重要的是,成圣不能依賴于人性本善的理論,而應當充分發(fā)揮后天的努力,才有可能實現(xiàn)圣人境界。盡管在人性問題上,荀子與孟子有很大不同,但是荀子人可積善成圣的思想仍然屬于儒學傳統(tǒng),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荀子之后的法家,這里無暇細述,僅就韓非來看,他的圣人觀已與儒家有很大不同,他反對法先王而主張法后王,故他提出了“新圣”這一觀念,值得注意,如其所云:“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韓非子·五蠹》)韓非甚至認為,古圣不足道,新圣若能做到“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則必可“超五帝,侔三王”!(《韓非子·五蠹》)這就意味著今不必不如古,今圣可以超越古圣。*按,秦漢以降,圣人被用作皇帝的一種尊稱,特別是在漢代,這一稱呼在定型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政治史、思想史上的曲折,可以參見上揭邢義田論文及蕭璠《皇帝的圣人化及其意義試論》,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1,1993年,第14-24頁。另按,關于先秦道家的圣人觀,本文未能涉及,可參徐復觀《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再檢討》附表二“《老子》用‘圣人’一覽表”,載其著《中國思想史論集續(xù)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頁。
六 宋代新儒學:“圣人可學而至論”
然而到了宋代,道學家對于荀子的成圣說卻不以為然,甚至有嚴厲批評,例如程頤便指出:“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荀子·勸學篇》)……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圣人?”[9](卷十八,P.191)這是說,荀子雖主張人可成圣,但他的思想宗旨在于“禮義為偽,性為不善”,由此出發(fā),荀子連“情性”問題尚不能領會,何以能夠達到圣人地位?這顯然是程頤從道學思想立場出發(fā)對荀子所作的批判。那么,宋代道學興起以后,道學家們對圣人問題又有何看法呢?*關于宋代道學中的“圣人”問題,可以參看姜廣輝《理學圣人觀漫議》,載氏著《理學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吾妻重二《朱子學の新研究》第2部第1章“道學の圣人概念”,東京:創(chuàng)文社,2004年。吾妻先生指出,在宋代的非道學派士人當中,很難找到圣人可學而至的觀念表述,他列舉了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洵等一些著名大學者為例來證實這一點,這個觀察很有啟發(fā)性(《朱子學の新研究》,第152-156頁)。
我們知道,在整個宋明時代,周敦頤(1017-1073)所說的“圣可學”*原文為:“‘圣可學乎?’曰:‘可。’”《通書·圣學》,《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9頁。可謂是儒者的共識,我們不妨稱其為“圣人可學論”,正是這一觀點對于后世仁人志士起到了極大的鼓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宋代道學之所以不同于宋代之前的儒學,原因之一就在于宋代道學首先倡導的這一“圣人可學論”。這一論點明確告訴人們,圣人之學的代表人物孔子不僅是學習的知識對象,更是每一個人都應努力實現(xiàn)而且是可以實現(xiàn)的人格目標。
不過,在周敦頤的場合,除了“無思而無不通,為圣人”[10](《通書·思》,P.21)以及“誠者,圣人之本”[10](《通書·誠上》,P.12)等個別敘述以外,總的來說,其有關圣人的討論并不多。這一情況的改觀則要等到二程的出現(xiàn),特別是程頤(1033-1107)對圣人問題討論尤多。他在為其兄程顥(1032-1085)所撰《墓表》中指出:“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11](卷十一,P.640)這里出現(xiàn)了“圣人之道”與“圣人之學”兩個概念,前者是指堯舜至周公這段歷史時期,后者則指周公至孔子這段歷史時期,程頤認為,圣人之道的存在以周公為分界線,而圣人之學的存在則以孟子為分界線。
可以看出,程頤的歷史認識未免悲觀,在他看來,圣人之道與圣人之學,在孔孟時代發(fā)生了巨變,首先在孔子時代,圣人之道已經(jīng)喪失不傳,其次到了孟子時代,就連圣人之學也已一并喪失,而這種狀況一致延續(xù)到程頤生活的時代。所以程頤又說:“道不行,百年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11](卷十一)前一句是說春秋末期,天下陷入了“無道”的狀態(tài),這是指政治沒落;后一句是說春秋戰(zhàn)國直至宋代初年,天下已無真正的儒者,這是指思想沒落。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兩重斷裂:一是從政治上看,治道上發(fā)生了斷裂;一是從學術上看,學道上也發(fā)生了斷裂。而這一狀況出現(xiàn)改善之征兆則要等到二程的時代,程頤說:
先生(按,指程顥)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jīng),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先生出,倡圣學以示人,辨異端,辟邪說,開歷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為功大矣。[11](卷十一)
這是說,自孟子以后1400年,圣道及圣學(“道學”一詞的由來)得以復續(xù),端賴于程顥。這里稱贊的是程顥對于孔孟儒學之功勞甚大,其實何嘗不包括程頤自己。若從歷史上看,二程對于復興圣人之道及圣人之學的確是有自覺承擔的強烈意識。也正由此,二程之后,“道學”遂成為后人指稱二程所倡導的學問之名稱。[12]例如朱熹(1130—1200)在乾道四年(1168)所撰《程氏遺書后序》中就明確指出:“二先生唱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后,可謂盛矣。”*按,其實早在紹興三年(1162),朱熹在《壬午應詔封事》中就已指出二程是“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見《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2頁)。
既然二程對承擔圣人之學有一種自覺意識,那么二程在圣人問題上又有何具體看法呢?我們可以從程頤的少年之作《顏子所好何學論》說起。據(jù)《伊川先生年譜》,該文為程頤18歲游太學時所作,得到當時執(zhí)掌太學的名儒胡瑗(993-1059)的極力稱贊。程頤該文一上來就開宗明義地說:
然則顏子所好何者,何學也?學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學而至歟?曰:然。[11](卷八,P.577)
這里提出了兩項劃時代的命題:“學以至圣人之道”、“圣人可學而至”。*按,黃進興指出這是“兩項劃時代的命題”,“被視為理學的石破天驚之論”,參見其文《理學家的道德觀——以〈大學〉〈近思錄〉與〈傳習錄〉為例證》,見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lián)經(jīng)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297頁。特別是后一句命題,與周敦頤“圣人可學論”可謂如出一轍,對后世的影響甚巨。所不同者,周敦頤所述不多,而程頤的這一觀念表述可謂一而再、再而三,例如:
人與圣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9](卷十八,P.203)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棄也。[9](卷二十五,P.318)
圣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于圣人。[9](卷十五,P.145)
……又況人與圣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yǎng)成就到圣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9](卷二十三,P.306)
這些說法大抵與孟子一致,都是從人與圣人同類的角度而言的,同時也強調學習的重要性,程頤相信,通過后天的不斷學習,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可以成圣的,重要的是,學習的目的就是成圣,如果放棄成圣的目的而從事學習,這在程頤看來,無異于自暴自棄。
誠然,人皆成圣的原因在于人與圣人同類,然而除此以外,又有何理據(jù)可以證明我們每一個人都可成圣,程頤拈出一個“理”字來進行解說,他甚至將孟子的“圣人,人倫之至”的人倫解釋成“人理”,同時又結合“性即理”這一理學的標志性觀念,指出:
圣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9](卷十八,P.182)
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涂人,一也。[9](卷十八,P.204)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圣人。[9](卷二十五,P.316)
這個說法顯然超越了“類”的觀念,采用具有普遍性的“理”來證明人可成圣。由于理在事中,所以我們只要隨事觀理,通過對事理的把握,也可以成圣,這就指明了成圣的具體方法。所謂隨事觀理,又與格物理論相關,所以程頤又說:
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9](卷二十五,P.316)
圣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9](卷十五,P.152)
這里的末句“所以然者”,在程朱理學的辭典中,也就是“理”字。可見,成圣的工夫離不開格物,這是因為圣人之道本無精粗之分,就存在于人世間的日常生活當中,具體而言,從“灑掃應對”到“精義入神”無不存在圣人之道。
順便指出,在程頤的心目中,圣人是有嚴格定義的,主要是指自堯舜以至孔子,而孟子尚無資格稱為圣人。他說:“顏子去圣人,只毫發(fā)之間,孟子大賢,亞圣之次也。”[9](卷十八,P.197)又載:“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圣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學已到至處。’”[9](卷十九,P.255)由此可見,程頤明確指出孟子未可稱為圣人,甚至連“亞圣”也稱不上,只有顏回才可稱為“亞圣”。*稱顏回為“亞圣”,又見周敦頤《通書·顏子》及胡瑗《周易口義·系辭下》。另據(jù)吾妻重二,孟子之被稱為亞圣始于元至順元年(1330,見《元史·祭祀志》五),至明嘉靖九年(1530)被確定下來(見《明史·禮志》四),與此相應,顏子則被稱為“復圣”,而東漢趙岐《孟子題辭》“命世亞圣之大才”的說法——即以“亞圣”稱孟子,只是孤證而已,這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并非主流觀點,參見上揭氏著《朱子學の新研究》,第193頁注23。
在程頤之后,南宋朱熹在繼承程頤之說的基礎上,對圣人問題更是屢屢涉及,這里僅舉幾例。例如朱熹曾說:“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13](卷五十五,P.1306)這是以孟子性善說為依據(jù),將成圣的可能性歸諸性善之本質性觀念。又說:“學之至則可以為圣人,不學則不免為鄉(xiāng)人而已。可不勉哉?”[14]可見,濂溪、二程以來學可至圣的信念也同樣為朱熹所擁有。朱熹不僅深信每個人都有成圣的可能,而且還主張不能把圣人說得太高太玄乎,相反,我們應當把圣人看成與普通人一樣,因為在本質上,人性之為善,故與圣人同,所以他說:“不要說高了圣人。高了,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圣人低,越有意思。”[13](卷四十四,P.1140)這段話值得吟味,這表明朱熹有一真實想法:圣人作為一種成德的理想,應當且可以在普通民眾中得以推廣普及,原因就在于“圣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賢為己任!”[13](卷八,P.133)不過,在圣人位階的問題上,朱熹認為堯、舜、禹雖為“天下之大圣”,然而孔子卻是在思想文化上繼往開來的人物,故在此意義上,孔子作為圣人更在堯舜之上。*朱熹《中庸章句序》:“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四書章句集注》,第14—15頁)按,孔子“賢于堯舜”為孟子引述宰我語,見《孟子·公孫丑上》。程頤對此解釋道:“語圣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于堯舜’,語事功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五,《二程集》,第76頁)據(jù)朱熹的解釋,此“事功”蓋指孔子推闡堯舜之道“以垂教萬世”(《孟子集注》卷十三《公孫丑章句上》)。
總之,在程朱那里,“圣人”主要是指具體的孔子包括儒家經(jīng)典中的“圣人之言”,如歷史上儒家傳統(tǒng)的圣人觀一樣,在他們看來,孔子既是最高的道德理想人格,同時又是儒家文化的精神標志。不過,程朱也有一種非常明確的意識,亦即認為傳統(tǒng)儒學主張人可成圣的依據(jù)在于人性本善,而人性本善得以證成的最終理據(jù)又在于性即是理,由于不論是圣人還是凡人,在人性本善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凡人就有成就圣人的可能。然而歸結而言,在程朱理學的場合,圣人仍然是外在的一種理想目標,成就圣人的可能性之實現(xiàn)取決于后天的實踐工夫之積累,因此圣人最終不過是外在的學習對象,這是程朱理學圣人觀的一個重要特質,而與后面我們將要看到的陽明心學意義上的完全內在化的圣人觀有很大不同。*按,至于心學家陸九淵的圣人觀,此不細述。簡言之,他是從“此心同,此理同”的心學立場出發(fā),主張“圣人可學而至”,可參見《陸九淵集》卷十三《與郭邦逸》等,并參上揭吾妻重二及姜廣輝的論文。
七 王陽明:內化為良知的圣人觀
及至明代王陽明(1472-1529),出現(xiàn)了一種不盡同于理學的圣人觀,我們姑且稱之為心學式的圣人觀,其基本特征是圣人已經(jīng)徹底內化為內心良知。
誠然,少年陽明在思想上曾經(jīng)被宋代道學的影響所籠罩,他盡管也抱有 “圣人可學而至”的信念,故其12歲就已表露出想成為“圣賢”的愿望,但他在將“圣人”作為學習對象的實踐過程中卻屢受挫折,因為他總覺得有一個根本問題難以消解:即儒家所說的圣人之道如何與自我本心吻合無間。這使陽明多次喪失信心,以為成圣需要一種大力量,而他自己正缺乏這種所謂的“力量”。及至37歲那年,陽明被貶官至貴州龍場驛,在那里經(jīng)歷了“動心忍性”、“百死千難”的磨煉以后,終于在思想上悟出了一層道理:“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由此覺悟使得陽明最終建立了堅定的信心而不復動搖:“決然以圣人為人人可到。”需注意的是,此處“吾性”一詞意同“吾心”,意謂圣人之道不在人心之外而就在人心之中。這場覺悟既標志著陽明思想的成熟,同時也意味著陽明的圣人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亦即圣人不再是二千多年前的那位歷史上的“活孔子”,也不是在孔廟祭奠著的帶有各種名號的“假孔子”,而是活在當下每一個人心中的精神意義上的“真孔子”。
也就是說,在陽明的心目中,所謂“圣人”既是傳統(tǒng)儒家設定的道德理想人格,更是人心良知的一種符號和象征,此即陽明之所以再三強調“心之良知之謂圣”[15](卷六,《書魏師孟卷·乙酉》《答季明德·丙戌》,PP.280,214)的用意所在。顯然,陽明意將圣人與良知等同起來,從而將圣人概念符號化。也就是說,圣人不再是單純的歷史上的孔子(或孟子)的具體稱謂,圣人已然化為了人心內在的良知。由于良知生來具足、人人圓滿,故圣人也就是每個人心中的本質存在。這樣一來,圣人就超越了時空的限制,而被完全內在化、普遍化。也就是說,一方面將圣人內化為良知存在,從而良知被提升為圣人境界;另一方面由于良知是亙古亙今、無所不在的普遍存在,所以人人心中自有圣人。也正由此,所以陽明說“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15](卷二十,《詠良知回首示諸生》,P.790)究極而言,外在化的偶像化的圣人已不復存在,內在良知就是圣人。
故陽明逝世前一年曾賦詩一首,闡發(fā)了這樣一種觀念:宇宙萬物因為有了“我”的存在而被賦予了價值和意義;歷史上的各種圣人只是過眼云煙,而唯一真實的圣人其實便是作為吾心之師的良知,他寫道:“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圣皆過影,良知乃吾師。”[15](卷二十,《長生》,P.796)可以看出,陽明從良知本體論的立場出發(fā),在圣人問題上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由于良知是人的本體存在,而良知即是圣人的同時,人人都有良知,所以結論就是人人都是圣人。
按照陽明的良知理論,良知永存而不會泯滅,故作為儒學道德人格之象征的“孔子”或“圣人”也是永恒長存的。這個觀念告訴我們,人人都有成圣的內在依據(jù)及潛在可能,都能成就道德主義的理想人格。不用說,孔子本身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距陽明的時代已有二千年,人死不能復生,但是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精神及其理想人格卻是永恒的,因此人格化、內在化、精神化的“圣人”才是激勵和指引我們人生未來走向的動力源泉。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千圣皆過影,良知乃吾師”無非是引導人們努力實現(xiàn)“超凡入圣”的一句思想口號;而王門當中出現(xiàn)的“滿街人都是圣人”之說,也就不值得訝異了,這個說法其實恰是“超凡入圣”的一個最好注腳。《傳習錄》有這樣一段記載:
先生鍛煉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按,即王艮)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圣人,滿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蘿石(按,即董沄)出游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4](卷下,第313條)
那么,“滿街人都是圣人”的理據(jù)何在?這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對陽明而言,“滿街圣人”不是一時脫口而出的泛論,其中自有深刻的思想緣由,當陽明批評王艮所說“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無非是自以為是的一種偏執(zhí)孤傲之見,這表明陽明對于滿街圣人說有所警覺,意味著陽明也意識到一方面固然須要樹立起良知具足、時刻圓滿的信心,但同時也要切忌自以為是的那種狂妄自大癖,因為良知具足并不意味著人在現(xiàn)實狀態(tài)中就可置工夫于不顧,換言之,“人人心中有仲尼”的“有”并不等于“是”這一事實描述,這層義理上的分疏對于陽明而言相當重要;其次,當陽明向董沄指出滿街都是圣人“此亦常事”之際,這顯然是就“良知見在”這一良知本體論的立場而言的,由此出發(fā),“個個心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謂圣”乃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非假設。故在陽明,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個體的有限性以實現(xiàn)道德主體的無限性之可能——亦即“成圣”,乃是其心學思想所指向的終極目標。
須注意的是,陽明一方面說“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另一方面又強調“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4](卷中,第139條)一方面,從良知本體這一存在事實看,圣愚一致,斷無可疑;另一方面,從人的現(xiàn)實狀態(tài)看,由于個人的致良知工夫有程度差異,故圣愚并不全然一致。由此看來,滿街圣人是就本體言,是說滿街人都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見在良知,若就工夫言,人們很難恒常地守住人心的圣人本質,而須不斷地將致良知工夫貫徹下去,未至成功而絕不罷手。陽明所說的圣愚之分,便是著眼于現(xiàn)實狀態(tài)中的工夫而言,因此滿街都是圣人并不意味實踐工夫可以放棄,這是理解陽明心學圣人觀的一個關鍵。
總之,若拋開心學理論的內部糾纏,就“滿街人都是圣人”這一命題本身來看,毋庸置疑,這是陽明心學將外在偶像的圣人內化為人心良知的結果,對當時人們的觀念所造成的沖擊與鼓舞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因為,圣人已不再是遠離現(xiàn)實、僅存于歷史中的抽象人格,也不僅僅是存在于孔廟當中供人頂禮膜拜的那尊孔子塑像,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人們心中的良知本身;也就是說,良知也不是某種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作為道德主體之個人都可努力實現(xiàn)的道德理想,這就為“超凡入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同時也意味著“圣人”必然走向世俗化、平民化,因為人人都在本然意義上可以成就圣人。誠然,儒學從來不是出世的宗教,而是具有積極入世精神的“成德成圣”之學,因而孔孟原創(chuàng)的儒學本來就具有世俗性特征,只是漢代以后儒學一度經(jīng)學化、學院化,及至宋代新儒學運動的興起,儒學世俗化之趨向才變得日益明顯,朱熹“不要說高了圣人”之說也正表明儒學的成德理想須建立在層層就下的學習努力上,并在世俗社會的日用倫常中,努力實踐以完成自身向終極存在的轉化,盡管如此,然而我們不得不說,徹底內在化的陽明心學意義上的圣人觀在整個儒學的發(fā)展史上具有獨樹一幟的理論意義。
八 小 結
綜上所述,從字義發(fā)生學的角度講,“圣”之本意不過是指聰明,是指具有超凡的感知能力的人;及至孔孟時代,圣人既是政治上、道德上的完美人格,同時也是儒家人文制度的設計者、制作者,特別是在思孟學派中,與其仁義內在的思想立場一致,“圣”作為一種內在德性而被強調;盡管對于人性本善的觀點荀子并不認同,但是在儒學指向的圣人理想這一根本問題上,正如“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所表明的那樣,孟、荀都以成德成圣作為自己理論的終極目標;先秦以降,歷史上的孔子被封上各種名號,圣人成為儒家文化的一種象征而被偶像化,及至宋代新儒學時代,圣人主要作為一種文化傳統(tǒng)以及學術傳統(tǒng)而受到格外的重視,出現(xiàn)了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學的概念,圣人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以及儒學文化傳統(tǒng)的標志;隨著陽明心學的出現(xiàn),圣人的內在化得以完成,圣人成了特指內心良知的一種抽象符號,也正由此,故圣人已不是廟堂之中的偶像,更不是超越人間的神秘存在,圣人其實就是我們每個人內心的良知本身,這就為儒學“超凡入圣”的理想提供了一種可行的實踐方式,即通過對內在良知的自我體認便可成圣,于是,圣人也就必然趨向于世俗化。
一般說來,儒學在實踐意義上被理解為是一種成德之學、成圣之學,這是沒有疑問的,儒學所追求的最終理想人格無疑就是“圣人”,這一點也是歷史上幾乎所有儒者的共識。然而如果說圣人是至善至美的——既是“盡倫者”又是“盡制者”,既是“百世之師”又是“人倫之至”,那么難道凡夫俗子在有限的生命中亦能成圣嗎?如果以西方傳統(tǒng)宗教的觀點為準,這樣一種近乎完美的理想人格似乎唯有“全能”的上帝才有資格具備,而人并不具備成就上帝的可能性。顯然這里所關涉的關鍵問題是“人雖有限而可無限”*按,“人雖有限而可無限”乃是以牟宗三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的一個核心觀點,對此觀點的分析,可參看施益堅(Stephan Schmidt)《當代東亞倫理學的兩種主體觀念——論和辻哲郎、唐君毅和牟宗三對哲學倫理學的進路》,載《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6卷第1期(總第11期),2009年6月,第145-160頁。的問題——亦即儒學史上“超凡入圣”如何可能的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需要我們回歸儒學的傳統(tǒng)觀念:承認人并不只是認知主體而更是道德主體,人雖是有限的存在,但在此有限中卻有無限性的可能,最終通過“物由心轉”這一終極性的轉化努力,人們可以向著“超凡入圣”乃至“天人合一”之理想境界的實現(xiàn)不斷趨近。*事實上,在晚明心學背景下,出現(xiàn)了大量有關“圣凡一致”的言論,如“圣愚無間”(王陽明)、“圣愚平等”(王畿)、“舉世皆圣人”(羅汝芳)、“圣愚一律”(李贄)乃至另一意義上的“圣凡一致”論——“無圣無凡”(劉宗周)等等層出不窮,引人深思,參見筆者為《中國理學》第四卷所撰“圣凡一致”條,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按,關于“天人合一”的問題,近來余英時有精彩論述,參其長文《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特別是第6節(jié)“從天人合一到內向超越”),載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lián)經(jīng)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1—93頁。設非若此,則儒學傳統(tǒng)所設定的具有超越私欲而不為物轉之能力的道德主體就不免變得消極乃至陷于沉淪而無法自拔,更無法實現(xiàn)“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終極理想,而“人人心中有仲尼”也只能成為一種空頭的虛設而無任何實踐意義,果真如此,則作為實踐哲學的儒家倫理學之理論建構恐怕就難以挺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即便說儒學“圣人觀”是牽涉對儒家道德倫理學究竟應如何理解與闡釋的一大關鍵問題亦不為過矣。
[1]顧頡剛.“圣”“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C]//中國哲學:第1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80-81.
[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經(jīng)韻樓藏本.592.
[3]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M].北京:中華書局,1984.880.
[4]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5]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2.283,289.
[6]陳來.竹簡《五行》與子思思想研究[M]//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9.
[7]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池田知久.郭店楚簡《五行》研究[M]//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曹鋒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76,83.
[9]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M]//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周敦頤.周敦頤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1]程顥,程頤.河南程氏文集[M]//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陳來.宋明理學[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9.
[13]朱熹.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4]朱熹.論語集注[M]//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83.
[15]王陽明.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TheConceptof“Sage”inChineseIdeologicalHistory
WU Z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s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 concept had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ose who ha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however, it had dual meaning: perfect moral personality and outstanding political figures. Since the time of Warring States when Confucius was made a sage, there came the trend of sacralizing sag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under the widespread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ical slogan of “l(fā)earning can help to become a sage”, the Learning and the Tao of sages became a symbol fo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turned out to be a learning of becoming a sage. And to the time of Yangming Xin Xue, the dominance of sages’ viewpoints in the society led to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sages became a secularized symbolic sign of human mind and conscience, rather than a mystic one. Such an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deserves our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how “an unconventional sage” embedded in Confucian values can be possible.
sage; sage-king; Confucius; Mencius; Wang Yangming; unconventional sage
2013-05-12
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人文學科研究重大項目“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儒學研究——海外與本土儒學研究的交錯與展望”(2011RWXKZD010)的研究成果。
吳震(1957-),男,江蘇丹陽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京都大學文學博士。
B2
A
1674-2338(2013)04-0013-13
(責任編輯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