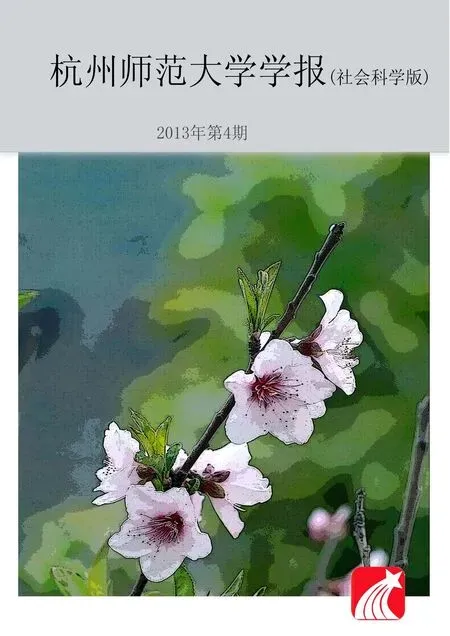人文理性:周作人所倡“科學”的實質內核
黃江蘇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文學研究
人文理性:周作人所倡“科學”的實質內核
黃江蘇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周作人對“五四”時期的主題話語之一的科學,保持著疏遠和警惕的態度,因為那時候他專注于文學的園地,強調人文藝術對人類精神的獨特價值。從20世紀20年代末期,他內心發生“由情轉智”的變化以及與革命文學的論爭以后,“科學”成為他最看重的文章主題。他把科學的源頭上溯到原始儒家的“疾虛妄”與古典希臘的“愛智慧”精神,實際上是人文理性的立場。這種主張人間生活倫理須以科學知識為本、科學理性又必須合乎人間生活之用的立場,強調“常識”的精神,對于科學工具理性的迷失與當今社會玄虛亂象的匡正,有著巨大的啟示意義。
周作人;科學;人文理性
一 科學的邊界與人文理性的定義
科學是“五四”時代風云里矗立著的兩面大纛之一。然而,“五四”時期中國提倡的“科學”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科學”?丹皮爾對“科學”的解釋是:“拉丁語詞Scientia(Scire,學或知)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是學問或知識的意思。但英語詞‘science’卻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學)的簡稱,雖然最接近的德語對應詞Wissenschaft仍然包括一切有系統的學問,不但包括我們所謂的science(科學),而且包括歷史,語言學及哲學。”[1]“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像陳獨秀、胡適,并非自然科學家,他們堅定地標舉自己的“科學”立場,都是取上述的拉丁語詞、德語詞中那個寬泛的“科學”的含義。陳獨秀在1920年寫的《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說:“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2]他們對科學有全盤的認識,對于自己的定位也很明確,那就是主要在人文社科領域里下工夫。例如胡適寫有《實驗主義》《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等文章,提倡在哲學研究、整理國故等學術事業中運用科學方法。在1923年張君勱等人用“人生觀”的名義向科學發起挑戰時,他們都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分別亮出“唯物的歷史觀”、“自然主義的人生觀”,[3](P.7,23)來捍衛科學在這方面不可動搖的合理性。羅志田認為,五四人“講‘科學’甚少往‘技術’方向走,講到西方的物質一面時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層次”,“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在實踐層面更首先落實在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以及史學的‘方法’之上”,這跟中國傳統“重學輕術”的思想傾向有關。[4]這也是一種很有參考價值的觀點。
與陳、胡等人一樣,周作人所提倡的科學,其實質內核并非是通常對應的科學——技術理性,而是人文理性。人文理性,簡而言之,可以說是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結合形態。它是與一般所稱工具理性、歷史理性相對的一種說法,對此王岳川教授較早有過論述,他認為工具理性帶來的科技力量和歷史理性推動的政治操控,都在帶來利益的同時帶來了巨大傷害,人類急需建立人文理性,它不僅是人文價值、人文關懷,更是理性的思索與反省。[5]還有學者認為,人文理性是認知理性、實踐理性、價值理性、交往理性等的總稱,是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的中間環節,是人們認知、批判、選擇和創造人文價值觀的能力。[6]朱德發教授也曾撰文論述現代文學創造中的“人文理性精神與主體人本藝術思維”的關系,[7]并指出早在嚴復那里,就曾發出過“西人謂一切物性科學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術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兩者往往相入而不可強分。科學之中,大有感情;美術之功,半存思想”的呼聲。[8]周作人可以說是嚴復這一先聲的回響,仔細分析周作人所提倡科學的實質內涵,其主張科學不可凌夷文藝,而人文關懷、倫理價值也須得以合乎科學理性為基礎的思想,正好高度契合“人文理性”的定義,而且考察其思想發展過程,有一條分明的從偏重人文到轉倡理性,再到人文理性的融合的明線。詳細闡述周作人這一思想,對于今天的人文精神建設仍然是大有裨益的,故以下分而述之。
二 情理分殊:人文立場對科學霸權的警惕
“五四”乃至20世紀20年代前期,周作人標舉“科學”的文字并不算多,比較明確的只有那篇曾歸到魯迅名下的《隨感錄三十八》。其中說,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9](第2卷,P.73)科學精神的提倡不是這時期他工作的重心,對于熱熱鬧鬧的“科玄之爭”,他完全置身事外。這個時期,他除了沉迷于新村運動,最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文學寫作,耕種“自己的園地”。以是之故,在他的心底里,重文學、“防”科學的傾向比較明顯。
為什么說“防”科學呢?周作人并不反對科學,這是必然的。胡適曾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3](P.9)胡適的話里已隱然透露出科學掌握著“霸權”的信息。周作人所防備的,就是科學過度的“霸權”,防備科學過度僭越而壓制文學的生命。更進一步說,就是警惕理性對情感的壓制。他曾說:“我們平常專憑理性,議論各種高上的主義,覺得十分澈底了,但感情不曾改變,便永遠只是空言空想,沒有實現的時候。真正的文學能夠傳染人的感情,他固然能將人道主義的思想傳給我們,也能將我們的主見思想,從理性移到感情這方面,在我們的心的上面,刻下一個深的印文,為從思想轉到事實的樞紐:這是我們對于文學的最大的期望與信托。”[10](《苦雨齋序跋文》,P.16)所以他經常將“科學”與“藝術”并舉,聲明兩者都不可偏廢。1924年他在《狗抓地毯》中說:“科學之光與藝術之空氣,幾時才能侵入青年的心里,造成一種新的兩性觀念呢?”[10](《雨天的書》,P.100)1927年他在《香園》中又說,“中國人落在禮教與迷信的兩重網里,永久跳不出來,如不趕緊加入科學的光與藝術的香去救治一下,極少解脫的希望。”[10](《談龍集》,P.85)在不可偏廢中尤其強調不能用科學的名義取消文學(或者是藝術、情感)的地位。1922年他在《文藝上的異物》中說:“科學思想可以加入文藝里去,使他發生若干變化,卻決不能完全占有他,因為科學與藝術的領域是迥異的。”[10](《自己的園地》,P.30)《真的瘋人日記》里有一段諷刺那些“用顯微鏡考察人生的真義”的學者。[10](《談虎集》,P.377)1923年發表的《鏡花緣》,他再次表達了對“用紀限儀顯微鏡來測看藝術”之人的抗拒,稱許P. Colum所說的“對于減縮人們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于凡俗的都市,對于商業的實利,對于從物質組織所發生的文化之嚴厲的敵視”,并由此稱許《鏡花緣》和王爾德童話中的“說誑”。[10](《澤瀉集》,P.9)在1925年寫的《唁辭》中,他甚至為希冀死后生活這樣的“迷信”辯護:“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里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既失卻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成畫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里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于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于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10](《雨天的書》,P.22)科學取消文藝及與文藝相關的想象、情感,會造成幻滅的不幸,而避免這一點的出路也只有相對地維護文藝及與文藝相關的這些事物,所以周作人在《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中說:“人間所同具的智與情應該平勻發達才是,否則便是精神的畸形……我相信對于精神的中毒,空想——體會與同情之母——的文學正是一服對癥的解藥。所以我推舉這部《漫游奇境記》給心情沒有完全化學化的大人們。”[10](《自己的園地》,P.56)
周作人這樣的態度與乃兄魯迅非常相像。五四時期魯迅也寫過專談科學的文章,例如《隨感錄三十三》,但是數量不多,似乎只是時代大合唱中的配合式發聲。郜元寶在分析他寫于1907年的《科學史教篇》這篇文言論文時,認為“恰恰是這篇專門討論科學問題的論文,標志著魯迅的短暫的科學時代的結束,以及他持守一生的文學生涯的開始”,因為在這篇論文里,魯迅已經超越了膚淺地追求科學的枝葉的階段,而致力于探求西方科學發達的“深因”、“本根”、“本柢”,也就是科學背后的精神之奮發、心靈之自由等總名之曰“神思”的事物。而魯迅在編輯《墳》的時候對早期四篇文言論文的編排,更體現出一個完整的思想構造:在《科學史教篇》之后繼以《文化偏至論》,指出科學發達的西方到了現代,已經出現“重物質而輕精神”之類的弊端,“立人”——尤其是“立心”,培育人的“內部之生活”已經成了當務之急。接下來便以《摩羅詩力說》闡釋了以文藝“涵養神思”的方案,未完成的《破惡聲論》更是一次為“迷信”辯護的具體文學實踐。[11]參照魯迅這樣的思想歷程來看,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及20年代前期對待科學的態度就像是兄長思想的一次遲到的翻版。他的科學與藝術并舉的觀點就像《科學史教篇》里談科學兼談神思,他在《唁辭》里講科學帶來的精神寄托的幻滅就像《文化偏至論》,而《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思路同步于《摩羅詩力說》。周氏兄弟早期思想的一致,尤其是周作人亦步亦趨于魯迅(去南京,去日本,從事譯書等文學運動都受到魯迅的影響),這又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說起來,魯迅和周作人都是學“科學”出身,魯迅從水師學堂轉到礦路學堂,到日本又進醫學院,周作人則從江南水師學堂被公派到日本學建筑。他們求學和最初成名的年代,都是科學在中國日益得勢終至于在知識界建立“霸權”的時候,可是他們在這時卻表現出對科學的知識霸權的警惕,在中國的知識界顯得非常超前。這跟他們都敏銳而全面地接觸了世界思潮有關。正如魯迅在《隨感錄五十四》中說的,“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各個不同時期的思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2]他們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生物學、化學等科學教育,一方面同時接觸了西方的浪漫主義等針對科學、理性而出現的反撥性的思潮(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提到拜倫、雪萊等人,還有他鐘愛的尼采都有對理性的批判,周作人早期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顯示他對這些人也并不陌生),因而造成了這種現象。對文藝事業的選擇,更促進了他們這種對待科學的批判性立場。
三 由情轉智:回溯儒家的“疾虛妄”與古希臘的理性精神
事情在1925年周作人宣布文學店關門之后有了變化。前面我已經談到這時期周作人內心發生了由情轉智的變化,發出“現在唯一的欲望是想多求一點知,盡我的微力想多讀一點書,多用一點思索,別的事且不要管”[9](第4卷,P.97)的愛智宣言,甚至認同“感情是野蠻人所有,理性則是文明的產物”。[10](《談虎集》,P.389)從這個時候開始,“科學”在周作人筆下分量越來越重,以前常常并舉的“文藝”則有隱居二線的趨勢。看起來,周作人似乎與時代潮流倒了過來,在眾人齊論科學的時候他很超前地警戒了一番實現科學以后的弊病,等到眾人都轉入各自不同的行當中去了,他再后退一步來提倡追求科學。
1925年之后的幾年里,周作人的文章中還沒有很多地體現出讀書求知的信息,倒是在1928年開始的革命文學對他的批評中,他比較徹底地意識到空有革命激情而不注重求知務實的弊端。《婦女問題與東方文明等》中說,要促進青年的思想改革,很重要的“即是科學思想的養成。我們無論做什么事情,科學思想都是不可少的”,“中國近來講主義與問題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一點,他們做著粉紅色的夢,硬不肯承認說帳子外有黑暗。譬如談革命文學的朋友便最怕的是人生的黑暗”。[10](《永日集》,P.98)他把這種只憑夢想提出主張的行為稱為“狂信”,并認為狂信是不可靠的,剛脫了舊的專斷便會走進新的專斷。要破除這種“狂信”,就要提倡“理知”、“學問”,實際上就是科學。“知與信是不大合得來的”,“這須得先有學問的根據,隨后思想才能正確”。[10](《苦茶隨筆》,P.68)
在與革命文學的論戰之后,他才真正轉向“閉戶讀書”。從他3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偏于“讀書隨筆”的集子《夜讀抄》來看,他一開始想讀的也多半是學術性的、“科學”的而非文學的書:《原野物語》《習俗與神話》《豬鹿貍》是民俗學、神話學著作,《蠕范》《性的心理》《蘭學事始》是關于生物學、性心理學、醫學的,此外還有《塞耳彭自然史》《金枝上的葉子》等與學術相關的書籍。從這樣的選擇不難看出他的用意。《蘭學事始》中,他比較同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醫學家的研究狀況,痛切地說:“中國在學問上求智識的活動上早已經戰敗了,直在乾嘉時代,不必等到光緒甲午才知道。”[10](《夜讀抄》,P.49)如今在新的歷史時期,他自然希望能通過提倡,讓中國的學術事業、科學事業,能夠發達起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隨著買書條件的限制等原因,他讀書越來越局限于中國古代的筆記。此時他更感到了提倡科學精神的急迫,因為在這些筆記里,充斥著各種烏煙瘴氣的思想,讓他讀來氣悶,更加意識到用科學精神救治的急迫性。他同時認為,這科學精神其實也并不是中國古來沒有的東西,“這本來是希臘文明的產物,不過至近代而始光大,實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謂疾虛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10](《藥堂雜文》,P.40)
由此可見,當周作人意識到必須求助于科學才能醫治時代的狂信以及歷史的迷信之后,他異常敏銳而明智地將視野擴展到了中西文化的源頭上去,將古希臘和所謂的原始儒家提了出來。在《過去的工作》中,他說自己很早就注意到國人談及西方文化時,大抵只憑工業革命以后的歐美兩國的現狀以立論,總不免是籠統,所以他提倡為得明了真相起見,對于普遍認為的文明之源的古希臘,非詳細考察不可。[10](《過去的工作》,P.82)以是之故,他極力鼓吹希臘的科學精神。《希臘人的好學》中說:“后世各部門的科學幾乎無不發源于希臘,而希臘科學精神的發達卻實在要靠這些書呆子們。……他們對于學,即知識,很有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態度”,“中國人如能多注意他們,能略學他們好學求知,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學風,未始不是好事,對于國家教育大政方針未必能有補救,在個人正不妨當作寂寞的路試去走走耳”。[10](《瓜豆集》,P.86)一方面他認為中國人應該學習希臘這種純粹的求知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中國并不是完全不曾有過類似的理性,在《自己所能做的》等好幾篇文章中,他就曾說過,“中國民族的思想傳統本來并不算壞,他沒有宗教的狂信與權威,道儒法三家只是愛智者之分派”。[10](《秉燭后談》,P.2)這其中又尤其是儒家,他本身的長處即是把古代許多迷信理性化,這是周作人早就指了出來的。[10](《談虎集》,P.343)但是后來怎么變壞了呢?周作人在1941年的《中國的國民思想》中給出了自己的診斷,他認為一個新的因素把健全的儒家思想搞壞了,那就是考試制度。考試制度造成兩大流弊,不說真話和胡說八道,“把真實的學問都阻塞了,因此中國的科學也不能發達了”。[9](第8卷,P.579)檢查清楚了這個弊端,就要把壞的部分去掉,中國思想也就能重新屹立無憂,所以他說“中國根本思想是好的,不過是后來變壞了,只要再加上科學文明,就可以把固有的國民性恢復過來”。
這就是周作人對中國應該有的科學態度總的觀點。他強調中國古代思想里已有科學精神,只是后來泯滅了,中國應該在固有的儒家思想基礎上去發展科學,而這樣做的途徑又不僅僅是學習現代的西方,還應該注意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思想中的科學精神。
四 常識與生活倫理:人文理性精神的最終落腳點
周作人在1944年寫的《文藝復興之夢》中說,“文藝復興應是整個而不是局部的。照這樣看去,日本的明治時代可以夠得上這樣說”,“中國近年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有了做起講之意,卻是并不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這運動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來嚷嚷,別的各方面沒有什么動靜,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狀態”。[10](《苦口甘口》,P.20)話雖如此,周作人畢竟也還屬于這“出來嚷嚷”的文人之一,“別的各方面”,因為他不是親身參與者,有了動靜他也不一定知道,或者秉持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以及“文人不談武”之類的原則,知道了也不一定多談。事實上,如果我們查考史書,就可以知道文藝、學術、科技等各方面在那個年代都不是空白的,而是有人篳路藍縷歷盡艱辛地開拓,即以自然科學為例,據說“從1916年起,在中國開始了以發展某種科學為目的的專門研究組織的建立,其中重要的有:中央地質研究所(1916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0年)……”也有竺可楨這樣比較重要的科學家,產生過一些世界領先的科學成果。[13]周作人何以對這些罔若無睹,視科學處于“偏枯”呢?從他的許多文章來看,他批評的還是民眾生活、思想領域中沒有科學精神,他著力強調的最終也只是一些指導普通人生活和思想的科學“常識”,強調這些常識最終指向的又是建立合理的倫理觀念。對于真正的自然科學研究的深入,是不在他的考慮范圍的。
有三個問題,周作人在好些文章中反復談到:螟蛉之子,腐草為螢,梟鴟食母。從1933年寫的《蠕范》開始,到1934年《廠甸》、1935年《貓頭鷹》、1936年《毛氏說詩》《螟蛉與螢火》、1944年《螢火》等等,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周作人反復不停地引用同樣的材料,反復指出歷史上許多儒生篤信不疑的“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不是實情,螢火蟲也不是腐草化的,貓頭鷹并不吃母親。之所以為這些事情花了這么大的力氣,首先是因為他從中看到了中國思想傳統中的一大弊病,那就是不求甚解,缺乏求真知的精神。他說,中國人如此“觀察不清則實驗也等于幻想”,“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學在中國之不發達蓋自有其所以然也”。[10](《苦茶隨筆》,P.52)在周作人看來,這種“格物往往等于談玄”的現象在中國學者中是普遍的,《毛氏說詩》一文中,他認為貴為一代宗師的朱熹,其《詩經集傳》格物不精、錯訛百出,被毛西河笑罵也是無怪。中國古代讀書人這些不求甚解,以訛傳訛,以耳為目,篤信前人的做法,其背后是頭腦的糊涂與混亂,這是周作人所極力批評的。在其他領域里周作人也常為此而嘆惜,例如《修辭學序》中說“文人學士多缺乏分析的頭腦,所以中國沒有文法,也沒有名學,沒有修辭學,也沒有文學批評”,[10](《看云集》,P.85)《文法之趣味》中則鼓勵人從文法書中訓練頭腦之清晰,理解之明敏。
除此之外,周作人反復地講這三個問題,還想引出另一個意見,即是在生物學及相關科學上建立起正確的倫理觀,這是一條明顯的經科學——理性到達精神——人文的路徑。《螟蛉與螢火》中他指出中國人拙于觀察自然,又往往喜歡去把它和人事連接起來,造成錯誤的倫理觀,例如烏鴉反哺、羔羊跪乳等,助長子女必須償還父母債務的錯誤的孝道觀。要救治這一點,只能求助于正確的生物學知識。周作人是個極端的生物學“粉絲”。他把中國人的許多思想問題都歸結到生物學的原因上去,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他在早年的《羅素與國粹》中說,中國人保守,沉迷國粹,都是“因為懶,因為怕用心思,怕改變生活”,[10](《談虎集》,P.13)20世紀30年代寫的《論泄氣》進一步說:“中國人許多缺點的原因都是病。如懶惰,浮囂,狡猾,虛偽,投機,喜刺激麻醉,不負責任,都是因為虛弱之故,沒有力氣,神經衰弱,為善為惡均力不從心。”[10](《夜讀抄》,P.190)這種扎根于生物學的思維方式使得他極力推崇生物學知識,談到人的生活倫理時必定用生物學比附,極力推崇與生物學相關的書籍。《蠕范》中說“讀一本《昆蟲記》,勝過一堆圣經賢傳遠矣,我之稱贊生物學為最有益的青年必讀書蓋以此也”,[10](《夜讀抄》,P.40)《百廿蟲吟》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這些文章都明確指出他的生物學興趣,并不完全出于純粹的研究興趣,而都是指向人的生活倫理,也即是為他后來總結的“倫理之自然化”服務的。
一方面鼓吹科學精神,希望人們格物真切,頭腦清晰,另一方面又用強烈的意愿把科學直接聯系到人事上去,這倒是完全符合英國的科技史家李約瑟所分析的儒家的特點。周作人自命儒家,看來的確不是虛言。李約瑟認為,儒家中有兩個根本矛盾的傾向:它的重理性,反對一切迷信,甚至反對宗教中的超自然部分,這是有利于科學發展的;但是集中注意于人與社會,而忽略其他方面,只對“事”研究而放棄一切對物的研究,又造成了科學發展的阻力。[14]周作人這種過于注重科學與人事的聯系,急于從科學過渡到倫理的思想,是否也會阻礙他對科學的深入認識呢?答案是顯然的。在《我的雜學》中,周作人坦承“關于生物學我完全只是亂翻書的程度,說得好一點也就是涉獵,據自己估價不過是受普通教育過的學生應有的知識,此外加上多少從雜覽來的零碎資料而已”。[10](《苦口甘口》,P.72)盡管不斷鼓吹科學,認為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在儒家思想之上再增加些科學精神,但是他并沒有真正成為任何一門學問里研究精深的專家,而是滿足于提倡“常識”。他認為只要持之以恒講述常識,也會對中國有益處,“我們如依據了這種知識,實心實意地做切切實實的文章……這樣弄下去三年五年十年,必有一點成績可言。說這未必能救國,或者也是的,但是這比較用了三年五年的光陰再去背誦許多新鮮古怪的抽象名詞總當好一點,至少我想也不至于會更壞一點吧”。[10](《苦竹雜記》,P.200)
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反復推重的中國思想史上的三盞明燈,他認為有著“疾虛妄”的科學精神的三個人——王充、李贄、俞正燮,在他筆下,實際上都并沒有顯現出多少科學精神。除了在《凡人的信仰》中寫到王充的無神論思想是偏重從科學精神方面立論之外,在《讀初潭集》《關于俞理初》《俞理初的著書》中,他反復稱揚李、俞二人“為婦人開脫”、“平等的兩性觀”,實際上還是偏重于倫理方面。對李贄的“童心說”、“六經皆史”說,對俞正燮的古籍訂偽考異的卓然成績、鄰邦邊境的深入研究,[15]他都沒有提及。在《俞理初的著書》中說:“俞理初可以算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常人了,不客氣的駁正俗說,而又多以詼諧的態度出之,這最使我佩服”,其駁正俗說之處,即“能尊重人權,對于兩性問題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論”。[10](《秉燭后談》,P.32)原本只是悃愊無華的學者俞正燮,被他推崇到中國思想史三燈之一,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不僅僅生物學,其他相關的醫學、性心理學以及人類學,周作人并沒有把它們當作研究室或書齋里的純粹科學知識來處理,它們都是作為周作人的“雜學”、常識之一部分,為著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的生活”服務的。這阻礙了周作人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可是這種取向卻深得人文理性的精髓,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正如海德格爾揭示的那樣,自近代以來有一個地球和人完全歐洲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實質就是歐洲近代以來的科學理性占據了支配性的地位,然而作為其成果的技術進步,卻損害了一切本質性東西的源泉。[16]周作人早在中國處于西學東漸的風潮之初,就敏銳地從“情理分殊”的立場出發,看到了科學理性不能侵害人文藝術的領地,在戰火動亂的年代里又堅持著革命激情不能妨害用理性清醒的頭腦去認識社會、認識人生,并進而倡導科學為人生所用、人生以科學為理據的道路,始終牢牢把握著以人為本、建設美好的人間生活的主線,體現了一個卓越的啟蒙思想家的本色。這對于今天各種“打通任、督二脈”之類的社會亂象,仍然不失匡正之力。
[1]丹皮爾.科學史[M].李珩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2]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J].新青年,1920,7(5).
[3]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M].黃山:黃山書社,2008.
[4]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M].北京:中華書局,2009.217.
[5]王岳川.呼喚“人文理性”的跨世紀詩學[J].詩探索,1996,(4).
[6]鄧周平.論人文理性[J].社會科學,2003,(9).
[7]朱德發.現代文學創造:人文理性精神與主體人本藝術思維[J].山東社會科學,2003,(4).
[8]嚴復.嚴復集:第2冊[M].三聯書店,1984.279.
[9]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0]周作人.周作人自編文集[M].止庵校訂.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郜元寶.魯迅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5-21.
[12]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60.
[13]陳廷湘.中國現代史[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563.
[14]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6.
[15]俞正燮.俞正燮全集[M].黃山:黃山書社,2005.13,16.
[16]海德格爾.林中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263.
HumanRationality:TheEssenceof“Scientific”WhichZhouZuorenAdvocated
HUANG Jiang-su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Zhou Zuoren kept alienated from and vigilant against “scienc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them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because at that time he focused on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 unique valu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to human spirit. In the late 1920s, after his change of mind and the controvers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science” became the theme of his most important articles. He traced back to the source of “science”, the original Confucian “disease falseness” and classical Greek spirit of “love of wisdom” which, in fact, is the position of human rationality. The claim that the ethics of human life must be based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must be in line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life on earth emphasizes the spirit of “common sense” scienc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ost in today’s mysterious social chaos remed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the loss of scientific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get rid of today’s mysterious social chaos.
Zhou Zuoren; science; human rationality
2012-06-19
黃江蘇(1983-),男,湖南永州人,文學博士,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I206.6
A
1674-2338(2013)04-0057-06
(責任編輯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