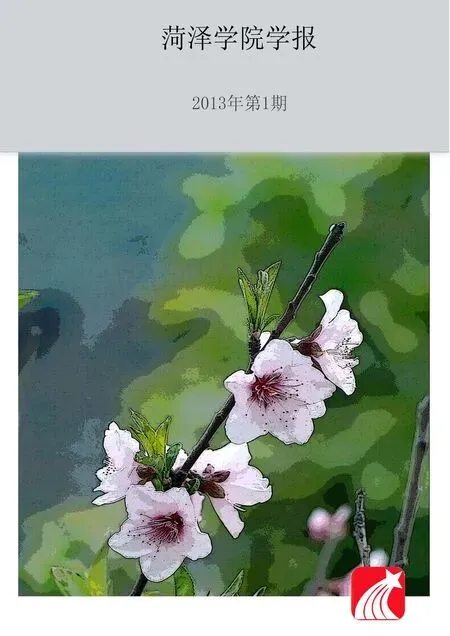接受美學視野下新版電視劇《水滸傳》的主題闡釋*
高日暉,李 欣
(大連大學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接受美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研究范式,把文學研究轉到接受者、讀者這一級,認為接受不是被動的反映,而是作品意義的積極建構。文學本文只有被閱讀、被接受才實現了意義的最后一環,才能稱之為作品。接受美學視野下任何文學本文都具有未定性特征,存在著許多“空白”和“未定點”,這種“未言部分”就對不同時期的接受者提供了一個“召喚結構”,需要接受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進行創造性“填空”。當然不同時代接受者的闡釋、接受又受到特定時代意識形態、文化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所以才形成了文學作品意義闡釋的多元化局面。《水滸傳》寫成于明代中葉,從它產生之日起便擁有了大量讀者,上至皇帝公卿,下至販夫走卒都不乏“水滸謎”。明代批評家把它列入“四大奇書”中的一種。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水滸傳》真可謂是空谷足音,它的出現給讀者打開了一個嶄新的閱讀世界。歷來的研究者在解讀這一文學巨著的過程中,由于所處時代文化環境的不同,形成了《水滸傳》主題接受的多元化局面。
一、《水滸傳》主題接受的歷史回顧
歷史上的明代中后期是一個思想解放、個性覺醒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起來的《水滸傳》受到了以李贄、袁宏道等當時名士為代表的讀者的高度評價,說它表現了梁山好漢“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1],把梁山英雄視為實現正義公平的社會良心,既肯定《水滸傳》的忠義思想,又高度評價了它的藝術成就。托名李卓吾《〈忠義水滸傳〉敘》也明確地指出《水滸傳》是宋代遺民施耐庵、羅貫中的“發憤之作”,其表現了“水滸忠義”的主題,認為他們借寫草莽英雄忠義參天的故事來發泄心中對于元代異族入侵統治的不滿。
一部《水滸傳》,有人稱贊它是“忠義”的教本,有人卻痛斥它是“誨盜”的淵藪。明清時關于《水滸傳》主題已然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忠義”說和“誨盜”說。清代是滿人入關建立的封建政權,為了加強專制統治,統治者實行嚴密的文化控制。面對《水滸傳》以及水滸戲的廣泛傳播和秘密結社、盜匪、農民起義的此起彼伏,此時主流社會輿論對《水滸傳》多持否定態度,認為它是“誨淫誨盜”之作,為不逞之徒立傳,視《水滸傳》為最敗壞人心的作品。例如,清代乾隆、嘉慶、咸豐三朝都曾明令禁止銷售、刊刻《水滸傳》以及水滸戲,俞萬春更是特作《蕩寇志》來消弭《水滸傳》的不良影響。
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許多研究者借《水滸傳》來比附當時的社會斗爭,故有“倡民主、民權”的“政治小說”提法。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認為《水滸傳》梁山旗上書“替天行道”,堂上書“忠義堂”,是“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施耐庵“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沉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2]。黃人在《小說小話》中指出《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對于有人借《水滸傳》喻“實行憲政”或“當代革命”,魯迅加以嘲諷道:“說《水滸傳》里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徑的假李逵。”[3]
新中國建立之后,研究者側重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文學研究工作,故“農民起義說”應運而生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宋史》中記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4]“農民起義說”從反映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水滸傳》反映了農民革命起義的歷史,是農民起義的教科書。“文革”時期,《水滸傳》又被認為是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關于《水滸傳》主題與思想內容的接受、闡釋往往與接受者所處時代的思想政治傾向、文化政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國人對《水滸傳》的態度,一直以來被看作是社會思潮的風向標。
新時期以來,伴隨思想解放風潮,學術界的面貌煥然一新,學術氛圍空前活躍。隨著西方新的文學理論的引進與接受,不少學者不再固執于一種說法,而是在肯定“主題多義”的前提下,全方位、多角度地對《水滸傳》進行闡釋,產生了許多新穎的觀點,例如:“為市民寫心說”、“忠奸斗爭說”、“倫理反省說”、“諷諫說”、“復仇說”、“明、暗主題說”、“游民說”、“多元融合說”、“泛農民趣味頌歌說”……,真可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二、新版電視劇《水滸傳》對小說主題的闡釋
小說《水滸傳》的內容結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逼上梁山和離別梁山,貫穿整部作品的價值取向是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宣揚的是如霆如電、如雷如火、血性陽剛的藝術精神。2011年版新《水滸傳》在接受歷來《水滸傳》主題研究中的“忠義說”、“忠奸斗爭說”的基礎上,結合當下的社會文化突出了“除暴安良”、“兄弟情義”、“護國安民”的主題。其中尤以“兄弟情義”、“護國安民”在景岡山演唱的新《水滸傳》片頭曲《兄弟無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兄弟投緣四海情兄弟交心五車話兄弟護國三軍壯兄弟安民萬世夸兄弟生離兩行淚兄弟死別一枝花。兄弟情夜空中萬千星點 兄弟情紅塵里無限光華。”
(一)電視劇“除暴安良”主題對小說俠義思想的接受
幾百年來,《水滸傳》一直為世人所喜愛,并奉為經典,究其原因之一,即小說通過描寫英雄的事跡、活動,酣暢淋漓地展現了水滸英雄除暴安良、嫉惡如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文化精神,感人至深。電視劇新《水滸傳》在接受小說俠義文化精神的前提下,運用現代影視技術,通過大量劇集、橋段來濃墨重彩地表現水滸英雄除暴安良、行俠仗義的俠義之舉。
魯智深無疑是除暴安良的典型,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人須救徹”(見百回本第九回)的精神令人敬仰,所以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將他推崇為“人中絕頂”、“上上人物”。新版《水滸傳》用大量劇集展現魯智深除暴安良的俠義行為。第四集即為“魯智深義助金翠蓮”,他在聽完金翠蓮、金老兒的悲慘經歷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將鎮關西的惡行告知小種經略相公,這不得不說是新版的一個全新演繹。新版《水滸傳》通過魯智深摔碎經略府中題為“松蔭堂”的牌匾展現其對官府的失望與徹底決裂。魯達送素不相識的金翠蓮父女五十兩銀子讓他們逃離渭州,并三拳兩腳打死了欺軟怕硬的惡霸鎮關西,是典型的仗義疏財、扶危濟困、除暴安良的俠義行為。新版《水滸傳》中魯智深在劉太公莊上痛打桃花山前來強搶民女的小霸王周通;瓦罐寺中與史進聯手殺死霸占民女,欺壓眾僧的惡人飛天道人丘小乙、黑和尚崔道成;大鬧野豬林解救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豹子頭林沖。魯智深這種路見不平仗義出手,救人于為難之中的行為,正是所謂的“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見百回本第三回)。令人讀之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魯智深無意為俠客,但是他的古道熱腸卻使他從一個草莽英雄向俠客華麗轉型。
小說《水滸傳》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蔣門神之后說:“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見百回本第三十回)歷來研究者認為,雖然武松自詡為“俠客”,但是他身上表現的更多是“義”的因素,他的所作所為無非是報答施恩對他的信任與賞識。電視劇新版《水滸傳》為了給廣大電視觀眾展現武松的除暴安良、行俠仗義,特意在血濺鴛鴦樓之后加上幾個百姓對于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的痛斥,“該殺、該殺”。由此可以作為一個縮影來窺探蔣門神、張團練等惡霸平日里對于普通百姓的欺壓魚肉,武松血濺鴛鴦樓相當于為民除害,這也就更貼近了新版《水滸傳》英雄除暴安良的主題定位。
新版《水滸傳》中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雄,七星聚義劫取不義之財生辰綱不是為了一生富貴,而是取不義之財,散之于民。新版更是通過劉唐之口交代了生辰綱的用處,原來晁蓋變賣生辰綱為東溪、西溪、石碣村三個鄉繳納租子,這不得不說是除暴安良主題另外一種形式的解讀。
(二)電視劇“兄弟情義”主題對小說“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接受
小說《水滸傳》中英雄之間的結義行為俯拾即是,通過結義的形式,異姓陌路人變為兄弟甚至比親兄弟更加親密。例如,武松與宋江、張青結為兄弟,林沖與魯智深結義為兄弟,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后,眾好漢“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見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一回)對天盟誓是總的結義。來自八方異姓的英雄豪杰嘯聚梁山,靠的就是“義”這個紐帶的聯絡,“義”是梁山英雄聚義的精神旗幟。正是在“義”字大旗的感召下,各路英雄好漢如百川歸海,齊聚梁山,成為與朝廷相對立的理想化的江湖世界。電視劇新《水滸傳》在將文學語言轉換為影視語言的闡釋過程中主要接受了原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提法(見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七十回英雄排座次情節),重點突出了兄弟“情義”這一主題,更多地演繹為“手足之情”。
新版電視劇《水滸傳》武松與宋江重逢在孔太公莊上,晚上在一處歇臥,回想初次相逢柴進莊上似乎是昨日之事,一見如故,情深似海,義結金蘭,宋江還勸告武松,憑著他的拳腳,日后到邊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可如今,二人都是臉刺金印的囚徒,所有的豪俠壯志都化為南柯一夢,可悲可嘆。只怕自從你走后,鐵獅子一哭會生銹。牽掛月月又年年,無眠半宿又一宿。新版《水滸傳》為表現魯智深與林沖之間的兄弟情義情深似海,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了嶄新的情節設計。新版《水滸傳》中,魯智深與林沖本為同門師兄弟,初次相逢即以武會友,義氣相投,結為兄弟。林教頭刺配滄州道,囑咐智深代為照顧林娘子,可就是因為魯智深的一次酒后誤事,導致林娘子葬身火海,一向嗜酒如命的魯智深發誓從此之后再不飲酒,并且自縛其身向林沖負荊請罪。魯智深六和寺坐化,林沖拎一壇清酒來墳前拜祭,此時畫面中運用視覺蒙太奇法閃回魯智深曾經的音容笑貌,江山非畫美如畫,豪杰壯士影疊疊,斯人已逝,徒留林沖無限感傷與思念。
新版《水滸傳》中梁山排座次及五臺山盟愿所言都是“只愿眾兄弟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斷阻”;宋江軍攻克杭州城時,擺設靈堂御酒灑地來祭奠陣亡將士;李逵為兄弟情義自己喝下毒酒,“生時服侍哥哥,去那邊也為哥哥做個先鋒”。
(三)電視劇“護國安民”主題對招安的新闡釋
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并序》,宋江起義不假稱王,而呼保義,并沒有贈予宋江忠義的桂冠。后來宋江故事在“說話”中不脛而走,“復經好事者掇拾粉飾,而文籍以出”[5],并且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被賦予“忠義”思想。《水滸傳》的雛形《大宋宣和遺事》中,廣行忠義、殄滅奸邪構成了這部話本的主旨。在民族矛盾激烈的元代,水滸英雄又成為見義勇為、為民除害的草澤義士,高舉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大旗。從“不假稱王”、“廣行忠義”到“替天行道”,“忠義”思想始終是制約水滸故事發展的軌跡,所以《水滸傳》作為一部文人在集體創作的基礎上完成的作品,不可能超越這個故事流傳過程中形成的“忠義”思想格局。《水滸傳》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描寫了受招安的內容,譜寫了一曲亂世忠義的悲歌。新版電視劇《水滸傳》在接受這種“忠義”水滸思想的基礎上,將其演繹為“護國安民”主題。新版《水滸傳》中的招安情節,不再是小說中眾英雄因“封妻蔭子”的目的而為,而是為了建功立業,還百姓清明大宋。
電視劇中,宋江率梁山軍馬攻打青州,一路對村民秋毫無犯,反觀青州太守屠村,下毒栽贓的行為真可謂是坦蕩磊落了,并且勸解呼延灼“忠義”并不是愚忠,殺慕容知府,待罪之身也要行替天行道、護國安民之事。新版《水滸傳》中楊志對吳用、晁蓋等劫取由他負責押運的生辰綱之事始終耿耿于懷,并借機非難吳用什么是忠,什么是義,吳用對曰:“對上無二心,對友無二心,梁山泊好漢都是忠義之士。”林沖滿以為被派去大名府做制使,可以征戰沙場,為國盡忠,沒想到是押解不義之財生辰綱,所以毅然請辭。燕青辭別李師師,出征方臘也正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宋江請求早日出征,徽宗以毒酒試其忠義,宋江道:“其本為卑微小吏,誤犯典刑,流配江州,酒后狂言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今蒙圣上寬恤收典赦免本罪,微臣披肝瀝膽尚不能報圣上之恩,我主陛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縱是毒酒,宋江感恩于心。”忠義之心可昭日月。吳用在蓼兒洼宋江墳前告訴花榮,他與公孫勝早就預測招安后難免兔死狗烹的下場,但是即便是這樣也要助宋江招安成功,其九死亦尤未悔。
三、當代價值觀與電視劇《水滸傳》的主題接受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經濟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大量涌入,其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重集體主義、愛國主義、輕個人利益的精神產生了劇烈碰撞。加之,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經濟、文化乃至人們的生活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變革,激發了人們新舊價值觀念、信仰的急劇沖突,人們更加注重個性、自由的發展,形成了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格局。正是在這種土壤之下,注重人性、人情、全民參與、平等性、娛樂性的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為普通大眾所喜愛,并且迅速崛起。影視藝術作為一種大眾文化,以其視聽結合的直觀特色,信息傳播的快速便捷,擁有了廣泛的受眾。在這個注重品牌和知名度的消費時代,一部古典名著無疑是一個著名的文化品牌,更能為廣大電視觀眾所接受,所以《水滸傳》也搭上了名著改編的末班車,新版以當下文化視野對小說進行了全新審視,展現了名著新的時代內涵。
新版《水滸傳》電視劇在接受小說俠義思想的基礎上,著力表現水滸英雄除暴安良的主題,對于原著中英雄的過度殺戮行為進行了糾正。編劇溫豪杰表示,梁山好漢必須是正直的,小說中的過度殺戮行為是少兒不宜的。新版《水滸傳》中還通過店小二之口大加贊揚魯智深的俠義精神:“我家提轄是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歹便打,這渭州大至六街三市,小到路邊小小茶坊,人人敬佩我家提轄,我家提轄可是好漢。”在當下人的意識中,人人生而平等,不容許欺壓弱小這等封建糟粕行為存在,水滸英雄當然被塑造成正義的化身,行俠仗義除暴安良,并且水滸英雄形象必然是正面的、積極的。所以新版中,觀眾看不到李逵排頭砍看客,水滸英雄拿壞人的心肝做醒酒湯這種鏡頭,就連母夜叉孫二娘賣的人肉包子也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在消費文化盛行的今天,人們日益被物質所包圍,激烈的社會競爭環境,漸漸導致人們情感交流的荒漠化,在代償心理的作用下,人們更希望在影視劇中獲得情感、人情的審美需要。新版《水滸傳》接受小說“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提法,將兄弟情義演繹得感人至深。兄弟非親心更親,情義蘭舟通彼岸,四海兄弟赴盟約。這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新《水滸傳》中為什么具有美化女性的傾向。新版的這種定位,賺足了廣大電視觀眾的眼淚,在名著翻版浪潮中贏得了不俗的收視。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新版《水滸傳》中的梁山英雄俱是忠義之士,身雖百死而無怨,俱懷忠義笑問天。“護國安民”主題體現了我國民族傳統文化中對于善的追求,對于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價值取向的肯定,同時也契合了當下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
[1]天都外臣.《水滸》評論資料[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94.
[2]馬蹄疾.《水滸》資料匯編[G].北京:中華書局,1980:425.
[3]魯迅.魯迅全集:集外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201-202.
[4]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11114.
[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中華書局,2010:85.
[6]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金元浦,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31.
[7]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06:38-42.
[8]王鴻卿.《水滸》主題新論[J].明清小說研究,2005,(2).
[9]宋克夫.亂世忠義的悲歌——論《水滸傳》的主題及思維方式[J].湖北大學學報,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