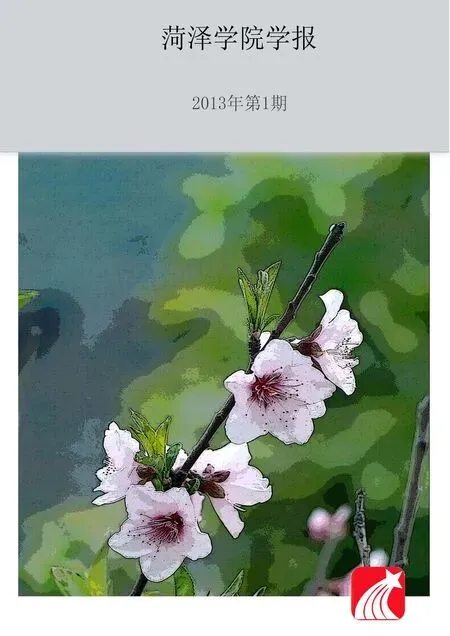難以忽視的文學史基點
——論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的異質性及文學史意義*
曹金合
(菏澤學院中文系,山東 菏澤 274015)
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摒棄單純的從黨派和政治等宏大的主流話語的角度來考察闡釋文學現象、文學思潮、作家作品、流派分析等比較僵化陳腐的原則的同時,遵循著人文知識分子不為外在的環境高壓和內在的世俗欲望的誘惑所左右的理性批判精神,以主體性、人文意識和人道主義精神去挖掘被歷史陰影所遮蔽的文學史上具有航標意義和基點性質的文學現象,從宏觀的思潮梳理到微觀的作品個案分析,本著“話語講述年代”的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的感悟性還原展示“講述話語的年代”的轟動效應,張揚的《第二次握手》作為潛流文學的手抄本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已浮出了歷史的地表。
《第二次握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與小說產生的歷史現場、書寫形式、創作方式、傳播媒介、讀者參與等異質因素在惡劣條件下的悖反互動有密切的關系。作為張揚在特定語境下的成名作有一個非常坎坷曲折的醞釀期和成熟期,它是張揚的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相互融合形成的文學情結以及生命信仰中的永恒質素締結產生的藝術寧馨兒。1963年的春天連續兩次高考都名落孫山的他,偶然聽姨媽和母親說起一段當年外公干涉舅舅純潔無暇心心相印的美好戀情的軼事,這喚醒了張揚潛抑和沉睡已久的文學創作沖動,感性與知性、形象與抽象、沖動與理性、內因與外因等各種異質因素在知識分子題材和愛情情節的酵母醞釀下,已經不可抑制地將空靈虛飄的靈感火花化為了具體實感的小說文本,這就是張揚到北京的舅舅家考察體驗后寫成的短篇小說《浪花》。1964年又改成中篇《香山葉正紅》,1967年到瀏陽縣大圍山區當知青的他,在閑暇之余又將《香山葉正紅》寫成了10萬字的長篇小說。1969年因發表攻擊“文革”和林彪副統帥的言論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張揚,逃亡期間再次將《香山葉正紅》第四稿改寫并將小說的名字改為《歸來》,1972年12月底因林彪叛逃墜機身亡而加在張揚身上的反革命罪名不復成立,所以獲釋出獄。此時的長篇小說《歸來》正以手抄本、改編本、油印本和口頭傳播等各種媒介方式和傳抄中以訛傳訛的五花八門的書名迅速地擴散開來,經過牢獄之災的張揚深知“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的目的與效果背反式的發展悖論和補償性的社會發展歷程,在是非顛倒陰陽混淆的文革時代對剝奪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來說,只能做一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旁觀者。但張揚的烈士遺孤的血性氣質、是非分明的正義感、肩挑重擔的責任感和敢于斗爭的錚錚傲骨又使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于1974年在大圍山又寫下了20萬字的第五稿,仍題名為《歸來》。1974年10月,《北京日報》內參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傳抄中受到廣大讀者熱情歡迎和高度贊揚的現狀而引起姚文元的高度警覺,于是以“利用小說反黨”的莫須有的罪名將張揚判為死刑,直到1979年1月18日,經多方奔走呼告才得以平反出獄。后來,他感慨地說:“這本書的初稿寫成于1963年春,然后又分別寫過三次。之所以要重寫,是因為幾乎每一稿寫成后就流傳出去無法收回,當時取名《歸來》。大約1974年被北京某廠工人改題為《第二次握手》,從首都向四面八方傳播,終于造成‘四人幫’謂之曰‘流毒全國’的‘嚴重惡果’。”[1]為了尊重在四人幫的淫威下冒著被摧殘遭迫害的文字獄而勇敢地傳抄和閱讀的廣大讀者的閱讀期待心理,張揚正式將書名《歸來》改為《第二次握手》,并于1979年7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三個月內發行量突破300萬冊,漢文本總發行量達到430萬冊,成為新中國建立以來當代長篇小說發行量僅次于《紅巖》的暢銷書。
當然,從短篇小說《浪花》到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歷時態的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地下手抄本的未定型到公開出版的定型性文本,傳播流通媒介機制的不同必然會造成不同版本的傳播問題。文革時期潛在寫作狀態下由手抄本的特殊形式形成的寫作和傳播流通范式,宿命地限定了《第二次握手》作為傳抄文本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特別是讀者積極參與文本的主觀化的建構方式對小說由短篇、中篇到長篇的文體嬗變歷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也帶來了不同的版本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文本生成、情節安排、審美機制、美學生態等方面的問題。但文學生產與流通過程的易變性、復雜性以及研究文本在特定歷史境遇中的定型性之間的矛盾張力,都形成了文學史中饒有興趣的話題。文學史的多元性、開放型的價值評價系統與本體性、內斂型的核心理念之間的悖反張力形成的入史的選擇和評價標準,實際上包含著文學史編纂主體與研究客體之間非常豐富復雜的審美和史觀意蘊。因為“文學史選擇作品的依據就是文學史觀及其與之相聯系的價值標準,即有什么樣的文學史觀及其價值標準就選擇什么樣的文學作品,被選中的文學作品就是文學史觀的實證根據和感性表征,其中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文本的話語蘊藉則是文學史觀最深層原創意義的淵源,也是最能顯示文學史獨特深度的象征喻體。”[2](P89)由此觀之,《第二次握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價值的節節攀升也意味著特定歷史語境下的題材和審美上的異質性,越來越得到文學史家在求同存異的前提下形成的共識和認可。
一、特定歷史語境下的題材和審美的異質性
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在尊重知識分子的人格和正視愛情的主體價值等人性人情話語的正常語境中,主題內容、思想蘊含、審美追求和藝術風格等方面的文本表現,由于與讀者的閱讀期待視野相契合而顯得稀松平常。但如果放到文本生成的特定的紅色年代的歷史現場和時代語境中進行對比、理解、分析、闡釋,那么文本在題材和審美方面與極左意識形態在價值判斷及審美意識之間的捍格產生的格格不入的異質性是顯而易見的,從當時張揚被捕所羅列的罪名也可窺一斑而見全豹:“利用小說歌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后臺周恩來總理,竭力吹捧資產階級臭老九知識分子,以科學技術重要宣揚反動學術權威,贊美腐朽黃色的資產階級愛情,為反動家庭樹碑立傳,實屬罪大惡極。”[3]由此可見,從人道主義的視角以真善美作為價值評判標準倒也從羅列罪名的內容中歪打正著地顯示出文本題材的異質性。這首先表現在知識分子題材的異質性上,知識分子由啟蒙的先生到被改造的學生的角色轉換在文革歷史語境中的極端化發展,就造成了知識分子在文本中由受人贊美和歌頌的主角到備受嘲諷和貶斥的配角的形象轉換,《第二次握手》讓科學家在文學的舞臺上占據中心地位并對其進行贊美,蘇冠蘭在藥物學以及葉玉菡在病毒學等學術方面的突出貢獻,特別是丁潔瓊在美國科學大會上敢于質疑并用無可辯駁的縝密的邏輯論證推翻了頂尖級權威席里提出的“席里結構”,以雄辯的“丁式結構”在美國科學界引起巨大的轟動,這在專業上為國爭光、為民族添彩的科學貢獻,確實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處于被動挨打的落后狀態下的中國人的壓抑、焦灼心理提供了得以舒緩釋放的途徑,顯示了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和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從蘇冠蘭暴風雨中冒著生命危險搭救溺水少女和火車上勇斗歹徒的見義勇為的細節打破了知識分子唯唯諾諾的卑瑣形象,葉玉菡幫助共產黨魯寧安全脫險時的臨危不懼的正義精神、為保護蘇冠蘭而讓特務的罪惡子彈射進自己的肉體的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為了科學事業將自己的青春年華無私奉獻的敬業精神,種種美好情愫和人格意識的百川匯集確實為一位普通樸實的女科技工作者唱了一曲贊歌,而丁潔瓊牢記恩師凌云竹的教誨學成回國報答祖國的養育之恩的愛國精神、在科學的崎嶇道路上勇于攀登的鉆研精神、感情上始終不渝的忠貞精神表現的高尚人格可與白璧無瑕的美玉相媲美。此外像老科學家凌云竹的追求正義及真理的責任感和愛國心,音樂家宋素波超越血緣倫理關系的博大的母愛,周總理對知識分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所有這些異質因素在“讀書無用論”、“知識分子是臭老九”、“交白卷上大學”等“紅”以絕對權威的政治話語壓倒“專”的人性話語的等級語境中,自然是無形中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極左價值進行了顛覆與消解。正因為如此,這部小說才被認為是“建國以來第一部正面描繪知識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繪周總理光輝形象的文學作品”。
其次表現在愛情題材的異質性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和片面化的理解導致了文學把表現人性人情的愛情母題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文學,在文革極端禁欲化的年代,革命的宏大話語對人性人情話語、公共話語對私人話語的壓抑和遮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存天理滅人欲”的最陳腐的封建道德觀念披著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演化并改造為換湯不換藥的“存教條滅人欲”的合法形態。因此,《第二次握手》在“談愛色變”的極左意識形態的語境下對愛情禁區的突破無疑具有題材上的重要意義。小說無論是手抄本還是出版本,無論是最初本還是定型本,對有情人難成眷屬的刻骨銘心的愛情痛苦的描寫都成為最打動讀者的永恒旋律和動人的母題。張揚也是按照愛情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動人旋律來謀篇布局表現主題的,在《第二次握手》扉頁上引述的恩格斯的語錄“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強烈的和最個人的——乃是愛情的痛苦”,首先向讀者先入為主的心理結構提供了這是一部愛情小說的媒介信息。而且在時過境遷的二十年后,作者又再次剖露心跡:“這部手稿寫的就是愛情的痛苦和痛苦的愛情”。小說描繪了三組三角戀情:其中以蘇冠蘭、葉玉菡、丁潔瓊之間的三角戀情為貫穿和表現作者愛情、婚姻觀念的核心情節,統帥起葉玉菡與蘇冠蘭、朱爾同以及丁潔瓊與蘇冠蘭、奧姆霍斯之間的精神之戀,核心與陪襯、關鍵與次要情節之間的相得益彰共同詮釋了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的神話母題。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生命旅程決定了一個健全的人格離不開靈肉的兩重因子的統治與組成,單純追求純肉欲的形而下的欲望本能與執著追求純精神的形而上的柏拉圖之戀都是對具有靈肉二重性的健全人性的割裂,真正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在性與愛相互融合的激情蕩漾中感受到的高峰體驗顯現出來的,以此標準來衡量,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感受和婚姻觀念是有缺陷之處的。比如丁潔瓊在異國他鄉身陷囹圄與蘇冠蘭音信斷絕的艱難歲月里,面對著魁梧健壯、英俊瀟灑、博學多識、忠貞善良、癡情專一的導師兼同事奧姆霍斯對她的苦戀竟冷若冰霜,在最需要男友的情感蘊藉和支持幫助時竟將一顆赤誠火熱的愛心拒之門外,用她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人愛情只有一次,只能有一次,也只應該有一次。”這種生死不渝的愛情所表現的愛情的堅貞很顯然是將三十一年前分別時的第一次握手當做了排遣內心孤獨的情感符碼和精神象征,她在給冠蘭弟的信中寫道:“愛情的結果并不一定是生活上的結合,它也可以是心靈的結合,是精神的一致,是感情的升華。即使我們將來不能共同生活,你也將永遠鐫刻在我的心靈上。”因此她的言語行動和情感表達都非常清楚地表現了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同樣的愛情價值觀也表現在男主人公蘇冠蘭身上,他也認為“真正的愛情一定能成功,但并不一定能結婚——‘成功’不等于‘結婚’。人具有感情,動物具有本能,這是本質的區別。真正的愛情具有深刻、崇高、雋永的精神感染力,這正是人類感情的偉大之處。”這當然是張揚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的中間物意識,經過感性化的媒介載體的審美轉化后的情感投射,是關注個體的生命存在的人道主義的大旗尚未在文學舞臺的上空獵獵飄揚的時代環境中,運用“他者”的審美眼光和價值標準對女性的愛情心理越俎代庖式的審美想象的結果。由此形成愛情描寫的兩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比較注重人物愛情心理的刻畫與描摹。除了葉玉菡明知冠蘭不愛她卻仍然一往情深地愛戀引起的情感的矛盾與困惑,丁潔瓊把冠蘭作為漫漫長夜里的情感寄托和愛情的最后歸宿地,以及苦戀三十一年后的希望被無情的現實撞得粉碎后,在內心掀起的滔天巨瀾之外,刻畫的最細膩、展示人物內在的情感矛盾最逼真的非蘇冠蘭莫屬,知識分子優柔寡斷、左右為難的夾板心理在具有同等價值的兩事物之間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造成的靈魂的分裂狀態,對這種心理意識的深度挖掘顯示了刻畫人物時設身處地與人物同歡喜共苦樂的人道情懷和悲憫意識。面對著救過自己的性命的終身伴侶葉玉菡對自己無微不至的關懷和體貼,內心深處難以忘記情投意合的瓊姐且無法把全部的感情轉移投射到自己現在的妻子身上,在理智上對情感意識的背叛行為發出嚴厲譴責,與此同時,當知道自己的戀人瓊姐為了忠貞不渝的愛情仍然信守諾言孑然一身時,自己的內心就像無形的鋼鋸在兩股相反的力量的作用下處于刀絞般的疼痛狀態,造成的法官和罪犯的雙重身份在心理上的相互駁難顯示出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刻畫人物的靈魂的深的藝術效果。二是背著傳統的因襲的重負在潛意識深處無意流露的“才子佳人”式的陳腐老套的愛情書寫模式。受傳統的審美文化底蘊熏染的張揚在創作中盡管受到現代的小說觀念的沖擊與影響,但先天形成的文化模式情結在無意識中作為文學創作的模糊底片和背景仍在左右著情節結構的布局安排。男女主人公蘇冠蘭和丁潔瓊都有令人艷羨的家庭背景:蘇父是譽滿全球的頂尖級的學術權威,丁父是留學歐洲的著名音樂家,符合才子佳人門當戶對的等級觀念模式,更為重要的是才貌雙全的男女主人公是一見鐘情、心心相印,更安排了黃浦江上不顧個人安危拯救美麗少女和火車奇遇孤身勇斗歹徒的故事情節,這顯然是“英雄救美”的傳統才子佳人模式的沿襲與翻版,父親蘇鳳麟出于圣賢的“信義”對于蘇丁愛情的干預和阻撓,顯然也借鑒了傳統的古典小說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權威話語對才子佳人的愛情話語的壓制和摧殘的情節功能,再加上特務查爾斯及其爪牙對愛情的挑撥離間、革命者魯寧運用辯證邏輯對蘇冠蘭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恩威勸說,安排了大量的有情人天各一方難以結合的曲折離奇的情節,最后,周總理親自到機場挽留執意離去的丁潔瓊,讓她為了祖國的科學事業和蘇冠蘭一起并肩戰斗,從而完成了事業和情感的雙重歸屬。由此可見,蘇丁之間一波三折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包含了“一見鐘情私定終身”、“小人離間愛情遭難”、“苦盡甘來喜慶團圓”的才子佳人的情節三部曲的固定模式。
最后,表現在審美風格的異質性上。文革公開出版的文學基本上遵循著極左政治意識形態所確立的政治與美學之間直接對等的創作原則和指示方針,文學創作的感性、直覺、迷狂等等神秘的非理性的思維方式的被驅逐導致了理性教條一統天下的公式化的樣板模式:“表象(事物的直接映像)——概念(思想)——表象(新創造的形象),也就是個別(眾多的)——一般——典型。”[4]這就形成了先有理論主題先行,后尋找材料進行填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美學風格。而張揚的《第二次握手》是從生活的實踐和體驗出發,融合著作家的生命感悟和審美追求的綜合美學因子締結而成的藝術寧馨兒,自然與主流意識形態認定的審美風格具有截然不同的異質性。這首先表現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打破了從觀念出發運用“三突出”、“三陪襯”、“多浪頭”、“多回旋”等文革文學必須遵從的三字經的審美風格的要求,將人物塑造成為某種觀念、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傳聲筒的教條模式,并對人物采取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人圣壇上脫冕化或者將漫畫般的牛鬼蛇神加冕化的方式將其還原為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中的人,無論是對蘇鳳麟絞盡腦汁百般阻撓其子愛情的反面行為的描寫,還是臨終前“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心理作用產生的對兒子的愧疚慈愛之情的刻畫,其心理性格和行為表現復雜性的樣態都超出了簡單的善惡價值判斷而成為圓形人物中的特定的“這一個”,即使是塑造的扁平人物丁潔瓊也使人感到就是生活在人們身邊的可親可敬的科學家,被她的高尚的人格、敬業的精神、愛情的忠貞所打動而并沒有突兀的感覺。第二是在審美結構上:中國和美國的空間維度、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時期的時間跨度,決定了小說要反映深廣的社會歷史原貌就必須采取大跨度、多線索的藝術結構。為此小說圍繞著蘇冠蘭、丁潔瓊和葉玉菡之間的愛情和婚姻生活設置枝蔓叢生的側線和副線,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鋪排渲染在主線的統攝下通過呼應性的細節安排,達到了綱舉目張繁而不亂的藝術效果。同時,在文本整體的倒敘結構中又采用插敘、回敘和順敘的方式以及傳統古典小說扣子的藝術技巧的靈活運用,使得長達三十多年的愛情故事呈現出搖曳多姿的美學形態,從而以“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藝術真傳和美學風格拉開了與主流文壇的審美距離。
二、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第二次握手》的主題意蘊所包含的愛國觀念、愛情專一、積極向上、無產階級信仰等教育認識功能與意識形態建構的合謀,奠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為“近百年來,文學史所承擔的教育責任,早已使它變成了意識形態建構的一部分,文學經典也是文化經典的一部分,文學經典的教育,直接導向一種文化價值觀念的成立,文學史常常給人的情感、道德、趣味、語言帶來巨大影響,甚至起到人格示范的作用。”[5](P161)特別是1990 年代以來,圍繞市場經濟的沖擊帶來的價值失落、精神混亂、信仰迷失、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形而上的問題,《第二次握手》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里形成的人之為人的價值操守無疑成為不信的時代里重塑信仰的燈塔。它的地位和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得到文學史的認可便是最好的明證。驗之文學史的書寫,90年代以前,受文學史視野的限制和文學史評判標準的影響而造成的文學史觀念的僵化自然把它摒棄在考察探究的對象之外。90年代以后,時間的積淀形成的史的一維的積極參與和相對寬松和諧的當代語境,使得文學史主體能夠以更加客觀超然的心態和眼光擇取鉛華洗盡本色方顯的經典作品充分地詮釋秉承的文學史觀。因此,《第二次握手》在文學史上便形成了所占篇幅越來越長、闡釋越來越詳盡的有趣現象,這也是它地位上升的典型表征。
具體體現在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1997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孔范今主編)講到“文革”和“文革文學”一節時,僅僅提到“影響較大的手抄本小說有張揚的長篇《第二次握手》”[6](P1011),并未對不容忽視的潛在寫作的手抄本小說的價值意義和文學史定位進行實質性的評定與闡釋,而僅僅作為文學現象稍稍提及。在1999年出版的三本很有影響的文學史教材中,由于編纂者不同的文學史觀帶來的評價標準不一,因此面對同一個考察客體所作的宏觀或微觀的辨析和定位便會出現見仁見智的多樣景觀。朱棟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介紹地下文學時,對《第二次握手》主要做了現象的描述:“以手抄本的形式,冒著極大的風險秘密流傳,成為‘文革’時期地下文學的代表作,作者因此而被捕入獄備受磨難,瀕臨死亡的邊緣。”[7](P16)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在提到它在文革時期流傳甚廣并導致了一次著名的文字獄等外部因素的說明外,還深入文本的內容在當時語境下的新意性進行分析,認為“其主要成就在于把曲折的愛情故事與對知識分子的歌頌以及愛國主義的主題融合了起來,這對正統文藝的清規戒律是一次很大膽的觸犯。”[8](P174)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手抄本小說一節中,用了近一頁的篇幅對《第二次握手》的流傳方式、成書過程、作品內容、歷史定位進行了史的脈絡梳理和價值評說,他從文學史主題的連續性認為“小說對于中國現代歷史和知識分子的道路的描寫,并沒有偏離50年代以后所確立的敘述框架。”[9](P216)真正對《第二次握手》的異質性探索在文學史的發展鏈條中所具有的價值意義進行公正的評說,并對其文學史的地位作出獨到的評價的是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董健等主編)。站在新世紀的歷史起點上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根本特征和歷史流脈進行恰切的定位和評述,就必須正本清源地對以往被遮蔽或未受重視的文獻文本拋棄左右對立的意識形態進行客觀的評價。“為了真實地描繪出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先’與‘后’,使歷史‘鏈條’中的各個環節合乎邏輯的銜接起來”[10](P3),《第二次握手》作為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與17年文學、新時期的傷痕文學之間在主題意蘊和藝術形式等方面的相似性或同質性所具有的承上啟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缺少了其中的一環是無法對中國現代文學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比較詳盡地勾勒出來的,也是無法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建構起血肉豐滿的文學史大廈的。因此,對它的文學史價值用了4頁3000多字作了詳細的闡釋,從以高級知識分子形象作為主人公而不再是“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以愛情悲劇作為情節線索而不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階級斗爭”模式謀篇布局,對蘇冠蘭與丁潔瓊刻骨銘心之愛情的真實描繪上顯示出現實主義的深度等方面對《第二次握手》的思想和藝術的價值意義進行了獨到的分析。[10](P324—326)當然,作為歷史的中間物不可能離開產生它的歷史語境而凌空蹈虛,文革時期刻畫人物的突出與陪襯、主流與支流、先進與反動、拔高與丑化等二元對立的思想觀念和藝術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小說中。因此,作為文革時期廣為流傳的手抄本小說,《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本著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認為“《第二次握手》仍然受到了1949年以后文學創作尤其是‘文革’時期‘主流文學’創作很深的影響。”[10](P324)既考慮到文本的創新突破所具有的異質性、斷裂性,又放到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中看到它的同質性、連續性,比較辯證地確立了小說在文學史的轉捩點所具有的地位和價值。
當然,《第二次握手》的主題思想和美學探索方面的異質性放到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語境中進行評估和衡量也許會顯得乏善可陳,但評價一部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意義只有在歷時態的發展脈絡中樹立中間物的價值尺度,才能以客觀公正的治史者的眼光發現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把《第二次握手》放到生成它的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還原并進入當時的歷史現場就會發現它至少在三個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文學史的意義:其一,它接續并恢復了五四時期開創的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地位和知識價值的優良傳統。知識分子作為人類文明的創造者、傳播者和傳承者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無可代替的重要價值和作用,但在解放后的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政治改造中淪落到連做貧下中農的小學生都不合格的可憐地位,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知識分子在心明眼亮的工農兵主角的襯托下,一律成為了妥協的、動搖的、兩面的、小資的反面角色,但《握手》中的主人公都是可親可敬、愛黨愛國、聰明勇敢、堅韌頑強、無私奉獻的知識分子,主角和配角、正面和反面的是非顛倒在歷史的撥亂方正的方針出臺以前的歷史語境中顯得那么可貴,以自身現代性的審美追求將貧血蒼白而又單調乏味的文革文學模式的一潭死水攪起了軒然大波,“它像閃電一樣猛烈地撕開文化黑暗,在人們眼前留下耀目的光明;又像幾滴甘露撒在文化沙漠之上。只有曾身處文革歷史環境中的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們,才能體驗到這幾滴雨露的寶貴。”[11](P322)只有在“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畸形的民粹主義思想極端泛濫的年代里過來的知識分子,才能真正體會到看似簡單尋常的《第二次握手》卻包蘊著不尋常的文學史的價值意義。其二它接續了現代文學以生命、靈魂為主體的敘事倫理,通過人性世界里的復雜感受的精細書寫來呈現人類內宇宙情感的豐富可能性。“敘事倫理學不探究生命感覺的一般法則和人的生活應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也不制造關于生命感覺的理則,而是講述個人經歷的生命故事,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關于生命感覺的問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12](P4)因此,在小說中它從生命偶在的個體出發打破單一的善惡判斷的道德結論,對反面人物蘇鳳麟對兒子的拳拳之心和愛憐之意作了精致的刻畫。同時,以生命的寬廣和仁慈來打量一切人與事,在愛情悲劇的試驗場上,蘇冠蘭的二難選擇的精神體驗以及靈魂的自我拷問和辯解顯示出來的靈魂的深的煉獄景觀,確實接續了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迅那里繼承來的敞開個體偶在的最本真的生命悸動的心靈辯證法。也通過主人公的生命痕印和經歷的人生變故實現了從個體自由倫理的小敘事到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敘述話語的轉變,愛國主義的宏大敘事經過個體情感的軟化過濾之后才真正血肉豐滿真摯感人,達到了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其三它開啟了新時期人道主義文學的航道。誰都無法否認,文學是“寫人的”、“人寫的”、“寫給人看的”,文學的創造主體、審美主體和文本主體都難以繞開以真善美為核心的人道主義主題,人性和人情話語是人之為人區別于神道及獸道的母題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中的應有之義,但文革文學將人道主義排除于革命的語義之外換來的是談人道色變的非人的文學泛濫成災,正是《第二次握手》對非人文學的公然反叛和挑戰開啟了對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進行維護的人道主義文學的河床,為在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中對人道主義進行正名的討論和爭鳴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1]陳守云.關于《第二次握手》[J].秘書,2006,(8).
[2]朱德發,賈振勇.評判與建構:現代中國文學史學[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
[3]陳聯華.作家張揚與小說《第二次握手》[J].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09,(10).
[4]鄭季翹.文藝領域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J].紅旗,1966,(5).
[5]戴燕.文學史的權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6]孔范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下冊[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7]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9]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0]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1]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M].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
[12]劉小楓.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