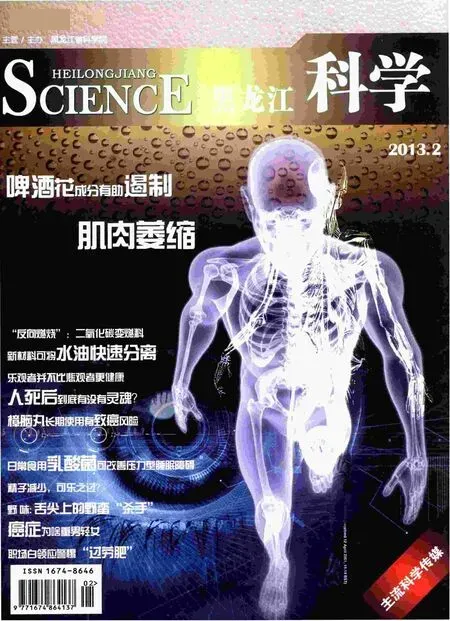商業銀行破產的理論邏輯初探
鄒德剛
(吉林大學法學院, 長春 130012)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強化了人們對于銀行失敗對經濟產生強大破壞力的認識。可以說,至今世界經濟還遠未破解金融風暴的猛烈打擊,各國、各界、各種力量與資源都被調集起來以消解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強大負作用,一個使世界經濟安全著陸的構想急迫地拷問著有關商業銀行破產及相關的制度。
成千上萬人的破產給了我們一個教訓:我們急切需要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系統性的監管規則。此外,對于當前審慎與監管的發展,就意味著我們需要賦予“相關力量(或為職能者)”以識別及將風險消解于早發階段的“權利”。否則,一旦特定的風險脫離了早期的這種甄別與控制,無疑將產生巨大的、系統性的破壞作用,誠如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一樣。而這樣的“賦權”實質上屬于商業銀行破產法律的內容,它已經越過國界,成為了具有國際屬性的一項訴求。這些訴求迫使銀行破產形成獨特的法律規則,用以應對實踐中陷入困境的商業銀行。利用有效的重組或關閉,限制其困境帶來的沖擊,以保護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解決巨大的金融危機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如若缺乏這種統一的法律步調,各國金融監管部門的干預就呈現一種無序狀態,要么被迫提供巨大的流動性支撐金融機構,要么對其提供上萬億的資產擔保。
商業銀行破產的法律制度源于普通公司破產法律構造,但又有重大區別。因此,我們需要回顧普通公司破產的法律制度,同時對于商業銀行的特性也需要重點探討。只有通過基礎破產的研究,我們才能推導出一個比較優化的商業銀行破產框架。
由于銀行的特殊性及其與法律制度的關聯[1],公眾的信任對于銀行業而言是生死攸關的,一旦信任失去,銀行將面臨擠兌。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擠兌造成極大的恐慌在銀行業蔓延出去,甚至傳導至整個經濟層面。例如,大批銀行的倒閉將直接中斷支付體系的正常運作、停止了必要的信用供給,從而引發貨幣危機,代價更是無法估量的。
普通的破產規則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是不適合的,因為它過于強調銀行債權人的利益最大化,從而無視整個銀行業的系統穩定性。雷曼兄弟的倒閉就是這個金融系統悲劇的極端表現。公眾基金也不是銀行失敗的萬能藥方。對破產銀行進行豐厚公共支援,將引導它們在正常的金融職能中為了利潤追逐更高的風險,形成事前的道德風險激勵。無條件的支助無疑會加重政府預算的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它必須給予銀行監管權威一種嶄新的權能,使其能夠逐步關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失敗銀行,從而徹底銷毀破產銀行的“系統性”底牌,否則,“大而不能倒”和“系統性風險”將成為銀行破產制度永久的噩夢。
2007年的金融危機使得銀行審慎監管的希望幻滅了,它既無法阻止商業銀行的破產,也無力應付這些破產所聯合產生的消極的外部效應。例如,存款保險以及隱而不顯的政府保障實質上是商業銀行風險喜好的刺激源,它們經常使銀行落入自己構建的風險陷阱之中,然而,有趣的是,這樣的刺激卻來自審慎監管的舉措。一個全新的銀行破產理念不僅要包含審慎監管的措施,更多的應該是訴諸市場競爭法則,以降低商業銀行風險喜好的刺激。事前減少存款保險、而事后將破產銀行的負擔盡可能地轉移到并不享有保險資格的銀行債權人身上,這種審慎監管與市場法則的結合正是我們商業銀行破產規則所追求的目標。
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基本的邏輯框架展現在研究者面前,我們不能削足適履,簡單地移植普通公司破產的相關制度,必須提請監管威權充分考慮商業銀行的特性,以便能制定適合的破產規則。換而言之,既不能簡單套用“原理式”破解方式[2],也不能無謂地放棄市場機制的理論。市場與監管分處權力的兩極,我們需要謀劃出一條路徑,告誡市場“破產并不是目的,而僅是一種手段”,同時提醒監管權威“應該考慮更多的市場法則”。如此,研究必然從如下路徑展開:(1)事前最優的規則;(2)監管力量及時地介入;(3)事后困境銀行的解決方案;(4)國際性協作的需求及解決困境銀行規則的統一性。
首先,事前的規則意味著規制銀行獨特規則的建立。這就需要特別注意銀行困境日益增長的可能性以及事前具有激勵效應的道德風險問題。解決之道最重要的在于引入“周期性資本比率”這樣的經濟概念,這就要求商業銀行在經濟景氣時期增持資本,通過經濟上升期減少風險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中的比重,以降低經濟下行時給銀行帶來困境的可能性,同時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此種累積式的緩沖平穩地開展業務,從而順利渡過困難期。
其次,“及時”,對于監管力量強制介入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要將銀行破產的影響降至最低的訴求。“前破產”階段的干預應該能夠較為從容地應對萌芽中的金融脆弱性。強制性的“干預”通過要求銀行增加新資本、限制一定的銀行活動等方式來達到目的,因為這種干預是監管者發現特定問題之后的舉措。為了保障這種“前破產的干預舉措”的成功,就必須要趕在銀行真實失敗或已經長期處于流動性困境之前完成,這需要通過明晰的啟動機制來達到此目標。
再次,事后規則強調在商業銀行破產與普通公司破產的解決方法上的顯著不同。普通公司破產著眼于破產企業的價值最大化,而商業銀行破產還必須考慮到銀行破產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因此,商業銀行破產就必須考慮固定化的模式,包括出賣銀行資產,可以全部也可以分開轉讓,或者轉讓給特定的實體作為新的繼受者,也可以進行臨時的公共式的控制。當然,資本的輸入可能會成為最常見的事后解決途徑。
最后,對于跨國銀行的問題急需國際性的協議。國家風險、匯率風險、系統風險等基礎概念已然進入了法律研究者的視野,并更大強化了法律與經濟跨學科對相應商業銀行破產問題研究的力度[3]。雖然這樣的國家間合作是一個挑戰而且仍需時日,但是,這樣的國際性框架一旦建立不僅能夠在應對商業銀行破產方面提供統一的規則,而且對于減少分歧發揮巨大的作用。只有這樣,世界各國才能放下國內保護及諸多主權因素,在銀行破產問題上真實面對問題、適當解決問題。這種協力是平等的起點,無論商業銀行地處何方,也不論其債權人遍及世界各地,他們都將在權利義務上實現真正的對等,損失的共享、監管的合作等等。全新的商業銀行破產理念將孕育這種責任共擔的公平精神,從而在破產相關程序中實現政策目標與利益的平衡[4]。
一個健全的商業銀行破產法律制度,應該給監管者和銀行管理者建立一個可以操作的機制,借此恢復中斷的金融系統、減少破產的損失以及破產所帶來的社會代價。這樣的機制還意味著關注利益最大化目標之外的其他福祉,系統的康復、市場的完善以及降低道德風險。
[1]艾娃·胡普凱斯.比較視野中的銀行破產法律制度[M].上海:中國法律出版社,2006.
[2]韋恩·莫里森.法律學:從古希臘到后現代[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1.
[3]張繼紅.銀行破產法律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209-211.
[4]丁文聯.破產程序中的政策目標與利益平衡[M].上海:中國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