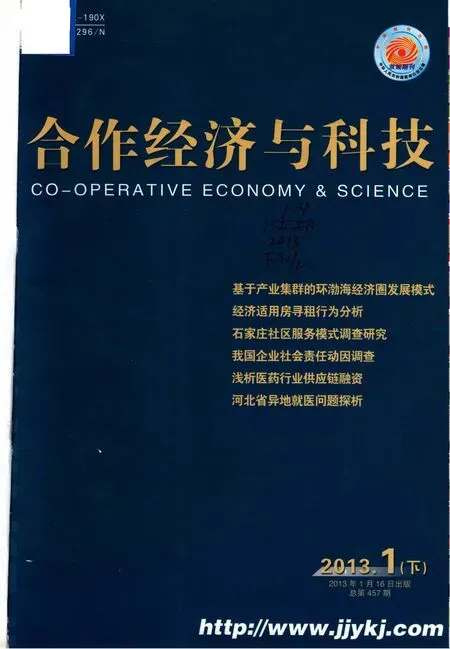黃庭堅儒釋道思想的融合
□文/趙增華
(河北大學 河北·保定)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年號涪翁,又稱豫章黃先生,黃文節公。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生于宋仁宗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卒于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他是北宋著名詩人、詞人、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黃庭堅與杜甫、陳師道、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之稱。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黃庭堅進士及第,歷任葉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他出于蘇軾門下,并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在書法藝術方面,黃庭堅與蘇軾、米芾、蔡襄并稱為“宋四家”,而在詩歌方面黃庭堅與秦觀、晁補之、張耒并稱“蘇門四學士”。黃庭堅61年的人生歷程,基本上是在清寒、貶謫、流離、奔波中度過的,一直到晚年在政治上仍然被忽視。
藝術家面對郁郁不得志的外在環境時,往往追求的是一種內在精神支撐,佛禪和老莊的一些思想理論被很多不得志的藝術家所推崇,甚至會遁入空門,潛心研究,尋求心理上的慰藉。黃庭堅也不例外,他不斷潛心研究,進而從中尋求消除人生苦痛的良藥,形成一種圓融的人生態度。通過參禪明心,去除我執,認識到真正的心性是不會受到外界的污染所改變的,如雪“皎皎不受塵泥涴”,又如月“黃流不解涴明月”,如金石在激流里不被動搖,如翠竹于枯榮中不受影響,形成了一組富有特色的意象群。黃庭堅認為,古人的隱居山野并非為了山川之美與不交世事,而是為了追求心性的完善與高尚的心靈境界。歸隱并非得道,而入世也未必不能解脫,關鍵是在心靈是否執著。在《答王子厚書》中曾說:“古之人不從流俗之波,自放于深山窮谷,非為山川之美與不交世事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己事,開百圣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故于彼有所不愿耳。”
《逍遙游》是莊子哲學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是擺脫一切束縛的絕對自由。黃庭堅把莊子的物化思想與佛教的般若空觀結合起來,把“逍遙”理解為無累于物,超塵拔俗,與道合一,心不執著的般若境界。如果實現了精神上的自由,人就不會為外物所累,為外境所動。黃庭堅用莊子“朝三暮四”典故,說明人隨外境變化而為之起伏的心態。如:“朝四與暮三,適為狙公玩。臭腐暫神奇,暗噫即飄散”;“狙公七芧富貴天,喜四怒三俱可憐”,等等。黃庭堅認為外物、外境的變化不過就像狙公賦芋,朝三暮四,情境雖異,實質相同。所以,面對外境時要不瞋不喜,無取無舍,榮枯隨時。這是莊子的“安時處順”,也是佛教的“以心轉物”,黃庭堅為佛莊二家在這里找到了契合點。
黃庭堅對佛家心的本質、修心的方法看得很透徹,文人如果能夠借鑒佛教修心的方法,那么就更容易體悟圣賢之心。在《跋雙林心王銘》中,黃庭堅指出,學人如果能從《心王銘》中領悟心的本質,并且從此心來讀《論語》,那么就“如啖炙,自己味矣”。在《與胡少汲書》中,他也說:“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于義理得宗趣,卻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辟,極少心力也。”充分肯定了佛禪在修心方法上的作用。
黃庭堅反對傳統漢學那種章句訓詁之學,而希望文人在學習的基礎上能夠反諸己身,自覺地以自身心靈去體悟圣人之心,來提高道德修養。他經常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表明自己的觀點,往往涉及道德問題,認為“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學習道術的目的在于樹立一種標準來把握人生方向,聞道是為了“養心”,用來涵養自己的道德修養,踐履忠孝之道。
“忍、默、平、直”也是黃庭堅一生的處世之道,在北宋嚴峻的政治形勢下進行自我調整并漸漸成熟起來的人生態度。這實際上結合了儒、莊、佛的思想內涵。黃庭堅由于孝養母親、養活家庭等現實問題不可能不入世,而且初期黃庭堅還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來入世,在幾任官職上,他綜合了儒家仁政思想、佛家慈悲教旨與道家無為而治的觀念形成了勤政愛民、恪盡職守、誓作砥柱的入世態度為立身之本。但是,自從經歷了新舊黨爭的政治風波,不但打消了他的入世理想,更讓他有一種不安全感,所以莊子全身避禍的思想開始進入黃庭堅的思想領域。再加上黃庭堅本身就喜歡自由閑遠的生活,時時向往著江湖歸去,所以他積極入世的理想蛻變成了一種與世周旋的態度,在不觸犯道義、氣節的情況下,他還是和光同塵的。這時“忍、默、平”,對外就成了他與世浮沉、“不犯世故之鋒”的全身手段,而對內則是他消解內心矛盾、保持平和心態的秘方。佛教有忍辱波羅蜜,“無可簡擇”是指以對境時無好惡之心。這些都給黃庭堅處理內心不平之氣提供了理論依據。佛禪的“平常心是道”、“真俗不二”、“煩惱即菩提”等思想也給他安于現實并在生活中培養超然的心態提供了精神資源。不過,雖然外在的際遇可作隨緣看待,靈活處理,但作為一位甘當砥柱、以金石不移、青松立節自比的儒士,黃庭堅內心里是時時抱持著“道義”、“氣節”等大的是非原則的,這些是不可動搖的。
儒釋道三教互融的結果,使黃庭堅的思想更加圓融,處世態度也更加自在。隨著佛教大乘精神與“不二”思想的熏習,他對出世和入世不再執著,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體會超脫的精神境界。由于佛、道思想的影響,他更強調知行合一,著重從凈化內心、明見心性的角度去體悟圣賢之心,而不僅僅是做一個拘泥于禮節的循吏。佛道思想的滲入,還使他在入世時保持了清醒與超然的姿態。審時度勢,安時處順,以時勢的沉浮作為自己進退的前提,是謂:“君子藏器,待時盤桓。于不中也,反身自觀。”在建功立業時不執著于功名——“成功萬年,付之面墻”;身處逆境時,也反身自觀,去除煩惱。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佛禪在心性修養理論與修持方法上的完備,黃庭堅更多的是用禪宗的觀照方法來達到一種無我的狀態,斬斷對自我的執著,“無死地以受眾人之彈射”,從根本上對治煩惱痛苦,從而獲得一種自由超脫的精神境界。
黃庭堅認為儒、佛二教的現實教化功能是不同的,六經是“政治之成法”,用以治世,而佛教是治心法,可以成為王者之治的有益補充:“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于世教豈小補哉!”意思是講,國家的刑罰獎賞用以約束人的外在行為,而佛教的因果之論——禍福,可以讓民眾內心策動自律,讓他們止惡向善。所以,黃庭堅認為王者以刑賞法律治理社會,佛教以因果禍福之道理來教化人心,儒釋互補、內外兼治,就可以天下太平。
黃庭堅一生踐履仁愛孝悌的儒家倫理道德,同時傾慕莊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遙之思,后又入佛門,參禪多年,終于在謫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心中廓然。他統合儒釋道三家,形成自洽的思想體系,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態度,構建了“俗里光塵合,胸中涇渭分”的獨特人格,在入世時以天下為己任,為地方官則仁政為民,憂民疾苦;為史官則秉筆直書,為后世留綱鑒;在卷入黨爭、兩遭貶謫時,則隨緣自適,心意平和。身處濁世卻自保氣節,屢遭挫折而心地泰然,貧無立錐仍禪悅充滿。嚴格來說,黃庭堅不是一個哲學家,并未提出新的哲學觀點或者構建一個思想體系,但是他以自身的思考和體驗,以所行證所思,實踐了自己構建的道德標準。
[1]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別集》卷十二.
[2] 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卷五,《見子瞻粲字韻詩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輒次韻寄彭門三首》.
[3]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正集》卷二十一.《晉州州學齋堂銘》之《君子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