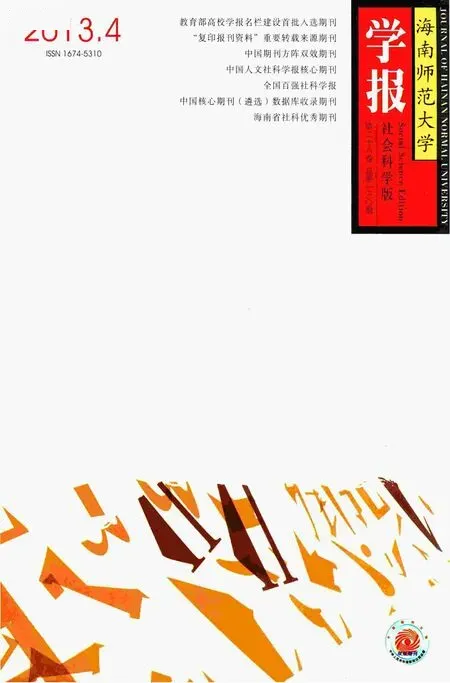愛欲與革命的異體同構——以《蝕》三部曲為例看愛欲對于革命的隱喻涵義
崔秀霞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革命+戀愛”這一小說模式的產生,有許多原因可循,這包括當時大革命的時代背景、對當時青年普遍的時代情緒進行反映的要求、流行風尚、商業因素的驅動等,這些都該劃歸外部因素,前人已做過很多探究,而很少有人從革命與戀愛這二者之間緊張的張力關系上去探究這一小說模式產生的內部因素。
革命與愛情之間存在一種矛盾、張力,而其在本質上又是異體同構、抵死糾纏的,這正構成了驅動“革命+戀愛”這一小說模式產生的內在動因。一方面,情色以其個人性、私密性完成了對國族、政治、革命宏大敘事的消解;另一方面,情愛毋寧說作為一種隱喻,從一個側面折射出革命的發展歷程。
如果說在“革命+戀愛”小說始作俑者蔣光慈筆下,“革命”與“戀愛”二者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革命決定或產生戀愛”的簡單化、概念化的圖解,那么在茅盾的《蝕》三部曲中則更多的表現的是“革命”與“戀愛”的更深層次上的異體同構關系。本文所要闡發的,正是茅盾小說中所體現出來的,愛欲對于革命的隱喻涵義。
一 愛欲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革命的動機
茅盾曾批評蔣光慈的作品“好像是憑空掉下一個‘革命’來到人物的身上,于是那人物就由不革命而革命”,[1]指出了蔣氏“革命+戀愛”小說的硬傷所在:人物缺乏有說服力的革命動機。而到了他自己的處女作《蝕》三部曲中,革命中所潛藏的情欲動機,毋寧說是茅盾為硬邦邦冷冰冰的革命所尋找到的人性上的依據。
郁達夫的一句話可以作為對這二者之間關系的佐證,“革命事業的勃發,也貴在有著一點熱情。這一點熱情的培養,要賴柔美圣潔的女性的愛”。追溯起來,革命者們革命熱情的來源,是女性之愛。這不僅是小說虛構,也是當時真實的社會狀況的反映。
讀《蝕》三部曲可以發現,情色構成了其中很多人物參與革命的原始動機。《幻滅》中的主人公靜女士經歷了革命與戀愛循環往復的幻滅。來看一下靜在省工會擔任辦事員,投身革命新生活后的一些情景描述,“同事們舉動之粗野幼稚,不拘小節,以及近乎瘋狂的見了單身女人就要戀愛”,①茅盾:《蝕》,《茅盾全集》第1 卷(小說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所引原文皆出于此,不再單獨標注。“鬧戀愛尤其是他們辦事以外唯一的要件。”還有慧女士請客時的情景,眾同僚們跟慧女士糾纏不已,提到慧的戀愛史,“這一伙半醉的人兒宛如聽得前線的捷報,一齊鼓舞起來了”。
靜女士發出的感想其實很能揭示出革命與戀愛這二者之間的糾結點之所在“‘要戀愛’成了流行病,人們瘋狂地尋覓肉的享樂,新奇的性欲的刺激”,“在沉靜的空氣中,煩悶的反映是頹喪消極;在緊張的空氣中,是追尋感官的刺激。所謂‘戀愛’遂成了神圣的解嘲”。在這里,戀愛顯然成了投身革命的青年們尋求感官刺激的流行病,《蝕》三部曲中激烈的革命與縱欲氣息的混合形成了奇特的景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亦可以為性與革命之間的隱秘關系提供理論上的支撐。
而另一方面,戀愛也是當時卷入革命洪流的時代女性們證明自身與舊的封建勢力的徹底決裂、及自身革命性的最有效力的方式。“單身的女子若不和人戀愛,幾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正如南帆所說:“性所隱含的心理壓力掀開了衛道士設置的重重路障,這種反抗姿態的確類似革命;無論是踐踏秩序、蔑視權威還是放縱自由、為所欲為,革命的狂歡與性的狂歡具有某種氣勢上的美學對稱。這導致了二者的相互象征。”[2]愛欲所代表的那種對固有倫理制度的激烈反抗姿態,與革命對舊有秩序的踐踏、對權威的蔑視及狂歡與放縱的氣息,二者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相似與對稱,這就構成了性愛與革命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象征與隱喻的依據。愛欲之解放,毋寧說,也是一種革命。
下面,通過“女體”這一意象,進一步闡述情愛對于革命的動機涵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情愛是革命的象征與隱喻,是具象化的、肉感的“革命”。
茅盾對于女體似乎有一種情迷,《蝕》三部曲中女體的正面描寫繁多,且筆調恣肆。毛話語時代,革命被正典化,情欲描寫成為禁區。而實際上在革命文學早期,“革命+戀愛”體現出的正是情欲的合法性表達,情欲描寫表現出一種未被規限的、原生態的蓬勃,屬于革命文學早期創作的《蝕》三部曲正把這一面很好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小說中的“時代女性”是“革命”的象征性能指,“她們的美、性誘惑和不可馴服,正是‘革命’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具象化的投影。”[3]三部曲中的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茅盾所塑造的這一系列“革命萬人迷”的形象,是革命事業公共領域的女性,擔當著大眾情人的角色,或者說叫做“革命公妻”。《動搖》中,便借林子沖之口,轉述了大家的普遍看法,“孫舞陽,公妻榜樣!”她們在革命事業的游走間,便儼然具有了革命的女神或者說化身的光輝,她們讓人想起西方的一幅名畫《自由引導人民》。畫面中,硝煙彌漫的戰場之上,坦胸的肉感女革命者,高舉手中的武器,振臂高呼,跟隨在她后面的是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來的人們。“女革命者形象,有著放蕩的身體加上革命的精神,這成為左翼意識形態指導下最普遍的文學表述。”[4]這些兼有革命精神與肉體美的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大革命的一個象征性指符。她們本身即是具象化的、肉感的革命。革命因其宏大而抽象,令革命青年們難以把握,而當其落實并具化到一具具青春鮮活、可觸可感的女體之上,革命便也成了切近的、可觸可感的存在。
情欲意義上的革命動機,也包括對身體資源進行再度分配的要求。如《動搖》中寫婦女協會的工作,各派勢力討論對于婢妾、孀婦、尼姑等女性的處置方式,胡國光等革命中的渾水摸魚之人主張把她們收歸公有,公家發配。當然這里面包含了對女性的極端的不尊重在里面,把女性完全地物化。但是這些情節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革命的不能夠說出口的隱秘動機之一,便是身體資源的再度分配。“即以茅盾為例,他筆下寫實主義的情愛修辭,無論得意還是落魄,無不映射著革命論述中的復雜面向,宛若一則動人的政治寓言。一方面挑動著社會自我改革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吁求社會在公共與個人領域中重新分配身體資源。”[5]在某種程度上,投身革命洪流中的革命者們,對于革命的熱望及對于女體的覬覦,二者相伴而生,并糾結成為復雜而隱秘的革命動機。被愛欲所驅動的革命帶給藝術強烈的感官刺激,建構起旖旎曖昧的革命話語,并對以后意識形態迷魅籠罩下,對于革命動機高尚而純粹的單一解讀形成了反諷。
二 情愛作為一種修辭,以互文方式實現對革命的隱喻
革命與愛情在三部曲中的《動搖》中是兩股交纏的線,茅盾顯然有以主人公方羅蘭在愛情中的動搖來隱喻革命的動搖的意圖。方羅蘭在革命新女性孫舞陽與妻子梅麗之間的徘徊動搖,正是其在“革命觀念、革命政策”上,于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動搖態度的隱喻。
方羅蘭每一次與孫舞陽之間的愛欲糾纏,似乎都和他在革命工作中所面臨的難題相伴而行。這種看似非常巧合的對應,只能說明情愛是作者有意為之的一種修辭,作者以情愛作為指符,揭示出這一時代沖突的焦點。
《動搖》中革命這一條敘事線索與戀愛這一條敘事線索,在敘事的節奏上有一種很巧妙的對應與互文。下面具體地對此加以梳理和說明。
胡國光與陸慕游因縣黨部要“處治劣紳胡國光”之事,去方家拜訪方羅蘭,因胡案正是方羅蘭職權范圍內的事,這正是方羅蘭卷入兩派斗爭的起始。而在情愛這一條線上,與此對應的,方羅蘭一邊聽著胡、陸二人的話,“一個艷影,正對于他的可憐靈魂,施行韌性的逆襲”,之后眼前出現了孫舞陽的幻象,把南天竹看成了孫舞陽墨綠色的長外衣,心旌搖蕩處發出“舞陽,你是希望的光,我不自覺地要跟著你跑”這樣的感嘆,而此時他還是努力找出方太太的許多優點來,借此來穩定自己心的動搖,“可以保證他尚是方太太的忠實同志”。此時,反映在政治上,方羅蘭對胡國光持的是冷淡的、保留的態度。
店員加薪風潮爆發之際,在對待革命上的態度,方羅蘭在與大家討論此事的會議上慨嘆道:“店員生活果真困難,但照目前的要求,未免過甚;太不顧店東們的死活了!”表示出對于各方意見不一致的無能無力的態度。“他總想辦成兩邊都不吃虧,那就更不容易”,這句話可以說是方羅蘭對于革命、也是對于情愛猶疑不決態度的一個雙重概括。在情愛這條線上,與此對應的,方羅蘭因收到孫舞陽贈的手帕而與方太太產生誤會,爆發家庭矛盾,方羅蘭為此而心神不寧,極力地向方太太解釋。
到了第六節中,方羅蘭在接見店東請愿代表時,很受了窘,看見群情憤激,很覺得為難,支支吾吾地敷衍著,始終沒有確實的答復,對于這些實際的問題,他似乎連個人的意見也像自己無權確定了,苦悶彷徨的心情正合著方太太說的幾句話:“我不知道應該怎么做,才算是對的。……這世界變得太快,太復雜,太古怪,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頭了。”與此對應的情愛上的態度,在婦女協會茶會上討論完婦女運動之后,方羅蘭在孫舞陽房中,觸動于孫舞陽的婉曼而善解人意,感覺對她“已發動了似乎近于戀愛的情緒了”,“對于太太的心胸狹窄,頗為不滿了”,觸到孫舞陽手指時,“異樣的搖惑便無理由地擊中了他……”
第九節中,在解放婦女運動之后,方羅蘭為情愛之事頗為煩惱,方太太忽變常態,他與太太之間,“似乎已經有了一層隔膜”。對于孫舞陽這方面則是“一天天地崇拜孫舞陽,一切站在反對方面的言論和觀察,他都無條件地否認”,“下意識的傾向已經成了每逢在太太處得了冷淡而發生煩悶時,便到孫舞陽跟前來療治”,并有了二人在張公祠的對談,方羅蘭為是否與方太太離婚而煩悶不已。而接下來第十節,革命中的爭斗也達到了一個白熱化的狀態,胡國光企圖發動暴動,趕走縣長,自己做縣長,對此方羅蘭是“不能不躊躇了”,“他并不是一定回護縣長,他只覺得胡國光這投機分子要這么干,就一定不能贊成”,其政治態度表現出在兩派之間的傾向性,但仍不是那么堅決,那么徹底,這與上述的他這一階段的情愛態度是有一致性的。
故事的最后,在革命這一條線上,是反革命敵軍進城,發動暴亂,燒殺擄掠,對女子慘絕人性地施暴,在暴亂之下方羅蘭的情緒也有極端化的波動,眼前出現了人頭與女尸的瘋狂而可怖的幻象;與此對應的,方羅蘭的情愛三角關系中,三個當事人終于出現在了同一場合,發生正面的交接與沖突,在此前的整個故事中,孫舞陽與方太太這一對“情敵”之間雖矛盾重重,是主角方羅蘭動搖之癥結所在,并推動故事跌宕起伏地向前發展,但二人并未發生正面沖突。而此時,三人因逃難而齊聚破廟之中,并且方羅蘭把坐在一起的孫舞陽與梅麗進行了一番對比。而當方太太陸梅麗看到方羅蘭與孫舞陽并肩親密地站在院中時,出現了化身為蜘蛛的瘋狂而可怕的幻覺。至此,三人的情愛關系也到了一個沖突的高潮點上。兩條線索都在故事的最后達致敘事高潮,并且互相呼應。
茅盾在《從牯嶺到東京》中曾作《動搖》之創作談,“不但在黨務在民眾運動上,并且在戀愛上,他也是動搖的。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正面描寫一個人物的政治態度,不必像屠格涅夫那樣要戀愛來暗示;但描寫《動搖》中的代表的方羅蘭之無往而不動搖,那么他和孫舞陽戀愛這一段描寫大概不是閑文了。”[6]
雖說是“不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茅盾有意無意間接續了屠格涅夫以戀愛來暗示人物的政治態度的傳統。而下面一句更加顯明地說出了茅盾的態度,戀愛不是“閑文”,并不僅僅是“革命+戀愛”這種小說模式中的一點可有可無的花邊性裝飾,并不僅僅是吸引讀者眼球的商業策略性手段,而是有著更加深層的本質性的意義包含其中。
對于革命的解讀,情愛是一個隱秘而獨特的進入角度。茅盾“大概不是閑文”的看似隨意的自我解讀,是不是也是企圖在字里行間為后世的解讀者作出一個暗示,指明一條隱秘的進入路徑?明眼者要從這里看出作者在創作意圖上即已設定的革命與戀愛二者之間的互文。
“時時注意不要離開了題旨,時時顧到要使篇中每一動作都朝著一個方向,都為促成這總目的之有機的結構。”[6]革命與情愛,二者并行而交互隱喻,共同“朝著一個方向”,指向大時代下普遍的、無往不在的動搖。
三 愛欲是革命失敗的頹廢低落中革命青年確認自身存在感的寄托
這一點主要以《追求》中史循與章秋柳的例子加以闡釋。
“懷疑派”史循,正代表了大革命失敗后青年們極普遍的一種精神狀態。《追求》開頭的同學會上,曼青和仲昭的談話定下了小說的基調,他們面對著“中國式的世紀末的苦悶”的“時代病”,“在這大變動的時代,我們等于零,我們幾乎不能自己相信尚是活著的人。我們終天無聊苦悶。”章秋柳慷慨激烈的談話也道出了大革命失敗背景下青年時代病的癥結所在,那便是對自身存在感的懷疑。
史循可以說是患著“時代病”的青年的一個極端化的顯現。史循出場時,反復強調他的“懷疑派哲學家”的身份,反復強調他的“枯瘠”、“衰頹”,“‘衰頹’已經成為這個人的特有氣味’”。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這樣說,史循是革命青年們懷疑、頹廢情緒的一個具化。故事開場的同學會上,章秋柳、王詩陶、龍飛等五人團團圍住史循跳tango 舞,要用“旋風般的熱情來掃除這懷疑的黑影子,在曼青的眼里,這個場景正同于受到黑暗和恐怖的侵襲的兒童大叫大喊著以自壯。熱鬧的圍剿里,所反映出來的革命青年對于史循的巨大畏懼,正是他們對于大革命失敗后濃重的時代情緒陰影的恐懼。
時代女性章秋柳以情愛方式對“懷疑論”者史循的拯救,有著很深的寓意在里面。這對于“懷疑論者”史循來說,是在其自殺未遂之后重又喚起了他微弱的生之希望;而反過來,對史循的拯救,也是以往單純“追逐肉的享樂的唯我主義者”章秋柳,發現以往在跳舞場、影戲院、旅館、酒樓中熱烈的痛快的經驗,最終由新奇變為平凡,在享樂與革命之間抉擇不定,猶疑、徘徊、頹廢時,尋找“生存的意義”的一種方式。她在紙條上寫下的“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請自今日始;刻苦,沉著,精進不休”的“悲痛的懺悔”,都足足說明,這種拯救是她重新尋求新生、尋求自身意義的一個契機、一種手段。看著史循把亂蓬蓬的胡須刮光的新面孔,章秋柳是抱著“藝術家鑒賞自己的得意杰作的態度”,“新生”的史循作為章秋柳塑造的“藝術品”,使她迷失的頹廢生活有了自證其存在的切實依據。
接續下來的小說情節也有可供解讀的深層意味在里面。
如,史循枯瘠身體與章秋柳豐腴肉體的對比。史循與章秋柳在炮臺灣的夜晚,二人情動,并脫去衣物裸裎相對的時刻,史循看到了旁邊鏡子里兩個人的形象。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史循在豐腴健康的女體面前通過鏡像反觀自身,在這種強烈的對照之下,確證了自身枯瘠而頹廢的存在,對于自身的病態有了鮮明而強烈的自知,并且落荒而逃。
史循死在章秋柳的石榴裙下。頹廢的“懷疑派”史循貌似被拯救,復而走向更加徹底的滅亡。而這種滅亡是充滿著狂歡與情色的濃烈色彩的,史循是在與朋友們帶有狂歡性質的野外聚餐拼酒中猝然倒地的,并且正好倒在了章秋柳裙下,聞到了女體“似香非香的氣味”,看見綢裙里很伶俐地動著的兩條白腿。在這一旖旎香艷的死亡場景中,愛欲與死亡如此接近。“他心里一動,伸臂想抱住這撩人的足踝”,而在這時,“驟然一陣眩暈擊中了他”,“腥血已經從他嘴里噴出來”。愛欲是瀕臨生命邊緣的史循最終看見的靡麗繁華、企圖抓住的最后一根生命稻草。而這最后一點確證自身的追求也已然落空,新生的追求徹底失敗。章秋柳其后對史循之死的評價是,“然而他的死,是把生命力聚積在一下的爆發中很不尋常的死。”在此,革命、愛欲、死亡混合成了蕪雜而奇異的景觀。
章秋柳染上了史循傳下來的梅毒。史循身上所代表的頹廢以這樣一種方式延續下來,并且對原本生命力旺盛的女革命者章秋柳形成了綿長并充滿破壞力的侵蝕,青年們所謂的“追求”陷入了無一絲希望的灰色,也宣告了以愛欲作為拯救方式的失敗。
回顧史循甫一出場時,曼青看到坐在一起的枯瘠的史循與明艷的章秋柳形成強烈的對照,因而感觸人生無常的憂哀,“將來的章秋柳終不免要成為現在的史循,或許更壞”,這似乎是一種歷史循環論的讖語。而作者所取的“史循”這個名字也饒有意味,它代表著“懷疑論哲學家”史循自身在頹廢與因情愛燃起的微弱生意、生與死之間的往復循環。而史循本人也秉持“循環論”,曾自言:“我所看見的,只是循環而已。”這是不是也間接地傳達出茅盾的歷史觀,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屬于革命青年們的命運也就是在“幻滅”、“動搖”、“追求”之間往復循環,由豐腴與希望最終走向枯瘠與頹廢?
作為革命“頹廢派”的史循,他第一次自殺后的被救,對于自身狀況的醒覺,乃至最終的死,幾番起落往復,都如此切近地與愛欲糾纏在一起。
這是大革命失敗后革命青年普遍的生活的一個概括性反映,還是毋寧說是革命與情欲關系的又一重隱喻?
上面所闡述的愛欲與革命相互纏繞的事實,構成了“革命+戀愛”小說模式產生的內在動因。二者之間之異體同構,構成了復雜糾葛的關系。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蝕》時曾刪掉大量的情色片段,革命被正典化,被意識形態所規訓,情愛與革命之間那一條隱秘的紐帶表面上被斬斷,但革命與情愛二者在本源上的抵死糾纏,依然以上述的方式在歷史與文學中暗涌,永不消歇。
[1]茅盾.關于“創作”[M]//茅盾全集:第19 卷(中國文論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2]南帆.文學、革命與性[J].文藝爭鳴,2000(5).
[3]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的“革命+戀愛”模式解析[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5).
[4]劉劍梅.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M].上海:三聯書店,2009.
[5]余夏云.迷魅化的講述——論王德威的《歷史與怪獸》[J].渤海大學學報,2010(3).
[6]茅盾.從牯嶺到東京[M]//茅盾全集:第19 卷(中國文論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