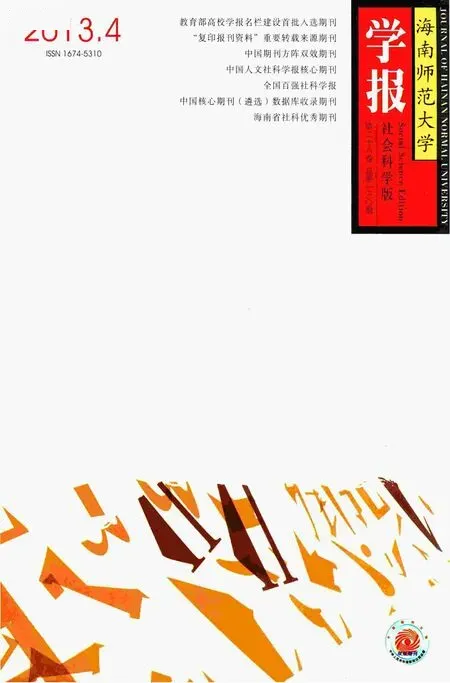魯迅研究的扎實成果與可喜收獲——評趙歌東《啟蒙與革命:魯迅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
譚五昌,馬媛穎
(1.北京師范大學 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北京100875;2.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100083)
在這個急速發展的文化時代,談論“現代性”問題似乎已經不再那么時髦與緊跟“潮流”了,畢竟在當下的語境中,我們早已進入“后現代”甚至“后后現代”了。時下一切有關魯迅的話題,似乎頗為“不合時宜”,因為魯迅及魯迅話題與當今社會的整體精神氛圍與思想狀態存在內在的沖突與不協調。然而,作為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位“繞不過去”的經典性作家,魯迅始終存在著,并且至今仍然在參與并影響著中國的思想現實及文學意識。站在當今的時代高度,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與評價魯迅呢?魯迅研究的價值及新意何在?趙歌東的學術新著《啟蒙與革命:魯迅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從研究者的角度而言,魯迅所具有的現代性意義是言說不盡的,其現代性體系所涵蓋的各類問題,即使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現實針對性,亟須我們去進一步發掘、審視與評估。
回顧近百年的魯迅學術研究史,我們看到,每個時代由研究者們所建構的魯迅形象均呈現著不同的時代性風貌,這一現象既建立在時代發展的客觀基礎之上的,又受研究者主體研究意識、研究方法等主觀因素影響。大致說來,1920年代的魯迅是作為啟蒙者的“文學的魯迅”;1930、1940年代的魯迅是“民族魂”和文化戰線的“斗士”;1950 至1970年代的魯迅是被極端政治化的、“革命的”化身,甚至一度成了政治大批判中的“尺子”或“棍子”;1980年代的魯迅是“思想的”、“批判的”、“文學的”;1990年代以來的魯迅,則是“文化的”、“矛盾的”、“歷史中間物”等多元化的。[1]由此可見,無論是研究者對魯迅形象的建構,還是人們對魯迅及其作品的接受與解讀,都經歷了一個變化與起伏很大的歷史過程,而這種情形還將會一直持續下去。可以說,關于魯迅的思考和界定仍然處在嬗變不居的“未完成”狀態。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來,魯迅研究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思想歷程:李長之在1930年代撰寫的《魯迅批判》是魯迅研究史上第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作者從普遍的認識意義和文學價值的角度來感受與評說魯迅,否定了魯迅思想家的地位,突出了作為文學家和精神戰士的魯迅形象,相比較同時期瞿秋白、馮雪峰等左翼知識分子稍顯政治化的魯迅研究,李長之具有自己的獨特研究角度,那就是他通過文本細讀深刻感受到了魯迅內心的孤獨,體悟并把握了魯迅的思想性格與精神狀態,努力復原魯迅的真實面目,因而影響深遠。建國后,王瑤和曹聚仁的魯迅研究影響較大,王瑤的專著《魯迅與中國文學》從宏觀角度對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進行了比較性研究,以揭示魯迅文學世界的面貌。曹聚仁曾與魯迅交往密切,其于1937年編著的史料匯編《魯迅手冊》對魯迅研究而言頗具價值;建國后,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于1956年完成了《魯迅評傳》一書,該書從多角度、多側面對魯迅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與評價;1967年,曹聚仁又出版了《魯迅年譜》。這兩部著作的出版以其資料的翔實可靠和評述的客觀公允在海內外的魯迅研究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至今仍然是魯迅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1980年代以來,魯迅研究界人才層出,成果豐碩,陸續涌現了唐弢、錢理群、王富仁、王得后、孫郁、張恩和、孫玉石等著名魯迅研究的專家學者。他們的論著對魯迅的文學創作、生平思想、文化意義等層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探討與研究,其有關論著視野開闊,理論方法新穎豐富,研究成果斐然。例如: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以魯迅的《野草》為論述重點,尋找“歷史偉人與平凡的自我之間的心靈通道”,對魯迅豐富復雜的心靈世界予以全方位的揭示;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對魯迅思想及魯迅小說的文化意義作了深刻的闡發和高度評價;王得后的《兩地書研究》、《魯迅與孔子》,圍繞著魯迅的愛情及魯迅與“國學”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思想剖析;孫郁的《被褻瀆的魯迅》、《對話魯迅》,論述并探討了魯迅在不同時代所遭遇的嚴重誤讀,提出了魯迅被邊緣化的悲劇性命運的等沉重話題……這些具有代表性的魯迅研究論著,是新時期以來多維視野中魯迅研究的標志性成果,這些著作對于糾正以往對魯迅的誤讀和歪曲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也為作為普通讀者的我們進一步走近魯迅、理解魯迅提供了可靠的理論參照。
在新時期以來的魯迅研究界,“回到魯迅”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其目的是要求研究者能夠按歷史的本來面目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要還原歷史的、真實的魯迅,當然離不開對魯迅原始資料和文本的認定和梳理,因此,在“回到魯迅”的口號聲中,研究者不約而同地回到魯迅早期的創作原典(以《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吶喊》、《彷徨》、《野草》為標志性文本) ,藉此重新發現作為啟蒙思想家和“反封建思想革命”先驅者的魯迅,回到一個有著獨特心靈世界的“孤獨者”形象魯迅那里……在這些闡釋和解讀中,大多數研究者把視野集中到了魯迅個人身上,或者把目光聚焦在魯迅思想的獨特性和深刻性,或者把目光聚焦在魯迅生命的孤獨感和悲劇性,并以此為基點,從啟蒙運動的起源意義上追尋魯迅啟蒙思想和生命意識的源流和嬗變,從而把魯迅與“現代意識”和“現代性”聯系在了一起,塑造出了一個痛苦的啟蒙主義者形象。近些年來,研究者們重提“回到魯迅”的口號,力圖讓曾經被高度政治化、符號化了的魯迅回到個性化、感性化的“文學魯迅”的層面上來。研究者普遍認為:受政治文化的影響,以往對魯迅的認識主要側重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主要關注點是對其啟蒙思想的客觀效應的闡釋,對作品的解讀也主要集中在文化評判層面,對其文學作品本身的詮釋及其“現場”效應關注不夠。因此,再度強調回到“文學魯迅”的層面看魯迅,一是要回到“五四”文學的原生態環境看魯迅,一是要以魯迅創作的原始文本為依據看魯迅,再者是要在中國現代啟蒙與革命及其相關的現代性思想流變的意義上看魯迅。這三者緊密結合、相互滲透,構成魯迅創作和思想的“歷史現場”,由此才能真正地還原和彰顯魯迅創作和思想的價值與意義。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新時期以來關于魯迅的接受和闡釋是一個不斷積累又不斷超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形象及其價值和意義經歷了一個從片面、單一、感性,到整合、全面、理性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是一個不斷突破研究者自身的理論盲區或文化盲點,不斷對魯迅創作和思想進行重新發現、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而言,趙歌東的《啟蒙與革命:魯迅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以下簡稱《啟蒙與革命》) 可以說是近年魯迅研究一個扎實的成果和可喜的收獲。
《啟蒙與革命》以“啟蒙”和“革命”這兩個中心概念為理論原點,展開對“魯迅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論述。不難看出,作者對魯迅文本的細節和魯迅相關歷史事件的原始資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全書邏輯清晰、層層推進,行文隱含著個人的思想傾向和情感立場,理性的分析中時時透露出“知人論世”的理解與感悟。全書圍繞著魯迅對“現代性”的選擇與堅守透析20 世紀中國文學的內在矛盾沖突,力求還原魯迅作為啟蒙主義者的獨立姿態和歷史形象。趙歌東指出:當前一些論者在使用“現代性”概念的時候,往往“在沒有對現代性的基本內涵及其在不同語境中的種種歧義做出歷史分析的前提下,簡單地從傳統性、后現代性或反現代性的角度質疑現代性的歷史進步性和合法性,從而也在某種意義上質疑和否定包括魯迅創作在內的五四新文學的現代性追求”。[2]1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從“現代性”意義上還原魯迅的真實面目,首先要在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歷史背景上,對“現代性”的辭源與詞性進行歷史的梳理,劃定出“現代性”擴張從西方到東方的概念內涵和歷史外延,才能對魯迅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做出恰當的定位分析。這樣的理論視角展示了作者穩重的現代性歷史觀和嚴謹、負責的學術態度,為全書奠定了歷史的、理性的學術品質。
趙歌東對“現代性”概念作了綜合性的歷史分析:“現代性”譜系是一個以“現代”為詞根的復雜話語系統,這一復雜的話語體系包含著“現代性”、“現代化”、“現代主義”、“后現代”等多重概念,共同構成了現代社會知識譜系的主體結構。[2]1在書的緒論部分,作者從“現代性”最初的辭源與詞性開始,討論了現代性在審美、社會、文化和技術層面上的涵義,回溯了“現代性”的歷史和歷史中的“現代性”,區分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以“天才的個性”為表征的現代性,和以對理性的崇慕為表征的啟蒙主義的現代性,顯示了作者開闊的理論視野和深厚的理論素養,這也使得《啟蒙與革命》一書的立論堅實而富有歷史感。
正如趙歌東所言:“現代性”是一個特定的歷史范疇,它首先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產物,其次是歐洲歷史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思想界標,再次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文化屬性。西方的“現代性”以“人的覺醒”為歷史背景,并建立在理性主義的進步理念之上——“人的覺醒”需要建立健全的理性,而確立健全的理性需要一個以“現代性”的認同與擴張為源動力的啟蒙過程。趙歌東所闡述并加以肯定的“現代性”,是一種建立在此種具有啟蒙意義的、基于“現代性”認同與擴張基礎上的理性主義和進步理念的歷史載體。在這個意義上看,作為“外源型現代化”范式內的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確立的“人的解放”這一中心論題,得以與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現代性追求接軌,加入到世界現代化變革的進程當中去,進而形成了以“五四”文學的現代性認同為源頭的現代化追求。在趙歌東看來,這種現代性認同和現代化追求在魯迅創作和思想中得到了最集中、最持久的實驗,但最終并沒有實現魯迅所堅持的現代化目標。這是魯迅個人的悲劇,也是20 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悲劇。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西方現代化進程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從物質變革到制度變革再到思想變革,后者是從思想變革到物質變革再到制度變革。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外源”與“內源”雙重合力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化,從內需要進行思想啟蒙;從外需要進行社會革命。在這一點上,《啟蒙與革命》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與魯迅創作和思想有機聯系起來,建立起一個以“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為內涵的現代化程式。由此,魯迅的文學史意義與文化形象得到歷史的定位與確立。問題的關鍵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著作為“內源”的傳統性與作為“外源”的現代性的沖突,而這一沖突的焦點在于“人”的觀念的轉變。趙歌東認為:魯迅對于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就在于他為中國現代化思想啟蒙確立了“立人”的目標,并在此基點上從內源、外源兩方面為中國現代化確立了啟蒙與革命的現代性選擇。這個結論并不完全是趙歌東個人的發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過以往歷代魯迅研究者反復論證而確認的一種歷史共識。但應該看到,在21 世紀的今天,自覺地認同這一歷史共識仍然具有艱難的現實性和挑戰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趙歌東的結論并不是對前人研究的簡單重復,而是對一種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歷史共識的嚴肅重申和艱難的持守。
在趙歌東看來,作為個體的魯迅是一個體現著矛盾沖突的綜合體——傳統與現代、啟蒙與革命、左翼與右翼,這些帶有鮮明時代標志的矛盾實體都在他的內心與形象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這些印記又恰恰體現出“現代性”沖突的歷史內涵和時代特征。“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魯迅的個人啟蒙及生活經驗就遭遇了文化上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他站在“中學”與“西學”之間,從兩者的不斷碰撞與沖突中,對晚清的思潮做了現代性的理論整合:從“中學”方面,形成了“從字縫里看出字來”的思維方式;從“西學”方面,則確立了“為人生”的文學創作主張,由此完成了其思想上的現代化啟蒙,并為其后發出劃時代的“吶喊”奠定了思想基礎。
趙歌東指出:從辛亥革命的政治變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變革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關鍵期,也是魯迅思想逐步深化、發展、成熟的時期。辛亥革命所倡導及確立的“民族—國家”觀念印證了魯迅早期的“立國”思想,而革命的失敗促使他從“立國”轉向以“立人”為根本的現代性追求,并最終確立了以“改良國民性”為基準的啟蒙主義文化思路。魯迅將眼光聚焦于“人”這一根本性因素,確立了“立人”這一論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具有的現代性價值。由此而言,魯迅思想及其創作是連接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表層政治變革與深層思想變革的一座橋梁。
從歷史上看,“五四”新文化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短暫的歷史階段,但它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這個運動本身。在思想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五四”精神對于中國現代化進程具有永恒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對“五四”精神的繼承與持守成為鑒別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立場的一個重要標志。趙歌東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后,知識分子群體發生了深刻的分化,不同派系的知識分子選擇了不同的“問題”與“主義”,魯迅自己也有過“彷徨”與掙扎,但他始終堅守著“五四”的啟蒙主義立場,他對知識分子的左翼和右翼同時保持著批判姿態,同時又通過與左翼與右翼的沖突和論爭使“后五四時期”的文壇保持著對立統一,因此而使其思想和創作成為“五四”之后的“一個獨立而完整的現代性事件”。魯迅的存在對“五四”之后啟蒙與革命的轉型、左翼與右翼的轉換與融合都具有重要意義。
《啟蒙與革命》一書對魯迅的現代性思想與啟蒙與革命關系的論述是其學術用力點,圍繞這一命題,作者對不同歷史階段人們對魯迅創作現代性問題的認識與分析的不同結論進行了簡要梳理,從中我們看到了傅斯年、張定璜等人如何從啟蒙意義的角度對魯迅創作進行分析,肯定了魯迅創作的啟蒙主義特征及其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開創性地位,在理論上確定了魯迅小說的現代性品質;看到了劉一聲如何從革命的角度肯定魯迅雜文創作的價值,卻又因為狹隘的革命立場而對魯迅“改良國民性”的現代性追求做出錯誤判斷,這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五四”之后的魯迅研究不可避免地背離了魯迅創作的現代性方向;我們也看到了“文革”結束后,人們在“回到魯迅那里去”的呼聲中重新確立“立人”思想和啟蒙主義立場在魯迅創作現代性追求中的重要意義。總的來說,作者在對各歷史階段魯迅創作現代性研究成果進行框架式梳理的同時,還呈現了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五四”精神與現代性問題的不同態度和不同理解,描述了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訴求在啟蒙與革命、傳統與現代的不斷矛盾沖突中得以發展、深入的過程。這些分析在一定意義上澄清了魯迅研究史上的某些盲點,對于還原魯迅的歷史形象無疑是有益的。
《啟蒙與革命》的論述對相關史實和史料條分縷析,史論結合,有理有據,令人信服。例如,在分析魯迅思想現代性追求的發生過程時,趙歌東指出:對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使魯迅意識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創辦《新生》的經歷使魯迅初步確立了“立人”思想并重新發現了自己;加盟《新青年》使魯迅思想由種族意識演進為民族意識,再進入到“改良國民性”,最終確立了啟蒙主義的現代性追求。這些論述層層深入,清晰地展現出魯迅思想演進的歷史進程。《啟蒙與革命》一書的后半部分,作者著眼于“革命”這一關鍵詞,結合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還原了魯迅與“后五四時期”的文藝論爭、魯迅與“左聯”關系始末、魯迅與“左聯”五烈士、魯迅與“兩個口號”論爭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再現了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路”上的矛盾與掙扎,使我們重新發現了作為革命“同路人”的魯迅在左翼文學陣營中不得不“橫站”的歷史姿態。
歷史地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魯迅是被塑造、被闡釋出來的。不論是“同路人”還是“圣人”,是“主將”還是“小兵”,甚或是歷史的“中間物”,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片面性,正如《啟蒙與革命》的“結語”中所顯示的: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魯迅形象是一個一再被誤讀的“先驅者”。魯迅不是什么“圣人”,但他的思想是崇高的——魯迅思想的莊嚴與神圣取決于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原創性與先驅性。對魯迅形象“解構神圣”是要回歸或還原“先驅者”魯迅的歷史本色,而不是“打倒”魯迅。魯迅思想是復雜的、多元的,卻也是簡單的——簡單就在于,魯迅確認并堅守的“立人”目標及其相應的“人的覺醒”的現代性訴求始終沒有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目標沒有完成,但這并不妨礙作為啟蒙先驅者的魯迅完成其思想涅槃并成為20 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一個固定標志。歷史上許多偉大思想家都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的選擇和姿態往往遠遠超出他們的時代。魯迅既是時代的先驅者,又是時代的先覺者,他沒有走完的路我們還要別無選擇地繼續走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我們的文學還沒有完成“人的覺醒”的歷史使命,魯迅思想及其創作就依然有繼續存在并被討論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21 世紀的今天,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連續性過程,我們依然行進在20 世紀以來“追求現代性”的歷史道路上。因此,今天談論魯迅及魯迅的意義仍然是必要的,我們需要通過闡釋歷史的魯迅而重新發現我們自己。這也許就是《啟蒙與革命》這本書值得我們關注與重視的理由所在。
[1]徐妍.新時期以來魯迅形象的重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0.
[2]趙歌東.啟蒙與革命:魯迅與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