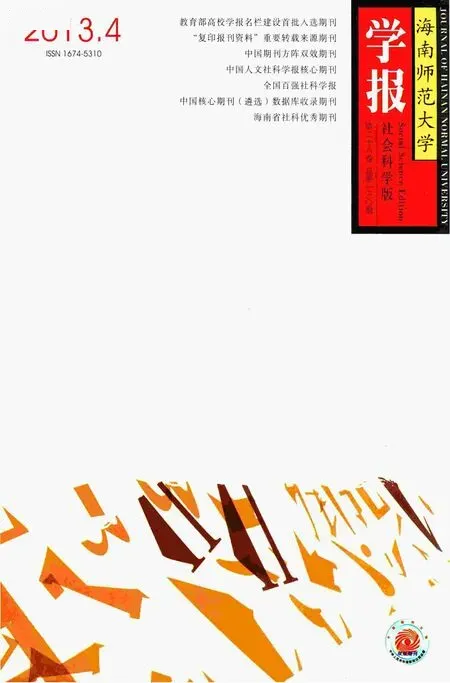現代作家筆名現象探究
殷 翔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筆名這個名詞源于西方的“pen name”,中國的近代國門被西方國家打開,報紙、雜志等新式媒體迅速發展,大量的文學刊物也在此時涌現,作家們經常署用筆名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許多作家的本名不為人知,筆名卻名聲在外。順便言之,同為文名,現代作家的筆名有別于古代的文人字號,古代的文人字號主要是文人自我標榜的符號,它具有固定性,現代作家的筆名更主要作家們掩飾真實身份的符號,它具有多變性,作家們筆名的數量之多,變換之頻繁,都是前所未有的。
從數量上看,筆名最多的10 位現代作家,第一是魯迅,①“魯迅”本是周樹人的筆名,但這筆名已經成為他的通用名,故在列舉作家時皆用通用名,下文皆如此。筆名213 個;第二是巴人,筆名132 個;第三是茅盾,筆名121 個;第四是周作人,筆名94 個;第五是夏衍,筆名75 個;第六是鄭振鐸,筆名71 個;第七是瞿秋白,筆名69 個;第八是王統照,筆名61個;第九是唐弢,筆名50 個,第十是沈從文,筆名47個。②以上統計參考徐迺翔、欽鴻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以下統計數據皆參考此書。以寫入《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213 位現代作家為例。其中只擁有1 個筆名或以本名為筆名的作家共10 位,占4%;擁有2 到10 個筆名的作家共123 位,占59%;擁有11 到20 個筆名的作家共47 位,占22%;擁有21 到30 個筆名的作家共15位,占7%;擁有30 個以上筆名的作家共18 位,占8%。可見,筆名的使用是現代作家文學活動中的普遍現象。
一
筆名的大量使用,是新的時代使然,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姓氏作為一種世襲品,是家族系統的標志,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名一旦被先人取下,也不能隨意變更。而“五四”時期,宗法制度受到強烈沖擊,姓名不再被看得那么神圣,有的人故意使用假名,還有更激進者主張廢除姓氏,馮文炳干脆以筆名“廢名”來宣示。“丁玲”這個筆名也是廢姓得來的,她原名蔣冰之,1921年丁玲來到上海平民女子學校讀書,一度廢姓用“冰之”名,后來“廢姓引起很多麻煩,只好隨便加了一個姓”,這個姓就是筆畫比較簡單的“丁”。1925年丁玲又萌發了當電影明星的念頭,于是改名“丁玲”,她說:“‘丁玲’毫無意思,只是同幾個朋友閉著眼睛在字典上各找到一個字作名字,‘玲’字是我瞎摸到的。”[1]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政府頒布了《報紙條例》、《出版法》、《報紙法》、《管理新聞營業條例》。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當局也出臺了《出版法》、《新聞檢查標準》。這些法律條例對文化出版物實行嚴格的檢查,作家們為了躲避文網,不得不變換筆名發表文章。1934年1月21日魯迅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了雜文《批評家的批評家》,使用的筆名是“倪朔爾”,這個筆名看起來有些古怪,后來有人解釋,“這個筆名是將英語Lusin(魯迅)的各字母依次倒寫,就成了Nisul(倪朔爾)。”[2]巴金1934年4月在《文學季刊》第1 卷2、3 期發表小說《龍眼花開的時候——一九二五年南國的春天》(即《電》),使用筆名“歐陽鏡蓉”,1934年4月《文學季刊》一卷二期發表散文《倘使龍眼花再開時》使用筆名“竟容”。在《〈愛情的三部曲〉總序》中巴金對這兩個筆名做過詳細說明。長篇小說《電》寫成后交給上海《文學》發表,刊物已將前兩章排好,但因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第一批清樣后,禁止發表。“我便又把小說帶到北平,決定在《文學季刊》上發表它。”“《電》在《文學季刊》上發表的時候分作了上下兩篇。題目改為《龍眼花開的時候》,另外加了一個小題目——一九二五年南國的春天。作者的姓名變成了歐陽鏡蓉。”“我當時要使讀者相信歐陽鏡蓉是一個生長在閩、粵一帶的人,《龍眼花開的時候》是費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在九龍寫成的一部小說,我甚至用了竟容這個名字寫了一篇題作《倘使龍眼花再開時》的散文,敘述我寫這部小說的經過。”[3]
刊物的編輯也經常變換筆名寫稿。1930年10月至1932年4月,老舍主持《齊大月刊》的編輯和出版工作,當時稿源嚴重不足,老舍便頻換挈予、挈青、舍予、舒舍予等筆名,自己動手湊稿子。編輯預約的寫稿者也如法炮制,巴人從1924年到1956年共使用了132 個筆名,其中在1937年就使用筆名72 個,使用這72 個筆名所寫的文章全部都是發在《立報·言林》上面。巴人說“在抗戰爆發前一年,我無以自活,《立報·言林》的編輯謝六逸同我相約,每月寫短評二十五則,致送酬金三十元,但不必署名,由編者自填。因恐引起獵狗之嗥嗥而不利于我。”[4]
二
更換筆名是為了掩蓋作者的真實身份,大多數筆名的取用卻并非隨意,經過作者的成熟思考后取的筆名,里面往往包含著命名者豐富的個人寄托。
胡適原名嗣穈,后改名胡適,他的許多筆名是由他的字“適之”演化而來,如“適庵”、“適廣”、“胡適之”。晚清時期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深的影響。在《四十自述》中胡適寫道:“有一天早晨,我請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兩字。后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5]
魯迅曾有過一個筆名“宴之敖者”,首見于1924年9月21日作的《〈俟堂專文雜集〉題記》。《故事新編》里面《鑄劍》中的主人公也叫“宴之敖者”。許廣平說:“宴之敖三字很奇特,查先生年譜,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載:‘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成,十一月修繕之事略備,與二弟作人俱迻入。’民國十二年,‘八月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十二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可見他是把八道灣屋買來修繕好,同他的兄弟迻入,后來才‘遷居’了的,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實。究竟為什么‘遷居’呢?先生說:‘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筆名表達了對那位弟媳的不滿。[6]
巴金年青的時候信奉無政府主義,曾留學法國追慕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有人認為“巴金”這個筆名是從他所崇敬的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事實并非如此有意。巴金在《談〈滅亡〉》中說:“有一個姓巴的北方同學(巴恩波)跟我相處不到一個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聽說他在項熱投水自殺。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殺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筆名中的那個‘巴’字就是因他而聯想起來的,從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個‘巴’字。‘金’字是學哲學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個時候我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前半部不多久,這部書的英譯本還放在我的書桌上,他聽說我說要找個容易記住的名字,便半開玩笑地說出了‘金’。”[7]
胡適、魯迅、巴金的筆名里面分別包含著對新的思想的追求、對兄弟感情失和的紀念、對友人不幸的緬懷和信仰寄托,這些情感是內指的。還有的筆名包含情感是外指的,這些外指的情感包含了對自我個性的張揚,對政治時局的態度,筆名將其突顯出來,比如郭沫若和蕭軍的筆名。
“愛牟”和“麥克昂”是郭沫若的筆名,“愛牟”是英語“I’m”的音譯,1924年郭沫若在《致成仿吾書》中首次使用這個筆名。1926年9月創造社出版的小說散文集《橄欖》,其中的《煉獄》、《十字架》、《行路難》、《未央》等篇也都以“愛牟”為作品主人公的名字,《橄欖》相當于郭沫若自傳性小說、散文集。“麥克昂”這個筆名首見于文藝論文《英雄樹》,發表于1928年1月《創作月刊》第一卷第八期。郭沫若說“‘麥克’就是英文maker 的音譯,‘昂’者我也,所以麥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張揚個性的時代精神于筆名中凸現。[8]
蕭軍原名劉鴻霖,他的筆名有“酡顏三郎”、“蕭軍”等。“酡顏三郎”這個筆名看起來象是日本人的名字,可以起到遮人耳目的作用,實際上卻有其內在含義。“酡顏”是酒后臉色發紅的意思,那正是他青春年少、紅顏赤頰的健壯體魄的一種恰當比喻。“三郎”則來源于他和兩個好友結拜,按年齡長幼他排行第三。“蕭軍”這個筆名是他在青島時期與魯迅通信時起的,取“蕭”為姓,是因為他喜愛京劇《打漁殺家》中的老英雄蕭恩,又因為他是遼寧省人,古時遼人多姓蕭;取“軍”作名,一則因為自己原本行伍出身,一個字可把他早年的經歷概括無遺,二則因為當時正處于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蔣介石調動白軍圍剿紅軍之際,他對此十分氣憤,為了表達自己對工農紅軍的感情,就把紅軍一詞一分為二,作了蕭紅和他的筆名。蕭紅和蕭軍的筆名相加,即是“小小紅軍”之意。[9]這可謂筆名政治的顯例。
三
筆名的使用又是和作品及作家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它可以與文學作品和文學活動聯系起來分析。從文學內部研究的角度看,把筆名視為文本闡釋的引線,可以利用它對文本進行進一步的闡釋。從文學外部研究的角度看,把筆名視為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的一個聯接點,可以借此研究文學作品產生的社會條件,認識這些條件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文學活動。
若把作品的正文視為正文本,就可把環繞在正文本以外的引語、題辭、注釋、筆名等視為作品的副文本,副文本既是文本的構成因素,又是正文本的闡釋因素。①“副文本”(peritext)的概念源自法國敘事學家熱奈特的《廣義文本之導論》(《熱奈特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是相對“正文本”而言的概念。從這個角度研究筆名對文本的闡釋有著重要意義,特別是作家使用新筆名發表新作品,筆名和作品之間往往具有互文性,可以“茅盾”、“逃墨館主”這兩個筆名為例。
茅盾原名沈德鴻,“茅盾”這個筆名首見于1927年9月《小說月報》上的小說《幻滅》。茅盾本來取筆名“矛盾”,后來經過《小說月報》主編葉圣陶的修改,筆名變成了“茅盾”,但加了“草”字頭并不能掩蓋其“矛盾”意蘊。茅盾說:“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為筆名?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漢又經歷了較前更深更廣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認識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會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結合茅盾小說的文本,他用“茅盾”這個筆名發表的三部小說(即《蝕》三部曲)確實反映了他說的各種矛盾,《動搖》中的劣紳胡國光與縣黨部的權力斗爭,反映著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特派員史俊與特派員李克處理店員風波和農民暴動的不同做法,方羅蘭的動搖與軟弱,反映出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靜女士感嘆“一方面是緊張的革命空氣,一方面卻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煩悶”,方太太自嘆“實在這世界變得太快,太復雜,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頭了!”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茅盾1927年夏在廬山失去了和黨組織的聯系,陷入了苦悶,這也是茅盾在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所以“矛盾”可視為解讀這個三部曲的關鍵詞。
再看“逃墨館主”這個筆名,這是《子夜》1932年1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時的署名,當時小說的題名為《夕陽》。“逃墨”二字出自《孟子·盡心下》:“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茅盾在自傳中稱:“我用‘逃墨館主’不是說要信仰陽朱的為我學說,而是用了陽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傾向于赤化的。《夕陽》取自前人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喻蔣政權雖然戰勝了汪、馮、閻和桂、張,表面上是全盛時代,但實際上已經在走下坡路了,是‘近黃昏’了。”[10]結合茅盾對《子夜》的寫作意圖的說法,他說這部小說同當時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有關。“當時的論戰者,大致提出了這樣三個論點:一、中國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革命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中,這是革命派。二、認為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應由中國資產階級來擔任,這是托派。三、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在夾縫中取得生存與發展,從而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子夜》通過吳蓀甫一伙終于買辦化,強烈地駁斥了后二派的謬論。”[11]這表明茅盾是傾向于第一派的,即革命派,印證了他對“逃墨館主”這個筆名的解釋,茅盾早就有“赤化”的傾向。
若將筆名視為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的一個聯接點,作為一種傳播策略,它的興起、高漲和衰退與新文學的發展進程有著密切的關聯。使用筆名的多是新文學作家,因為新文學在發軔期不見容于當時的主流文學話語,即舊文學話語,在這種情況下要爭奪文學話語權,新文學作家不得不署用假名發表文章,比如錢玄同與劉半農的“雙簧戲”。錢玄同在《新青年》第4 卷第3 號上以“王敬軒”的筆名發表反對新文學變革的文章,劉半農等一批新文學倡導者群起而攻之,一些不明就里的舊派文人站在“王敬軒”的立場上幫助“王敬軒”說話,而這恰恰是新文學倡導者設下的陷阱。通過與舊文學的論爭,新文學漸漸確立了其合法地位。
越來越多的新文學作家使用筆名發表作品,當作家用某一筆名發表的作品成為其代表作時,這個筆名往往會取代作家的真名成為他的通用名,并且成為他的象征資本。①象征資本,就是不管屬性怎么樣(無論哪種資本,有形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這種屬性被社會行動者所感知,他們能感受它,確認它使之有效。見皮埃爾·布爾迪厄:《實踐理性:關于行為理論》,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95 頁。魯迅用“魯迅”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之后,好評如潮,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就從未換過筆名;巴金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時署用筆名“巴金”,這個筆名就一直保留下來;“老舍”這個筆名是舒慶春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署用的筆名,這個筆名也成了他的主用名。筆名往往凝聚著作家的創作風格、作品特色,一個作家的筆名被廣大讀者認可,也就意味著這個作家所代表的文學傾向、審美趣味被認可。隨著新文學作家的筆名成為招牌式的通用名,筆名的作用已漸漸從對新文學作家真實身份的遮蔽轉向了對新文學作家“作家”身份的彰顯。
40年代,筆名浪潮開始衰退。從使用筆名最多的幾個作家來看,茅盾在20年代更換筆名20 個,30年代更換筆名16 個,40年代以后更換筆名19 個;巴人在20年代更換筆名8 個,30年代更換筆名120個,40年代以后更換筆名7 個;郭沫若在20年代更換筆名10 個,30年代更換筆名6 個,40年代以后更換筆名6 個;巴金在20年代更換筆名19 個,30年代更換筆名12 個,40年代以后幾乎沒有更換筆名,由此可見,“30年代末期以后,筆名使用的普泛化程度降低,筆名對文學發展的實質性影響銳減。中國現代文學的質地也發生了微妙的調整,如果說此前的新潮文學、白話文學與傳統文學比,充斥著挑戰者的姿態,那么此后,新文學已經成為了時代的新寵,那些‘以假亂真’、‘混水摸魚’的匿名發表作品策略都不必再用,新文學統治地位的取得與新文學家真名意識的膨脹相互協調、互相印證。”[12]
四
作為一種歷史沉淀物,披沙揀金,現代作家筆名仍然有挖掘的價值。通過筆名的考證可以確認文章作者的真實身份,對于文學史料的整理有很大幫助。通過發掘作家新的筆名,又可以藉此找到作家的佚文。無論是史料的整理還是佚文的發現,它們都可以充實、甚至改變作家在文學史上的論述。
1928年8月《創造月刊》2 卷1 期發表了一篇文藝批評《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作者署名“杜荃”。文章攻擊魯迅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st”等。此文發表多年一直無人知曉“杜荃”是誰,直到1979年有學者提出大量論據,論證“杜荃”即是郭沫若,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13]聯系到郭沫若某些筆名的含義,“杜荃”這一筆名的含義可試解為:杜,是郭沫若的母姓,郭沫若為紀念母親曾以母姓取過“杜衎”、“杜頑庶”、“杜衍”的筆名;荃,一種香草名,亦名“蓀”,屈原《離騷》有“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之句。作為一篇創造社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代表性文章,“杜荃”這個筆名的發掘,對于廓清“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詳情,以及研究郭沫若文藝思想的轉變,都有重要意義。
研究文章的署名可以確認文章的作者,發掘出作者的新筆名,又可以從新筆名下手,發現作家的佚文,佚文的發現可以充實對作家的研究。例如,《周作人筆名“牧童”及佚文兩篇》一文,②刊于《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 期,作者劉濤。通過閱讀北平《世界日報》1936年6月4日、5日《明珠》副刊,發現一篇散文《蒼蠅》,作者署名“牧童”,而《蒼蠅》是周作人早期散文的名篇,最先發表于《晨報副鐫》1924年7月13日,署名“樸念仁”,后又刊登于《小說月報》第15 卷12 號“文章選錄”欄,署名“周作人”。確認了“牧童”即是周作人,通過對“牧童”這一筆名的考察,研究者又發現了周作人用這個筆名發表的《抽煙與思想》、《都市的熱》這兩篇佚文。《“五四”女作家蘇雪林筆名考辨》一文,①刊于《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 期,作者王翠艷。通過對《益世報·女子周刊》上發表的新文學作品的筆名進行考辨,發掘出蘇雪林的“伽”、“病鶴”這兩個筆名,明確了《女子周刊》的主編兼主筆“伽”即蘇雪林。借助《女子周刊》的文章,又可以發掘蘇雪林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價值趨向,從而為探索以她為代表的過渡時代女性知識分子的復雜人格獲得第一手的可靠史料。就這一意義而言,蘇雪林以“伽”為筆名寫下的文章,不僅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及蘇雪林近80年的創作生涯中具有引人注目的開端地位,在蘇雪林本人的思想和精神發展史上亦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目前對作家筆名的研究多側重在筆名的收集與考證,或對某個有特殊意義的筆名進行闡釋。對現代作家筆名的研究,還存在著拓展的空間。筆名雖小,但是它包含著豐富的信息量,“筆名是文本的一部分,它不是空洞無物的能指,而是作者所處時代、自身經驗和身份的多棱鏡。轉動這面鏡子,我們看到的是文本正文暗示過但又無法企及的無數其他文本。”[14]對在創作的不同階段使用筆名較多的作家,研究他們的筆名,發掘新的史料,對作家的研究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幫助。
[1]丁玲.丁玲文集:第10 卷[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100.
[2]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92.
[3]巴金.巴金選集:第4 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455.
[4]王任叔.巴人雜文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521.
[5]胡適.四十自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7.
[6]許廣平.許廣平文集:第2 卷[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46.
[7]巴金.巴金選集:第10 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1.
[8]郭沫若.郭沫若文集:第8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286-287.
[9]紀維周.蕭軍筆名的由來[J].世紀,2005(4).
[10]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505.
[11]茅盾.茅盾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560.
[12]袁國興.隱身與遮蔽:“筆名”對發生期中國現代文學質地的影響[J].文學評論,2009(3).
[13]單演義,魯歌.與魯迅論戰的“杜荃”是不是郭沫若[J].西北大學學報,1979(10).
[14]朱桃香.副文本對闡釋復雜文本的敘事詩學價值[J].江西社會科學,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