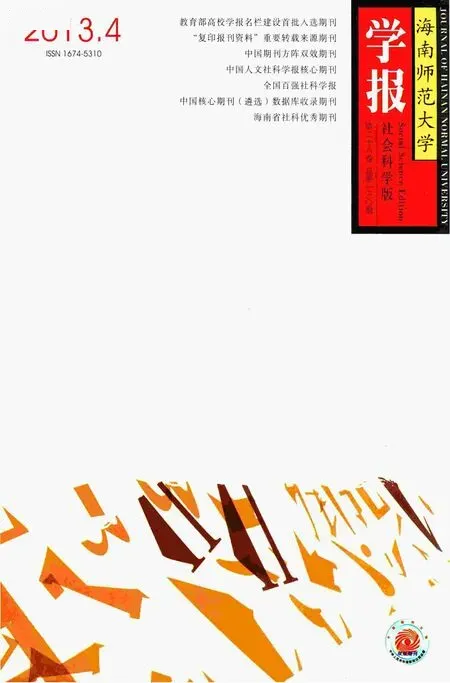從“集體記憶”中突圍:“后革命”視域下的“文革”書寫
馮 雷
(北方工業大學 文法學院,北京 100144)
假如說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是現代性的追求的話,那么革命其實也是一種追求現代性的方式。然而在全球化、一體化的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和產業工人階級的迅速萎縮,革命似乎成了一個歷史的玩笑。在現代化軌道之內,伴隨著發展民族經濟成為新的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理想和徹底改造社會的革命性政治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了明日黃花。當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逐漸取代革命的豐功偉績而成為政權合法性更有力的佐證時,“后革命”的歷史反思和文學表達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革命,固然體現為炮火連天、坼天陷地的軍事斗爭,但是革命的影響卻并不會隨著軍事斗爭的偃旗息鼓而煙消云散,其發酵與揮發是一個更為內在和長久的過程。具體到中國來講,“革命”便成為一個不斷“擴容”的詞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被公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標志,由此,中國大陸基本告別了烽火硝煙的軍事戰爭年代而逐步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①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9 頁。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又給中國上緊了階級斗爭的發條,直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的發生,才促使晚年毛澤東“文革”政治理想逐漸瓦解。[1]但也有學者認為應當把時間下限再稍稍后延,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經過短暫而又漫長的“在徘徊中前進”,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了極“左”路線,“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斗爭基本結束”,②見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5 頁。這本來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做出的判斷,但是隨著后來的“反右”擴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展開,這一正確判斷卻被否定了。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對這一判斷重新予以確認。“全黨工作的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2]因而從1978年開始,革命才真正成為歷史。[3]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則把中國革命延長到了1980年代中期。[4]1985年,他把自己對中國革命系統觀察、思考全部付諸書稿,當然這不是全部的原因,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一書不如說是延續了他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對中國革命的思考。在他眼中,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是一段在西方影響下、漫長而充滿顛簸的“現代化”的過程,所以他才把回望歷史的眼光一直上溯到1800年,所以具有豐富言說性的“文革”才是“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所以中國革命也并不因為“文革”的結束而結束。事實上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整肅說明政治禁忌依然極其敏感。80年代末的蘇東劇變又一次刷新了人們對于歷史和革命的認識。在汪暉看來,1989是一個真正的歷史性的界標,它不僅標志著暴力革命時代的終結,而且預示著國家屬性的微妙改變,“兩個世界變成一個世界: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國社會的各種行為,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甚至政府行為,都深刻地受制于資本和市場的活動”。[5]中國由此真正進入“后革命”時代。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無疑大大強化了赤色“革命”時代的終結感。中國語境下,革命話語的讓渡是如此的一波三折,則“后革命”的到來和訴求又怎能不分外“曖昧”?
因此,對于中國革命來講,你死我活的、軍事斗爭形態的革命已經終結,可是革命的理想和記憶卻并未終結,并且還于有形和無形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革命的影響和作用泅渡穿過逐漸成為歷史記憶的“文革”和正在進行中的“改革”直達現實生活的岸邊,于是乎“文革”便成為中國語境下“后革命”不應忽略的一個部分。
一 理想主義的浮橋
對于“文化大革命”,“新時期文學”采取了與主流政治相合作的態度。文學幾乎是毫不遲疑地共享了高層政治對于“文革”的歷史解釋——主流政治對于“文革”的時間界定不僅成為文學史分期的又一重要坐標,而且在立場、態度上,文學和政治一樣,也把“文革”視為是歷史的倒退,對“文革”的揭批、控訴以及所謂的“反思”也成為“新時期文學”最初的情感主調。時至今日,“文革”已然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一個特殊的、重大的題材領域,如許子東所說“如何回憶和敘述文革的過程與細節,如何梳理和解釋文革的來源與影響,這是一個很少中國(特指大陸,下同)當代作家能夠忽視和回避的題目”,[6]1-2幾乎所有“文革”之后的重要作家都曾貢獻過他們各自對于“文革”的回憶和思考,當然,這些表態和反思必然是順應主流政治的。于是,“文革”的歷史成為中國文學乃至中國社會一段非常特殊的“一體化”的集體記憶,“文革”總是意味著政治陰謀、經濟崩潰、文化頹敗以及人性的深淵,這些關鍵詞同許諾光明、美好“未來”的革命背道而馳。這或許可以理解為,在“新時期文學”的“模板”上,“文革”同“革命”是必須嚴格區分開的,“文革”是對革命理想的盜竊和歪曲,是“五四”以來種種人文精神的跌落,總之,至少在文學領域里,“文革”的“債”不能記在“革命”的“賬”上,相反,革命理想是要繼續弘揚的——在80年代,宏大者如“四項基本原則”和被喻為“革命”的種種改革,精微者如教育中小學生每天在“革命”的名義下“保護視力”,進入90年代,當市場化浪潮襲來之時,革命理想又同商業運作、大眾文化結合,隨“主旋律”作品之風潛入千家萬戶豐富的夜生活之中。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文革”題材的創作或者說文學對于“文革”的態度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許多作品主動將“文革”和“革命”對接起來。例如紅極一時的《亮劍》(都梁,2000)、《歷史的天空》(徐貴祥,2000)、《英雄無語》(項小米,1999)等“老兵新傳”,“革命”時期的揮斥方遒和“文革”期間的耿直不屈共同譜寫了“老兵”們的英雄傳奇,而且正由于作品的前半部分即“革命”年代里“老兵”們生龍活虎、出生入死的傳奇經歷的映襯,“老兵”們隨后在“文革”歲月中的凄苦遭遇便顯現出為理想而殉難的品質。隨著李云龍們晚年將星閃耀、修成正果的“大團圓”結局,“老兵”們被“正典化”,革命理想、革命情懷穿越了革命和“文革”兩個時期,經受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考驗,最終重新得到弘揚。“文革”期間,趙剛在批判大會上慷慨陳詞:
我趙剛1932年參加革命,從那時起,我就沒有想過將來要當官,我痛恨國民黨政府的專制和腐敗,追求建立一種平等、公正、自由的社會制度。如果我以畢生精力投身的這場革命到頭來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這黨籍和職務還有什么意義呢?[7]
盡管“文革”依舊是作為歷史的錯誤部分而受到批判,但“文革”和“革命”卻由于共同的“理想主義”精神而發生了深刻的聯系。“文革”和“革命”之間原本清晰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曖昧了,這是當初“新時期文學”里所不曾有過的。同樣,在《舊址》(1993)、《圣天門口》(2005)、《山河入夢》(2007)等“歷史追問和質詢”中,也紛紛把“文革”和“革命”合在一起作為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而這種結合相比較于“老兵新傳”又往往體現出某種自覺的思考和探索。對于李銳而言,《舊址》也好,《銀城故事》(2002)也罷,都是圍繞探求“文革”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而展開的。①李銳在一篇訪談中講到:“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成為這些苦難追問的中心。我用不同的人物,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去反復地追問和表達……而我的銀城系列,還是這樣的追問,但更多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展開的。”參見李銳、鐘紅明:《〈銀城故事〉訪談——代后記》,《銀城故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 頁。而《圣天門口》我想除了體現出劉醒龍的抱負之外,還體現出他相當的耐心,他以七十多年的時間跨度來描述和思考革命理想、革命理論的是是非非,這種思考集中體現在傅郎西這個人物上,從早年的熱衷于暴動和殺戮,到晚年幡然醒悟,否定暴力但不否定革命。這樣,“文革”和“革命”之間的聯系就不僅僅只是故事時間上的對接,而是體現為更為深入、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的演變,于是“文革”和“革命”二者渾然一體,就此而言,在“文革”與“革命”的整合方面,或者說在對“新時期文學”“斷裂”式的認識框架的破除方面,《圣天門口》是我所讀過的諸多小說當中做得最好的。在這些作品里,“文革”和“革命”之所以能夠被貫通,其中最重要密鑰便是以激進的“革命理想”為浮橋,不露痕跡地跨越“經驗”和“教訓”之間的天塹。在“老兵新傳”里,革命理想在“文革”時期“落難”,“革命”成為一份“被背叛的遺囑”。而在劉醒龍、李銳那里,“文革”則是導源于“革命”這一現代性工程內部的缺陷、漏洞,是這些缺陷、漏洞不斷升級、擴大而又遲遲沒有得到有效修正的歷史必然結果。事實上,黨的官僚化和知識分子的貴族化是革命勝利之后毛澤東最為擔心的問題,②參見黃平、姚洋、韓毓海:《我們的時代——現實中國從哪里來,往哪里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83 頁。因此在革命陣營內部要整風學習“繼續革命”,而對于知識分子則必須進行史無前例的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所以“文革”的爆發便不能不說是出于高層政治的特殊考慮,是“革命內部的革命”,也不見得就是歷史的無厘頭鬧劇。至于說“文革”在其中后期瀕于失控,則自然是背棄了高層政治和革命理想的初衷。換個角度來看,“文革”很明顯承襲、發揮了“革命”的負面效應,李澤厚、劉再復把這些負面效應具體化為“迷信意識形態”和“迷信斗爭經驗”,[8]而“文革”在話語宣傳方式和社會組織、動員方式上也同“革命”如出一轍,這樣一來,“文革”和“革命”便無法截然分開,“新時期文學”的基本認識框架便宣告失效。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文革”可以而且也應當被作為“革命”的一部分,重新進行反思,但是反思“革命”很明顯同反思“文革”不是一回事,于是談及“后革命”時又該如何吞咽“文革”這塊思想和文學的飛地呢?
二 “集體記憶”的代價
事實上,“新時期”以來,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開始,當代作家便開始不斷地敘說“文革”、回憶“文革”、思考“文革”,并且在現代性觀念的慫恿之下,他們的寫作通常也被視為是不斷進步、不斷深化,取得了豐碩成果的。相比較于威嚴的政治文件,個人化的文學作品更具親和力也更具感染力,“新時期”以來的“文革”題材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參與了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的創造過程”[6]3。但是如前所述,從一開始,“新時期文學”就毫不猶疑地接受了高層政治對“文革”的解釋,因而文學想象催生的“集體記憶”莫不如說是在政治意識要求下形成的一種自我撫慰:“‘文革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兼有歷史記載、政治研究、法律審判及新聞報道的某種功能,而且這些‘故事’的寫作與流通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政治、法律、傳媒乃至民眾心理的微妙制約。”“這種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與其說‘記憶’了歷史中的文革,不如說更能體現記憶者群體在文革后想以‘忘卻’來‘治療’文革心創,想以‘敘述’來‘逃避’文革影響的特殊心理狀態。”[6]3今天看來,80年代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幾乎全部都是“憤怒”和“控訴”的文學,這些“憤怒”和“控訴”的矛頭當然是指向“文革”的,但“文革”從何而來?起碼從作品中來看,作者們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文革”是因為“四人幫”、林彪反革命集團。這樣,在文學參與形成的“集體記憶”之中,“文革”這個歷史的毒瘤便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是因為一些人為的原因而導致的,“文革”“被記憶”為一個“人性惡”的深淵,或者說人們往往自動地從“人性惡”的角度、從“個人陰謀”的角度去清算“文革”。裴曉云、劉麥克(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1982)理想與生命的終結,錢文(王蒙:“季節系列”)的失落和彷徨,高愛軍、夏紅梅(閻連科:《堅硬如水》,2001)的迷狂和驚悸等等,這些“文革”記憶所共同宣泄的其實都是“文革”對個體心靈和個人命運的戕害,毫無疑問,這樣的“文革”“集體記憶”當然是真實的,但或許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文革”“集體記憶”更加“正確”——“它們不僅從對幸存者們的有用性這個意義上說是正確的,而且從社會接受性這個意義上說也是正確的。”[9]也就是說,“文革”“集體記憶”的“真實”是以“忘卻”許多追問和質疑為代價的,而那些被“忘卻”的部分又往往被劃定為“不正確”、“不合適”,從而長久地擱置在一個背光的世界里。換句話說,“新時期”以來的“文革”“集體記憶”都是在就事論事式地討論“文革”,就“文革”而論“文革”,而對歷史的結構性問題并沒有能進行更多的思考和追問。關于“文革”的“集體記憶”是被限定在一種單一的認識和闡釋框架之內進行的,這一框架被賦予了權威、客觀、科學的重重魅影,因而鎖閉了其它認識和闡釋的可能空間,希望藉此來維系對歷史的闡釋方式及其有效性。但歷史從來都不是斷裂式的,而是動態聯系著的,順著“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追問,順理成章地便可發問道:沒有“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沒有革命化的“左翼”文學和“十七年”文學,又何來“文革”文學?但恰恰是在這里,關于“文革”的“集體記憶”止步不前,這使得“文革”成了一件“無頭”公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不禁覺得盡管距離“文革”結束已經過去快40年了,可是對“文革”的反思力度卻有必要重新估量,反思的角度和向度也還有待重新尋找和調整。在“后革命”的召喚之下,費盡心機地去討論和解讀那些反映“文革”的小說實屬徒勞,它們那原地轉圈的方式離所謂的“徹底”反思實在相距太過遙遠。
并且在我看來,當前這種“集體記憶”的羸弱和不徹底或許恰好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今天,在“文革”過去快40年之后,“新左派”會傲然崛起,他們當中不乏其人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為“文革”翻案、為“兩條路線的斗爭”辯護。當然,他們的論辯方式也很獨特,他們往往是把“文革”和“毛澤東思想”、和“革命”進行對接,從“革命”形勢發展的角度來梳理“文革”的必然和必要,于是“文革”便自然成為“革命”棋盤上的一枚棋子。這種“對接”同前面討論到的文學作品里的對接可謂殊途同歸。很明顯,這種“對接”同“新時期”以來的歷史模版是相抵觸的,同“文革”的“集體記憶”也是不相容的。因而,這種“對接”難道不應當視為是對舊有的社會“集體記憶”的一次突圍嗎?由此又使我想到“季節系列”和《堅硬如水》等“文革”題材的小說里,大量對“文革”話語和口號的借用。這其中的諷刺、鞭撻之意不言而喻,只是鞭子是打在“文革”的屁股上,而真正受罪的又該是誰呢?
三 “文革”書寫的“后革命”追認
另一方面,近年來“文革”題材的作品本身也發生了許多饒有趣味的變化。
每個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在這有限的生命當中青澀而短暫的青春年華無疑是最為美好和寶貴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革”當中受害最深的是裴曉云、錢文、王二(王小波:《黃金時代》等)、高愛軍、夏紅梅等這樣的“青年人”,他們的理想被撕碎,他們的青春被擱淺,他們的生命被荒廢。而在當前“文革”題材的作品里,主人公往往比這些“青年人”更加年輕,簡直就是一群孩子,比如《生逢1966》(胡廷楣,2005)里的瑞平和蓓蓓(兩人都不滿19歲①陳瑞平“要到今年冬天才到19 歲”,蓓蓓“還要小一點,要到明年過年才是19 歲”。參見胡廷楣:《生逢1966》,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 頁。),《啟蒙時代》(王安憶,2007)里的南昌(約十六七歲②南昌“在相對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參見王安憶:《啟蒙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 頁。),《兄弟》(余華,2008)里的李光頭和宋鋼(李光頭14 歲,宋剛15 歲[10]),《沉默之門》(寧肯,2004)里的李慢(13 歲,小學六年級[11]),《英格力士》(王剛,2004)里的劉愛、李垃圾(小學五年級[12]4),《扎根》(韓東,2003)里的小陶(約八九歲③“小陶生于三年困難時期”,而故事發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參見韓東:《扎根》,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5、第3 頁。),甚至于在《大浴女》(鐵凝,2000)和《蒙昧》(柯云路,2000)里,主人公尹小跳、尹小帆和茅弟在登場之初竟還是童蒙未啟的少兒。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對“文革”的反思逐漸從偏重于政治層面逐漸滑向偏重于心理層面,從與主流政治共享若干重要歷史前提和框架的階段滑向歷史開掘、反思的個人化時期?值得注意的還有,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沉痛、凝重相比,當前新一批“文革”題材的作品的內在氣質和情緒則表現得相當平靜甚至是輕松。假如說在《英格力士》里,劉愛把“Long Live Chairman Mao”記作“狼立屋前門毛”[12]24只是王剛偶一為之、小說雖然局部不失戲謔而總體仍然嚴肅的話,那么在《漫游革命時代》(2007)里,“我”把英語的“毛主席萬歲”記作“狼禮服前門貓”[13]112則想必近乎于林白“文革”經歷的真實狀態,在林白的《致一九七五》(2007)和《漫游革命時代》兩部長篇小說里,“文革”不再意味著血腥和恐怖,插隊、下鄉也不再等同于勞動和絕望,如小說題目所示:“漫游”,這其中透露著從容、輕松、自由和歡快——“我早已厭倦家庭和父母,想著早些到那個叫做‘廣闊天地’的地方去”,[13]103實際上這也正是作品呈現出來的情感基調。與之相類似的是,在《扎根》、《沉默之門》等小說里,作者不再以渲染“苦難”、“悲痛”為能事,相反表現出相當的柔緩、平靜的韻味。而在《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血色浪漫》(2004)以及《與青春有關的日子》(2006)里,“文革”則幾乎完全等同于狂歡,作為“黑五類”之列的、受到沖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鐘躍民并不像在“新時期文學”里那樣郁郁寡歡、惶惶不可終日,而是和鄭桐、袁軍等年輕人一起獲得了空前的“解放”,這同80年代初期“文革”題材、“知青”題材的作品形成了何其鮮明的對比!
而更耐人尋味的是,經歷了二三十年的所謂批判、反思之后,“文革”時期的話語符號居然在文化市場上出現“回潮”和“復興”:革命老歌的復制和熱銷(例如1993年的《“紅太陽”:毛澤東頌歌新節奏聯唱》①包括《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翻身農奴把歌唱》、《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陽》、《亞克西》、《八月桂花遍地開》、《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戰士歌唱東方紅》、《情深誼長》、《頌歌獻給毛主席》、《祖國頌》、《日夜想念毛主席》、《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我愛北京天安門》、《中華兒女志在四方》及《紅軍戰士想念毛主席》、《蝶戀花 答李淑一》、《受苦人拿起槍鬧革命》、《紅燈頌》、《眾手澆開幸福花》、《我愛這藍色的海洋》、《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萬泉河水清又清》、《想念毛主席》、《滿懷深情望北京》、《紅梅贊》、《毛主席派人來》、《大紅棗送親人》、《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北京有個金太陽》共30 首歌曲。),“樣板戲”、“紅色經典”的改編和熱議,取代了如來、觀音而搖曳在汽車駕駛室后視鏡上的革命偉人照片,以及大量粗制濫造的、印有毛澤東、雷鋒以及切·格瓦拉頭像的綠色軍用帆布書包,真可以說“紅太陽熱”、“毛澤東熱”、“紅色經典熱”、“紅色旅游熱”、“文革文物熱”是一浪接著一浪。當然這背后的文化寓意是十分復雜的,有的是激動的懷舊,有的是商業利益的表達,有的則純粹是政治波普。現實生活中對于“文革”的不同態度的對峙也殊為有趣,老干部、老教授們為“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而搖旗吶喊,文壇每有新作出版便欣然命筆評說一二,現實生活的不平和不滿則大大激發了彌漫在中年群體中的“文革”懷舊情緒,對于更為年輕的一代來說,“文革”是“聽說過沒見過”(崔健的歌詞)的“新長征上的搖滾”——“‘文革’都成歷史了,還要讓人沉重多久啊”。②這是《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張藝謀后擬定的新聞稿的題目,并非張藝謀的原話,題目與張藝謀的原意略有不同,但出入不大。張藝謀的原話是:“你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改變,我們中國人幾乎從‘文革’的陰霾中走出來了。我們的80后90 后已經把‘文革’看做歷史了,如此長的一個十年浩劫,中國民族都挺過來了,那場政治運動觸及到人人的靈魂啊,我們都可以走出來。”參見夏辰、張英、俞崢:《“文革”都成歷史了,還要讓人沉重多久啊》,《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這究竟該說是老干部、老教授們刻舟求劍、落伍得有些可愛,還是文藝達人、潮人洞明世事,超前得近乎玩世不恭呢?是商業文化對民族夢魘的可怕洗腦,還是社會框架對“集體記憶”的有意“催眠”呢?但不管怎么說,與“革命歷史”題材的“后革命”改寫幾乎同步,“文革”題材的作品也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形,這種“同步”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是當代的文化意識把“文革”追認作了“革命”的一部分,從而溢出了“集體記憶”之外呢?如果我們承認“文革”可以作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應當把“文革”放置在“革命”思潮之中來予以反思的話,那么顯然“后革命”也理當包括對“后文革”的整合,只是鐘躍民他們“無處安放的青春”又當如何填充進“后革命”的格局當中呢?如何才能克服“文革”的改寫之于“后革命”的那種方枘圓鑿的尷尬呢?
[1]祝東力.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轉折[J].批判與再造(臺灣),2005(16):17.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C]//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
[3]任劍濤.后革命與公共文化的興起——《后革命時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J].開放時代,2007(2).
[4]〔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M].劉尊棋,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5]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M]//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42.
[6]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 篇文革小說[M].北京:三聯書店,2000.
[7]都梁.亮劍[M].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395.
[8]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M].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84-102.
[9]〔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有多真實? [M]//〔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社會記憶.季斌,王立君,白錫堃,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66.
[10]余華.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2,1.
[11]寧肯.沉默之門[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27.
[12]王剛.英格力士[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13]林白.漫游革命時代[J].西部華語文學,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