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藏記》貶損了商人嗎?——關(guān)于《論〈東藏記〉的誤區(qū)》的誤區(qū)
楊 惠,方維保
(安徽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安徽 蕪湖 241000)
自宗璞最新力作《西征記》發(fā)表以來(lái),其長(zhǎng)篇系列小說(shuō)《野葫蘆引》自2005年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以后再次獲得關(guān)注。重新閱讀《野葫蘆引》的前兩部《南渡記》和《東藏記》,不由平添幾分溫故而知新的喜悅,理解了許多當(dāng)年未曾注意的細(xì)節(jié)。然而當(dāng)閱讀到柴平的評(píng)論文章《論〈東藏記〉的誤區(qū)》,卻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對(duì)《東藏記》的批評(píng)有些強(qiáng)詞奪理,讓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柴平的《論〈東藏記〉的誤區(qū)》(下稱柴文)最主要的觀點(diǎn)是,認(rèn)為《東藏記》有崇儒抑商傾向,“充斥著大量的賤商話語(yǔ),呈現(xiàn)出明顯的思想方面的缺陷。……從文本中可以看出,對(duì)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捍衛(wèi),使宗璞以保守主義態(tài)度對(duì)待西方文化資源……”[1]為了證明這一觀點(diǎn),柴文列舉了幾個(gè)例子,“在小說(shuō)中,她讓在資源委員會(huì)做經(jīng)濟(jì)情報(bào)的掌心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對(duì)在課余賺外快過(guò)舒適生活的教師尤甲仁冷嘲熱諷,最為明顯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極力貶低、嘲諷商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丑化歪曲商人呂香閣的形象。”[1]
小說(shuō)《東藏記》果真貶損了商人嗎?要弄清楚這部小說(shuō)是否貶損了商人,就必須對(duì)其中三個(gè)人物命運(yùn)及其最終結(jié)局進(jìn)行分析,也必須追溯到《南渡記》,將兩部小說(shuō)看成一個(gè)前因后果的序列,才能真正完整地還原小說(shuō)人物的命運(yùn)。
一 關(guān)于“掌心雷”的死亡問(wèn)題
《野葫蘆引》系列整體風(fēng)格繼承《紅樓夢(mèng)》,①關(guān)于《南渡記》對(duì)《紅樓夢(mèng)》的繼承吸收,可參看卞之琳:《讀宗璞〈野葫蘆引〉第一部〈南渡記〉》,載《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1989年第5 期。以含蓄典雅為主,對(duì)于一件事情的交待往往“草蛇灰線”,伏筆千里,一兩句話點(diǎn)到為止,很少大喊大叫地說(shuō)明,只讓讀者以耐心和慧心來(lái)暗自忖度。“掌心雷”的人生就是在這樣的敘事中完成。
“掌心雷”本名仉欣雷,“掌心雷”是由其本名諧音而起的外號(hào),從《南渡記》到《東藏記》,他露面的機(jī)會(huì)不多,但有限的幾次出場(chǎng)都或隱或顯地暗示了他對(duì)明侖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孟樾長(zhǎng)女峨的愛(ài)慕以及峨對(duì)他的無(wú)動(dòng)于衷。仉欣雷在《南渡記》開(kāi)頭第一次出現(xiàn)時(shí),是明侖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系二年級(jí)學(xué)生,“七·七事變”前一天晚飯后,來(lái)孟家看望剛剛中學(xué)畢業(yè)的峨。在稍后的篇章里小說(shuō)及時(shí)暗示了峨對(duì)父執(zhí)明侖大學(xué)生物系教授蕭澂的暗戀,已經(jīng)預(yù)示這兩人愛(ài)情的不可能。在《東藏記》里,仉欣雷大學(xué)畢業(yè)前,請(qǐng)峨幫助決定畢業(yè)去向,是去香港與家人團(tuán)聚還是去重慶的資源委員會(huì),而最終促使他做決定的,僅僅是因?yàn)槎腚S口說(shuō)出的一句話“資源委員會(huì)……似乎和二姨夫有點(diǎn)關(guān)系”[2]138。最后一次出現(xiàn)則是他的意外死亡。峨隱晦地向蕭瀓表示自己對(duì)他多年的暗戀,被友好而明確地拒絕后,在極度痛苦和迷亂中,遇到從重慶來(lái)的仉欣雷。他向峨求婚,峨毫不遲疑地答應(yīng)了。兩人第二天去拜見(jiàn)峨的父母,不料為躲避迎面而來(lái)的軍車滾落懸崖,峨受傷,仉欣雷身亡。
由此可見(jiàn),仉欣雷確實(shí)是“突然死亡”,但絕非“莫名其妙”,從情節(jié)上來(lái)說(shuō)源于一場(chǎng)意外的交通事故,而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則源于他在追求一份不屬于自己的感情。峨對(duì)他自始至終很冷淡,毫無(wú)愛(ài)戀可言,他們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對(duì)好情侶、好夫妻。仉欣雷在小說(shuō)里一如峨所說(shuō),是一個(gè)比較注重現(xiàn)實(shí)存在的俗人、好人,缺乏超脫現(xiàn)實(shí)的崇高理想,但也正是這個(gè)俗人,一直在堅(jiān)持追求一份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愛(ài)情,從北平追到昆明,無(wú)論峨對(duì)他多么冷淡他卻從不退縮,這恐怕是他凡俗人生中最不俗的一面。而峨則完全是另一種人,本性上她生性怪癖,沉默寡言、耽于幻想;感情上她從少女時(shí)代起一直暗戀蕭瀓,對(duì)仉欣雷毫無(wú)好感。以《東藏記》第一章為例。峨突然邀請(qǐng)妹妹嵋陪她一起上晚上的大二公共英語(yǔ)課,嵋在課堂上見(jiàn)到了仉欣雷,而他比峨高兩個(gè)年級(jí)。下課后仉欣雷對(duì)嵋解釋說(shuō)自己因?yàn)槿闭n太多需要補(bǔ)學(xué)分才來(lái)上課的,不管這個(gè)解釋是真是假,仉欣雷從香港來(lái)到昆明,顯然與峨有關(guān),他想接近峨的追慕心理顯露無(wú)遺,而這也正是峨突然請(qǐng)嵋陪她上課以躲避仉欣雷的原因。
無(wú)論從哪個(gè)方面來(lái)看,仉欣雷和峨都是兩個(gè)完全不相容的個(gè)體,但這兩人在追求不可能屬于自己的愛(ài)情上的執(zhí)著和執(zhí)拗,卻又有幾分相似。而那結(jié)局,早已注定是一場(chǎng)空,正如峨所求的簽上的偈語(yǔ)“強(qiáng)求不可得,何必用強(qiáng)求!隨緣且隨分,自然不可謀。”[2]143他倆之所以能夠訂婚,對(duì)于峨是強(qiáng)求失敗后的心灰意冷,對(duì)于仉欣雷則是陰差陽(yáng)錯(cuò)的偶然驚喜,完全是生命軌跡剎那錯(cuò)位產(chǎn)生的相交,他們的訂婚帶來(lái)的必然不是幸福而是悲劇,所以小說(shuō)才安排了仉欣雷突然死亡的慘劇,以了結(jié)這本不應(yīng)該存在的勉強(qiáng)至極的婚姻。這并非是作者用佛家語(yǔ)故弄玄虛,而是因?yàn)樗麄儌z都在“強(qiáng)求”一份不屬于自己的感情,即使勉強(qiáng)求得,也終因違背了現(xiàn)代婚姻最基本的“自然”——兩情相悅的愛(ài)情,終將是鏡花水月,此所謂“強(qiáng)求不可得”。相比之下,小說(shuō)中另一個(gè)同樣為情所困的女孩吳家馨,也求得了和峨同樣的簽,最終通過(guò)仉欣雷的死亡徹底了悟強(qiáng)求一份感情的可怕。因此,仉欣雷的死是必然的,不通過(guò)這種方式意外死亡,也會(huì)被無(wú)愛(ài)的婚姻所窒息,絕不是“莫名其妙”。
而按照柴文的意思,宗璞之所以安排仉欣雷死亡,是因?yàn)樗谫Y源委員會(huì)里做經(jīng)濟(jì)情報(bào)工作,屬于商人一流,其實(shí)這是柴文對(duì)“資源委員會(huì)”望文生義的誤解。
“‘資源委員會(huì)’是南京國(guó)民政府興建和經(jīng)營(yíng)國(guó)家重要工礦企業(yè)的重要經(jīng)濟(jì)機(jī)構(gòu)。其前身是國(guó)防設(shè)計(jì)委員會(huì),1932年10月成立,……隸屬國(guó)民政府參謀本部,……主要任務(wù)是從事軍事、國(guó)際、財(cái)經(jīng)、文教、工礦、交通、農(nóng)林、地貿(mào)、資源等方面的調(diào)查研究和撰寫(xiě)各項(xiàng)專題報(bào)告。1934年4月,改組為資源委員會(huì),隸屬軍事委員會(huì),……主要職能已由調(diào)查研究轉(zhuǎn)為國(guó)家重工業(yè)建設(shè)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機(jī)構(gòu)。……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1938年3月,改屬國(guó)民政府經(jīng)濟(jì)部,……主要任務(wù)是創(chuàng)辦和經(jīng)營(yíng)管理基本工業(yè)、重要礦業(yè)和電力事業(yè)以及主持戰(zhàn)時(shí)工業(yè)的內(nèi)遷。……它對(duì)中國(guó)資源的調(diào)查研究與開(kāi)發(fā)、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工業(yè)基礎(chǔ)的奠建,對(duì)先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的引進(jìn)、以及抗戰(zhàn)的勝利都作出了貢獻(xiàn)。”[3]①關(guān)于“資源委員會(huì)”的發(fā)展始末,還可參看鄭友揆著作《舊中國(guó)的資源委員會(huì)——史實(shí)與評(píng)價(jià)(1932—1949)》,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1年。
可見(jiàn),資源委員會(huì)前期主要是為國(guó)民政府提供經(jīng)濟(jì)信息的咨詢機(jī)構(gòu),后期則主要是管理國(guó)家重工業(yè)的經(jīng)濟(jì)部門(mén)。仉欣雷本是經(jīng)濟(jì)系學(xué)生,畢業(yè)后進(jìn)入資源委員會(huì)堪稱對(duì)口就業(yè),而其從事的經(jīng)濟(jì)情報(bào)工作也并非經(jīng)商。而柴文卻無(wú)視小說(shuō)已經(jīng)明確暗示的前因后果,硬將仉欣雷的死歸結(jié)于作家對(duì)這個(gè)從事經(jīng)濟(jì)工作的人的貶低和蔑視,是不實(shí)的。
二 關(guān)于對(duì)尤甲仁的冷嘲熱諷
不可否認(rèn),《東藏記》對(duì)于明侖大學(xué)教師尤甲仁的冷嘲熱諷是非常明顯的,但原因并不在于其“在課余賺外快過(guò)舒適生活”。我們完全可以舉出反證,小說(shuō)里不止一次提到明侖大學(xué)的師生由于貧困而在校外兼職,《東藏記》第一章第三節(jié)明侖大學(xué)教師李漣“說(shuō)起給學(xué)生發(fā)放貸金的事。……法幣貶值,物價(jià)漲得快,伙食愈來(lái)愈糟。有些學(xué)生開(kāi)始找事做,看來(lái)找事的會(huì)愈來(lái)愈多。……‘最近有一個(gè)藥店要找個(gè)會(huì)計(jì),也就是記賬,很好學(xué)。好幾個(gè)學(xué)生爭(zhēng)著去,叫我很難辦。’”[2]30不但聯(lián)大學(xué)生到處找事掙錢吃飯,聯(lián)大的老師也迫于生計(jì)不得不賺外快貼補(bǔ)家用,如數(shù)學(xué)系教授梁明時(shí)也到聯(lián)大師范學(xué)院設(shè)立的華驗(yàn)中學(xué)兼課,到小說(shuō)第九章,曾為學(xué)生謀兼職的李漣自己也不得不“在一個(gè)暑期學(xué)校講授文史知識(shí),為了那點(diǎn)兼課費(fèi)”[2]327。當(dāng)提到這些人在課外兼職掙錢時(shí)作者并沒(méi)有任何貶低、鄙視之語(yǔ),相反在看似平淡的敘述中卻隱含著同情和尊重,完全不存在由于“在課余賺外快”而被嘲諷的情況。因此尤甲仁的被嘲諷,決不是由于“在課余賺外快過(guò)舒適生活”。
事實(shí)上,小說(shuō)每次提到尤甲仁、姚秋爾夫妻二人,確實(shí)總不免夾槍帶棒、冷嘲熱諷,在《野葫蘆引》這樣一個(gè)整體風(fēng)格含蓄雋永、品評(píng)人物點(diǎn)到為止的小說(shuō)中實(shí)為罕見(jiàn)。以尤甲仁夫婦第一次出場(chǎng)為例。先是一段肖像描寫(xiě),“兩人身材不高,那先生面色微黃,用舊小說(shuō)的形容詞可謂面如金紙,穿一件灰色大褂,很瀟灑的樣子。那太太面色微黑,舉止優(yōu)雅,穿藏青色旗袍,料子很講究。”[2]169再形容兩人說(shuō)話的情形,“兩三句便加一個(gè)英文字,發(fā)音特別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齒,不時(shí)互相說(shuō)幾句英文。”[2]169繼而寫(xiě)夫妻倆互相吹捧對(duì)方英文說(shuō)得如何好,文章寫(xiě)得如何棒;最后讓中文系功底最不扎實(shí)的錢明經(jīng)教授以司空?qǐng)D《詩(shī)品》中的一段話來(lái)小小試探一番,果然尤甲仁空有超凡記憶而毫無(wú)個(gè)人創(chuàng)見(jiàn)。尤甲仁夫妻二人第一次出場(chǎng)即被作者從外表、語(yǔ)言、行為、學(xué)識(shí)等各方面著實(shí)嘲諷了一番,后面凡涉及到這夫妻二人之處,總讓他們顯示自己的所謂淵博、清高、公允而實(shí)則刻薄、庸俗、市儈的一面,連他們居住的地點(diǎn)也命名為“刻薄巷”。原因何在呢?
其實(shí),凡是看過(guò)這部小說(shuō)的人,只要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稍微有點(diǎn)了解,都可以看出,尤甲仁實(shí)則是在影射錢鐘書(shū),比如尤甲仁的留英經(jīng)歷、對(duì)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經(jīng)典倒背如流、喜歡賣弄才學(xué)與英文、與人爭(zhēng)論常帶嘲諷等,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早已有人指出。①詳情可參見(jiàn)余杰:《漫畫(huà)錢鐘書(shū)? ——我看〈東藏記〉的暗藏機(jī)鋒》,《粵海風(fēng)》2002年第5 期。錢鐘書(shū)在西南聯(lián)大時(shí)的恃才、傲岸眾所周知,而馮友蘭、宗璞父女與錢鐘書(shū)夫妻的不和也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②關(guān)于馮友蘭、宗璞父女和錢鐘書(shū)、楊絳夫婦不和的詳情,可參見(jiàn)李洪巖、范旭侖:《為錢鐘書(shū)聲辯》一書(shū)中“楊絳宗璞筆墨官司的來(lái)龍去脈”一節(jié),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因此宗璞才以西南聯(lián)大歷史掌故為基礎(chǔ),結(jié)合后人回憶以及個(gè)人情感,在小說(shuō)中凡提及尤甲仁處皆涉語(yǔ)成諷。《東藏記·后記》里的一段話正可以稍加解釋,“在寫(xiě)作的過(guò)程中,曾和許多抗戰(zhàn)時(shí)在昆明的親友談話,是他們熱心地提供了花粉。……我也參考一些史料,當(dāng)然我寫(xiě)的不是歷史而是小說(shuō),雖然人物的命運(yùn)離不開(kāi)客觀環(huán)境,畢竟是‘真事隱去’的‘假語(yǔ)村言’。我還是那句話,小說(shuō)只不過(guò)是小說(shuō)。”[2]337
三 關(guān)于丑化歪曲商人呂香閣的形象
事實(shí)上,小說(shuō)貶低呂香閣是真,但并非像柴文所說(shuō)是由于呂香閣經(jīng)商。呂香閣在第一部《南渡記》里并不是個(gè)商人,但小說(shuō)筆墨已經(jīng)加諸不屑,而《南渡記》里出現(xiàn)的其他一些真正的商人則并未受到嘲諷。如小說(shuō)開(kāi)頭,以家常而隱含深情的筆墨回憶抗戰(zhàn)爆發(fā)前北平大學(xué)教授家庭的日常生活。
清晨,隨著夏日的朝陽(yáng)最先來(lái)到孟宅的,是送冰人。……送冰人用鐵夾子和草繩把冰從車上搬到室外,最后抱到冰箱里。然后在已經(jīng)很濕的圍裙上擦著手,笑嘻嘻和柴師傅或李媽說(shuō)幾句閑話,跨上車揚(yáng)鞭而去。接踵而來(lái)的是送牛奶的。再往下是一家名叫如意館菜店的伙計(jì)。他們包攬了校園里大部分人家用菜。[4]15
接著看常來(lái)孟家推銷小食品的“廣東挑”:
廣東挑的主人是地道老北京,和廣東毫無(wú)關(guān)系,可能因?yàn)閾?dān)上貨物大都是南味食品,因而得名。這種貨挑很講究,一頭是圓的,如同多層的大食盒,一格格裝著各樣好吃的點(diǎn)心。一頭是方的,由一排排小玻璃匣,裝著稻香村的各種小食品,……每次廣東挑來(lái)了,碧初(按:孟樾的妻子)都得買這種點(diǎn)心。……廣東挑笑嘻嘻地把東西撿出來(lái),收了錢。[4]17-18
再看孟家常光顧的一家綢緞商:
他們又到一家熟識(shí)的綢緞店,帶著瓜皮小帽的掌柜高興地說(shuō):“孟太太,可老沒(méi)見(jiàn)了。”……問(wèn)清要求,好幾個(gè)伙計(jì)把各種花色的綢緞打開(kāi),鋪平在柜臺(tái)上。有的搭在自己身上,……掌柜也幫著發(fā)表意見(jiàn)。在黯淡的燈下,各色鋪展開(kāi)來(lái)的綢緞發(fā)出幽雅的彩色光輝,滿店堂喜氣洋洋。他們沉浸在古老北平買和賣的友好藝術(shù)氣氛中,幾乎忘記北平已不屬于他們。[4]179
以上三個(gè)例子都和做買賣有關(guān),并沒(méi)有什么諷刺和貶低之處。送冰人、送牛奶的、如意館菜店伙計(jì),這三個(gè)跑腿的伙計(jì)雖然算不上什么生意人,卻用自己和善而堅(jiān)韌的勞動(dòng)體現(xiàn)著各自背后店家勤勞本分的生意經(jīng)。“廣東挑”、綢緞莊掌柜,則毫無(wú)疑問(wèn)是生意人,也許對(duì)綢緞莊老板有幾許輕微的遺憾,但更主要的還是對(duì)其尊重主顧、尊重自己生意的態(tài)度的贊美。且看那個(gè)做小點(diǎn)心生意的“廣東挑”,把他的貨擔(dān)收拾得多么干凈整齊,這一付擔(dān)子,既是他維持生存的來(lái)源,也是他保持做人的自尊的體現(xiàn)。正是在這些平和的敘述中,飽含著作者對(duì)童年生活詩(shī)意的回憶,對(duì)普通而勤勞的生意人的贊美和尊重,他們那么和善那么自豪地將自己的生意當(dāng)作事業(yè)來(lái)追求,務(wù)求盡善盡美,從而營(yíng)造了老北平悠閑、適意的生活氛圍。
但小說(shuō)并不是不嘲諷商人,事實(shí)上在《東藏記》里,經(jīng)常跑滇緬路做生意的中文系教員錢明經(jīng)、昆明首富朱延清都是諷刺的對(duì)象,但原因并不是因?yàn)樗麄冏錾狻eX明經(jīng)最為人詬病之處在于其沒(méi)完沒(méi)了的風(fēng)流韻事;朱延清讓人受不了的是他以為用自己豪奢的莊園就可以買到愛(ài)情。
以上幾個(gè)例子已經(jīng)證明,商人并不必然成為作者嘲諷的對(duì)象,換句話說(shuō),是否成為被貶低的對(duì)象,最主要的是這個(gè)人是否有自己的人格修養(yǎng)和道德良心。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衡量,則可知呂香閣必然成為嘲諷和貶低對(duì)象。
呂香閣何許人也?她的父親呂貴堂是孟樾岳父呂清非老人的本家,由于躲避債務(wù)帶著女兒來(lái)到呂老人家寄食。呂香閣在《南渡記》里第一次出場(chǎng),其實(shí)就暗含著作者的批評(píng):
呂貴堂掀簾進(jìn)來(lái),后面跟著十六歲的香閣。碧初每次見(jiàn)她,都覺(jué)得她又長(zhǎng)大了,更惹眼了,每次也更感到她伶俐有余渾厚不足,卻不知為什么。……香閣先看碧初臉色,覺(jué)得沒(méi)有阻攔之意,方從衣袋里拿出兩個(gè)彩線角兒來(lái),帶著亮晃晃的長(zhǎng)穗子,笑說(shuō):……[4]33-34
在這個(gè)亮相中,借助呂碧初的眼睛,看出這是一個(gè)長(zhǎng)相俏麗、身形豐潤(rùn)、聰明外露、極善于察言觀色的少女。
再看《南渡記》第四章中的一段情節(jié)。北平淪陷后,呂老人每天教幾個(gè)孩子練拳。一次嵋和呂香閣練習(xí)對(duì)打,嵋比呂香閣小好幾歲,個(gè)頭也差一截,幾個(gè)招式以后,小說(shuō)這樣寫(xiě)道:
嵋也有點(diǎn)累了,正要收式時(shí),忽覺(jué)手腕發(fā)疼。定了定神見(jiàn)是香閣攥住她的手腕,正向她笑。
怎么會(huì)有這樣的笑容!嵋很奇怪。這笑容好像有兩層,上面一層是經(jīng)常的討好的賠笑,下面卻露出從未見(jiàn)過(guò)的一種兇狠,幾乎是殘忍,一種想撕碎一切的殘忍。拳里也沒(méi)有這一招,為什么攥住人家手腕啊!
“啊!”嵋有些害怕,叫了出來(lái)。
香閣仍不撒手,反而更捏緊了,還盯著嵋的眼睛,好像說(shuō),你還有什么能耐!眾人都不明白她們比什么。這時(shí)蓮秀(按:呂老人晚年續(xù)娶的繼室)快步走過(guò)來(lái),抓住香閣的手臂,“嫩骨頭嫩肉的,收了吧。”
“我和小姑姑鬧著玩。”香閣松手,她的內(nèi)層笑容驟然消失了,只剩外層,十分甜美。……
蓮秀拉著嵋的手要走。香閣笑嘻嘻地說(shuō):“小姑姑別走,我跳繩給你看。”嵋站住了,向她的笑容中尋找下面一層,卻找不到,只覺(jué)她唇紅齒白很好看。香閣很快搬來(lái)一條窄長(zhǎng)高板凳,拿了繩子,縱身上凳,輕盈地跳起來(lái)。……
嵋早忘了那獰笑和發(fā)紅的手腕,開(kāi)心地笑叫……
這時(shí)傳來(lái)一陣笑語(yǔ)之聲,絳初、玹子與峨走進(jìn)正院。香閣驀地躍下,連同繩、凳迅速地不見(jiàn)了。[6]119-120①引文中著重號(hào)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摘引這長(zhǎng)長(zhǎng)的一節(jié),是因?yàn)檫@一小段情節(jié)準(zhǔn)確地傳達(dá)出呂香閣的性格心理。這個(gè)情節(jié)共有幾層轉(zhuǎn)折,通過(guò)攥手腕、笑、跳繩、迅速消失等行為動(dòng)作,一層層剝露出這個(gè)少女隱秘的內(nèi)心世界。她跟隨父親從家鄉(xiāng)躲債到北平的深宅大院,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由于生存環(huán)境的不同而產(chǎn)生的不平等,這在她十六歲少女的心里引起的是翻江倒海的不平衡和嫉妒,這種強(qiáng)烈的嫉妒心又衍生出強(qiáng)烈的報(bào)復(fù)心。因此呂香閣心中對(duì)給與自己恩惠的呂家人毫無(wú)好感,對(duì)于嵋等在養(yǎng)尊處優(yōu)、平等自由的環(huán)境里長(zhǎng)大的孩子懷有一種極為強(qiáng)烈的嫉妒和憤恨,一有機(jī)會(huì)就不動(dòng)聲色地下狠手報(bào)復(fù),得逞之后又很巧妙地掩飾自己的行為,逃避責(zé)任以免受罰。她那可怕的雙層笑容正是以表面的諂媚遮掩內(nèi)心猛獸般的施暴欲望。
在《南渡記》的結(jié)尾,呂香閣毫無(wú)顧忌地表明了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
說(shuō)實(shí)在的,我很恨這地方,恨北平城,包括我爹……
……
“我就愿意走,上哪兒都行。最好明天就走!”香閣輕輕地笑著。[4]245-246
“往后你就知道了。以前誰(shuí)也不知道我。我爹怕我當(dāng)漢奸,才這樣忙著讓我走。……”香閣的口氣很放肆,眼光活潑潑亂轉(zhuǎn)。……香閣的眼光似乎有兩層,外面的像狗,里面的則像狼,溫順罩住兇狠。[4]264
這里明確表示出幾點(diǎn)意思:一,對(duì)于呂香閣來(lái)說(shuō),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擺脫她在偌大的北平偌大的呂家所感受的嚴(yán)重內(nèi)心壓抑。二,以前展現(xiàn)在別人面前的她只是表面的恭順和伶俐,在擺脫壓抑后,她將充分施展自己的手腕和能耐讓別人都知道她。三,再次印證呂香閣身上那種集諂媚與兇殘于一體的感覺(jué)。別人在她眼里只分兩種,可以利用的和不可以利用的,不管對(duì)方是誰(shuí),可以利用則溫順如狗,百般奉承,無(wú)法利用則兇狠如狼,殘忍絕情。
在整個(gè)《南渡記》里,呂香閣并不是商人,可以說(shuō)沒(méi)有做過(guò)任何買賣,但那種為達(dá)目的不擇手段的如狗如狼的品性已經(jīng)顯露無(wú)疑,而《東藏記》中呂香閣的所有行為不過(guò)是其性格的延續(xù)和展示,相比較而言,開(kāi)咖啡館做生意不過(guò)是其謀生手段之一倒并無(wú)什么不妥之處。問(wèn)題在于,呂香閣即使不開(kāi)咖啡館,哪怕她從事任何一項(xiàng)與做生意毫無(wú)關(guān)系的職業(yè),以這樣的本性也著實(shí)讓人無(wú)法贊同,這跟她從事何種職業(yè)無(wú)關(guān)。
柴文提出,“……呂香閣個(gè)人主義的幸福觀具有個(gè)性解放的特征。對(duì)個(gè)人幸福強(qiáng)烈追求的愿望是合理的,是符合人性的。……香閣是一個(gè)以個(gè)人主義為本位的人,有著合理的利己主義欲求,……但卻被描繪成漠視國(guó)難,見(jiàn)利忘義,違背起碼的倫理道德底線,喪失人性,淪為資本的人格化或金錢的人格化,這是《東藏記》思想上所存在的巨大局限。”[1]
柴文認(rèn)為呂香閣的所作所為都是出于個(gè)人主義精神。這里柴文其實(shí)沒(méi)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個(gè)人主義精神,濫用了“個(gè)人主義”這個(gè)概念。一個(gè)現(xiàn)代意義上的個(gè)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是基于個(gè)人主義,這是有其特定內(nèi)涵和外延的,它并非損人利己和享樂(lè)主義的代名詞。史蒂文·盧克斯《個(gè)人主義》一書(shū)指出,真正西方現(xiàn)代意義上的個(gè)人主義,應(yīng)該包括個(gè)人尊嚴(yán)、自主、隱私、自我發(fā)展等概念,而這些概念里面同時(shí)也包含著一個(gè)底線,就是每個(gè)人在最大限度地實(shí)現(xiàn)自己個(gè)性發(fā)展的同時(shí),都應(yīng)該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5]對(duì)照這個(gè)概念,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呂香閣身上體現(xiàn)的絕不是真正的“個(gè)人主義”。
首先呂香閣不懂得個(gè)人尊嚴(yán),不尊重自己。僅舉一小例為證。一天晚上,澹臺(tái)玹、峨、嵋、凌雪妍和呂香閣五人在呂家大院里玩帶有神秘性質(zhì)的蠟燭游戲,以各自認(rèn)領(lǐng)的蠟燭燃燒的時(shí)間長(zhǎng)短來(lái)預(yù)示命運(yùn)的好壞,凌雪妍的白色蠟燭最先熄滅,呂香閣的黑色蠟燭燃燒時(shí)間最長(zhǎng)。呂香閣趕緊說(shuō):“這全是鬧著玩,只該我的先滅。全顛倒了,可見(jiàn)不足為憑。”[4]156五人中,除呂香閣外都是從小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小姐,但她們并未由于蠟燭的早滅而遷怒于她,只是感到命運(yùn)的神秘和不可預(yù)測(cè),呂香閣卻自覺(jué)自愿地自我貶低,毫無(wú)個(gè)人尊嚴(yán)和自主精神可言,有的只是一個(gè)心機(jī)沉重的少女在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的諂媚之態(tài)。
其次,呂香閣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他人在她眼里只是墊腳石和攀爬的階梯。俗話說(shuō)“盜亦有道”,也即任何一個(gè)行業(yè)都有自己基本的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和道德底線,商業(yè)行為也不例外,做人更是如此。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哪怕是戰(zhàn)爭(zhēng)年代,仍然存在某些普世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和道德原則,而不是上帝已死為所欲為。而呂香閣的問(wèn)題恰恰在于不顧一切謀求更好生活的野心,行為處事百無(wú)禁忌,只要對(duì)自己有利,明知會(huì)損害與她毫無(wú)利害關(guān)系的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一個(gè)真正的個(gè)人主義者應(yīng)該奉守的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的精神底線,恰恰在呂香閣身上是缺失的。
以柴文極力贊同的呂香閣對(duì)待澹臺(tái)玹的美國(guó)男友保羅的態(tài)度為例。
忽然有一個(gè)想法,可以把發(fā)展自己和破壞別人結(jié)合起來(lái)。夜深人靜,呂香閣坐在床邊,她的兩結(jié)合計(jì)劃已經(jīng)完成。首先是向保羅借錢,她要描述自己的夢(mèng)想,那就是開(kāi)一家舞廳,如果保羅肯借錢,澹臺(tái)玹必然很不高興,這是第一步。還有第二步,第三步,還要仔細(xì)規(guī)劃。她很快進(jìn)入夢(mèng)鄉(xiāng),而且睡得很好。[2]248
玹子走過(guò)去,看見(jiàn)男女二人靠得很近在低聲說(shuō)話,正是保羅和呂香閣。香閣見(jiàn)玹子來(lái),更把頭靠在保羅肩上。……保羅忽然警覺(jué),抽身站起,……這時(shí)呂香閣也走過(guò)來(lái)搭訕,一口一個(gè)玹子小姐。說(shuō)今天用的是保山咖啡,別看是土產(chǎn),很不錯(cuò)的。[2]249
在呂香閣對(duì)待澹臺(tái)玹和保羅的關(guān)系上,如果她對(duì)保羅情有獨(dú)鐘,反倒說(shuō)得過(guò)去,但事實(shí)上呂香閣并不是出于愛(ài)情而接近保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想蓋過(guò)玹子的風(fēng)頭發(fā)泄自己當(dāng)年在呂家感受的壓抑。即使以最大的善意來(lái)揣測(cè)呂香閣的心思,也不過(guò)理解為一個(gè)女子在亂世不得已的權(quán)宜之計(jì),不得不鎖定保羅為結(jié)婚對(duì)象而惡意拆散他和澹臺(tái)玹,但理解不等于認(rèn)同,不等于贊美。
如果說(shuō)呂香閣的上述行為還讓人有一點(diǎn)點(diǎn)理解的話,那么呂香閣對(duì)待凌雪妍的行為則讓人無(wú)法原諒。呂香閣在李宇明和凌雪妍的帶領(lǐng)下一路逃離北平,途中對(duì)諸多艱難、不便多有抱怨和后悔,這本情有可原,任何人都有趨利避害、貪圖享受的本能欲望,何況是在那樣一個(gè)隨時(shí)都有生命危險(xiǎn)的戰(zhàn)亂年代?但呂香閣在昆明站穩(wěn)腳跟后,對(duì)別人散播凌雪妍和李宇明的謠言又是為了什么呢?如果說(shuō)商人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時(shí)不得不打擊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而很顯然凌雪妍和李宇明在任何時(shí)間任何地點(diǎn)都不可能成為她的生意對(duì)手,那么呂香閣為什么要無(wú)中生有地制造這個(gè)莫須有的桃色新聞呢?除了自己的道德缺陷和內(nèi)心的不干凈外,恐怕很難有其他解釋。
呂香閣這個(gè)形象其實(shí)是有著豐富的心理學(xué)基礎(chǔ)和文學(xué)的飽滿性的。她的父親呂貴堂因妻子病死而欠了許多外債,不得已帶著女兒到北平投奔呂老人,在呂家的深宅大院里做一個(gè)客居者。由于呂貴堂知書(shū)達(dá)理又忠厚能干,因此頗得呂老人賞識(shí)。但呂貴堂在呂家的地位很特殊,雖然是呂老人的本家,但實(shí)際卻是來(lái)寄食的;雖然幫著料理家務(wù),卻不是名正言順的管家和傭人;雖然人到中年,但按照中國(guó)家族制度來(lái)說(shuō)輩分很低,和呂家的外孫們同輩。種種尷尬之處使呂貴堂在呂家的地位非常奇怪,以至于不好稱呼,家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直呼其名,包括呂老人最小的外孫6 歲的小娃在內(nèi)。在中國(guó)這樣一個(gè)非常講究稱呼、名分的國(guó)家,一個(gè)成人被別人直呼其名顯然帶有某種不言自明的輕視。父親的這種地位在女兒心里必然會(huì)引起某種不平以及自卑。
而與呂家孫輩的幾個(gè)孩子相比,呂香閣自身?xiàng)l件并不差,但卻由于出身環(huán)境的不同而處于天壤之別的狀況,一邊是嬌生慣養(yǎng)、輕松自由的少爺小姐,一邊卻需仰人鼻息、寄人籬下,正處于最敏感年齡的呂香閣必然感觸頗多,羨慕、嫉妒、自卑、憤恨……如果呂香閣是一個(gè)沒(méi)有什么才能因而認(rèn)命的少女倒也罷了,但她偏偏是一個(gè)頗有能耐希望出人頭地的姑娘,這就使她心機(jī)頗深,處處察言觀色,壓抑自己的本性、討好奉承以求得較好的生存環(huán)境。但沒(méi)有受過(guò)多少教育而又處在長(zhǎng)期的自我壓抑中,必然會(huì)造成心理失衡,一定會(huì)變相尋找發(fā)泄的途徑,因此一旦有機(jī)會(huì)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她必然要放縱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以實(shí)現(xiàn)自己早年被壓抑的愿望。而這種變態(tài)心理則在一個(gè)由于戰(zhàn)亂而失范的社會(huì)里被放大和充分實(shí)現(xiàn),而不必受到正常社會(huì)的道德壓力。因此呂香閣在小說(shuō)第二部《東藏記》里,日益顯露出自己原來(lái)一直隱藏和壓抑的本性,為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欲望敢于挑戰(zhàn)任何對(duì)手,行為處事更是百無(wú)禁忌。
總之,無(wú)論是《南渡記》還是《東藏記》,贊揚(yáng)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氣節(jié)是真,但并未因?yàn)槌缛宥稚蹋瑢?duì)于遵守最基本的商業(yè)道德的商人,小說(shuō)是尊重的,柴文所列舉的幾個(gè)被貶低的例子是不成立的,尤其在呂香閣這個(gè)人物身上,作者貶低呂香閣和她是否經(jīng)商完全無(wú)關(guān)。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基本原則應(yīng)該是在熟悉和尊重文本的基礎(chǔ)上發(fā)揮個(gè)人見(jiàn)解,而不能抱著某種先在的理念或成見(jiàn)來(lái)生拉硬套,張冠李戴,否則既容易造成對(duì)人物理解的偏差,也失去了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基本價(jià)值和意義。
[1]柴平.《論東藏記》的誤區(qū)[J].當(dāng)代文壇,2004(3).
[2]宗璞.東藏記[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4.
[3]許嘉璐.中華史畫(huà)卷·現(xiàn)代卷[M].海口:海南國(guó)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149.
[4]宗璞.南渡記[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4.
[5]〔英〕史蒂文·盧克斯.個(gè)人主義[M].閻克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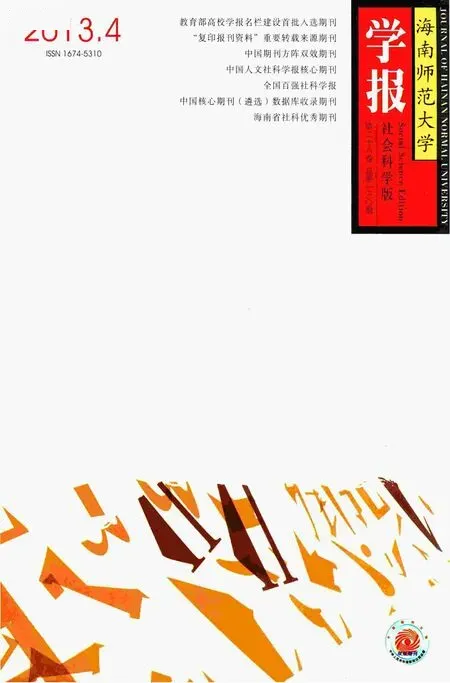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4期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4期
-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中山大學(xué)“南方文談”今日中國(guó)大學(xué)的文學(xué)教育
- 唯勤唯新——評(píng)章羅生《中國(guó)報(bào)告文學(xué)新論》
- 魯迅研究的扎實(shí)成果與可喜收獲——評(píng)趙歌東《啟蒙與革命:魯迅與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
- 雜糅與裂隙:海南本土作家地域書(shū)寫(xiě)側(cè)記
- 近期海南長(zhǎng)篇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概況
- 2012:“戲劇與影視學(xué)”的學(xué)科發(fā)展與年度創(chuàng)作評(píng)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