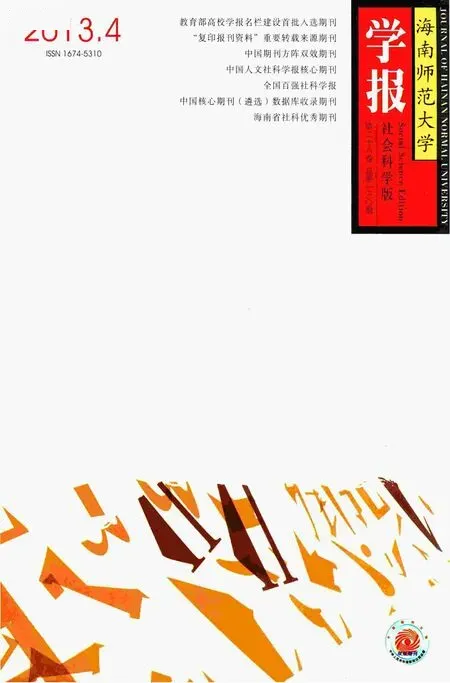得失與啟示:重讀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詩
顏紅菲
(1.南京工程學(xué)院 外語系,江蘇 南京211167;2.華中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79)
“政治抒情詩”,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來理解。廣義的政治抒情詩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自人類社會(huì)有史以來,只要有國家、階級(jí)及其意識(shí)形態(tài)就會(huì)有政治抒情詩。作為一種詩歌形態(tài),廣義的政治抒情詩指的是文學(xué)與政治的聯(lián)姻,以文學(xué)形式表達(dá)政治感情。在內(nèi)容上往往有很強(qiáng)的時(shí)事性和政治性,在藝術(shù)風(fēng)格上多表現(xiàn)為凝重、雄渾、激越、熱烈,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崇高和壯美的美學(xué)風(fēng)范,具有很強(qiáng)的政治鼓動(dòng)性與藝術(shù)感染力。狹義的“政治抒情詩”,是指“‘十七年’時(shí)期出現(xiàn)的一種‘詩人’以‘階級(jí)’(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現(xiàn),來表達(dá)對(duì)當(dāng)代重要政治事件、社會(huì)思潮的評(píng)說和情感反應(yīng)”[1]的創(chuàng)作傾向,具有宣揚(yáng)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等鮮明特征的詩歌。20 世紀(jì)50年代出現(xiàn)的政治抒情詩,到了60年代初以后逐漸形成當(dāng)時(shí)最主要的一種詩歌形式。它以時(shí)代重大政治問題為題材,立場(chǎng)鮮明地為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服務(wù),情感充沛,語言恣意而汪洋。在“十七年”期間,幾乎所有的詩人都從事過政治抒情詩的寫作,但其中成就最高、最引人關(guān)注的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是郭小川和賀敬之。本文擬以郭小川政治抒情詩為個(gè)案,將這一詩歌形態(tài)置于歷史語境中,通過梳理其生成、發(fā)展、繁榮及式微的歷程,探討其美學(xué)意義和思想價(jià)值,揭示其得失與成敗,看一看他的詩對(duì)當(dāng)下中國政治抒情詩創(chuàng)作有何借鑒與啟示。
一
從價(jià)值層面上考察一種詩歌形態(tài),不僅要聯(lián)系其意義的當(dāng)下語境,也要考慮其存在的歷史語境;既要討論它的藝術(shù)范式,也要估量它能達(dá)到的思想深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進(jìn)行歷時(shí)性與共時(shí)性的、宏觀的和局部的、審美規(guī)范與個(gè)人表達(dá)的考量,才能辯證全面地評(píng)估這一詩歌形態(tài)的價(jià)值與意義。
作為“十七年”最優(yōu)秀的政治抒情詩人,郭小川詩歌在思想傾向和藝術(shù)造詣上不僅體現(xiàn)出鮮明的時(shí)代特色,也有其獨(dú)特的個(gè)人風(fēng)格。“作為詩人,郭小川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他對(duì)他所親歷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以及特定的時(shí)代精神的獨(dú)特把握,和同時(shí)代的詩人相比,還在于他具有更大的超越性。在那個(gè)思想和藝術(shù)都推行標(biāo)準(zhǔn)化的特殊時(shí)代,郭小川保持了詩人最可貴的獨(dú)立精神。”[1]謝冕此話可以幫助我們從兩個(gè)方面理解郭小川的意義:首先是作為“革命戰(zhàn)士”的郭小川,其詩歌在內(nèi)容上體現(xiàn)了時(shí)代精神,表現(xiàn)出一種社會(huì)形態(tài)之美,同時(shí)又以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完美地表現(xiàn)了詩歌主題。其次是作為詩人的郭小川,其詩歌實(shí)踐體現(xiàn)了獨(dú)立而獨(dú)特的表現(xiàn)形式。
伊格爾頓認(rèn)為:“如果離開了處理作品時(shí)特定的社會(huì)和體制的形式,就沒有‘真正’偉大的或‘真正’有價(jià)值的文學(xué)可言。”[2]特定的社會(huì)和體制產(chǎn)生特定的時(shí)代風(fēng)尚和時(shí)代精神,由此而生發(fā)出與此相適應(yīng)的詩歌形式和詩歌內(nèi)容。能真實(shí)地把握時(shí)代脈搏并加以藝術(shù)化的表現(xiàn),就有可能成為“真正”偉大的或“真正”有價(jià)值的文學(xué)。郭小川的詩歌可以說是把握住了時(shí)代風(fēng)尚,體現(xiàn)了時(shí)代精神,表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之美。李澤厚先生在《美學(xué)論集》中對(duì)社會(huì)美有這樣的觀點(diǎn):“億萬人民改造世界的雄偉實(shí)踐,為先進(jìn)事業(yè)奮勇獻(xiàn)身的英雄人物的高尚的思想、頑強(qiáng)的意志、豐富的情感、健壯的體魄,成為社會(huì)美的主要表現(xiàn)。”[3]這種許多時(shí)代所缺失的“社會(huì)美”,正是“十七年”文學(xué)藝術(shù)的審美要求和審美特性。郭小川對(duì)時(shí)代精神的準(zhǔn)確把握,首先表現(xiàn)為自覺地將個(gè)人的事業(yè)、情感與時(shí)代精神相融合,使自己投入“火熱的斗爭(zhēng)”,用詩人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感完成對(duì)時(shí)代精神的書寫。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無產(chǎn)階級(jí)文藝的發(fā)展方向就是為人民大眾報(bào)務(wù),首先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文藝為政治服務(wù)的功能,在此基礎(chǔ)上規(guī)定了文藝寫作和藝術(shù)審美的規(guī)范。《講話》精神要求抒情詩歌不再是詩人獨(dú)立于政治之外的個(gè)人情感的宣泄,而是作為階級(jí)利益的表現(xiàn)者,具體說來就是為人民大眾服務(wù),表現(xiàn)這一階級(jí)的精神風(fēng)貌。只有真心擁護(hù)那個(gè)時(shí)代,真正熱愛那個(gè)時(shí)代,忘我地投入到時(shí)代中去,才能使自我的思想境界和情感體驗(yàn)與時(shí)代精神同步合拍,才能把握住時(shí)代的脈搏,唱出時(shí)代的聲音,表現(xiàn)出“社會(huì)美”來。郭小川不斷地呼吁“我要下去啦”:“我的習(xí)性還沒有多少變移,/沸騰的生活對(duì)我有著強(qiáng)大的吸引力,/我愛在那繁雜的事務(wù)中沖撞,/為公共利益的爭(zhēng)吵也使我著迷,/我愛在那激動(dòng)的會(huì)議里發(fā)言,/就是在嘈雜的人群中也能生產(chǎn)詩。/而那機(jī)器轟隆著的工地和揚(yáng)著塵土的田野呀,/我的心沒有一天不向你們飛馳……”(《山中》) 郭小川的詩不是在書齋象牙塔里精雕細(xì)刻出來的,而是深入到工農(nóng)大眾的實(shí)際生活中去,去感受他們的感受情感和生活,這是其詩歌為什么能如此準(zhǔn)確集中地反映時(shí)代精神、把握住時(shí)代脈搏的根本原因。在郭小川的絕大部分詩作里,個(gè)人價(jià)值取向自然地與時(shí)代政治的目標(biāo)統(tǒng)一起來了,個(gè)人命運(yùn)自然地與人民群眾的命運(yùn)聯(lián)系起來了。其詩歌作品歌頌偉大的時(shí)代,歌頌戰(zhàn)斗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充滿了激情和真誠,那是發(fā)自肺腑、從詩人生命里生長出來的情感。詩人盡情地抒發(fā)這一情感,情感抒發(fā)的熾熱真實(shí)和思想表達(dá)的形象質(zhì)樸,使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個(gè)人的審美創(chuàng)造在社會(huì)大時(shí)代中取得了高度的共鳴。
郭小川的自身經(jīng)歷也促使他在政治抒情詩寫作上取得超越常人的成績。他是新中國培養(yǎng)出來的詩人,十幾歲就去延安參加了革命。在革命風(fēng)潮里,延安的政治環(huán)境與他的詩歌寫作是同調(diào)同步的。在他那里,沒有老詩人們跨越不同時(shí)代復(fù)雜的個(gè)人生活經(jīng)歷,也沒有受到西方各種現(xiàn)代詩潮的影響。從延安到北京,他和革命集體一起走向了勝利,所經(jīng)歷的苦難是集體的,同時(shí)也是他個(gè)人的,所享有的勝利是集體的,同時(shí)也是他個(gè)人的。正是因此,他才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革命集體之中:“我也是這些兵士中的一個(gè)呀,/我的心總是和他們的心息息相通。/行軍時(shí),我們走著同一的步伐,/宿營了,我們做著相似的好夢(mèng),/一個(gè)伙伴在身邊倒下了,/我們的喉嚨里響起了復(fù)仇的歌聲,/一個(gè)新兵入伍了,/我們很快就把他引進(jìn)戰(zhàn)斗的人生。”(《山中》) 在這種相互的融合中,時(shí)代精神和革命的“大我”成了郭小川生命自我的一部分,使作為對(duì)象性存在的自我在融合中得到了確證,使其個(gè)人生活和詩歌創(chuàng)作都有一種“單向性”。這種單向性也恰恰與時(shí)代精神特征相吻合,正是這種單向性使其詩歌超越了同代人,顯得純粹而真誠,濃烈而酣暢,充滿了火一般的力量和激情,具有一種強(qiáng)烈的穿透力。
郭小川個(gè)人對(duì)詩歌形式的天才把握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條件。郭小川的個(gè)人性情與政治抒情詩張揚(yáng)“大”的情感是適宜的。郭小川“喜愛大、喜愛動(dòng),喜愛鮮艷的東西,喜愛驚天動(dòng)地的聲音,喜愛沒有遮攔的談話,喜愛寬闊平坦的道路,喜愛一望無際的靈魂”。[4]他是一個(gè)充滿激情的真誠的詩人。詩人飽滿充沛的激情與藝術(shù)形式表達(dá)完美地結(jié)合,使思想表達(dá)更加強(qiáng)烈,更加激動(dòng)人心。在詩體形態(tài)上,強(qiáng)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論式的觀念敘說結(jié)合得很好。其政治抒情詩追求大氣勢(shì)和大境界,情感激越豪邁,富于力量的健與美,語言表達(dá)明快、直接和徹底,從而達(dá)到它在社會(huì)生活和群眾中的戰(zhàn)斗性和鼓動(dòng)宣傳作用;同時(shí)運(yùn)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表述某一政治理念或方針政策,從具體的個(gè)人微觀角度入手,以小見大,直賦其事,以速寫素描式的方法,表現(xiàn)人物的堅(jiān)定信仰和火熱的建設(shè)生活;或從宏觀入手采用俯視鳥瞰的視角,以充滿激情的歌喉去熱情歌唱,但所有情感內(nèi)容和生活現(xiàn)象都被限定在為闡發(fā)某一理念或政策的軌道中。比如《投入火熱的斗爭(zhēng)》:“不馴的長江/將因你們的奮斗/而絕對(duì)地服從/國務(wù)院的命令,/渾濁的黃河/將因你們的雙手/變得澄清,/北京的春天/將因你們的號(hào)令/停止了/黃沙的飛騰……”其政治抒情詩一般都是長詩,詩人往往采用賦體手法,抒情、議論、敘述三者緊密結(jié)合,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對(duì)所要表現(xiàn)的觀念和情感進(jìn)行渲染、鋪陳,經(jīng)常使用音步鏗鏘、節(jié)奏明朗、聲調(diào)高昂的“樓梯式”。《向困難進(jìn)軍》從對(duì)個(gè)人經(jīng)歷的敘述出發(fā),與時(shí)代抒情相結(jié)合,用三個(gè)“你們?cè)俨灰窃鯓印迸疟染涫絹礓秩句伋桑x起來氣勢(shì)昂揚(yáng),鏗鏘嘹亮。從民歌中獲取形式和語言的“民歌體”,也是郭小詩作中常見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詩歌表現(xiàn)形式日益成熟,形成了特有的“郭小川體”:格局比較嚴(yán)整、章節(jié)大致對(duì)稱、音韻鏗鏘。正如馮牧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標(biāo)志著郭小川的獨(dú)特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形式,常常是把中國古典詩詞的嚴(yán)謹(jǐn)、豐富的結(jié)構(gòu),中國民歌的健康、樸素、粗獷的表現(xiàn)手法和我們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生動(dòng)、簡潔的群眾語言熔鑄在一起,這種藝術(shù)手法和藝術(shù)形式在我們的新詩作中是別開生面的。”[5]
二
“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詩,在為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高唱戰(zhàn)歌的同時(shí),也消弭了此類詩歌的多重功能,特別是其批判功能,許多詩人只能為現(xiàn)行的政治綱領(lǐng)、路線、政策、觀念唱贊歌。他們用政治和階級(jí)斗爭(zhēng)表現(xiàn)一切矛盾,包攬所有的情感,使政治成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惟一標(biāo)準(zhǔn)。在強(qiáng)大的政治壓力下,詩人們失去了自己的個(gè)體性和獨(dú)立性,導(dǎo)致在集體話語和政治話語下的個(gè)體失語。郭小川以真誠、不甘平庸的個(gè)性以及對(duì)藝術(shù)執(zhí)著的探索精神,艱難地對(duì)人性進(jìn)行深刻思考,對(duì)詩歌內(nèi)容也進(jìn)行深層挖掘。這種嘗試和努力,使他的部分作品在審美維度上表現(xiàn)出對(duì)個(gè)體實(shí)現(xiàn)本質(zhì)化過程中的裂痕、矛盾和沖突的關(guān)注,在情感維度上表現(xiàn)出對(duì)個(gè)體價(jià)值的尊重,對(duì)人的生命體驗(yàn)的豐富性和情感內(nèi)涵的復(fù)雜性的關(guān)注。在《月下集》的“權(quán)當(dāng)序言”中,他說:“核心問題是思想。而這所謂思想,不是現(xiàn)成的流行的政治語言的翻版,而應(yīng)當(dāng)是作者的創(chuàng)見。”所謂“作者的創(chuàng)見”自然是包含著作家個(gè)人主體的審美思想、審美方式和審美情感的綜合。“文學(xué)畢竟是文學(xué),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穎而獨(dú)特的東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眾的生活的海洋,但它應(yīng)當(dāng)是從海洋中提煉出來的不同凡響的、光燦燦的晶體。”[6]所謂“新穎而獨(dú)特的東西”自然是題材的創(chuàng)新,“不同凡響的、光燦燦的晶體”是多棱的,它從無數(shù)個(gè)鏡面反射出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絕不是單一向度所能概括的。題材的創(chuàng)新實(shí)質(zhì)上是指對(duì)單一單質(zhì)內(nèi)容題材表現(xiàn)的擯棄,是避免理論圖示的抽象和生硬的有效途徑,這時(shí)作家主體性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郭小川再三強(qiáng)調(diào)作者自己創(chuàng)見的介入。表現(xiàn)內(nèi)容上的深層思考,使他在題材和主題方面向人性的禁區(qū)介入。他的兩首抒情詩《致大海》(1956)和《望星空》(1959)就是詩人力圖沖破當(dāng)時(shí)流行政治語言的禁錮,表達(dá)自己“創(chuàng)見”的探索之作。《致大海》敘說“我”兩次面臨大海的不同感受和體驗(yàn),表現(xiàn)了個(gè)性人格與革命相沖突的迷惑與苦悶的困境以及思想感情的艱難轉(zhuǎn)變過程。“大海”是革命隊(duì)伍的自然外化,“我”則是一個(gè)具有個(gè)人主義色彩的知識(shí)分子,歷史的莊嚴(yán)性通過“我”這一生命個(gè)體的漫長審視與探究后,才得以顯現(xiàn),進(jìn)而被認(rèn)同與接受下來。《致大海》中的抒情主體“我”,在思想和情感上還保持著一致性,而在《望星空》中,抒情主體的言說卻并不統(tǒng)一,前后分裂成兩種話語形式:“個(gè)體話語”與“革命話語”,政治上的敏感使作者最后不自然地將“個(gè)人話語”消解于“革命話語”之中,兩種話語之間的嫁接存在著難以彌合的縫隙,顯得生硬、突兀。在郭小川最重要的三首敘事詩中,“革命話語”和“個(gè)人話語”也一直是詩歌中并行的兩條線路,兩種聲音,一個(gè)顯一個(gè)隱,一個(gè)高亢一個(gè)微弱,最后的結(jié)局都是“個(gè)人話語”被“革命話語”所規(guī)訓(xùn)和消解。由于特定時(shí)代的關(guān)系,郭小川詩歌突圍的努力最終宣告失敗,郭小川的失敗同時(shí)也宣告了政治抒情詩在他的時(shí)代的失敗。
郭小川抓住了政治抒情詩的本質(zhì)之一,而這正是從1949 到70年代末整個(gè)30年的政治抒情詩的缺失:作家成為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傳聲筒,喪失了其創(chuàng)作的個(gè)體性和獨(dú)立性,在思想上表現(xiàn)為空洞的說教,喪失了文學(xué)性,墮落為為政治服務(wù)的工具。具體到政治抒情詩的創(chuàng)作來說,文學(xué)是人學(xué),是關(guān)于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的藝術(shù),不是抽象的階級(jí)和本質(zhì),文學(xué)應(yīng)當(dāng)立足人、思考人并且表現(xiàn)具體生活中的人,那么表現(xiàn)政治生活中的人或者說表現(xiàn)人的政治生活則是政治抒情詩不可避免的內(nèi)容。郭小川在“革命話語”中納入“個(gè)人話語”,在“政治維度”中織入“人性維度”,通過表現(xiàn)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個(gè)體自我本質(zhì)力量對(duì)象化的過程中的彷徨、思考,尤其是情感體驗(yàn),從真實(shí)的個(gè)人政治情感中反映出時(shí)代精神和政治風(fēng)貌,這種表現(xiàn)更真實(shí)、更豐富、更深刻、更富于審美性。然而,郭小川突圍的最終失敗,也使其政治抒情詩所追求的對(duì)時(shí)代的超越,只是一種努力而未能成為一種現(xiàn)實(shí)。一首好的政治抒情詩首先要有歷史使命感,必須能深刻地把握時(shí)代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當(dāng)下的政治情感或揭露時(shí)代的政治黑暗;同時(shí)它必須是文學(xué)性和政治性的完美結(jié)合,能通過藝術(shù)化和個(gè)性化的審美傳達(dá)表現(xiàn)政治情感,成為既有深刻的價(jià)值意蘊(yùn)又有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的有機(jī)整體。其中,詩人個(gè)人的價(jià)值取向和主體性精神是達(dá)到這一目標(biāo)的必要條件。
當(dāng)今是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不斷擴(kuò)張導(dǎo)致其對(duì)于公共政治領(lǐng)域的侵占,并使其發(fā)生蛻變,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包括文化生活正在大面積“非政治化”。以物質(zhì)需要的滿足為核心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延續(xù)一個(gè)多世紀(jì)的公共政治關(guān)切,社會(huì)重大轉(zhuǎn)型體現(xiàn)在大眾消費(fèi)熱情空前高漲的同時(shí),政治冷漠到處蔓延。同時(shí),政治體制的內(nèi)在弊端所導(dǎo)致的腐敗和分配上的不公正正日益蔓延,社會(huì)貧富分化現(xiàn)象也日益嚴(yán)重,窮人富人的概念在消費(fèi)時(shí)代變得日漸明晰,窮人日益處于社會(huì)底層的屈辱地位,大多數(shù)人處于“失語”狀態(tài)。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中,被文學(xué)性所清洗的“政治”、“階級(jí)”、“利益”、“對(duì)抗”、“意識(shí)形態(tài)”這類語詞,又一次成為本質(zhì)現(xiàn)實(shí),成為時(shí)代的真實(shí)和主題。政治再一次強(qiáng)烈地要求詩人們從個(gè)人情感呻吟的象牙塔里走出來,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以郭小川所有的使命感和責(zé)任感,積極投入社會(huì)生活,把握時(shí)代脈搏,自覺地成為底層階級(jí)的代言人,成為社會(huì)黑暗的掘墓者,成為心靈家園的守護(hù)神,成為理想信念的火炬手。當(dāng)代的詩人們只有從物欲橫流的文化市場(chǎng)中,從中產(chǎn)階級(jí)的精英立場(chǎng)中,從淺唱低吟的小資情調(diào)里,奪取曾經(jīng)失去的陣地,為人民服務(wù),為真理歌頌,才有前途。同時(shí),當(dāng)今的文壇,也只有遵循“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則下我們必須堅(jiān)持人的立場(chǎng)、生命的立場(chǎng);在不歧視政治的作用下我們必須堅(jiān)持文學(xué)的立場(chǎng),藝術(shù)的立場(chǎng)”[7]這一道路,堅(jiān)持詩歌的文學(xué)性和政治性,堅(jiān)持詩人的個(gè)體性和獨(dú)立性,才能避免重蹈郭小川的覆轍,才能追隨郭小川讓自己的詩歌實(shí)現(xiàn)個(gè)人與時(shí)代的高度統(tǒng)一與高度融合,成為能夠代表一個(gè)偉大時(shí)代的真正的杰出詩人。郭小川并不是一個(gè)個(gè)人主義者,然而他也并不是一個(gè)沒有政治立場(chǎng)與個(gè)人獨(dú)立人格的詩人,在他的詩中大量地保存著他對(duì)于時(shí)代的驚喜與困境,他自我的心靈與精神都可以從其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詩中得以洞見,《秋天》是如此,《團(tuán)泊洼的秋天》是如此,《深深的山谷》與《白雪的贊歌》等長詩也是如此。請(qǐng)問在今天,我們有哪一位詩人可以與郭小川相比呢?有哪一位詩人的作品產(chǎn)生過像郭小川當(dāng)年那樣的社會(huì)影響呢?今天的詩歌境況并不完全是由于時(shí)代變遷所造成的,與詩人們的政治與藝術(shù)選擇也存在直接的關(guān)系。需要反思的不是郭小川們,而恰好是我們自己。
[1]謝冕.郭小川的意義[J].中國圖書評(píng)論,2000(4) .
[2]伊格爾頓.文學(xué)原理引論[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87:237.
[3]李澤厚.美學(xué)論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164.
[4]王富仁.充滿真實(shí)的青春激情[M]//大海晨歌——郭小川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3.
[5]馮牧.不斷革命的戰(zhàn)歌和頌歌[J].詩刊,1977(10) .
[6]郭曉惠,等.檢討書:郭小川在政治運(yùn)動(dòng)中的另類文字[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144.
[7]胡少卿.當(dāng)下詩歌中的“人民性”及其啟示[J].文藝?yán)碚撆c批評(píng),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