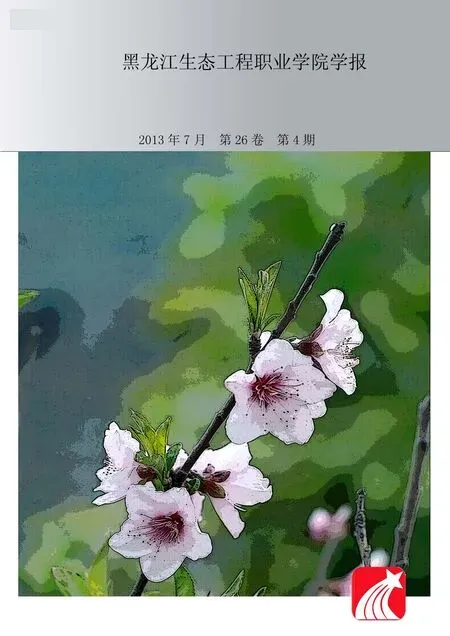淺析刑法中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別
劉 通
(華北水利水電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11)
刑法解釋是指對刑法條文的真實含義的說明[1],通過對規范的解釋,闡明某種行為是否為刑法打擊的對象。對刑法的解釋,應該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礎上,透過文字尋找正義的過程,對刑法所有的解釋,都必須受制于刑法的目的即罪刑均衡。所以我們在進行解釋時,心中當永遠充滿正義,既要懲罰犯罪,又要保障人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法的正義性、安定性與合目的性。
對刑法進行符合目的的解釋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然而何種解釋方法是被刑法所接受的,關鍵在于這種解釋方法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和正義,這就涉及刑法解釋學的核心即刑法解釋的限度——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分問題。
1 一則案例引發的思考
有這樣一個案例:甲(女)坐在無人的公園里的長凳上休息,臨行時將其手提包(內有手機和千元現金)遺落在長凳上,覬覦已久的乙(男)趁機拾包而去。甲走出20米遠后發現忘記拿手提包遂轉身跑向長凳,包已不見。碰巧此時甲的手機鈴音響起來,甲循聲望去見乙拿著自己的包從草叢中迅速跑出,甲立即追上乙奪回手提包。本案中乙的行為是盜竊還是侵占?可能從一般人的法感覺來說更傾向于盜竊,但如何論證乙的行為屬于盜竊呢?這就涉及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分問題。
2 刑法允許擴張解釋與禁止類推解釋的緣由
2.1 允許擴張解釋的依據
擴張解釋是擴張行為概念的范疇,將相應的事例納入到概念中,從而將其包含于法條的處理范圍,但這種擴張必須被牢牢限定在條文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之內。擴張解釋并未創設新的規則,只是明確了行為概念的真實含義,納入處罰對象的案例事實原本就包含于行為概念之中。
雖然成文刑法是正義的文字表述,但并不意味著僅僅根據文字就可以發現刑法的全部真實含義[2]5。文字或語言的通常意義是在事實的發展中形成,僅憑文字來揭示刑法的真實含義是不可能的。現代法治要求刑法的穩定性,但語言、正義是會隨著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被賦予新的含義。我們必須正視語言的開放性,懂得語言含義的發展會不斷填充法律的真義,所以刑法允許適度擴張詞義,從而保證刑法的適應性。
2.2 禁止類推解釋的緣由
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將后者的法律效果適用于前者。類推解釋雖然承認成為問題的行為不能通過罰則包含在處罰的對象中,但以該行為與成為處罰對象的行為在惡害性、當罰性方面是相當的為理由,將該行為也作為處罰的對象[3]14。我國1979年的《刑法》采用類推制度,1997年的新《刑法》廢除類推制度,并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類推解釋實質是事后造法,如果允許類推,人們對自己的行為無可預測,法的不安定性加強,違背了犯罪和刑罰必須基于國民的意思事先予以明確規定的罪行法定原則,《刑法》的規定對于司法權的限制將會通過解釋而徹底消除,故而刑事法治排斥類推解釋。
3 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
3.1 傳統的區分標準
自上世紀日本刑法學家團藤重光提出的 “是否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以及德國刑法學家羅克辛提出的 “不得超出口語的范圍”,即不得超出刑法用語的可能含義以來,這樣的區分標準被中國刑法學界普遍接受。遺憾的是,這種區分標準過于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不易操作。不過這種理念的確立為我們尋求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區分的技術標準指明了方向。
張明楷教授提出了“上位概念”,即將一個行為概念擴張到另一行為概念,二者是否需要借助共同的上位概念尋求一致性來區分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例如某年的司法考試試題將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中的“婦女”解釋為包含男子在內。眾所周知,婦女與男子是兩個相反的概念,只能借助共同的上位概念“人”才能找到二者的一致性,顯然這種解釋方法屬于類推而非擴張。雖然“借助共同的上位概念”這一標準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對于《刑法》第四十九條“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司法解釋將“審判時”擴張到“偵查羈押時”被認為是擴張解釋,然而審判與偵查羈押并不一致,需要借助于共同的上位概念“刑事訴訟”來尋求一致性,顯然張明楷教授的技術標準并不當然有效。
3.2 重新認識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
其實,從罪刑法定主義的見地出發得以允許的擴張解釋與不被允許的類推解釋之間的不同或區別,未必在于結論上的不同,而在于將該結論予以正當化的論理的不同[3]13。也就是說,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有時得出的結論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二者得出結論的方式或過程不同。例如司法解釋認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破壞交通工具罪中的“汽車”包括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機。以往多數學者認為承擔交通運輸職能的大型拖拉機受到破壞時同樣會危害公共安全,所以將大型拖拉機納入處罰的范圍。前文已經論述擴張解釋雖屬擴張行為概念,但具體的案例事實原本就包含在概念之中;而類推解釋是從危害性出發來認為概念是可以包含具體的案例事實。所以上述解釋是以擴張解釋之名而行類推解釋之實,但上述解釋確屬擴張解釋,只是得出結論的方式不正確。因為汽車是指以可燃氣體作動力或有自身裝備動力驅動的運輸車輛,可見汽車的概念范圍原本就包含大型拖拉機,并不需要借助上位概念“交通工具”或基于危害性相當來尋求二者的一致性。
再看一下前文將“審判時”擴張到“偵查羈押時”是不是擴張解釋。在西方,偵查過程中的各種令狀都是由法庭簽發的,法庭的審理不僅包括對案件做出實質的處理,還要對拘捕令狀以及偵查程序進行審查,在這個層面上說審判的整個過程是可以囊括偵查羈押的,故而上述解釋屬于擴張解釋。
3.3 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分在《刑法》分則中的應用
《刑法》分則中盜竊罪與侵占罪的區別最能說明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盜竊罪的對象必須是他人占有的財物;侵占罪的對象是自己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埋藏物。再看第一部分提出的案例中乙的行為屬于盜竊如何論證。如果我們認為案例中遺落的包屬于遺忘物并且承認他人占有的財物與遺忘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案例中時空距離如此之近,危害性相當而將其作為盜竊處理則屬類推:如果我們認為占有不僅包括物理支配范圍內的支配,而且包括社會觀念上可以推知財物的支配人的狀態[4]662,而案例中甲雖然暫時性遺忘,但甲與其財物的時空距離如此之近,隨時可以實現控制,這時應該理解為財物屬于甲占有,這里我們只是擴大了占有的范圍,所以乙的行為屬于盜竊。
由此可見,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本質區別并不在于結論的不同,而在于二者的邏輯進程不同。
4 結語
在保障人權與尊重自由的法治時代,任何違背民主和自由的解釋都應當剔除,所以我們有必要區分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嚴格限定刑罰的范圍,將相似的行為排除在《刑法》的處罰范圍之外,從而保障公民“不給他人制造麻煩事”的自由。但需要強調的是,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分標準并不是絕對的,“法律意義”并非固定不變的事物,它系隨著生活事實而變化[5]89,生活事實的發展會不斷填充法律的含義,這對于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分無疑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作為解釋者,必須從生活事實中發現刑法文本的真實含義,正確解釋刑法,從而實現刑法的正義和穩定性。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解釋理念[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12):140~149.
[2]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日]山口厚.刑法總論[M].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德]亞圖·考夫曼.類推與“事物本質”——兼論類型理論[M].吳從周,譯.臺北:臺灣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