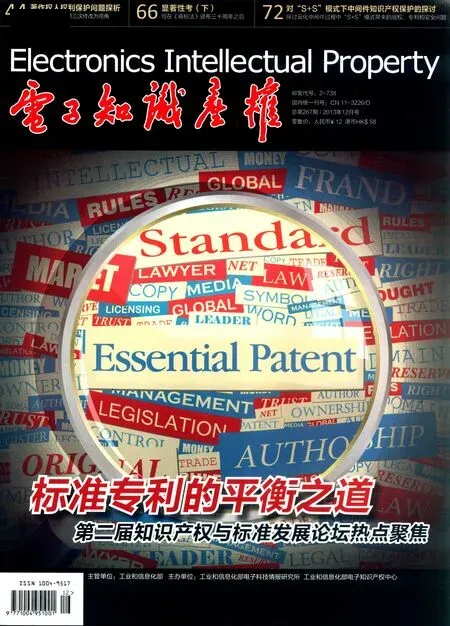走出商標行政訴訟的誤區
文 / 譚乃文 /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走出商標行政訴訟的誤區
文 / 譚乃文 /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本期法苑將焦點集中在討論新商標法59條3款的理解和適用上。法官視角欄目中法官作為筆者與大家分享了其對于該條從形式適用條件、實質適用條件以及法律后果上的理解,并討論了該條在現行狀態下適用中的一些問題。此外,法評熱點中本期推出《走出商標行政訴訟的誤區》,同樣是來自司法審判實踐一線對于法律運用的一些建議。這些內容,在條文本身與審判實踐之間搭起一座橋梁,更有利于權利人行使自己的權利,從而推動司法實踐和理論向更進一步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商標授權、確權引發的商標行政訴訟呈爆炸式增長,反映了當前人們知識產權法律意識正不斷增強。然而,在商標行政訴訟的特殊性也使得一些當事人容易出現法律上的誤區。商標行政訴訟是一場博弈,更何況,一方是強大的國家商標行政機關。商標業界流傳著一句話,一件商標可以決定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在商標行政訴訟這盤棋局之中,布局落子之間,一著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對近年來審理的商標行政案件特點進行分析、梳理,結合最新的案例,與大家探討如何走出商標行政訴訟的誤區。
一、訴訟策略失誤
在商標行政訴訟中,原告的訴訟請求無疑是案件的關鍵性問題。一些當事人甚至代理人往往對商標行政案件的實體和程序問題了解不足,進而導致訴訟策略的失誤,以下是當事人經常出現的四種訴訟策略失誤的情況。
(一)訴訟請求超出法院審理范圍。
很多當事人及代理人,在商標行政案件的訴訟請求中主張:“請求人民法院判決申請商標/被異議商標獲準注冊。”類似這樣的訴訟請求不勝枚舉。殊不知,這樣的主張是超出法院審理范圍的。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1.主要證據不足的;2.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3.違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職權的;5.濫用職權的。
顯然,根據法律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判斷是一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選擇。因此,當事人關于主張判決申請商標被異議商標獲準注冊之類的請求,超出了法院的審理范圍。
(二)訴訟費用的承擔是獨立的訴訟請求嗎?
當事人或代理人一般都會把訴訟費用的承擔作為一項訴訟請求提出,這樣的做法也值得商榷。根據2007年實行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當事人不得單獨對人民法院關于訴訟費用的決定提起上訴。由此可見,訴訟是為了解決當事人實體方面權利的爭議,訴訟費用的承擔不是單獨的訴訟權利。且訴訟請求都有相對應的訴訟標的,都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為實現某種權利而提起的,而訴訟費用則是行政訴訟原告或上訴人為進行訴訟向法院預交納的法定費用,屬國家規費性質,體現的也是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公法上的關系,不是訴訟標的,也就不能作為訴訟請求的基礎。因此,即使當事人并未對商標行政案件訴訟費用進行主張,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仍然會判決由敗訴方承擔。若當事人將訴訟費用的承擔作為一項單獨的訴請提出,只能視為其對法院工作的提醒和暗示,不能起到法律上分配訴訟費用承擔的依據,當然勝訴方自愿承擔的除外。
(三)對法院審查程序了解不足。在商標行政訴訟中,很多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是其在商標評審階段從未提出的新主張。那么,這樣的主張法院會考慮嗎?
商標行政案件的司法程序的設立,其目的在于,賦予那些不服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或者裁定的的當事人,以一定司法救濟的途徑。而根據人民法院不告不理原則,法院的審查范圍應當僅限于當事人的請求。根據正當程序原則,在商標授權、確權行政程序中,申請人未明確主張作為異議復審的理由的法律條款,不屬于法院的審理范圍。
(四 )實體法律適用錯誤。一些當事人或者代理人由于缺乏對商標法律法規的了解,而在訴訟中濫用條款。比如,很多請求司法認定馳名的商標行政案件中,原告都會主張《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的內容。然而,該條款的立法目的僅在于規制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其他不良影響的標識,使其不能作為商標使用。而從具體法條的內容出發,判斷一個商標標識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響,應當考慮該標識或者其構成要素是否可能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產生消極的負面影響。很多當事人及代理人在商標行政糾紛中,只涉及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情況下,仍然濫用此條款提起訴訟,導致最終敗訴。

二、搜集證據不力
經北京一中院知識產權庭調研發現,設計馳名商標認定的案件,在商標行政訴訟中的比例居高不下。以北京一中院2012年審理的商標行政案件為例,涉及知名商標認定及保護的案件占全年全部商標行政糾紛案件的31.2%。然而相當一部分當事人,對于馳名商標認定的舉證存在問題。
(一)證據過于單薄。有的當事人對主張馳名的商標主觀上產生過于自信的過失,認為申請馳名的商標、標識已經足夠知名,從而在商標行政階段及訴訟階段提交的證據過于片面及單薄,使得法院在認定馳名時,認為其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以某著名眼鏡品牌為例,其僅提供了不足十份銷售合同證明其商標馳名,并無其他證據佐證,顯然證據過于單薄,法院無法通過證據來證明其主張。
(二)證據證明力有限。有的當事人提交的涉外證據尚沒有經過公證認證,甚至沒有進經過翻譯,缺乏采信證據的必要條件。有的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形成于被異議商標申請日前,無法證明其證明目的。有的當事人列舉了大量的自制證據,可是這些證據有的沒有顯示時間,有的甚至連商標標識都沒有出現。例如,法國克里斯提昂迪奧爾香料公司請求法院認定其Dior商標在化妝品等商品上馳名。但是,原告提交的專柜列表和產品手冊系其自行制作,證據廣告宣傳及報道證據的形成時間晚于被異議商標申請日,僅憑這些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在被異議商標申請日之前其已達到馳名的程度。最終法院沒有支持迪奧公司的主張。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在證據搜集上的失誤,往往導致當事人不得不承擔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三、對于商標禁用權范圍理解過于夸大
商標權是一個集合概念,它的內容包括商標的專有使用權、禁用權、轉讓權和許可使用權等。其中,商標專有使用權和禁用權構成了商標權的主要權項,也是企業商標管理過程中遇到問題最多、爭議最大的部分。商標專用權與商標禁用權范圍不同,一些商標權人往往對其商標禁用權理解過于夸大,導致一部分濫訴的發生。
《商標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注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準注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第二十一條和第二十二條又有補充規定,“注冊商標需要在同一類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應當另行提出注冊申請”,“注冊商標需要改變其標志的,應當重新提出注冊申請”。由此可見,我國《商標法》對于商標權人通過商標注冊所取得的專用權范圍,有明確嚴格的規定,即核準注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商標禁用權是指注冊商標所有人擁有的禁止他人使用、仿冒或混同,以及禁止其他構成對注冊商標實質性侵害的間接權利。該項權利具有消極的不作為意義,故商標禁止權也可以被稱為商標注冊的消極效力或商標權人的消極權利。
由于歷史等綜合因素,不同權利人之間的商標專用權及商標禁用權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重合和沖突。權利人維護自身權益的前提,是保證自身權利的實現不妨礙他人的正當權利,不妨害正常的社會秩序。比如,不同語種的外文文字商標字型相似,但發音不同一般不宜認定為相近似。博瑞坦克斯洛姆兒童安全有限責任公司訴商標評審委員會商標駁回復審為例,英文字母Roamer與引證商標的德文字母Romer二者因為語種、讀音、釋義、呼叫均不相同,不屬于近似商標。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浪琴表公司主張,根據《商標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被異議商標“龍井LONG JING及圖”與其著名商標“LONGINES”構成使用于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標。雖然從文字商標的字形上,“LONGINES”與“LONG JING”雖然部分字母相同,但由于中國消費者以中文為認讀語言,易將“龍井”作為顯著部分加以識別,況且被異議商標中“LONGJING”是“龍井”的漢語拼音,中國消費者并不會將之與引證商標相混淆。因此,兩商標在呼叫、構成要素以及整體視覺效果上區別明顯,不屬于近似商標。即便考慮引證商標的知名度,由于被異議商標的標識本身與引證商標具有顯著區別,亦不會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最終浪琴表公司的相關主張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中文拼音和英文以及其他語種分屬不同語系,而商標以語言為媒介,所以語言文化上的差別在商標上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來。在判斷不同語種的外文文字商標字型相似的時候,如果發音不同、含義不同、字母不同等情況,一般不會認定兩商標屬于近似商標。
結語
商標作為一個商業符號,它把一種商品或服務和其他的競爭者相區分,在日常生產經營及生活之中扮演者日趨重要的角色。針對商標行政訴訟中的誤區進行調研后,北京一中院知識產權庭提出如下建議:一是了解《商標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避免訴訟策略失誤;二是進一步掌握證據規則,防止因證據搜集不力造成的訴訟失利;三是合理設置自身商標禁用權空間,理性合法維權。
枯燥的法律條文背后,是一個個鮮活的案例。而從案例中不斷的總結與歸納,積累了走出誤區的經驗。商標行政訴訟如同一場競技,而《商標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就如同重要的比賽規則,以用理性的方式理解并使用這些規則,才能有效保障每一個人應有的、合法的訴訟權利。